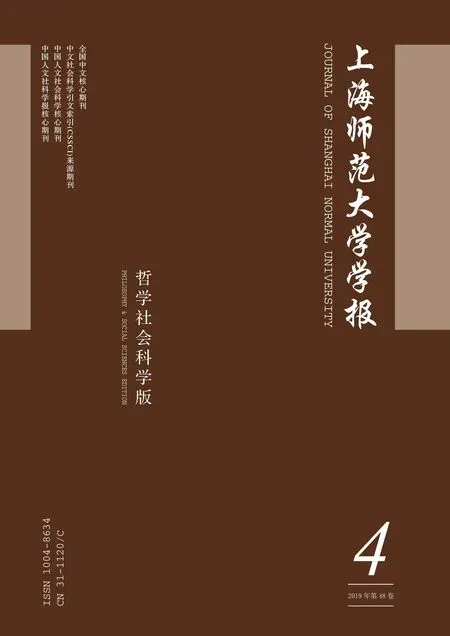张恨水《啼笑因缘》与20世纪30年代武侠电影叙事模式的嬗变
陈伟华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于1929年开始创作,随后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啼笑因缘》(上、中、下)1930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啼笑因缘续集》(长篇小说),1933年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后被改编成话剧、电影、弹词等多种形式。
据张恨水自述,《啼笑因缘》的销售数超过他的其他作品,除去私人盗版盗印的不算,他估计前后已超过20版。因为书销得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注]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严独鹤指出:“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注]严独鹤:《一九三○年〈严独鹤序〉》,载张恨水:《啼笑因缘》,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啼笑因缘》小说单行本出版之后,反响之大,前所未有,甚至还引发了官司。如《中国新书月报》1931年第1卷第5期刊有《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所发表张恨水控告赵凤林等贩卖翻版啼笑因缘的判决书》,1932年第2卷第8期刊有《三友书社禁止侵害啼笑因缘之著作权》。当时文坛和学界对这部小说赞誉之辞甚多,还有人专门对该书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如陆澹盦在《金钢钻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发表了《啼笑因缘之商榷》,对小说中的日期、方位等诸多细节进行了考证。因《啼笑因缘》影响巨大,很快有电影公司找上门来。据张伟的研究,明星影片公司最初计划拍上、中、下3集,后来又扩为6集,并将全部无声改为局部有声,每集的最后一本拷贝还特地摄成了彩色片。[注]张伟:《纸上观影录(1921—1949)》,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小说”兴起以后,曾于19世纪下半叶风行一时的侠义小说一蹶不振。直到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出版,以侠客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才重新走红。此后数十年,武侠小说成了市场上销量最大的小说类型。[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4页。无独有偶,在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一个高潮。该期出品的武侠电影在100种以上,其中许多著名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如出品于1927—1938年的系列电影《儿女英雄》(文逸民导演)改编自文康同名小说,出品于1928—1931年的《火烧红莲寺》(张石川导演)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出品于1930—1936年的《荒江女侠》(陈铿然等人导演)改编自顾道明的同名小说,出品于1930—1934年的系列电影《江湖二十四侠》(王天北导演)也改编自同名小说。改编自《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电影都有多种版本。在这众多电影中,张石川导演的《啼笑因缘》(1932)和其他各种由《啼笑因缘》改编而来的电影,如李晨风导演的《啼笑姻缘》(1940)、关山与罗臻导演的《故都春梦》(1964)、王天林导演的《啼笑姻缘》(1964)、楚原导演的《新啼笑因缘》(1975)等,成为中国现代言情武侠电影的先行者;它们尝试创建中国现代言情武侠电影的典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武侠电影模式的嬗变。
一、创新侠客理念及侠士、侠女形象
1.从单面侠士、侠女到多面侠士、侠女
《啼笑因缘》中的典型侠女是关秀姑,典型侠士是关寿峰,樊家树作为另类侠士而存在。梳理小说史和电影史,可以发现,在《啼笑因缘》之前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和电影中,侠士、侠女大都为扁平人物,典型者如《江湖奇侠传》(系列电影《火烧红莲寺》)中的红姑、《荒江女侠》(系列电影《荒江女侠》)中的方玉琴、《儿女英雄传》(系列电影《儿女英雄》)中的十三妹等。而且,小说改编成电影之后,侠士与侠女的单面性更加明显。
而在《啼笑因缘》中,同一人物有多副面孔,其性格也具有了多元性。深入考察,可见何丽娜、关秀姑与沈凤喜实则为一人三面。小说还特别设计,何丽娜与沈凤喜长相几乎完全相同,樊家树因为照片而弄出了很多误会。这三女,既有分,又有合,形成巨大的叙事张力。《啼笑因缘》中侠女的多面性还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岳剑秋、方玉琴在进洞房之前,基本上仅仅是好搭档,而非真正意义的情人(《荒江女侠》);紫玲姐妹与司徒平相约“情如夫妻骨肉,却不同室同衾”。[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他还指出,真正写好侠客的“儿女情”,把“侠情小说”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的,可能得从王度庐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等算起。[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第81页。陈平原把“侠情小说”的节点放在王度庐的小说中,是基于武侠小说类型来立论的。倘若把视角放在局部的武侠叙事上,则《啼笑因缘》是一个重要节点。在该小说中,关秀姑身为侠女,但充满对爱情的向往。小说有意渲染了她与樊家树之间的朦胧爱情,如关寿峰生病、樊家树相助时,关秀姑产生了对樊家树的爱情想象(事见小说第四回)。在受约写《啼笑因缘》之前,张恨水在写言情方面有很深厚的功底,对写武侠小说则尚未尝试。因为上海文艺界比较喜欢肉感的或者武侠的两类,《新闻报》主编严独鹤便要求他加上两位侠士,这才有了关寿峰与关秀姑。[注]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5页。没想到这一加,竟使小说显出了独特的风貌。当然,对武与侠,张恨水并不陌生。据他的自述,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他自己不懂。[注]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第45页。在这种背景下,张恨水塑造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侠女。
《啼笑因缘》对侠士形象的塑造也有突破和创新。在《儿女英雄传》和《火烧红莲寺》中,侠士大多会武功,如邓九公、孙明甫、查士雄等。而《啼笑因缘》中的侠士樊家树则是一介书生。传统侠士凭借武功除暴安良,樊家树则因为良心和情感而仗义疏财。因为樊家树仅有侠义之举而毫无武功,或许会有人质疑他的侠士身份。可是,对比金庸笔下几乎不会武功的韦小宝,称樊家树为侠士也未尝不可。当然,书中的关寿峰是典型的传统侠客类型。
无论是《儿女英雄传》还是《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其中的侠士、侠女的性格都显得单一,即作为侠的化身和义的代表。他们身上的复杂人性和七情六欲基本上被隐藏。《儿女英雄传》中,侠女十三妹何玉凤虽然嫁安骥为妻,但其叙事重点不在儿女私情,而在何玉凤的侠义。其中安骥多次遇险,何玉凤多次将其救出。换言之,何玉凤与其说是情人,不如说是女性保镖。《关东大侠》中,侠女和侠士之间的亲密关系以亲情巧妙地掩饰起来。如孙明甫与兰珠为表兄妹,查士雄与赵窈娘为表兄妹。这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侠士、侠女的单面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侠义”的表现在《啼笑因缘》中也与其他作品有区别。在《儿女英雄传》《火烧红莲寺》等作品中,“侠义”主要表现为匡扶正义,除恶惩奸。侠客凭借高超的武艺赶走暴徒,帮助弱者。而在《啼笑因缘》中,“侠义”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其一是传统式的,侠士以武力行侠仗义,如关寿峰与关秀姑设计杀死刘将军,解救沈凤喜;其二是非武力层面的,如樊家树资助沈凤喜读书,樊家树为关寿峰支付医药费等。
传统的侠士行侠仗义通常是一心行侠,不求回报,毫无私心。如果以此来衡量樊家树,则显得另类。因为,他之所以资助沈凤喜,是因为看上了她。他送她进学校,也可以解读为想借此提升其地位和身份,使他们的婚姻尽量往门当户对的主流标准靠拢。他跟关寿峰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多少跟他对关秀姑的朦胧好感有关。正因为这个原因,关寿峰病重之时,樊家树慷慨解囊。这一方面可以真正帮助关寿峰,另一方面还可以博得关秀姑的芳心,一举两得。而在之前的小说及电影中,侠士、侠女四处行侠仗义,基本不与被帮助之人发生情感联系。侠士、侠女与被救者的相遇和相助也是偶然的、毫无征兆的、毫无计划的。
“言情”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近现代通俗小说的重要特征。张恨水将言情与武侠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侠士、侠女成为侠义与情感的综合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无独有偶,当今深受欢迎的武侠小说及武侠电影也大都是这种模式,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雪山飞狐》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娇》等,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
2.从有意模糊年龄到刻意塑造青春偶像
对于叙事类的文艺作品而言,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不同时期的电影,关于人物的理念有所不同。在《啼笑因缘》之前,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中的主角大多没有太多的年龄限制,有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如《水浒传》《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如电影《火烧红莲寺》中的杨赞廷、常德庆、甘瘤子、杨赞化、红云老祖、吕宣良等人物。《啼笑因缘》中则出现了较多青春偶像型人物。其主要人物樊家树、关寿峰、关秀姑、何丽娜、沈凤喜中,除关寿峰之外,其他人都是有着广泛人缘的未婚青年:樊家树英俊潇洒,沈凤喜温柔漂亮,关秀姑柔中带刚,何丽娜热情奔放。
当然,单纯从女性角色而言,强调青春妙龄并非从《啼笑因缘》开始,《儿女英雄传》《关东大侠》《荒江女侠》皆有此倾向。但细致分析,可见它们与《啼笑因缘》有较大差异。因为,在这些影片中,男女青年虽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却不是唯一的角色。每当危急时刻,总会有一个或多个武功超群的老年女侠及时出现,如《火烧红莲寺》中有沈栖霞等人物。
3.歌女与侠女同为主角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和电影中,侠女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小说而言,中国现代是女性觉醒的时代,所以女性在小说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当然,女侠一直都在武侠及侠义小说中有一席之地,如《虬髯客传》中有红拂女,《水浒传》中有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等。对电影而言,女侠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电影是视听艺术。而在无声电影时代,它几乎是单纯的视觉艺术,观众与其说是去看电影,不如说是去看女影星。鲁迅就曾经说他的《阿Q正传》不适合搬上银幕,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漂亮的女主角。[注]鲁迅:《鲁迅书信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61—262页。武侠电影中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在当时的流行小说及武侠电影中大都有一个漂亮的女主角,如《儿女英雄传》中有十三妹何玉凤(电影《儿女英雄》中由范雪朋饰演),《荒江女侠》中有方玉琴(同名电影中由徐琴芳饰),《江湖奇侠传》中有红姑(电影《火烧红莲寺》中由胡蝶饰演)。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商业的因素,因为漂亮的女主角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也有社会思潮的因素,因为在近现代中国女权运动逐渐兴起,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了,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作为影片的主角其实暗含着社会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盛行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中,较少出现以侠女和普通女性同为主角的情况,典型者如《儿女英雄传》《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而在《啼笑因缘》中,不但有侠女关秀姑,而且出现了不会武功的女艺人沈凤喜。这一文一武、一动一静,使得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更为多元化,也使社会生活得到更全面、更好的表现。
事实上,歌女形象在世界电影和中国电影史上的歌舞片中较为常见,如《爵士歌王》(TheJazzSinger,Alan Crosland导演,1927年)、《歌女红牡丹》(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1931年)等。武侠电影中出现作为主角的歌女,则较为少见。《啼笑因缘》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始作俑者,而且收效良好。小说《啼笑因缘》后来又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如李晨风导演的《啼笑姻缘》、孙敬导演的《啼笑因缘》,以及岳枫等人联合导演的《故都春梦》等。在这些影片中,歌女沈凤喜成为影片重点发挥和演绎的对象。
歌女的存在,不仅仅丰富了银幕的视觉形象,也为调节电影的叙事节奏和氛围提供了许多方便。一方面,可以使得电影在刀光剑影的紧张氛围之中借助歌女的歌声轻而易举地转入舒缓的节奏。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歌声营造出特定的氛围。比如,在《啼笑因缘》中,出现多处沈凤喜唱歌的情形,如为樊家树唱歌、为刘将军唱歌等,其歌声和场景都极富感染力。不同的唱歌场面相对照,映照出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内蕴。
4.从纯粹复仇行侠到兼具儿女私情
总观在《啼笑因缘》之前流行的武侠小说及电影中的女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即大多有私人复仇的诉求。如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女侠何玉凤有为父复仇的诉求,1927年出品的《儿女英雄》(改编自《儿女英雄传》)第一集《十三妹大破能仁寺》,详细地介绍了何玉凤复仇的原因;[注]《儿女英雄(第一集)》,载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107页。《荒江女侠》讲述了侠女徐琴芳为父复仇的故事;《江湖奇侠传》(系列电影《火烧红莲寺》)涉及江湖恩怨和帮派争斗,同样有复仇的元素。甚至,在这些改编的电影中,复仇几乎是唯一的情节动力。而在《啼笑因缘》中,关秀姑行侠仗义,已无为私人复仇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关秀姑之所以拔刀相助,恰恰是因为她对樊家树的个人情感因素。小说《啼笑因缘》中有一段樊家树观看电影《能仁寺》之后躺在床上的心理活动:“秀姑的立场,固然不像十三妹,可是她一番热心,胜于十三妹待安子、张姑娘了,自己就这样胡思乱想,整夜不曾睡好。”[注]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60页。由此可推测,樊家树可能在从伴侣的角度思考他与关秀姑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出,“侠女十三妹”形象对张恨水塑造自己的侠女形象有深刻影响。
从复仇女侠变身为儿女情侠,其中暗含了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变化。毋庸置疑,无论是为父报仇,还是为本门本派的人复仇,都是一种载“道”行为,其中含有舍“小我”为“大家”。 而在儿女情侠中,“小我”被显现出来,“载道”功能被弱化。换言之,对复仇女侠而言,她们作为道义和正义的化身而存在;而在儿女情侠身上,女侠的个性得到体现。在这方面,《啼笑因缘》做了一次尝试。可惜生不逢时,电影《啼笑因缘》在当时的市场上反响甚为寂寥,据相关史料,明星影片公司虽然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但由于影片脱离了当时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战激情,因此在营业上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注]张伟:《纸上观影录(1921—1949)》,第107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张恨水这种创新性的尝试才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如前已述,除张石川导演的《啼笑因缘》,该小说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多种电影,李晨风编导的《啼笑姻缘》、罗臻导演的《故都春梦》、楚原导演的《新啼笑因缘》、王天林导演的《啼笑姻缘》等都值得一看。
在《儿女英雄》《关东大侠》《荒江女侠》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大都是武林侠客,且以女性角色为主。改编自《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电影也大多以男性角色为主。在这些电影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大都没有情感上的关联。然而,在《啼笑因缘》中,男女主角已创造性地变为情侣关系。其女性角色之一的关秀姑为侠女,男性角色的樊家树为大学生。这种女强男弱的模式在《儿女英雄》中也出现过,但两者又不尽相同。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儿女英雄》中的安骥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而《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则成为义的化身。樊家树虽然不会武功,但是他凭借表哥为政府官员的特殊背景,得以行侠仗义、锄强扶弱。
与复仇女侠变为儿女情侠的人物关系变化相呼应,《啼笑因缘》中构建了多男对多女的情感纠葛模式。凭借三角恋的男女情感,该小说及电影营造出了丰富的矛盾冲突。
值得指出的是,表兄妹情侣在《啼笑因缘》之前的小说与电影中较多出现,在《啼笑因缘》中这种关系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与侠女、侠士与学生的关系。在现代大学教育兴起之前,男女之间的交游局限于本地,又因为女性多在家庭中长大成人,使得亲戚关系成为男女相识的重要前提,表兄妹年龄相仿,接触较多,故有较多的机会发展为恋人。现代大学兴起之后,男女都前往都市中求学,因此,男女交游的范围大大扩大,青春年少、情窦初开的学生自然成为爱情故事的主角。从这个角度来说,《啼笑因缘》确实算得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情感叙事模式。
二、寓行侠仗义于情感纠葛及现实关怀之中
小说《啼笑因缘》及其改编而成的电影和同时代其他小说及影片相比,表现出新的特征,即它不再以行侠仗义为主线,而转变到以情感纠葛为核心。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它从借助官府力量转变到避开政府法律,而主要依靠侠客、义士的力量。张石川导演的《啼笑因缘》第1至6集类似今天的电视连续剧,各集一方面独立成段,另一方面在情节上又具有连续性。从故事情节上看,该《啼笑因缘》电影的故事情节“串联”的意味更强,而改编自《江湖奇侠传》的《火烧红莲寺》的故事情节“并联”的意味更多。该《啼笑因缘》电影往往以悬念结束每一集,而《火烧红莲寺》《儿女英雄》《关东大侠》等电影往往每一集都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一个伟大的作品出来之后,往往会贡献一个经典的模式,并进而催生一系列仿作。当一个模式被过度使用之时,其内部和外部又会产生新的创新需求。文艺就是这样不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当代武侠小说大家古龙曾经总结过现当代武侠小说的模式。他说:“一个有志气,‘天赋异禀’的少年,如何去辛苦学武,学成后如何去扬眉吐气,出人头地。这段经历中当然包括了无数次神话般的巧合奇遇,当然也包括了一段仇恨,一段爱情,最后是报仇雪恨,有情人成了眷属。——一个正直的侠客,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武功,破了江湖中一个规模庞大的恶势力。”[注]古龙:《代序》,载《全本楚留香传奇(一)血海飘香》,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古龙总结出来的这些特点,在张恨水创作《啼笑因缘》时并不全有。张恨水擅长创作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他在创作《啼笑因缘》之前已经有《春明外史》闻名于小说界。可以说,他是以创作社会言情小说的底气来创作《啼笑因缘》的。当出版机构根据读者的阅读趣味要求张恨水在其中加入“武侠故事”时,也就意味着张恨水开始了“言情”+“武侠”融合叙事的尝试。也可以说,正是张恨水等一批擅长写言情小说的小说家加入武侠小说的创作阵营,才促使中国现代言情武侠小说的发展和成熟。可惜的是,张恨水并没有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他创作了《剑胆琴心》和《中原豪侠传》两部反响并不大的武侠小说之后,转而回头继续去创作他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去了。所以,后来人们提及言情武侠小说这一新样式时,更多地提及王度庐、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等人。但无论如何,张恨水将言情与武侠有机融合来构建故事情节、寓行侠仗义于情感纠葛之中的叙事尝试不容忽视。
整体看来,《啼笑因缘》在进行武侠故事情节的建构时体现出如下尝试:
1.从复仇兼行侠变为报恩行侠
关于行侠的动因和机缘,《啼笑因缘》表现出新的特点。简言之,之前的武侠小说如《荒江女侠》《儿女英雄传》《江湖奇侠传》等作品,喜用复仇兼行侠作为侠客的行侠仗义动因,是“感同身受,以己推人”,进而“仗义行侠”“除暴安良”。在《关东大侠》中,赵窈娘为报父仇而习武行侠,甚至不惜落草为寇。在《荒江女侠》中,方玉琴为报父仇而拜师学武,学成后行侠仗义,被称为“荒江女侠”。在《儿女英雄传》中,何玉凤也是因报父仇而拜师学武,在寻找仇人复仇的过程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女十三妹”从此传开。而在《啼笑因缘》中,报恩成为重要的行侠动因。关寿峰父女之所以要设计杀死刘将军,其根由不是刘将军与他们有仇,而是因为他逼疯了沈凤喜。樊家树在关寿峰病重之时为其慷慨解囊,使其得到医治,关氏父女因受滴水之恩而涌泉相报。樊家树托他们帮忙照顾沈凤喜,他们由此以江湖艺人之身份完成了英雄侠义之举。
2.从以行侠仗义为主到以情感纠葛为核心
在20世纪初期流行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中,通常是一个侠义事情构成一个回目或一集电影,侠士、侠女不变,获助者则不断变化。一些改编自武侠小说的电影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前述友联影片公司1927年出品的《儿女英雄》第一集《十三妹大破能仁寺》即以侠女为父报仇过程中的行侠仗义为线索。[注]《儿女英雄(第一集)》,载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 107—108页。在《儿女英雄》第二集中,十三妹护送安骥赴京应试,遇仇人金毛吼,两人在穿云岭比武大战,后在邓九公的帮助下,十三妹大败敌人。[注]《儿女英雄(第二集)》,载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 159页。在《儿女英雄》第三集中,安骥科举考试合格,南归淮扬绿杨村,后被委任为盐城知县,金毛吼之党羽虬驼与白云庵老尼云秋及黄勇合伙谋害安骥一家,十三妹智斗群恶,后在官兵的帮助下成功脱险。一同获救者还有王桂芳父女。[注]《儿女英雄(第三集)》,载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 201—202页。在该系列电影《儿女英雄》中,由于何玉凤与安骥在第一集中就已经结婚,所以,两人的情感戏事实上也不便设为电影的叙事重点。在第二至四集中,何玉凤其实更多的扮演了保镖的角色。何玉凤在保护安骥的过程中,同时惩恶除奸、行侠仗义。换言之,《儿女英雄》在情节安排上更侧重于武功打斗而非情感演绎。
1928—1931年出品的《火烧红莲寺》同样如此。《火烧红莲寺(第1集)》由明星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在该电影中,陆小青与柳迟等人与红莲寺中的恶僧的较量是叙事核心。[注]《火烧红莲寺(第1集)》,载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第169—170页。从小说《江湖奇侠传》到系列电影《火烧红莲寺》,有重大改编,其主要手法和特点是:(1)以某人或某件事为中心,构建电影故事情节。如第1集主要以红莲寺的故事为中心;第6集主要以柳迟的故事为中心。(2)取小说中的人物为其填充故事。如第13集讲述红姑与东方氏的故事,该集的故事大都为电影新编;第16集借用红云、联珠、万清和、常德庆等人物重新构建了故事情节。(3)借用第1集中江湖与朝廷结合的叙事模式,不断发挥第1集中的美女、英雄以及奇功、奇事等元素,形成新的故事,所以整体看来其叙事模式比较单一。(4)除第1集忠于原著之外,其他各集均有较大改编,特别是最后几集几乎可称得上是重新创作。
再比如电影《关东大侠》,其第1集讲述查士雄等侠士在九峰山报国寺除奸僧之事;第2集主要情节为赵窈娘惩治恶徒程鬼,孙明甫与赵窈娘枪毙吴虎臣,两人一起投身国民军。
总之,上述这些电影作品无论对原作的改编程度如何,在侠和情方面均取侠而舍情。而在《啼笑因缘》的小说及电影中,行侠者与受帮助者的故事贯穿作品始终,表现出与前述众小说及电影完全不同的风貌。《啼笑因缘》中的男女主角都处于未婚状态,一男(樊家树)与三女(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关系。他们之间既有友情成分,又有爱情因素;既有男追女(樊家树追求沈凤喜),又有女追男(何丽娜追求樊家树),还有互相暗恋(樊家树与关秀姑)。这四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小说(电影)结束都没有最终结论。这种充满悬念的情节建构,使得该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这种以“言情”为主,武侠为辅的小说和电影,到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言情武侠小说和言情武侠电影类型。
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20世纪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发展,除了增加文化味道(书卷气)外,主要是突出小说的情感色彩。“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情”并非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港台武侠小说家的专利,而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新趋势。[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第78页。这种看法非常在理。事实也是如此,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的创作并非凭空出现的,他们的武侠小说创作笔法有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影子。
3.从借助官府力量到避开朝廷法律
在1932年以前出现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中,官府力量往往成为解决矛盾冲突的决定性力量,官府是左右故事结局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论及,他指出:“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然当时于此等书,则以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注]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而在《啼笑因缘》中,官府成为一种背景,侠客行事有意避开了朝廷法律,完全依照江湖规矩办事。这种思路,应该说对现代江湖世界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因为,从法律角度看,个人没有权力剥夺他人性命,而侠客行侠仗义又免不了杀人,这势必触犯法律,形成悖论。可以想象,一旦政府力量介入,则所谓的快意恩仇和驰骋江湖肯定要大打折扣。
在《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小说中,官府力量得到较多的表现。在电影《儿女英雄》《火烧红莲寺》各集中,侠客也大都在官府力量的帮助下取得胜利。比如,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本为朝廷官员之后,其丈夫安骥也是朝廷官员之后,而且他正打算通过努力读书进入官场。小说《江湖奇侠传》中,帮派之争是主体,但决定胜负的仍是官府力量。而《啼笑因缘》虽也涉及官场、官员,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官方的力量(人力、法律等)在矛盾冲突过程中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甚至在政府官员刘将军被关寿峰父女杀死之后,也仅有新闻见于报端,官府并无作为。
这种避开朝廷法律的笔法,可视为另一种现实关怀。它借此提醒观众,侠客之仗义杀人仅可在小说和电影中做到,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无法实现。
4.侠士从军作为一种归宿
侠士从军也是《啼笑因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啼笑因缘》续集中,张恨水安排关寿峰和关秀姑投身革命。张恨水指出:他扭不过人情,写了短短的续集。他所安排的人物结局是:关寿峰父女在关外加入义勇军而殉难,沈凤喜疯癫得玉殒香消,以樊家树与何丽娜的一个野祭结束全篇。[注]张恨水:《〈啼笑因缘〉的尾巴》,载《我的写作生涯》,第65页。张恨水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到,《啼笑因缘》面世之后,他自己没有续写,却出现了一些由别人写的《续啼笑因缘》《反啼笑因缘》《啼笑因缘零碎》等,全都是违反他的本意的。同时,三友书社不断催促他续著,又正值日军大举进攻东北,所以他就在续集中写了民族抗日的事。[注]张恨水:《从〈啼笑因缘〉起决心赶上时代》,载《写作生涯回忆录》,第147页。张恨水的回忆耐人寻味。
侠士从军的情节是小说续集中增加的,故电影《啼笑因缘》中没有。然而,在当时的武侠电影中,这种情况也有。例如,在月明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的《关东大侠(第2集)》(任彭年导演)中,孙明甫与赵窈娘枪毙吴虎臣之后,一起投身国民军。[注]《关东大侠(第2集)》,载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第163页。这种侠士从军的情况其实是时代烙印。《关东大侠》与《啼笑因缘》的时代背景都是战乱时期,从军报国是当时突出的社会现象。
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的尾巴》和《从〈啼笑因缘〉起决心赶上时代》等文章看来,安排关寿峰父女从军有应景的成分。他所设计的理想情节模式应当是“言情+武侠”。事实上,在《啼笑因缘》之后所出现的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这种套路。因为抗战的原因,中国现代武侠电影发展到《啼笑因缘》时事实上已告一段落。直至20世纪80年代,武侠电影再度兴起,总观当时的影坛,可见《啼笑因缘》开启的这种“言情+武侠”的叙事模式被发扬光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品种众多,形式多样。《啼笑因缘》的叙事模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在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作品以及由这些作品改编的电影中,观众很容易看到《啼笑因缘》的影子,而《少林寺》(张鑫炎导演)、《武当》(孙沙导演)、《武林志》(张华勋导演)、《南拳王》(萧龙导演)等电影走的又是另外不同的路子。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从军作为侠士的一种归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中经常出现,比如由冯骥才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神鞭》中的主角傻二最后就走向从军抗敌之路。总之,小说原著红遍大江南北,张石川导演的《啼笑因缘》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票房,小说续集中出现侠士从军的情节设置,这诸种现象表明,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观众在观看武侠电影时,并非完全以消遣、娱乐之心待之,他们对这类作品有着现实关怀的期待。
三、结语
就“言情+武侠”的叙事模式而言,无论是在中国小说史还是电影史上,《啼笑因缘》都不是始作俑者。但是,将言情置于武侠之上,使言情的比重超过武侠者,《啼笑因缘》确实算得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张恨水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创作出更好的言情武侠小说作品,有他个人的写作兴趣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梳理中国小说史和电影史,可以看到,言情武侠小说和言情武侠电影的新类型经由数代人努力,最终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重要类型。
行侠仗义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通常也是受内心的情感驱使而产生的。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注]休谟:《人性论》(全两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36页。或许,其他驱动力也与爱情一样会使侠客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回报,但是,基于爱情的动因可能是最能够使侠客得到回报的动因。而且,爱情作为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情,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引起人们的共鸣。小说《啼笑因缘》自面世以来,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电影公司将其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很好地证明了它有着较强的生命力。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被称为“当代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他们的作品也是影视改编的常客。若细读他们的作品,可见《啼笑因缘》的影子。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啼笑因缘》以一种独特的言情武侠小说面貌出现,或许也属于这种情况。正如张恨水谈《啼笑因缘》成因时所谈到的,由于报社担心小说里没有豪侠人物会减少对读者的吸引力,他于是照办,没想到小说的反响奇佳。[注]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第44—46页。武侠小说的盛行有其复杂的因素,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由于投合孤立无援的中国人的侠客崇拜心理和喜欢紧张曲折的欣赏习惯而可能风行,经由书商和作者的通力合作批量生产,很快成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通俗艺术形式”。[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插图珍藏本)》,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而电影从小说中寻找素材,可由此获得良好的观众基础和市场基础。张石川导演的《啼笑因缘》,就当时的市场反响而言的确不及由《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但从整个中国电影发展史来看,其影响同样巨大,意义不同一般。凡创新之作,并非一定是典范之作。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意识,为中国文学、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说,《啼笑因缘》不但可以在中国言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也确实值得一提。同理,电影《啼笑因缘》在中国电影史上同样有着非常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