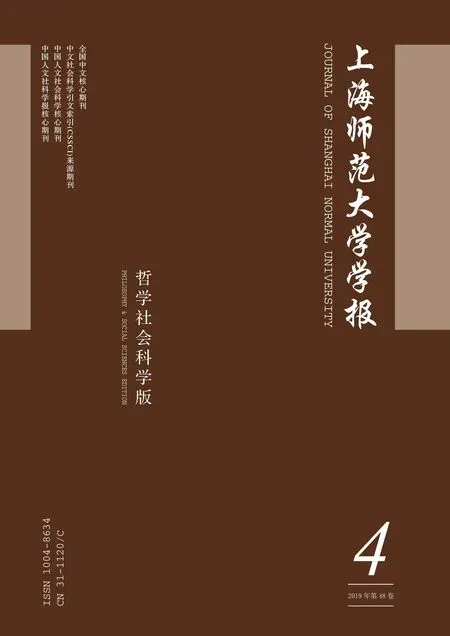先秦汉初经典中的“精”与“神”及“精神”古义探源
翟奎凤
“精神”是一个典型的并列合成词,在早期中国哲学经典中,“精神”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在此之前的较长时间里“精”与“神”两字也常关联出现,在战国后期逐步凝合为一个合成词。“精”在春秋时期的思想经典中是一种心意修养的工夫,与“精”相对的“神”往往有一定的宗教人格神意味。战国时期出现“精气”一词,精成为一种本体性的纯能量,而且这种精、精气是一种灵气、神气,是人的灵魂的来源。与“精气”相对,密切关联的是本体化的妙道之“神”或神明。战国晚期,随着“神明”具有本体、主体二义,“精神”也有天地精神、人心精神二义;后来“精神”更多地约定为人的心神。目前,关于“精气”的研究有不少文章,但关于“精神”范畴的探源研究还很少。[注]郑开在《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五章“境界形而上学”第二节“精神哲学”中对“精神”一词做了勾勒,他认为在汉语语境下“精神哲学以反求诸己、滋养自身生命为基本特征,其中消解了生命和学问的隔阂,换言之,精神哲人掠过了思想和践行(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间离,而进入知行合一的境界”(第340页)。丁原植的《精气说与精神、精诚两观念的起源》(《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对此也做了探讨。
一、心意修养之“精”与宗教人格“神”
“精”本义为上等细米,纯粹的好米,《说文解字》说“精:择也。从米青声”。[注]许慎撰、徐铉校、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精”在经典中出现并富有义理意味大概是在春秋时期,这在《国语》《左传》等典籍中有集中体现。周惠王十五年(前662),“有神降于莘”,周惠王问内史过是怎么回事,内史过在解释此“降神”问题时有下面一段话:“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注]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卷一《周语上·内史过论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这里把“齐明”“衷正”“精洁”[注]公元前665年,即晋献公十二年(系年据《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骊姬与优施欲谋害太子申生,优施论申生性格曰:“其为人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洁易辱,重偾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又说:“甚精必愚。精为易辱,愚不知避难。”参见《国语》,卷七《晋语·优施教骊姬远太子》,第177、178页。韦昭注曰“小心,多畏忌;精洁,不忍辱”,“精洁”也就是说人格修养纯粹,不能容忍自己有人格污点。优施为优人,人文素养不高,“精洁”之语不可能是他首次使用,应该说,在此前后“精洁”之语可能已为人们熟知。及“惠和”作为君之四德,“精”与修养关联了起来。内史过接着又论“虢必亡”说:“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这里“精意”之“精”为虔诚之意,也有后世工夫论的意味。
周襄王四年(前649),同样是内史过论“晋侯无后”说:
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则以训之,制义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孚,信也。然则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今晋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赂,虐其处者,弃其信也;不敬王命,弃其礼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恶实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注]《国语》,卷一《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第24页。
内史过这段话非常有意味。“祓除”为古代除灾去邪的一种祭祀,《周礼·春官·女巫》曰:“掌岁时祓除、衅俗。” 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 贾公彦疏:“一月有三巳,据上旬之巳而为祓除之事,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八册,第2075页。《后汉书·礼仪志上》载:“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注]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下),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076页。因此,“祓除”有“洁净”“纯洁”之义,内史过这里所说的“祓除其心”就是洁净其心的意思。韦昭注也说,“祓,犹拂也”,“精,洁也”。结合后面所说的“以恶实心,弃其精也”,“祓除其心”也可以说就是“以善实心”,使心纯净、纯洁。内史过这里的“祓除其心,精也”“非精不和”,与其前面所说的“精洁”“精意”相互呼应,应该说在他这里“精”被赋予了丰满的主体修养论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这里说“昭明物则,礼也”,也让我们联想到《大学》的“格物”,这可能是“格物”的一个比较古老的源头或理解方式。
公元前593年,周定王对晋侯使者随会论肴烝之礼说:“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建。古之善礼者,将焉用全烝?”[注]《国语》,卷二《周语中·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第44页。这里的“精心”也是使其心精纯之义。
《国语》之《楚语下》载,春秋末期观射父与楚昭王论绝地天通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注]《国语》,卷十八《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第376页。这段话也让我们联想起内史过所说的君之四德“齐明、衷正、精洁、惠和”,“精爽”与“精洁”的意思是接近的。而且,这两处文献也都谈到“降神”的问题,只不过内史过所说的是指上天降临显现的一些祥瑞的自然现象,而观射父这里所说的是指神降临到人身上,有点类似后世所说的附体之巫婆、神汉的意味。《楚语下》又载,观射父与楚王论礼之丰啬说:“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注]《国语》,卷十八《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第380页。这里说“神以精明临民”,也让我们想起《左传·僖公五年》所载宫之奇针对虢公的“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注]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其意思是,不能说谁祭祀的东西丰盛,神就眷顾、向着谁,根本的还是看德性修养、内心精明之德。
总体上来看,春秋时期,“精”主要是指心意的一种纯洁、虔诚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往往与“神”相应,有一定宗教性;内心精洁、精纯,可以感应神明。上面所论及的一些关键词,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出现。关于“精洁”,《韩非子·孤愤》说:“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注]韩非、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四《孤愤第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关于“精爽”,《左传·昭公七年》子产论伯有为鬼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注]《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十四,第1248、1249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乐祁佐之语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注]《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一,第1446页。《楚辞·七谏·怨世》说:“专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注]刘向辑、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孙雪霄校点:《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关于“精明”,《礼记·祭统》说“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又说“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注]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53页。从这些经典语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精洁、精明、精爽是心的一种德性状态,这种状态是“交于神明”——与神明交感的必要条件。在这些文献中,“精”与“神”可以说已经在一个密切关联的语句中同时出现了。然而,这些表达往往还有些宗教意味,应该还不能说是后来“精神”一词的直接源头。
作为内心修养工夫的“精”在《管子》中也多有论说。如《法法篇》说:“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注]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上册,第307页。又说:“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第312页。《帛书·易传·二三子问》载孔子论龙说“戒事敬命,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注]于豪亮:《马王堆帛书〈周易〉释文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又论艮卦说“能精能白,必为上客;能白能精,必为囗囗。以精白长众,难得也”。[注]于豪亮:《马王堆帛书〈周易〉释文校注》,第183页。《尚书》中唯一出现“精”字,见于《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篇文献为古文《尚书》,一般认为是后世所伪造,但结合上面的文献来看,无论如何,“精”作为修身工夫这种观念的表述是相当早的。
二、精气与哲学本体化的“神明”
春秋时期,“精”主要是“心之德”的一种修养工夫和状态;到了战国时期,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意义的“精气”说开始出现。而以《管子》为代表的“精气”说,一般认为导源于《老子》的“精”论。《老子》第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作为一种“恍惚”之存在,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这种“精”似可理解为一种生生之纯“能量”[注]一般的英译本都将“精”译为essence,陈荣捷的英译注说“The word Ching(essence) also means intelligence,spirit,life-force”。林语堂也英译为“life-force”,转引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7页。。《老子》第55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攫鸟猛兽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注]《老子今注今译》,第274页。这里的“精”进一步接近于精气[注]周立升、王德敏认为“精气论是从老子的理论体系中脱胎出来的”。参见周立升、王德敏:《管子中的精气论及其历史贡献》,《哲学研究》1983年第5期。。这里的“精”与“和”也较为类似,内史过也说过“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都是以“精”与“和”对举;只不过内史过之“精”“和”更多是指主体的德性功能,而老子的“精”“和”有较多客观义,是一种精气、和气。但在老子这里,这种“精和”之气于赤子婴儿而言有先天性,对成人来说也是“含德之厚”的结果,跟主体的德性也是有关联的。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早期中国思想史演变的脉络。
“精气”一词的直接出现,目前学界多认为首先体现在《管子》中。[注]李存山先生指出:“‘精气’概念不见于春秋和春秋以前的历史记载和著作,而首见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水地》篇(笔者同意以《水地》篇中所列齐、楚、越、秦、晋、燕、宋之水断定它作于战国前期的观点),又见于《易传》等著作。”参见李存山:《〈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探微》,《管子学刊》1989年第2期,第3页。区分出“精气”,似乎与之相对的就是粗气、浊气,《文子·九守篇》说:“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与这段话类似,《淮南子·精神训》也说“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庄子》亦屡以“精粗”论物道。《管子》之《内业篇》说:“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43页。这种“精气”,主要还是指在特定心术(专意、一心、止、已)状态下激发出来的“精气”。《水地篇》中说“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815页。,这种“精气”是指人身客观的气,而且偏于生殖之精气,与心德修养无甚关系。[注]这种生殖之“精气”,《易传·系辞》也说:“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五行篇》中说“货曋神庐,合于精气”,[注]姜涛的《管子新注》(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23页)认为,“货曋神庐”的意思是“教化深入内心”,“‘货’,与‘化’同声通假,教化”,“‘曋’,据丁士涵说,当为‘覃’,及、至”,“‘神庐’,内心,与‘精舍’同义”。《侈靡篇》中说“且夫天地精气有五,不必为沮”,[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742页。显然,这些“精气”都是客观的,甚至是外在于人的。
《管子》中的“精”字甚多,其中不少就是指“精气”。如《内业篇》中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37页。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31页。《老子》第39章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联系这里来看,“精”“精气”与“一”“道”是类似的。《管子·心术下》又说“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又说“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也进一步说明“精”“一”“道”之间的贯通性。由这些也可以推测,《管子》中的精、精气说可能是渊源于《老子》论“精”,在《老子》中“精”与“道”已建立了密切关联。这种气的存在状态非常类似于老子描写的“道”——无形无象、遍在一切,是生化万物的根本,是万物生命力的根本,要想获得这种气,不能靠力量,只能通过修德来摄取、安固精气。这种“德”在《管子》中主要包括“虚无”“清静”“正定”,因此《内业篇》中又说:“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37页。“精舍”就是说在“正、静、定”状态下,精气会来充溢身心。《内业篇》中还说:“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38页。这种“精”“精气”,在《管子》中与“神”也非常类似,如《心术上》说:“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759页。其后面又接着对此句话解说道:“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世人之所职者精也。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故馆不辟除,则贵人不舍焉。故曰不洁则神不处。”[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765页。迎接贵人的到来,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要接纳最为尊贵的“神”的入住,内心更是要纯洁、清静、虚静、一尘不染。我们能看到内史过所论的“精洁”“祓除其心,精也”,以及观射父所说的“精爽”,与《管子》上面的一些论述有接近处,只不过,在《管子》中“精”明显已经客观化为一种类似于道的气,“神”也已经没有了人格神意味,而成为一种精气、灵气。[注]《管子·内业篇》用到“灵气”一词:“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50页。可见,在《管子》中“精”“神”“灵”“道”等范畴是贯通的,可以相互诠释,精气也是一种灵气。而内史过、观射父所说的“精”较为接近于《管子》中所说的“静”,指内心的一种虚静、纯净状态。基于此,很多学者认为《管子》中的“精气”与“神”是一致的。《内业篇》中也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945页。这里“精”与“形”相对,“精”是人的灵魂、心神的基础,“精气”是一种灵明之气,“神”更侧重其功能之妙。对于“道”“精气”“神”的内在贯通性,丁原植也指出,“以‘道’所定名的天道运行,就其构成的质素而言为‘气’,就其本然的情状而言为‘精’,而就其运作的效用而言为‘神’”。[注]丁原植:《精气说与精神、精诚两观念的起源》,第16页。
帛书《黄帝四经》论及“精”,与《管子》很接近。例如,《经法·道法第一》:“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注]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页。《经法·论第六》:“强生威,威生惠,惠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帝王者,执此道也。”[注]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134页。《道原》:“恒无之初,迵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迵无名。”[注]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399页。“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谓能精。”[注]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406页。陈鼓应也指出(第407页),这里的“精”很接近于“神明”。《易传·系辞》云“通神明之德”,《荀子·儒效》云“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综合来看,这里的“精”既有主体修养义,也有客观精气义;“精则神”一语进一步揭示了精与神的关联和区别,“神”是在“精”的基础上的一种不测妙境,“精”与“神”在这里紧密关联在一起。
与《管子》《黄帝四经》中的“精”“神”说接近的是《易传》。比如,《乾·文言传》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及“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精”“精气”是生命活力的根本能量。关于“神”“神明”,《系辞上》说“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系辞下》中,“精”“神”还同时出现在一个语句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比较《易传》与《管子》及《黄帝四经》的“精”“神”说,应该说《易传》的哲学性、思想性更强,当是在受到稷下黄老思想影响后发展起来的。对此,陈鼓应的《易传与道家思想》中有揭示。[注]参见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第三部分“《系辞》与稷下道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8、109页。在《易传》中,“神”比“精”更重要,其神化哲学在北宋张载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总体上来看,《管子》《黄帝四经》《易传》所论“精”“精气”“神”“神明”是非常接近的,可以相互发明。在这些论述中,“精”与“神”密切关联在一起,“精”主要指精气,“神”常指“神明”,这里的“神”已经没有人格神意味,而是变化妙道之精微。[注]白奚也指出,“《管子》借精气理论表达的‘神明’,已完全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了”。见白奚:《〈管子〉中的精气与神明理论》,载《两岸清华“气论与中国哲学”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值得一提的是,《大戴礼记》把精气分为阴阳,“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注]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五《曾子天圆第五十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7页。大致说来,这些文献把“精”加以“神”化,把“神”本体化,“精气”是一种灵气、生命力的象征,有了“神”性,而这种“神”是《易传》中所说的本体化的“不测”之神、“妙万物”之神。精气是生命力的根本能量,同时也是灵气、灵明之气,人的聪明智慧、能否认知事物也源于精气。在这些文献中,虽然“精”与“神”已经非常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精神”一词已经呼之欲出,但是,无论是《管子》《黄帝四经》还是《易传》,都没有真正出现合成词“精神”。
三、合成词“精神”的出现及其本体、主体二义
从战国晚期的经典文献来看,《韩非子》《庄子》《荀子》等中都已经出现了“精神”一词。到汉初的《淮南子》时,“精神”一词大量出现,频率非常之高。早期的“精神”用语能看出其意义基本上是“精气”与“神明”的融合,本体义比较强,但后来则偏指人的精神状态及其心智、心理活动。
《礼记·聘义》载孔子论玉之德曰:“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郑玄说“精神亦谓精气也”,[注]郑玄注、孔颖达疏、喻遂生等整理:《礼记正义》(五),卷第六十三, “《四库》家藏”从书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4页。把“神”弱化了。《本草纲目》论“玉井水”说“山有玉而草木润,身有玉而毛发黑”,[注]李时珍撰、胡双元等校注:《本草纲目》,水部第五卷“玉井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精神见于山川”之义的发挥。如果说,诚如郑玄所解,这里的“精神”偏指精气,那么,此“精神”一词即便未必真为孔子所言,其出现可能也是比较早的。当然,完全以“精气”解这里的“精神”也未必十分准确,它没有把“神”特有的妙意和灵性揭示出来。
《荀子》有两处论及“精神”。一是《成相篇》中说“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及,一而不贰为圣人”,杨倞注曰“好而不二,则通于神明也”及“‘相反’谓反覆不离散也”。[注]“王引之曰:‘反’当为‘及’字之误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贰。杨说失之。”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八《成相篇第二十五》,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1页。显然,这里的“精神”应该就是前面“思乃精”“神以成”的组合。“思乃精”也让我们想起《管子》中所说的“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以及“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专一、专精能够通神明,这是《荀子》中比较突出的思想。“精神相及”也让我们联想起《易传·系辞》中所说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也就是说,《成相篇》中的“精神”实际上严格说来还不算是一个合成词,“精”“神”是两个词并放在一起的。《荀子·赋》颂云“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杨倞注曰:“至精至神,通于变化,唯云乃可当此说也。”[注]《荀子集解》,卷十八《赋篇第二十六》,第477页。“至精”“至神”见于《易传·系辞》的“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其实,这里的“精神”应该说作为一个词,凝合性比较强了,但其重在“神”,有点类似后来常说的“神通广大”的意思。总体上来看,《荀子》中的两处“精神”还不是后来通常所说的作为人之主体心灵意义上的。《荀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已经出现主体意义上的心神之义,但是《荀子》中没有后来《韩非子》《庄子》中大量出现的主体心神意义上的“精神”一词。
《庄子》中8次使用到“精神”一词,但是诚如刘笑敢所指出的,“精神”一词在《庄子》中皆见于外杂篇,一般认为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比内篇要晚。[注]《庄子》内篇虽然没有出现“精神”一词,但“精”与“神”有相对出现,如《德充符》篇载:“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庄子》中有三处“精神”与“心”并提,如《天道篇》中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注]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卷五中《外篇·天道第十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三册,第457页。,以及“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注]《庄子集释》,卷五中《外篇·天道第十三》,第三册,第468页。《知北游》中载老聃回答孔子何谓至道时说“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注]《庄子集释》,卷七下《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第三册,第741页。这三处“精神”与“心”相对,偏指人心之神明。“心”是具体心理活动状态,“神明”是在特定心理状态下的一种高级境界。《刻意篇》说“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注]《庄子集释》,卷六上《外篇·刻意第十五》,第三册,第544页。,这段话类似见于《淮南子·道应训》,但后者中“精神四达并流”作“神明四通并流”;这里的“精神”“神明”,与客观或本体本源性的“道”比较接近。类似地,《知北游》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注]《庄子集释》,卷七下《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第三册,第741页。《天下篇》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注]《庄子集释》,卷十下《杂篇·天下第三十三》,第四册,第1098、1099页。这几处“精神”似均可理解为与“道”较为接近的“神明”。《列御寇》中说:“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注]《庄子集释》,卷十上《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第四册,第1047页。这里的两处“精神”,包括前面的“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澡雪而精神”,都是指作为人之主体的心神。“澡雪精神”一语也颇值得深思,按“精神”本义,精气与神明都是纯粹光明的,而需要“澡雪”的精神显然是卑污、蹇浅的精神,是习气熏染下被污染的精神,不再是精神的本来面目。总体上看,《庄子》中的“精神”可以理解为“神明”,或为客观本体之神明,或为主体人心之神明。
《韩非子》一书中9处出现“精神”,而且仅见于《解老》《喻老》两篇。《解老》中说“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注]王先慎集解、姜俊俊校点:《韩非子》,卷六《解老第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又说“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注]《韩非子》,第176页。这两处“精神”很明确是指人的“精神”,是“心神”能量;今天我们也常说要“爱惜精神”,其最早出处当在于此。《喻老》中说“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注]《韩非子》,卷七《喻老第二十一》,第196页。《文子·九守》说:“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血气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声色”,这句话相似的也见于《淮南子·精神训》。对比来看,“精神”即是“神明”的意思,都是在主体意义上来讲的。神明有本体意义上的天地神明,也有主体意义上的人之神明(即心神),“精神”与此类似,也有天地精神、人之精神二义。“精神竭于外貌”就是“费神”的意思,其相反也是说要“爱精神”。《解老》中又说“凡所谓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上盛畜积,而鬼不乱其精神,则德尽在于民矣”,[注]《韩非子》,第168页。以及“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注]《韩非子》,第182页。这里所说的“精神乱”的问题,与上面“爱精神”主要是指心神能量不同。这里的“精神”主要是指心智活动;心智活动不能错乱,要神志清晰。当然,如果费神多,不爱惜精神,可能会导致神志不清、精神错乱。但无疑,前者还是偏于心神能量,后者则偏于心智功能的正常发挥。《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中说“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注]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51页。《仲秋纪·论威》说“敌人之悼惧惮恐,单荡精神尽矣,咸若狂魄,形性相离,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注]“形性相离,犹言魂不附体”,见张富祥注说:《吕氏春秋》,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这两处的“精神”都是指人的心神,而且与“形”相对出现。《楚辞》中“精神”一词两见——“独冤抑而无极兮,伤精神而寿夭”[注]《楚辞》,卷十三《七谏章句·怨世》,第317页。和“众人莫可与论道兮,悲精神之不通”[注]《楚辞》,卷十三《七谏章句·谬谏》,第332页。——也比较明确是指“心神”“心意”。
《文子》《淮南子》两书中很多语句相似度很高,[注]过去关于这两本书谁影响谁争论很多,本文倾向于认为《淮南子》因袭了《文子》。白奚指出:“《文子》与先秦两汉很多传世文献在文字表述上都有交叉关系,仅以上引材料涉及的《文子》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交叉为例来看,《文子》一书更可能是成书于战国晚期,它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类集腋成裘式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见白奚:《〈文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太一”概念引发的思考》,《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10页。而且其中的“精神”一词出现频率非常高:《文子》有20多处,《淮南子》有40多处。从两书中关于“精神”的具体阐述来看,其具体内涵很大层面上与《庄子》《韩非子》也比较类似。《文子·精诚》中说“是故圣人内修道德,而不外饰仁义,知九窍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注]彭裕商:《文子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7页。这句话类似地也见于《淮南子·俶真训》。何谓“精神之和”?《庄子·德充符》中说“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精神之和”与“德之和”应该是一个意思,这样,“精神”与“德”同义。《管子》之《内业篇》中也说“形不正,德不来”,关联起来看,“精神之和”的“精神”应该是从本体意义上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道”“德”是一致的。当然,《文子》《淮南子》中的精神更多是从主体心神意义上来讲的。如《文子·九守》中说:“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注]彭裕商:《文子校注》,第51页。,这句话类似地见于《淮南子·精神训》,这里“精神”类似后来所说的与形体相对的灵魂。《文子·九守·守弱》中说“夫精神志气者,静而日充以壮,躁而日耗以老,是故圣人持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浮沉”,[注]彭裕商:《文子校注》,第70页。这句话类似地见于《淮南子·原道训》,这里的“精神”与心神之“神”是一致的。《文子·九守》中说“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注]彭裕商:《文子校注》,第54页。这句话类似地见于《淮南子·精神训》。《文子·下德》中说“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不能惑”,[注]彭裕商:《文子校注》,第175页。这句话类似地见于《淮南子·泛论训》。关于“精神内守”,《黄帝内经》中也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注]《黄帝内经·素问》,卷一《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医经典导读丛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内守”话语下的精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心意、意识、意念等。《黄帝内经》中讨论“精神”的也非常多,而且非常独特,如说“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注]《黄帝内经·素问》,卷一《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第35页。,以及“五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注]《黄帝内经·灵枢》,卷六《平人绝谷第三十二》,中医经典导读丛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可见,与抽象的哲学讨论的不同,《黄帝内经》中论“精神”多强调其与气血、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所论的“精神”,有时也与精气的意义相似,如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注]《黄帝内经·素问》,卷一《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第33页。
四、结语
中国哲学早期经典之“精神”范畴,总体上来看其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春秋时期,在宗教话语下,“精”是心意修养的工夫,与之相对关联出现的“神”往往有人格神意味;二是战国早期、中期,“精”是一种“精气”、灵气,与之密切关联的“神”成为一种不测的妙道本体;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晚期,合成词“精神”出现。作为合成词“精神”,既可以指本体性的天地精神,也可以指主体性的人的心神。秦汉以后,“精神”更多是指人的心神。但同样是作为心神意义上的精神,其内涵及具体用法又有些差别,有时偏重指灵魂,有时指向与物质相对的人的心念意识活动。在近现代与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的交融中,进入现代世界的“精神”一词也突破了其传统内涵,可以指一个事物的本质、实质,乃至存在的理念世界,如汉语语境下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绝对“精神”一词。总体而言,现代学术语境下的精神往往偏重某种思想性、意志性存在,与早期古典话语下偏重生命活力能量之体或人心灵性能量之体有所不同。当然,在生活语境特别是养生语境下使用的“精神”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与战国末、秦汉时期经典中的“精神”还是一脉相承的。
——修身与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