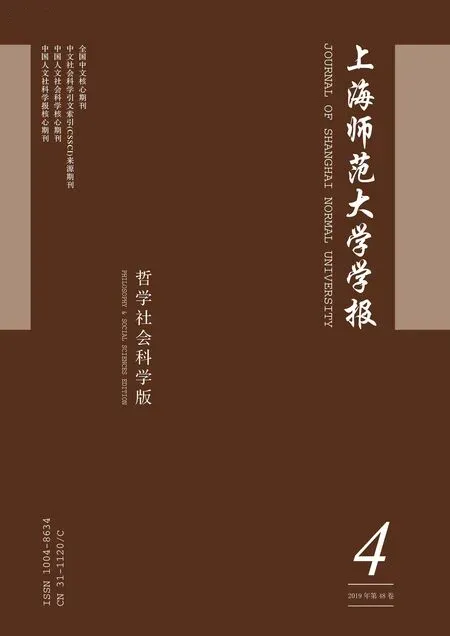隋代县令杂考
刘 啸
汉唐时期,县是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因此,县的长官县令、县长,或以县为国称相者,是最基层的地方行政长官。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县府组织,严耕望先生已有经典性的研究;关于唐代的县,学界也一直给予相当的关注。[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五章“县廷组织”,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6年影印第5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卷上,第六章“(魏晋南朝)县府组织”,及卷下,第六章“(北朝)县府组织”,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0年第3版。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四章“县令”,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版;《唐代基层文官》,第三章“县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张玉兴的《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则是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唐代县级官府组织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余不备举。相对于汉魏六朝及唐代,隋代县的研究却乏人问津。其原因:一是因为史料的问题。众所周知,传世典籍的记载大都重中央轻地方,隋代又国祚短促,文献不足征。二是由于“隋唐”作为研究领域不言自明的前提,加上唐制的确大部分继承了隋制,所以用唐代的县制来说明隋代,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注]吕思勉先生认为:“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见氏著《中国通史》,“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本文尝试勾稽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关于隋代县政的一些史料,并以县令为例探讨这一以往研究中比较忽视的问题。
一、县的等级
隋初,地方行政有州、郡、县三级,开皇三年(583)“罢郡,以州统县”,改三级制为两级制。炀帝虽然又“罢州置郡”,[注]《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792、802页。以郡统县,实际并无不同。
隋县千余,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地位有高低,选任有考量。隋初继承北齐之制,县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的差别,形成三等九级制。其中,京兆所属大兴、长安两县与他县不同。两县县令官品在从五品下,不仅高于从六品上的上县令,而且高于正六品上的下郡太守;其每县属员合计147人,不仅多于上上县的99人,而且多于上上郡的146人。[注]《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783、784、786页。虽然崇重京县权威是北朝以来的传统,[注]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25—626页。但县令地位高于郡守,以下凌上,行政运作中也确实有滞碍难通之处。隋改三级制为两级制,大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内。后来隋炀帝虽然改州为郡,并将“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令,并增为正五品”,[注]《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802页。但他同时也提高了郡太守的品级,当时的下郡太守被提高到了从四品,还是比这四县令的官品要高,地方行政制度中的层级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三等九级制本是区分等级的惯用手法,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大概也与此有关。[注]中正清定九品,一品徒有其名,是不授人的,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5页。另参见刘啸、潘星辉:《从“以多为贵”到“以少为贵”:品秩数列反转探微》,收入虞万里主编:《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但这种区分诸县等级的方法在隋代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载隋文帝“(开皇)十四年……改九等州县为上、中、中下、下,凡四等”。据此可知,开皇十四年时,除大兴、长安两县外,将原来三等中的中等分出中下一级,形成了新的四等制。隋文帝划分四等制的原因、依据,我们都不知道。同卷又载隋炀帝时“诸县皆以所管闲剧及冲要以为等级”。[注]《隋书》,卷二十八,第793、802页。这次的依据是闲剧及冲要,并再一次划定诸县的等级。
那么,隋炀帝时期,全国县的等级,除了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以外,是三等九级制还是四等制呢?笔者认为,大概仍是开皇十四年新划定的四等制。众所周知,唐代县有赤(京)、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等之差。[注]按照区分标准的宽严,也有七等之说,两者实际相同,参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236—251页。赤(京)、畿、望、紧的划法不见于前代,是唐代的首创,但划分的依据显然也是以闲剧及冲要。除此以外的县按四等划分,却是继承了开皇十四年的隋制,唐初似乎没有对诸县的等级问题进行过讨论。这说明这种四等划分之制自隋代建立以后没有经过反复,也就说明隋炀帝时的县的等级是四级。赖瑞和先生认为,唐代州县分为十等是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由裴行俭创始的。[注]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248—251页。应该指出的是,新创的唐制中包含了对隋制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县的等级,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载隋文帝时王、二王后及公、侯、伯、子、男国均有国令,等级从流内视从六品至视正八品,这其中当然有以县为国者,但是大概都不是治民的县官,所以,以后隋炀帝把国令都改成了家令,同时只留下王、公、侯三等爵位,并没有引起什么混乱。[注]《隋书》,卷二十八,第790、801—802页。本卷说文帝时“子、男无令”(第782页),但官品表的“流内视品十四等”中又说“子、男国令”在视正八品(第790页),未知是否曾有改动。另外,本卷载,隋代百官之中只见县令,未见县长。众所周知,自汉代以来,以户数为标准,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魏晋南朝虽不严格执行此标准,但有令有长。北魏前期有令有长,后期授任渐滥,居县者皆为令;北齐、北周则都是县令。[注]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317—324、625—630页。隋代是否上承北齐、北周而只置令呢?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一五·县令》:“隋县有令、有长。”[注]杜佑:《通典》,卷三十三,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19页。这明白地指出隋县既设令也设长。但隋代以什么原则来区分县令、长,却很不清楚。即使隋炀帝以闲剧及冲要为县划分等级,但似乎也并未执行。例如,《隋书》卷七《李密传》载:“(李)密攻下巩县,获县长柴孝和,拜为护军。”[注]《隋书》,卷七十,第1628页。《资治通鉴考异》引《略记》及《杂记》系此事于恭帝义宁元年(617)二月,[注]《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条,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722—5723页。此时巩县的长官为县长。巩县,隋代属河南郡,有兴洛仓;唐代也属河南郡,是畿县。[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第834页;《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第982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134页。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巩县西至唐代东都洛阳仅一百四十里,四面有山河之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隋炀帝时,河南、洛阳两县上升至京县地位,近旁的巩县的地位恐怕也不会太低;再加上巩县是兴洛仓之所在,军事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隋书》卷七《李密传》载:“(李)密与(翟)让领精兵七千人,以大业十三年春,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注]《隋书》,卷七十《李密传》,第1628页。这批“道路不绝”的老弱中,大概也是以巩县之民居多。无论是从战略地位、经济意义还是人口规模来说,巩县的地位都应该在中县之上,但这个县却是设县长而非县令。
又如,《崔长先墓志》载:“释褐黄州黄陂县尉,以治政有功,超迁监察御史。……出为许州司兵参军,转襄城郡主簿,迁河南郡新安县长……于时东夏未宾,圣皇旰食,以公艺用优洽,谋略纵横,可绥静方隅,弼成岳牧,以本官检校陕州总管府长史。王世充窃名假号,旅拒三川,秦王受赈出军,方清四险。……以武德八年岁次乙酉七月癸巳朔,十四日景午,终于洛州公馆,春秋六十有二。”[注]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录文见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崔长先卒于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六十二,上推其生年在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即使崔氏18岁释褐,也已经是隋开皇元年(581)。他又以许州司兵参军转襄城郡主簿,迁河南郡新安县长,前州后郡,则崔氏任新安县长必在隋炀帝改州为郡之后。新安县,隋代属河南郡;唐代也属河南郡,是畿县。[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第834页;《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第983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第142页。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安县东至唐代东都洛阳仅七十里,而且隋代还有冶官设于此地,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都不差,但也是设县长而非县令。
再如,《姜謩墓志》载:“隋文受禅,授秦王右府司兵,迁长史东阁祭酒,除博州清平县令……病免久之,除并州晋阳县长。仍属隋政不纲,生灵涂炭,群后有瞻乌之望,天下成逐鹿之情。”[注]《姜謩墓志》,未见图版。录文见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二,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版,第15984页。标点为笔者所加。姜謩,新、旧《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卷五十九《姜謩传》载:“謩,大业末为晋阳长,会高祖留守太原,见謩深器之。”[注]《旧唐书》,卷五十九,第2332—2333页。《新唐书》,卷九十一《姜謩传》略同,第3791页。隋末有太原郡而无并州,墓志只是以习惯称之。太原是防守北方突厥的门户之一,唐高祖李渊当时就受命镇守于此。太原因为是李渊龙兴之地,所以唐代的晋阳县是赤县,而隋代的定级恐怕也不会在中县以下。相对于前面所说的巩县、新安县,晋阳县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载:“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注]《旧唐书》,卷五十七,第2290页。据此,则大业末年晋阳县又设有县令。按照惯例,县令地位要高于县长,但两者是否可以同时设置,还是晋阳县长官已由县长升为县令,这些都不清楚。
应该注意的是,上述三位县长的任命都是在隋炀帝朝。《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说“(炀)帝自三年定令之后,骤有制置,制置未久,随复改易”,[注]《隋书》,卷二十八,第803页。从县长的设置来看,确实如此。
二、县令的迁转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载隋文帝时“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注]《隋书》,卷二十八,第792页。这是隋文帝时全国县令迁转的一般规则。正如上文所说,县是有等级的,由下县令任中县令是迁,由县令任州、郡官员也是迁,这中间的弹性就很大了。
县令中的第一等当然是长安、大兴两县的县令,隋炀帝时还要加上河南、洛阳两县的县令。据《隋书》卷六十二《梁毗传》载:“开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鲠正,拜治书侍御史,名为称职。寻转大兴令,迁雍州赞治。”[注]《隋书》,卷六十二,第1479页。本条称“雍州赞治”而不称“雍州司马”,必在开皇三年(583)“罢郡、以州统县,改别驾、赞务,以为长史、司马”[注]《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792页。“赞务”应作“赞治”,唐人避高宗讳改。之前。大兴令官品在从五品下,雍州赞治官品在从四品下,后者官品上直接跃过了正五品。雍州为京师所在,大概也只有长安、大兴县的县令可以直接升任雍州州官。[注]《隋书》,卷六十六《高构传》(第1556页):“高祖受禅,转冀州司马,甚有能名。征拜比部侍郎,寻转民部。……迁雍州司马,以明断见称。岁余,转吏部侍郎,号为称职。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转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复拜雍州司马,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高构以前曾任过雍州司马,只是坐事左迁盩厔令,后复拜,与长安、大兴令直接升迁雍州州官不同。而且盩厔虽然不是长安、大兴,但它是雍州属县,属于下文讨论的县令中的第二等。
不仅如此,长安、大兴两县的县令,还经常由中央官来兼任。如《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附从子炽传》载:“还授太子仆,加谏议大夫,摄长安令。……寻领右常平监,迁雍州赞治,改封饶良县子。”卷六十二《刘行本传》载:“在职数年,拜太子左庶子,领治书如故。……复以本官领大兴令,权贵惮其方直,无敢至门者。……未几,卒官。”卷六十六《郎茂传》载:“茂自延州长史转太常丞,迁民部侍郎。……仁寿初,以本官领大兴令。炀帝即位,迁雍州司马,寻转太常少卿。”[注]《隋书》,卷五十一,第1329页;卷六十二,第1478页;卷六十六,第1555页。长孙炽是以太子仆摄长安令,刘行本是以太子左庶子领大兴令,郎茂是以民部侍郎领大兴令,他们都是中央官领或摄县令。其中,刘行本卒官,长孙炽与郎茂以后都迁雍州赞治(司马),[注]郎茂是以民部侍郎领大兴令迁雍州司马,民部侍郎在文帝时官品为正六品上,不仅低于从四品下的雍州司马,而且低于从五品下的大兴令,这种升迁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长孙炽,他是以太子仆摄长安令,以后又领右常平监,迁雍州赞治,文帝时太子仆官品在正四品上,不仅高于长安令,而且高于雍州赞治,这里的“迁”字似只能理解成同一品级之间的调任了。关于“迁”字的含义,参见王寿南:《隋唐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18页。与前举梁毗的迁转途径有相似之处。
县令中的第二等是除大兴、长安两县县令之外的雍州诸县县令。《隋书》卷七十三《循吏·房恭懿传》载:“时雍州诸县令每朔朝谒,上见恭懿,必呼至榻前,访以理人之术。”由此可见,京师所在的雍州诸县县令“每朔朝谒”,经常有觐见天颜的机会,这是他州县令甚至上县县令也没有的特权。这些雍州所属的县令,不仅有接触皇帝的机会,而且由于地属京畿,其所作所为也会被朝廷亲贵知晓,从而获得被推荐的机会。如上举《循吏·房恭懿传》还载:“开皇初,吏部尚书苏威荐之,授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上闻而嘉之,赐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赐分给穷乏。未几,复赐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赈贫人。上闻而止之。……苏威重荐之,超授泽州司马,有异绩,赐物百段,良马一匹。”[注]《隋书》,卷七十三,第1679页。房恭懿是由苏威推荐出任新丰令的,新丰是雍州即京兆郡的属县。房恭懿为政清廉,赈济穷乏,不仅获得了隋文帝的赏识,而且也获得了重臣苏威的第二次推荐。
除了以上两类县令之外,剩下的全国县令的等级、地位,就与他们所掌的县一样,可谓模糊一片。《隋书》卷七十一《诚节传》中记录了多位地方县令的履历,但他们都是因临难不妥协,事后才获得朝廷的嘉奖从而超迁的,并非平时的事例。如《隋书》卷七十三《循吏·刘旷传》载:“迁为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尚书左仆射高颎言其状,上召之,及引见,劳之曰:‘天下县令固多矣,卿能独异于众,良足美也!’顾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于是下优诏,擢拜莒州刺史。”[注]《隋书》,卷七十三,第1685页。从《循吏·刘旷传》的记载来看,地方县令只有在考课时获得“天下第一”,才能获得尚书台长官的推荐,也才能有超授的机会。但“天下县令固多”,又谈何容易。刘旷能“独异于众”,所以才能由临颍令擢拜莒州刺史。这说明地方县令如果想获得超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清名善政,二是考课时获得高等。二者缺一不可。再如《隋书》卷六十六《房彦谦传》载:“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尝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颎定考课,彦谦谓颎曰……颎为之动容,深见嗟赏,因历问河西、陇右官人景行,彦谦对之如响。……后数日,颎言于上,上弗能用。以秩满,迁长葛令……仁寿中,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马。”[注]《隋书》,卷六十六,第1562页。房彦谦在长葛令任上政绩突出,又被巡行州县的使者评定为天下第一,所以才能超授鄀州司马,与刘旷的事例完全相同。
至于地方上的其他县令,很可能就只能在地方上不断迁转,更上一层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如《隋故韩城县令白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志主白仵贵“起家为滕王记室……俄迁北川县丞。……改授北川县令。……迁授韩城县令”。[注]图版及录文见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五册,第四三二号,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16页。据《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北川属汶山郡,韩城属冯翊郡。[注]《隋书》,卷二十九,第823、809页。冯翊郡为三辅之一,一般来说,韩城县的地位应该高于北川县,所以白氏应该是由等级较低的县令升为地位较高的县令。其墓志铭中说白仵贵“以大业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河南郡河南县安众乡安众里”,并非死于韩城县官舍,说明他是以韩城县令为终官致仕的。他的一生,除了短暂地担任过王府低级官僚外,都是在地方上担任县级官吏。《隋故武安郡肥乡县令萧明府墓志铭并叙》载志主萧翘“陈亡入朝,除介州司功、邵州亳城令、汾州昌宁令、武安郡肥乡令。累官著称,俗号廉平,吏弗敢欺,门无夜掩,考绩为最,朝野式瞻。……以大业十年七月廿七日终于魏郡,春秋七十有三。……绛州曲沃县令济阳蔡书悌制文。”[注]图版及录文见《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五册,第四六一号,第270—271页。萧翘历任亳城、昌宁、肥乡县令,这三个县之间的等级高下无法判断。萧翘在大业十年(614)死于魏郡,而不是武安郡的肥乡县,说明他也是以肥乡县令致仕的。虽然其墓志铭中说他“考绩为最”,大概也只是撰者的谀墓之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墓志铭是由一位在职县令撰写的,至于双方是怎样的关系,现在也无从稽考了。《郭通及夫人王氏合葬墓志》载郭通“开皇八年,诏举贤良,起家卫州汲县尉。十八年,除慈州滏阳县丞……仁寿三年,除沁州沁源县令……”[注]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二册,第10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6页。郭通也是一直在地方上担任县职,这一墓志的可贵之处在于,详细地标示了郭通任官的年份。郭通开皇八年(588)担任汲县尉,开皇十八年才除滏阳县丞,也就是任县尉长达11年;仁寿三年(603)除沁源县令,也就是任县丞长达6年。这就表明《百官志》中所说的“佐官四年一迁”的原则只是规定了佐官满四年就可以迁,却并不是一定会迁;这些秩满的佐官只是最有资格获得迁转而已。因此,所谓“县令三年一迁”的原则也只是指秩满的县令是最有资格获得迁转的。如前述《隋书》卷七十三《循吏·刘旷传》就记载刘旷在平乡令上任职七年后方调任临颍令,[注]《隋书》,卷七十三,第1685页。可作为佐证。
通过以上简短的分析可知,隋代县令中,雍州(京兆郡)所属县令由于地属京畿,有更多机会接近朝贵、皇帝,所以仕途较他州县令为佳。其中,长安、大兴两县的县令常由中央官兼任,常迁雍州州官,非其他县令可比。而地方县令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需为考选者所知,只有考课优异者才能获得超迁的资格,不然多数只能在地方上任职一生。
三、县令的职责
县令的职责,《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所载隋代制度中并没有记录。《唐六典》卷三十《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官吏》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若五九、三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若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至于课役之先后,诉讼之曲直,必尽其情理。每岁季冬之月,行乡饮酒之礼,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于堂下,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节。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注]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十,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53页。《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第1921页)以及《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第1319页)所载县令职掌都不如《唐六典》完备,或许都是截取自《唐六典》所载的一部分。本段所载虽然是唐代县令的职责,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时间点,比如何时造簿历、何时给授田地等,那么,将它看成隋代县令的职责大概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文中,自“京畿”至“务知百姓之疾苦”句,是职权综论。自“所管之户”至“必尽其情理”句,是指清定户口以及与之相关的田地给授、赋役摊派问题,另外还有狱讼问题。隋代开皇年间曾屡次派使者巡行天下,检括户口。大业五年(609)曾在全国“大索貌阅”。[注]这里采用的是唐长孺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大索貌阅”实际只在隋炀帝大业五年实行过一次,并不是在文帝开皇五年(585),但文帝时常派员检括户口。见唐长孺:《读隋书札记·隋代大索貌阅的时间》,收入氏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5—319页。高颎又以“输籍定样”之法“定户上下”。[注]《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1页。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解决户口的问题。自“每岁季冬之月”至“尊卑长幼之节”句,是指县令有主持“乡饮酒礼”,使民知尊卑长幼有序的责任,这是先秦以来“尚齿”传统的延续。[注]参见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收入氏著《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299页。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2—425页。自“若籍帐”至“县令皆综焉”句,则是明确县政诸项事务由县令负总责。
县令既然有这么多的权责,那么什么才是重中之重呢?赖瑞和先生在研究唐代刺史的职掌时,认为刺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收税,所以他称刺史为“税官”。[注]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第十七章“唐刺史的税官角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6年版,第475—479页。唐初,复改郡县两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刺史是一州最高长官,也是州的最高“税官”;为了完成州向朝廷缴纳足额赋税的任务,刺史势必督责下辖的各县县令也去充当“税官”的角色。赖瑞和先生认为收税是唐代县令的“当务之急”,[注]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四章“县令”,第318—319页。这恐怕也是隋代县令的首要任务。
《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注]《礼记正义》,卷六十,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5页。标点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3年版,第11页。这是讲君子对“德”“财”应持的态度。虽说德为本而财为末,但帝国从中央到地方处处“有用”,也就处处需财,财才是根本。财从哪里来?从人与土中来。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记高颎所创“输籍定样”之法有云:“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注]《隋书》,卷二十四,第681页。所谓“定户上下”,就是定户等“以入籍帐”,也即“县令巡人”的目的,这是对人的控制。同书同卷又云:“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注]《隋书》,卷二十四,第680、682页。《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载:“(大业五年春正月)癸未,诏天下均田。”[注]《隋书》,卷三,第72页。隋朝立国之初,就依北齐制度颁行田制。承平日久,人口激增,造成地少人多,衣食不足,乃至开皇十二年(592)、大业五年(609)两次均天下之田。国家对于田地的控制落实到基层,就必然是县令的责任。唐代的县令是要“亲自给授”田地的,隋代的县令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对土地的控制。
在经典意义上,“财为末”,所以在官方文献上很少能够见到地方官汲汲于征税的事例。不过,杜甫在《兵车行》里写道:“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注]杜甫撰、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元结在《舂陵行》里写道:“军国多所须,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竟欲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注]元结:《唐元次山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正德郭氏刊本,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a—第1页b。另见加藤敏:《元结の「舂陵行」と「賊退示官吏」について》,《千葉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第45卷,第193—198页。李贺在《感讽五首》的第一首中写道:“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注]《王琦汇解李长吉歌诗》,卷二《感讽五首》,蒋凡、储大泓点校,收入《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4页。这些虽都是唐代郡县官员刻剥租税的写照,但用之于隋代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虽然财税的征收是县令的首要任务,人口与土地的控制只是为了达成收税这一目标的手段,但到底是选择上揭唐诗中描写的那种横征暴敛的官吏,还是选择善抚百姓、殖产兴业的官吏,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显然也会选择后者。从经典的意义上来说,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人与土之间,人又是根本,得人者即所谓“有德”,就是君子,具体到官吏身上也就是循吏。《隋书》卷六十六《房彦谦传》载:“以秩满,迁长葛令,甚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仁寿中,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马。吏民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其后百姓思之,立碑颂德。”[注]《隋书》,卷六十六,第1562页。同书卷六十三《循吏·刘旷传》载:“开皇初,为平乡令,单骑之官。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及去官,吏人无少长,号泣于路,将送数百里不绝。迁为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注]《隋书》,卷六十三,第1685页。房彦谦与刘旷离职时,吏民都号哭相送,所谓“惠化”“德化”都是指两位县令为有德君子,所以才能广收民心。虽然房、刘两氏德化乡里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税收,但客观上说,良好的政治环境必然会使两县赋税足额上缴,否则两人的考绩绝无可能是“天下第一”。
但并不是所有县令都能像房、刘两氏那样以民生为己任。如《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载:“(苏)威又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注]《隋书》,卷四十二,第1200页。可见吏部铨选全国数百县令,能“称其才”者并不多。又如,同书卷五十五《侯莫陈颖传》载:“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以镇抚之,于是征颖入朝。”[注]《隋书》,卷五十五,第1381页。岭南地方在隋代有多次叛乱,虽然该地区夷夏杂处,易动难安,但纷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刺史、县令多贪鄙”。据《南齐书》卷三十二《王琨传》载:“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注]《南齐书》,卷三十二,第578页。可见岭南物产丰饶,地方官员多中饱私囊,激起民变。
东晋南朝,常有因家贫求为外任的官员,其中不乏求为县令者,[注]《晋书》,卷四十九《胡毋辅之传》(第1379页):“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贫,求试守繁昌令,始节酒自厉,甚有能名。”同书,卷七十五《王述传》(第1963页):“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同书,卷八十二《干宝传》(第2150页):“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同书,卷八十三《江逌传》(第2171页):“以家贫,求试守,为太末令。”《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陶弘景传》(第1897页):“家贫,求宰县不遂。”《陈书》,卷二十一《张种传》(第280页):“种时年四十余,家贫,求为始丰令,入除中卫西昌侯府西曹掾。”由此可知,任职县令不失为致富的一条捷径。隋文帝当然不希望有这样一批饕餮之徒牧守地方,所以他要“妙简清吏”,要对那些考绩天下第一的县令优诏褒扬,不吝提拔。他就是希望全国的县令见贤思齐,都能成为循吏,那么,天下太平,府库自然也就会充盈了。
税收是县令掌县的首要职责,达成这一职责的手段就是“安民”。县令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则是“保境”。上举县长史料中有一条说“(李)密攻下巩县,获县长柴孝和,拜为护军”,似乎是巩县县长柴孝和抵抗之后为李密所俘,但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皇帝上·义宁元年》,“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条引《略记》云:“于是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等举县降贼。”[注]《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第5722页。从柴孝和被李密拜为护军一事来看,可能《略记》的记载更为可信。据此可知,县令(长)对全县大小事务负总责并不是一句空话,他们甚至可以“举县降贼”。而有人降贼就有人抗贼,如《隋书》卷七十一《诚节·杨善会传》载:“善会,大业中为鄃令,以清正闻。俄而山东饥馑,百姓相聚为盗,善会以左右数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后贼帅张金称众数万,屯于县界,屠城剽邑,郡县莫能御。善会率励所领,与贼搏战,或日有数合,每挫其锋。”[注]《隋书》,卷七十一,第1647—1648页。另,本卷记有仁寿中抗贼的繁畤令敬钊,也是力战城陷。杨善会作为鄃县令,面对张金称数万之众,并没有弃城或降敌,而是以鄃县令所领的武力与之对抗,守土有功。隋炀帝“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注]《隋书》,卷五十九《炀三子·齐王暕传》,第1443页。应该也是考虑到包括叛乱在内的突发情形需要负总责的县令及时处理。
除了保境安民以外,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就是狱讼了。《隋书》卷六十六《郎茂传》载:“寻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释免者百余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晖谓茂曰:‘长史言卫国民不敢申诉者,畏明府耳。’……有民张元预,与从父弟思兰不睦。丞尉请加严法,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于是遣县中耆旧更往敦谕,道路不绝。元预等各生感悔,诣县顿首请罪。茂晓之以义,遂相亲睦,称为友悌。”卫国,开皇六年(586)改名观城,属魏州。[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第845页。卫国民众的辞讼完全由卫国令负责,只要民众不申诉,本州刺史就不会过问。也就是说,原则上县令拥有全县的决狱权。但是郎茂并不是那种以法绳下的县令;准确地说,他是那种曲法循情的官员。关于张元预一案,郎茂“遣县中耆旧更往敦谕”,并没有听从丞尉“加严法”的请求。郎茂仍然是以德服人,而非以法治县;仍然是有德之君子,而非滥刑之酷吏。这件事被写进郎茂个人的传记里,说明无论是在隋代还是唐代,官方都认可他的这种行为。法治为下,德治为上,决狱的目的也是为了安民。
四、小结
隋代的县是有等级的,除了长安、大兴等少数县以外,起初全国的县被划成了三等九级。开皇十四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隋文帝将全国的县改为了四等制,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后被唐代沿用了下去。
与县的等级相对应,县令也有等级之差。长安、大兴两京县的县令地位最高(隋炀帝时还要加上河南、洛阳两县),常由中央官兼任。雍州诸县的县令由于地属京畿,且有朝谒的制度,所以面见皇帝与亲贵近臣的机会很多,相应地,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有很多。除此以外的全国诸县县令,除了要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以外,还要获得非常高的考课成绩,才能获得超迁。
县令的职责最重要的是向朝廷缴纳足额的赋税,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强对人口与土地的控制。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要地尽其利,就必须安抚民众。因此,理想的县令是那些有德之君子,是循吏,平时能够代天子抚养民众,乱时能够恪尽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