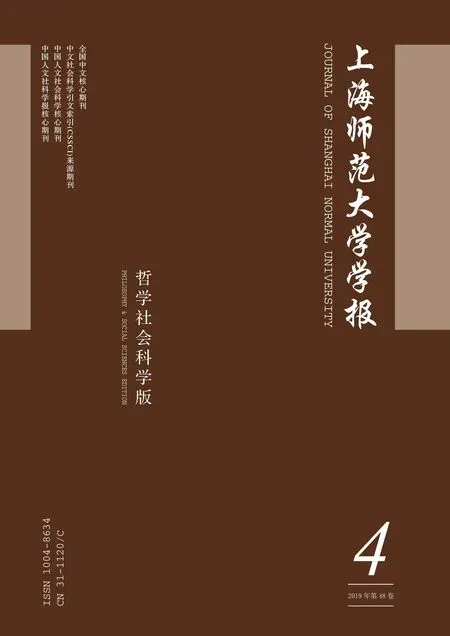章学诚“文”“史”汇通明义学术观念之新探
薛璞喆,俞 钢
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堪称集大成者。历来关于章氏《文史通义》的研究,学者们往往受限于现代学科的区分,或从“文”或从“史”的角度加以阐释,大多偏向于对“史义”的解析,[注]关于“史义”,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精华,参见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持基本相同看法的还有瞿林东的《中国史学通论》,张国刚、乔治忠的《中国学术史》,谢保成的《中国史学史》等。对于“文史”的解读则相对较少,如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说:“通常,学者们是将章学诚作为史学家来看待,而他本人的看法则正如其著作之标题所示……而所谓文史,又大体涉及了所有的著述。”参见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此外,钱志熙的《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梁结玲的《章学诚的文史之辩》(《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陈其泰的《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俞钢、薛璞喆的《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薛璞喆的《章学诚之“文史”辩》(《学术交流》2017年第3期)等文也都有所涉及。而少有对章氏文、史汇通明义学术观念进行整体性探讨的成果。笔者认为,尽管《文史通义》以“文史”命名,但它并不囿于文、史之学的格范,其义旨在梳析文、史脉络,跨越传统四部之学,构建中国古代学术史新的认识体系。诚如钱穆所言:“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眼光卓特处。”[注]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3页。因此,本文试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视野,就章氏文、史汇通明义学术观念进行再讨论,以求证于学者。
一、“后世之文”源出于《诗》教
考察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可以发现,他将中国古代学术大致分为文、史两大体系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探寻同源异流的演变轨迹,进而阐发汇通明义的学术观念。
就“文”一脉而言,他在《诗教下》中指出,后世“文”的兴盛,源头就是三代“六艺”之学中的《诗》。本来《诗》“托于声音,不著于文字”,故可“无有散失”,得以传承流播。后世“竹帛”的出现则使文字胜于声音,由此造成“文”的繁茂。尽管《诗》之文的演变“古今时异 ”,但都是“以礼乐治天下”,所谓“出于一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显然,章氏通过回溯中国古代学术史“文”之渊源,找到了汇通明义的依据和出发点。
在章氏对“文”的具体论述中,屡屡提及“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等概念,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的“文”之内涵的认识。在章氏看来,“文”一脉的阶段性演变,大致可分为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和后世之文三类。六艺之文,随着周代的衰亡而文弊道息,尽管“诸子争鸣”代起,但其作为源头的功能依然存在,只是“人不知”而已。战国之文,发生了较大的流变,表现出“著述之事专”、各种文体完备、“裂于道”等特点,但考究其源头,则“皆出于六艺”。至于后世之文,因袭战国之文而发展,尽管洋洋大观,其实也“源多出于《诗》教”。由此考镜源流,章氏知人所不知,阐发了中国古代学术史“文”之流脉导源于六艺之文,尤其是《诗》之文的学术观念。[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60页。
那么,如何理解六艺之文的特点呢? 章氏在《易教下》中说:“《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8页。这里,章氏分析了《易》《诗》《礼》《春秋》等的特点,强调六艺之文虽有不同的功能,但殊途归一,所谓“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至于物杂为文和事比有类,也都可以归于六艺之文的范围。显而易见,章氏通过论证想要告诉我们,六艺之文统领后世之文,而后世之文只是六艺之文的流脉。
在六艺之文中,章氏特别重视《诗》之文对后世之文的影响,其《校雠通义·汉志六艺》他认为,《诗》与《春秋》是相表里的,“学《春秋》者,必深于《诗》”,这就是韩婴《诗外传》、司马迁《史记》等所博取的旨趣。[注]章学诚:《校雠通义校注》,见《文史通义校注》,第1024页。
再来看后世四部之学中的集部之文,虽以《诗》为源头,但以诗文、歌赋、戏曲等为主体的学术成果已经蔚为大观。对此,章氏《诗教上》云:“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61页。缕析章氏对后世文集之体演变的认识,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后世之文集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经义、传记、论辩三体,以及辞章之属。第二,文集三体的兴起和繁盛,主要是因为经学、史学、立言的“不专家”,从而造成“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第三,辞章之属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也”。大体而言,后世之文的体盛,实是六艺之文尤其是《诗》之文影响的结果。
文集自魏晋以后兴盛,章氏在《诗教上》中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原本并无“参差庞杂之文”,其后专门传家为了显其业、传其徒,略有为文之举,也仅此而已。两汉文章逐渐丰富,往往仍成一家之言,未尝“汇次诸体”而裒为文集。魏晋时期,文章繁杂,文集之名虽未立,但文集之实已具,“自(西晋)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其后,文集泛滥横裂,“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无复“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63页。显而易见,章氏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高度,循“文”一脉之源流,揭示出了后世之文的演变,论述极富有创造性。可以认为,尽管在章学诚之前,一些学者也多少提及“文”一脉从口耳相传到文字撰述的变化,但是都未能厘清由六艺之文到《诗》之文,再到战国之文,进而到后世之文的演进轨迹,这也就难以达到中国古代学术史“求会同”的旨归。
总之,章学诚通过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一脉的探源析流,阐明了各个时期“文”的内涵特点和演变轨迹,其目的是为了将与“文”有关的古代学术成果加以合理的整合,以便于从以《诗》为代表的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和后世之文的变化中求得汇通明义。应该说,身处中国古代社会末期,章氏回溯中国古代学术史“文”一脉的演进,梳理出清晰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整体理解中国古代学术史极具启发意义。
二、“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
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一脉的认识,章学诚更是独具慧眼,他在系统梳析史学发展源流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六经皆史”等学术主张。关于学术之渊源,章氏在《说林》中明确提出“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55页。并通过考辨“六经”“三史”的内涵,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学术“史”之脉的影响。理解章氏的这一论断,需要深入探寻章氏学术观念形成的脉络。
首先,就“六经”而言,章氏是先从辨名开始的。章氏《经解上》认为,原本并无“经”的概念,“经”之名的形成始于孔子之后。[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93页。具体来说,孔子“既殁”,学术纷乱而无统宗,其弟子门人以各种方式“录文起义”,由此形成了称为“六经”的《诗》《书》《礼》《易》《乐》《春秋》。此外,章氏还辨析了荀子和庄子对“经”的阐释,进一步强调说:“荀庄皆出于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93页。我们发现,在《文史通义》中,章氏使用“六艺”和“六经”的表述是有所不同的,“六艺”多用于孔子之前,而“六经”则多用于孔子之后。
对于“六经”的内涵,章氏在《经解中》中云:“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94页。在他看来,“六经”是纲维天下的“先王之政教典章”,以此为出发点“疏别六经”,就可以达到治国知教的效果。分析章氏之论,据其《经解上》所云,着重阐述了三点:第一,周官之“旧典”,包括太卜所掌的《易》、外史所掌的《书》、宗伯所掌的《礼》、司乐所掌的《乐》、太师所掌的《诗》,以及国史所存的《春秋》“六艺”内容,本非孔子之书。第二,孔子“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因而“师弟子之传业”,其后才形成了“六经”之书。第三,孔子之后,“六艺”演变为“六经”,成了衡量一切的准则。[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93页。据其《原道上》所云,章氏认为,“六经”包涵了万事万物,旨意闳深,不可专攻一经之隅曲,而应加倍兼通“六经之功能”,由此则可“独见天地之高深”,识“天地之大”,进而“窥古人之全体”。[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38页。通过章氏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六经”本于“六艺”,而“六艺”实为“先王政教典章”,孔子“述而不作”,弟子门人为了传业之需,才逐渐形成了“六经”,并被后世奉为治国知教的准则,当然也是中国古代学术之源。
其次,就“三史”而言,一般是指三部后出的史书,徐坚《初学记·史传二》就说:“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注]徐坚:《初学记》,卷九,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3页。如果以此来理解章氏所言“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中的“三史”,显然无法说通。从时间上看,《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是两汉时期的史著,皆晚于《春秋》《左传》等先秦著述;从内容上看,《史记》《汉书》《东观汉记》都是史书,尚不能反映中国古代学术的全部内容。从章氏表述看,“六经”与《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书的地位并不对等,在传统学术环境下“六经”的地位一直高于这三史书。毋庸置疑,章氏提出的“三史”另有所指。检索他的《方志立书三议》云:“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572页。可知,章氏所认为的“三史”是指《诗》《礼》《春秋》三部经书。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学术依然导源于经,只不过章氏将《书》《春秋》视为同一性质,用《礼》代替了《书》而已。
其三,就“六经”与“三史”的关系而言,章氏也进行了具体论述。在章氏看来,《乐》亡而归入于《诗》《礼》,《书》亡而归入《春秋》,于是“六经”演化为了“三史”。[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2、573页。至于“六经”中的《易》,章氏《易教中》云:“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2页。《易教下》云:“《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20页。显然,章氏认为,上古三代“详天道”,而后世“详人事”。尽管《易》“以天道而切人事”,但后世更注重“《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由此“六经”逐渐演变为《诗》《礼》《春秋》“三史”,即“三史”可归于“六经”,皆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源头。这也就可以理解,章氏所言“六经三史,学术之源”和“六经皆史”的内涵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章氏并不视“六经”为形而上的道,而仅仅视其为形而下的器。据其《原道中》,[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32页。很明显,章氏不认同后世称“六经”为载道之书的观点,而是认为“六经”皆为器。按照他的识见,既然“六经”皆为史,自然史也成了器,而非载道之书。
章氏认为,后世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六经三史”的流脉。其在《方志立书三议》里直言“六经皆史”,并重点分析了《诗》《礼》《春秋》三史与后世纪传正史、掌故典要、文征诸选等的关系,指出《春秋》是“纪传正史”之源,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礼》是“掌故典要”之源,如杜佑《通典》等;《诗》是“文征诸选”之源,如《文鉴》《文类》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572页。由此观之,章氏“六经皆史”之“史”包括了《诗》之文,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86页。
对于中国学术“史”之脉的源头,章氏特别强调本乎《春秋》。其《答客问上》云:“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面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70页。这里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即指后世史学的根本实在于《春秋》。
在章氏的学术观念中,后世史书的体例颇得益于《春秋》笔削之义,《春秋》之流脉堪称“家学”可贵,所谓:“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50页。而汉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史学著作都是模仿《春秋》的。对此,据《经解下》,章氏并不认同后世“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的看法,主张《史记》和《汉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其本纪为《春秋》一脉家学,书、志、表、传等则“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所以后世著史尤需深明《春秋》大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11页。
我们注意到,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之脉的认识,章氏一方面主张“《春秋》之史”,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六经皆史”。在他看来,原本只有“六艺”的说法,而无“六经”的尊称,其后诸子立说,才由孔门弟子改称“六经”,并逐渐演化为历代尊奉的经典。因此,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一脉的演变,其实史在经前,经为史包。正如章氏所言:“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第86页。
在探源的基础上,章氏还在《书教下》中对“史”之流脉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辨析了同为经典的《尚书》和《春秋》对史学的影响,认为《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所以“《书》之支裔,折入《春秋》”,《春秋》成了史之源。《尚书》一变,而有守定例的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一变,而有通变化、分类例的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史记》一变,则有守绳墨、断代的班固《汉书》;故比较而言,左氏《春秋》为编年之祖,《史记》和《汉书》可称为纪传体之祖。如果再做精微辨析,则《史记》难成定法,而《汉书》因循《史记》之体,有“一成之义例”,可以传世行远,实为后世史学“不祧之宗”。然而,后世史家不明史之流变,自称“祖马宗班”,由此久失史学的要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9页。从章氏的认识来看,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史”之脉的论析极为深刻而富有创见,其所揭示的《尚书》支裔折入《春秋》,《春秋》是史之源,以及史之脉左氏《春秋》及《史记》《汉书》的不同特点和功用,颇有益于我们准确理解他的文、史汇通明义的学术观念。
简言之,章学诚通过考辨中国学术“史”之脉的源流,明确提出了“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六经皆史”“《春秋》之史”等独具匠心的学术主张。特别是他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高度,精微缕析了史学的流变,从而使头绪纷杂的“史”之脉最终归于《春秋》之源,这也就为他提出汇通明义的学术观念找到了理论依据。
三、汇通“文”“史”而明义
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命名其所撰的学术理论著作,目的并不止于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两脉的探源浚流,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探寻“通义”的学术宗旨,重新建构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认识体系。因此,在《文史通义》中,章氏从不同的视角阐析了汇通明义的学术观念。
我们注意到,章氏汇通文、史而明义的学术观念,是对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唐代刘知几《史通》等传统学术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如,他在《与严冬友侍读》中指出:“日月悠乎,得过多日,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马班,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第333页。可见,《文史通义》与《文心雕龙》《史通》之间的延承关系。
《文心雕龙》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南朝以前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以“文”为核心的学术观念,所谓“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注]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因经而作文。据本文统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讨论了35种文体。在这些文体中,如史、传等不少文体其实并不属于“文”的范畴,但刘勰将其归于“文”的体系之下,明显反映了他以“文”为核心总汇南朝以前学术成果的观念。章氏对此颇为赞赏,评价道:“《文心》体大而虑周……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559页。《史通》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唐以前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以“史”为核心的学术观念。其《史通·自序》云:“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注]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明确表达了刘知几以“史”为核心总括唐以前学术成果的观念。章氏对《史通》亦多有评论,如其《书教中》及《说林》。[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0、355页。显然,《史通》的学术思想同样对章氏学术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由刘勰的偏“文”到刘知几的偏“史”是一脉相承的,章氏自言“下该《雕龙》《史通》”而作《文史通义》,反映了他对已有学术理论思想的借鉴,前后传承关系极为明晰。
为了建构中国古代学术史新的认识体系,章氏还对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进行了梳理,试图将中国古代学术成果汇通于“文”“史”两大流脉之下加以重新整合。就四部之学而言,历来首推经部之学,以“六经”为源头,逐渐演变为“九经”“十三经”等,形成了儒家经典理论体系。正如章氏所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7页。史部之学仅次于经学,甚至其源头早于经学,流脉绵长,故章氏所言“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和“六经皆史”实际上是将经部和史部之学视同一类,而以“史”涵括。子部之学,属于诸子百家言,从先秦儒家学说开始逐渐形成了墨、道、名、法等诸子百家学说,其后佛学、理学等入流。由于诸子百家探讨人类和自然的专门问题,乃私家之思想和智慧,故立于四部之一的地位,并成为后世集部之学的一个源头。至于集部之学,章氏基本视其为“文”,主要涵括诗文、戏曲、小说等总集和别集。这样,章氏大致把汇聚中国古代学术成果的四部之学,缕析为了“文”“史”两大体系。
对于文、史之间的汇通,章氏《释通》曰:“《说文》训通为达,自此至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72页。《原道下》曰:“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38页。从中可见,章氏一方面注重学术的通达,所谓“通天下之不通”;另一方面则强调“六艺并重”方可以言道,最终达到独见天地之高深的境界。
文、史的汇通,还具有“交相裨益”的功用,在章氏看来,左氏编撰《国语》时就曾“引谚证谣”,而《诗经》中的《国风》则未尝不可以隶于史,这就是文史交相裨益的典型例证。[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828页。
章氏认为,文史之间是春华和秋实的关系。[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0页。一方面,文可辅史。如他指出,《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837页。他在《丙辰札记》中又说“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三,第835页。也即这些小说作品明显得益于史。另一方面,史亦可益文。如他指出,归有光、唐顺之的文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286页。
我们发现,章氏文史汇通的观念主要是针对四部之学而言的,其目的在于汇通中国古代学术,并求取蕴含其中的义旨,因此它十分接近于“学术”的概念。据我们的统计,在章氏的论著中使用“学术”一词共有102次,其中《文史通义》中有55次,《章氏遗书》中有39次,《校雠通义》中有8次。分析章氏使用时的含义,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指学问,如“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262页。二是指学术流派,如“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651页。三是指典籍文章,如“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38页。四是指学术规律,如“学术之学术”;[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26页。五是指体例,如“总古今学术,纪传一体规乎史迁”。[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17页。显然,这五个方面都可归属于“学术”的含义之下,实与章氏文史汇通的观念相一致。
章氏的《文史通义》直接以“文史”入书名,思虑精深,富有创见,正如他所云:“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注]章学诚:《校雠通义校注》,见《文史通义校注》,第591页。“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第76页。甚至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中声称与前人之说“不相袭”,也强调了“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是他有所发明之新见。[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第86页。可以说,章氏对传统四部之学进行重新梳理,最终归结为“文”“史”两大流脉,并加以汇通释义,实际上就是在用“学术”的概念客观地揭示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之流脉传承的本质,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学术史新的认识体系。然而,章氏《文史通义》的问世,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以为此书仅仅论文、史的通义,而忽视了汇通明义的本意。所以,章氏极力辩解说:“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衍古今。”[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第330页。“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三,第774页。显然,章氏想要告诉我们,他所提出的文史汇通的学术观念具有疏通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意蕴。
章氏不仅注重文史汇通的学术整体性,还以此为出发点强调了汇通明义的重要性。考察《文史通义》所言“义”的内涵,除了专指学术成果的体例外,还特指文、史汇通之大义。如其《经解上》云:“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乖,于是弟子门人,备以所见、 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71页。《答客问上》云:“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70页。《申郑》云:“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取乎尔。”[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464页。《言公上》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71页。这些都表露了章氏求取学术义旨的思想。
在章氏看来,义存乎天人之际,是以“六艺”为宗旨的伦理法则,而传统“文”“史”一脉相承的学术成果则应是“存义之资”。对此,章氏在《言公上》中通过分析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的体例,指出了史家在处理义、事、文三者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取义明志,所谓“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171页。
章氏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探究汇通明义的学术义旨。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学者仅具备才、学、识三者是不够的,而更应有“德”。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由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史家“三长”推演为学者应具备的“史德”和“文德”。章氏认为,“史德”乃“著书者之心术”,而“心术”的核心则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即客观地探寻历史演变内在的规律,不能以个人的善恶作为标准。[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19页。至于“文德”,章氏在梳理前贤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在他看来,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也即把握“敬恕”的尺度。他进而从心气论出发,强调其要旨是“临文主敬”,所谓“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及“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这才可以说是“文德之敬”。[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278页。
我们认为,章氏论“史德”“文德”的出发点和辨析思路是一致的,其本质是以德为史,以德为文,以德为学术,进而达到揭示存乎天人之际的“义”的境界。这其实就是章氏汇通明义的学术观念的主旨。正如章氏所言:“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不得史义,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三,第310页。
四、结语
要言之,章学诚在对中国古代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汇通明义的学术观念。他继承和发展了《文心雕龙》《史通》等传统学术理论思想,系统梳理了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演变,力图将中国古代学术成果汇通于“文”“史”两大流脉之下而加以重新整合。在他看来,文史之间是春华和秋实的关系,文可辅史,史亦可益文,两者的汇通就可以求取蕴含其中的义旨;这实际上就是在用“学术”的概念,客观地揭示中国古代学术史演进的规律。章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注重文史汇通的学术整体性,还以此为出发点指出了明义的重要性。他强调义存乎天人之际,是以“六艺”为宗旨的伦理法则,而传统“文”“史”一脉相承的学术成果则应是“存义之资”。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学者除了具备才、学、识三者外,更应具有“史德”和“文德”。显然,通过系统的论析,章氏构建了中国古代学术史新的认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