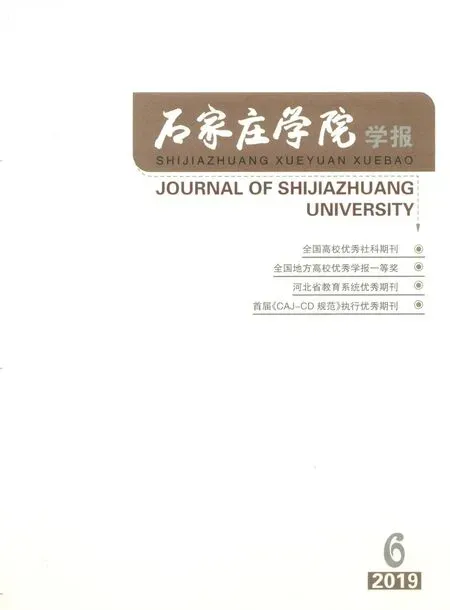文化游客的自我凝视
——“日常生活”在博物馆体验中的延续
宋厚鹏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0 引言
博物馆与旅游作为两种事物,虽然在概念上有差异,但实际上,二者间存有内在的联系,因为,虽然旅游吸引物从不视博物馆为同属物,但博物馆天生就是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博物馆”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字眼,它在希腊语中最初的含义是献给缪斯女神的任何东西,即一座山、一座神殿、一个花园、一个节日,甚至是一本书.然而,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这样一个抽象字眼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产品,并在社会文化机制的驱动下作为一个集艺术、历史、文化与科学为一体的大型机构,进而在为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服务.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俯瞰历史的风风雨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认为,博物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面对过去的方式,与别的时代和其他模式的生活形成意义隽远的交流,它从一开始只是偶然收集文物和“贵重物品”到建立非正式的藏品保险库和陈列室,因此博物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保存记忆的功能.鉴于此,无论在哪里,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都要从博物馆开始,它已名副其实地扮演了地方意识的传播机器.随着博物馆对地方魅力与经济活力的有效刺激,旅游经济与博物馆间的共鸣愈来愈受大众的眷注.就博物馆的游客而言,在业界人士的眼中,“文化游客”普遍构成了博物馆观光群体的主要成员,而之所以会有此观点,原因就在于博物馆是现代人文旅游体系的重要组成,且每一类旅游所特有的游客,都会因不同的旅游动机产生出不同的体验.
“游客凝视”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它会随着不同社会、社群和历史时代而有所改变.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2]认为,游客之所以会不时地远离日常生活而到异地旅游,其目的就是为了凝视那些与自己日常生活不同的景观,并以此获得愉快、怀旧、刺激等体验.就此层面来说,“游客凝视”实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它并非仅是一种观看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将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代表了旅游者对“地方”的一种作用力[3],同时,它还与知识、权力和话语等现代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凝视有着一种“阶级性”.在这里,游客品味的差异暗含了教育、生活背景、知识水平的不同,因而也代表了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文化资本的不同.鉴于此,为了说明文化游客“日常生活”在其观览博物馆展品和取得高品质经历的先验基础,本研究将基于“日常生活”在人文旅游中的延续,从建构游客的“自我凝视”这一概念的角度来分析以博物馆为代表的人文旅游的观光效果与文化游客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1 文化游客的旅游动机与行为认知
近年来,尽管有部分学者基于外出游客动机多元的情况而不提倡将游客类型细分化,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当下的旅游文化.因为,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旅游作为人们世俗环境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对其的需求逐渐更为明确和集中,因为当今的游客,其旅游的目的绝不像过去那样仅停留在一般的“走马观花”上,而是更加强调参与和主观感受,注重旅游主体的想象力和感官体验——这便是后现代旅游体验的特征之一.那么鉴于时代的转变,虽然游客出行的理由呈多元化,但它仍然存在主次之分,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类型的旅游概念则生成了出来,且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客也相应得以划分.
游客的类型,大体可分为观光型游客、娱乐型游客、文化型游客和生态型游客等[4],而在此其中,文化型游客即可谓是一种高尚的旅行者,其所从事的旅游则是一种旨在观察社会、体验民风民俗、丰富历史文化和增长知识的旅游形式.如果要特意标榜文化型游客在现代语境中的特立独行,不妨将其同在发达国家所有旅行者中占比最大的娱乐型游客进行一番比较,即:娱乐型游客通常会倾向在旅游中调节生活,即体验社交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而文化型游客在旅游中则是以升华审美情感为主要体验,且以丰富人生经历为延伸目的;娱乐型游客通常是以松弛精神、享受临时变换环境所带来的欢娱为主要目的,而文化型游客在旅游的行程中,却并不过多地去追求物质享受.
文化游客是当今很多对现代社会内虚外实的物质追求感到厌恶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相信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很多东西都是虚假与枯燥的,按照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说法,现代环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联合,一个分裂的联合,它将人们卷入到了永久的瓦解与更新、斗争与矛盾、模糊与痛苦的大漩涡中[5],因此,文化游客就是意在通过观光游览,并结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去尽可能地追寻那已被现代化亵渎和消散了的“一切坚固的东西”,具体到人文旅游来说,就好比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一承载着千百年来的人类艺术作品的崇高殿堂之中,当文化型游客(如艺术家)漫步或驻足于展厅的某一处,并对其中的一幅作品(如梵高的自画像)进行欣赏和沉思时,不仅会同大众一样从内心中迸发出恭敬和崇拜之感,而且作为精英阶层,还会基于对艺术史和艺术创作经验的积累来自由放空和任意遐想,从而通过知识与艺术品交流来消解现代性的焦虑.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化游客行为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旨在通过人文旅行来达到积极的欢乐与趣味,并同时通过自己的知识来与场景空间相交流获得启迪,即他们进行的是一种融入地方文化的“真实性体验”,而并非是在异地进行的一种“真实符号”的收集活动,然而,他们的观光模式之所以会在博物馆这样的人文旅游中与大众不同,根本源泉就在于其“日常生活”话语中独特的文化、社会和个性等因素.
2 文化游客的日常生活及其在旅游中的延续
旅游和生活的关系,从来都是旅游的基本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关系[6].曾几何时,旅游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躲避现实的方式,因为旅游活动发生的前提,必然是旅游主体与其惯常环境的短暂分离.然而,正如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7]在其长篇小说《在路上》中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在路上”.
由此,便可以想象到,有的人(这里特指文化旅游者)漫游旅途并非全然旨在逃避现实生活的异化,相反,他们更希望将生活中的最初经验投放在旅行中进行检验,并进而在旅行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和思考来将生活想象性地延续.因此,很多将旅游体验与游客“日常生活”相割裂的做法或观点,需要进一步的商榷.
“日常生活”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即指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也是人类生命所有日常活动和经历的总和.“日常生活”的哲学内涵,通常与胡塞尔所提出“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即它是生成人类一切生存常识的“场所”,人类一切意识形态的总和,甚至也是每个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经验基础[8].而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舞台,“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在不同科学话语中的内涵则有所不同,例如在现象社会学中,它被视为是促使“文化再生产”的条件;在功能学派中,它被当作是巩固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媒介;在符号论中,它被看作是促使个体角色社会化的助推器等.
20世纪60年代末,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9]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一书中,曾就“日常生活”这个概念进行了见解独到的论述.按照赫勒理论中的第一种界定,日常生活是指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个体的再生产包含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生产、消费和交往等一系列使人的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则形成了人类稳定的生存方式,即风俗、习惯、规则、规范等,因此每一地区或个人都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便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这种说法与文化哲学对文化的定义是不谋而合的,文化哲学所致力探讨的,是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日常生活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机制,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和给定的规则等.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实则就是“人的生存样法”,就是对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方式的保留与展现.鉴于赫勒以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论证,日常生活无疑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是一个个体置于社会之中的过程,因此根据这样的一种界定,游客的行为与其日常生活活动二分对立的观点显然是不稳妥的.
那么就文化型游客而论,文化游客于生活中的行为同旅游体验间的关系相对可谓是较透明的,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扎根的家庭环境、社交环境、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都对其意识和观念的形成起着比一般生活环境更为积极的滋润作用,因而文化游客在生活土壤中所根生的生存样法与思想理念,则对其旅游体验(特别是人文旅游)有着直接的影响,即出游的动机源于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作用于旅游体验层次的高低.因而基于这一问题的梳理,或许就可以相信,当今博物馆将观众视角及感受作为评估博物馆观光质量的标准之一是存在合理性的.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博物馆评论员约翰·福尔克(John Falk)和林恩·迪尔金(Lynn Dierking)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即从观众的经验视角来评估博物馆体验,而不是从博物馆视角来评估.他们提出了一种“互动式体验模型”,它与一位观众的博物馆体验在如下三个方面产生了交集:观众的个人兴趣爱好、参观的社会动态和博物馆的物理环境[10].那么基于这一理念,福尔克和迪尔金又对博物馆的观光体验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博物馆参观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因为这里涉及到:
1)每一位观众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他/她借助先前的知识、经历和信仰来理解信息;
2)所有的观众都会以自己个性化的方式来接受博物馆的信息,以此来帮助他们的理解和丰富他们的体验;
3)每一位观众来到博物馆时,都有自己的规划,并且对博物馆的参观有很多的期望……[10]那么,从这一具体实例而论,游客在人文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实际与其生活中的经验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他们基于生活经验所生成旅游体验,其质量也是诸如博物馆这样的人文旅游场地所衡量自身的重要标准.因此倘若依照传统观点将两者间的纽带割断,这种认识就很容易会使人文旅游与生活的关系陷入泥潭.
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旅游的先验基础,无论是从文化、社会还是个性层面上,都决定了游客的旅游动机及其对景区事物的感知和认识,而在这一体现上,文化型游客尤为典型,因为他们同常人比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背景、个人兴致、教育环境和职业属性,构成了其所特有的符码,而这既是他们最能在旅游中摆脱世俗体验的特质因素,也是他们因何对文化事物有着卓尔不群的凝视与深思,按照赫勒的话[9]:“每个人都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的特殊的个体.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和素质都是自然秉赋,并且它们将伴随他终生;无论何时,只要他对自己进行估量,都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因素”.这便就是文化游客的日常生活在人文旅游想象中的延续.那么,博物馆作为人文旅游中最为典型的场景之一,它与文化游客的生活经验又有着一种怎样的默契呢?
3 文化游客在博物馆体验中的“自我凝视”
文化游客“日常生活”在旅游中的延续,必然反映在对旅游景地文化事物的感知上.在众多的人文旅游目的地中,博物馆可谓是承载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神圣殿堂,即它作为一种高品质的旅游资源,使旅游活动从纯粹的娱乐升华为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这也说明游客在博物馆中的心灵体验受其自身文化知识、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要远远大于馆内的解说与展示系统,如达·芬奇所创作的《蒙娜丽莎》作为法国卢浮宫的象征符号,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所蕴含的神秘意味,所以游客若想以这种符号去领会客体的意蕴,旅游主体较好的审美能力则是必需的[11].因此,文化游客作为具备较高审美能力的群体,其“日常生活”的延续在博物馆这样一个人文场景中可以说是映现得淋漓尽致.
博物馆参观作为文化游客“日常生活”的延续媒介之一,游客在参观过程中,不但可以凝视旅游场景中的事物,同时也可以经其而“自我凝视”,即反向凝视“日常生活”中的自己.也就是说,游客在观光体验中对文化事物的“凝视”,也通过感知为其行为本身延伸出另一个层面.具体而论,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游客的体验是具有个人性和阶层性的,个体对相关事物的“凝视”质量,与他们各自对其所包蕴内涵的理解与转化能力必然是成正比的,而个体对任何一种事物的体悟,则取决于他们观念中对所视事物的知识储备,所以从这种意义来看,文化展品的存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游客的受教育水平、人文素养和生活经验.
可见,游客对博物馆形成怎样的凝视,都取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定位与文化积累.在此,所谓“自我凝视”,其实就是“反凝视”的一种表现,意指“凝视”作为一种携带着权力运作或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和延长了的观看形式[12],不仅是一种解读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是认识自我的方式.游客作为凝视主体,借以感知文化事物对生活世界施以自身价值理念与知识模式的先验影响的“自我凝视”,生动揭示了博物馆体验的能力与效果,最为典型的,就是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以“浪漫凝视”去找寻展品背后的真实性,而普通人仅会以“集体凝视”获得一种只是亲身经历过的“真实”.
总之,文化游客作为博物馆文化展品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凝视是不可能与生活经验分离的,而其在博物馆体验中对相关文化、艺术、历史等内容的感悟与虔敬,都是根植于知识积淀与个人兴趣等日常生活内容之上的.换言之,文化游客亦是在知识、性格、环境三者所建构的生活世界体系上,辅之馆内展览系统的媒介,而得以在更新知识的过程中升华精神世界的.
“日常生活”是文化游客各种阅历与知识得以建构的场所,也是其在博物馆体验中凝视行为的先验基础,他们在依据自己生活阅历的基础上,既在“凝视”博物馆的同时对人文旅游做出了解读,而且也在“自我凝视”的过程中对自身原有的知识进行了验证.相应地,博物馆作为人文旅游重要的空间场所之一,所演奏的文化旋律承载了文化游客对日常生活的各种憧憬;所陈列的精美展品映射了文化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结构;所展示的内容验证了文化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能力;所传递的知识更新了文化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基础.
4 总结
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区和文化的中心,其高高在上的光环一直都使它保持着远离世俗的姿态.所以,博物馆旅游活动的“崇高”品质,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于文化型游客这一群体,而馆内观光体验的程度和质量,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它与文化游客间的互动与共鸣,即文化游客于此期间对相关事物的“凝视”与“自我凝视”.基于本研究的层层分析,文化型游客通过人文景区对日常生活“自我凝视”所映射出的个人文化、社会和品性,直接影响着游客对博物馆展列事物的认知效果,同时也决定着博物馆游览体验是否能够达到一种沉醉之感,所以可以这样说,博物馆等人文旅游空间的积极成长,与文化型游客“日常生活”及生存方式的层次是有直接关联的.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生活是每个人自己的,但却又是惯常环境以外的,生活铸成了每个人的认知能力,但却又同生活以外的事物紧密相连.被现代性异化的人,往往会去追寻更为现代性的活动;被都市景观蒙蔽的人,往往会去寻找更多地标性的建筑;被金钱圈养的人,往往会去眺望更大的购物型场所;而被文化熏陶的人,则往往会去仰望更多承载知识的文化空间.结合哈贝马斯的观点,虽然每类人基于“日常生活”所从事的旅游活动有所不同,但他们每个人的旅游行为,实则都是其生活世界的延伸[13].因此,文化游客在博物馆凝视中对个体日常生活的“自我凝视”,则暗示了人文旅游不仅是个体认知相关事物的活动,而且也是个体审视和升华“自我”与“现实”的神圣时刻.
当然,尽管本研究意在强调文化型游客是博物馆这一人文旅游的重要游客群体,但笔者并无意否定现代博物馆对大众游客所产生的意义.正如艾琳·胡柏-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在《规训社会中的博物馆》一文中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新‘真理’、新理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由此一种新机构即公共博物馆的新功能出现了[14]”.因而,伴随着从专制权力的象征变成了教育公民而服务于国际集体利益的工具[15],在面对观众(游客)对展览的感兴趣程度及他们知识涵养所存在的差异时,现代博物馆的“公共性”始终都在努力昭示一种民主,并且它的“建构主义”理念始终都在深思.在这里,引用乔治·海因(George Hein)于1998年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观众在博物馆内获得意义,他们通过构建自己的理解而学习新知识.对博物馆而言,问题在于确定观众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其体验中获取了怎样的意义,并依据对环境的控制,最大限度地塑造观众的这一体验……观赏每一件展品都会让人产生反思,即使有些观众并不能理解展品的内涵或其意义……[10]”.因此,考虑到游客“日常生活”的经验,博物馆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解决针对观众的这一多层次方法?并且博物馆实验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它在“建构主义”的未来中应发挥怎样的功效来迎合多元观众的品味和经验?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