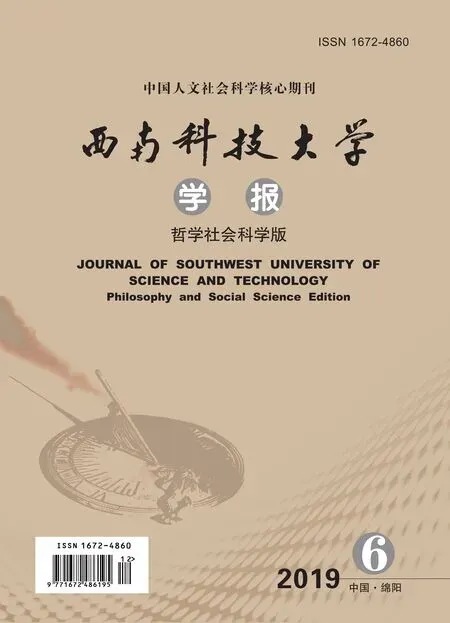语言乃帝国伴侣:西班牙帝国征服阶段的命名探析
王延鑫
语言乃帝国伴侣:西班牙帝国征服阶段的命名探析
王延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1492年西班牙著名学者内弗里哈提出“语言总是帝国的伴侣”这一命题。作为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式,命名在西班牙帝国征服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究其原因,灵活的命名方式是命名发挥作用的外在手段,而命名中所蕴含的丰富含义则是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支撑。依托于上述两种因素,看似无足轻重的命名实际在航海导向、经验指导、辨别敌友、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从而有利于征服活动的展开。探究这一议题,既有助于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源头,也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文化征服;欧洲中心论;西班牙帝国;命名;阿兹特克
众所周知,公元1492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萨贝尔的支持下,率领三艘帆船与美洲不期而遇;而同一年,西班牙语言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弗里哈向伊萨贝尔女王进献了历史上首部《卡斯蒂利亚语语法》。在书的前言部分,无论是希伯来语、希腊语,还是拉丁语,都随相应帝国的兴衰而上下起伏,并由此提出一个划时代的命题——语言总是帝国的伴侣,以此向王室表明伴随西班牙统一进程的顺利推进,规范、推广卡斯蒂利亚语对于巩固西班牙疆域的重要意义[1]。随着时光流逝,这一命题在当代引发回响,如: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在其代表作《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一书中,多次提及、阐释这一命题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此揭示西班牙王室及传教士如何运用语言的力量,对美洲土著人进行殖民统治,进而阐明文艺复兴的隐暗面,即“古典传统的重生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2]。
值得注意的是,从时间节点看,米尼奥罗和很多学者一样,重点关注埃尔南·科尔特斯完成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军事征服之后,而非征服过程本身。虽然语言辅助西班牙帝国统治主要在军事征服之后[3][4][5]332-346,但忽视具有转折意义的军事征服过程,则使人们难以洞悉在帝国兴起阶段语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尽管有众多论著探究科尔特斯率众征服成功的原因[6],甚至有学者注意到土著翻译在征服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5]311[7],但却忽视了语言尤其是命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语言的重要表达形式,命名为我们探究上述问题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切入点。故此,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以下简称《信史》)的记载为中心,通过探究命名的方式、内涵及作用,以此帮助人们全面认识语言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新的视角解释西班牙成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原因。
一、命名的外在方式
从1517年2月首次探险开始,一直到1521年8月特诺奇蒂特兰城沦陷,作为士兵,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参与了两次探险以及最后跟随科尔特斯的征服活动。作为颠覆阿兹特克“帝国”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的《信史》一书为后世了解探险及征服活动,提供了宝贵资料,而其史料价值亦早有公论①。
据《信史》记载,在探险和征服活动中,抓获的土著人在受洗取名后,常用来充当翻译。翻译梅尔乔即是一例[8]7-8。他的名字可能取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记载的某位“东方博士”。后来在跟随科尔特斯的征服中,他在战斗中趁机逃跑,并很可能因不够忠诚,而获得了鄙称“梅尔乔雷霍”[8]18。在科尔特斯夺取了塔巴斯科村及附近地区后,当地部落酋长送来二十名土著妇女,在科尔特斯的要求下,她们全都皈依基督教,并且拥有自己的名字,由此成为新西班牙最早的女基督徒。其中有一名妇女非常出众,受洗后取名为堂娜玛里娜(Doña Marina)[8]77,Marina这一名字可能由神父名字Cortés、Matín、Cristina混合产生②,她后来成为科尔特斯的情人兼翻译。除土著妇女外,也有酋长的儿子经受洗后成为基督徒,并重新取名[8]377。
为命名方便,借用身体特征及土著语音也会成为重要的命名方式。如有的酋长因体形肥胖,被称为“胖酋长”[8]105;又比如有的土著人被称为“洛佩卢西奥人”,这是托托纳卡语,意为“大人、尊敬的大人”之意。这些土著人初次见科尔特斯时,用“洛佩卢西奥人”称呼他,结果反被以此命名。“洛佩卢西奥人”的语言、服饰与墨西卡人不同,并且与当时阿兹特克的最高统治者蒙特苏马之间存有矛盾[8]95-96。
相较于人名,地名的命名方式更为多样。地理、文化、军事、家乡、发现权等诸多方面都会成为命名时的参照因素。在地理方面,曾有滩地因鳄鱼较多而被称作鳄鱼滩[8]15,也有白沙铺地的海岛被称作白岛,相应的,树木葱郁的海岛则被称为绿岛[8]33。在文化方面,宗教再次展现了它的影响力,拉撒路村便是由于探险船队在拉撒路日(3月22日)登陆而得名[8]11。在军事方面,波通昌村成为与印第安人恶战的代名词[8]13。在个人发现权方面,探险者曾将一条河流以当时的统帅格里哈尔瓦命名,他们认为是统帅发现了这条河流,并以此取代原有的名称塔巴斯科河,而后者则是附近村庄的酋长之名[8]26-27。类比家乡的城镇也是重要的命名方式。在随科尔特斯向特诺奇蒂特兰城进发的过程中,某个村子的平屋顶刷得很白,并且酋长的房屋和神堂全都高大整洁,这使得队伍中的葡萄牙士兵想起了家乡的卡斯蒂尔布兰科镇,认为二者很像,于是就将这个村子命名为卡斯蒂尔布兰科村[8]137。
除上述原因外,也有些地名是多方面因素叠加产生的。科尔特斯将自己首战告捷的地方,命名为“圣玛利亚德拉维多利亚”[8]73,该地名便是将宗教与军事两方面相结合的结果。原因在于,这场大战在当年三月的圣母节获胜,因此,地名的前半段“圣玛利亚”是纪念圣母节之意,而后半段“维多利亚”则取军事获胜之意。而在第二次探险航行中,胡安·德·格里哈尔瓦率队登上一个小岛,统帅向翻译询问,为何当地人要用熏香一类的东西熏染他们,由于翻译口齿不清,只能听到“乌卢阿”的声音,又因当时的统帅名叫胡安,再加上那天恰巧是“圣胡安节”,综合宗教、土著语及统帅之名三种因素,伴随历史的机缘巧合,该岛被命名为“圣胡安德乌卢阿”[8]35。
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探险范围有限,因而所涉及的名称并不多,在认识上也比较粗浅,只存有直观感受与大致印象。相关命名也仅是为了实用方便、易于标记,诸如鳄鱼滩、白岛、绿岛等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样的命名方式实际也与探险者的航海目的有关,其目的不在于深究某地,而在于初步探险,摸清海况,探查港口,绘制海图,了解大概,从而为后续的征服与殖民活动铺垫。随着以后征服活动的扩展,大量土著地名与人名不断涌现,考虑到要及早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为使用方便,征服者开始更多借用土著语音开展命名活动。当然,在某些场合下,基于同样的征服目的,其它命名方式也会不断呈现,甚至考虑到性别、阶层及忠诚度等问题,也会冠以不同的名称,如上述针对印第安妇女、酋长之子以及土著翻译的命名活动,便反映出这一点。
总之,从探险到征服,从男性到女性,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从阿兹特克东部海岸到腹地都城,命名方式始终受探险与征服目标的影响。随着征服者接触的土著人口越来越多,到达的地方越来越深,命名的对象也日趋复杂化,命名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常常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就人名来说,有尊称亦有鄙称,有宗教考虑,也有简便称呼。但受制于传统的天主教文化及起名惯例,宗教方面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点不但反映在命名程序上,即先受洗礼后命名,也反映在命名内容上,即宗教名字占有较大比重。就地名来说,或考虑单一方面,如地理、文化、军事等,或考虑多种方面相叠加,如宗教与军事因素相结合。无论是人名上的因人而异,还是地名上的“因地制宜”,归根到底,都是有利于探险征服活动统一高效进行。而在灵活的命名方式背后,命名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则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二、命名的内在含义
首先,命名中体现出较大的宗教色彩。就地名而言,诸如拉撒路村、圣玛利亚德拉维多利亚以及圣胡安德乌卢阿都体现出这一点,并且宗教人物圣玛利亚以及宗教节日圣胡安节都是作为地名的前半段融入其中,足见宗教在命名者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名称实际上是延续自中世纪的宗教观念与征服者在新大陆的经历相结合的产物,是自身文化背景在新大陆的能动反映。就人名而言,取得名字的先决条件是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否则便无从起名。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它们都是早期征服者将军事实力与宗教观念相结合,进而迫使土著人进行宗教文化认同的阶段性成果,因此,命名也是文化征服的产物。简而言之,命名是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标志。
第二,地名中流露出较强的长官意志,体现出军事长官在团队中不同寻常的地位③。例如以统帅之名命名的格里哈尔瓦河,以指挥官之名命名的圣胡安德乌卢阿等都体现出这点。一方面这是由于欧洲中世纪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在当时尚未丧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探险、征服队伍内部所实行的相对严格的等级制度。凭借此种制度,军事长官获得了较大权力,而普通成员的财富、荣誉甚至是生命等核心利益都与长官息息相关。由此,军事长官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而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也得以保障,最终使征服活动高效统一进行。在征服过程中,作为征服队伍的首领,科尔特斯便多次惩罚不忠诚的士兵[8]100,128-129。正是在这种制度及中世纪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下,集体的发现权往往归结到长官一人身上,进而在命名主导权上有所体现。
第三,地名中体现出较多的伊比利亚半岛气息。卡斯蒂尔布兰科村、拉兰布拉、塞维利亚等都体现出这一点。很多探险者及征服者文化水平一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新大陆,参与探险及征服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黄金,实现“发财梦”。因此,他们缺乏对新大陆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的源动力,只能抓住表面的相似之处,运用头脑中原有的地理空间概念,进行满足自身航海与征服需要的简单命名。就人名而言,梅尔乔、梅尔乔雷霍、堂娜玛里娜等,都带有不同于土著文化的西班牙色彩。由此看出,命名活动实际成为构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重要抓手。
第四,命名体现出征服者对土著人重视程度的差异。虽然形式上是有无“堂”或“堂娜”的差别,但实际上,这不仅和土著人原有的社会地位相关,也和征服者所要表达的尊敬之意及土著人的忠诚度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与土著人所具有的利用价值的大小密切相关,与征服目标和策略密切相关。对于征服活动,从人数上讲,早期征服者并不占优势,因他们要想成功就需要利用土著社会的原有矛盾,通过分化瓦解土著人以达壮大自身之效。对此种策略,科尔特斯在给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信件中并不讳言[9]69-70。因此,除非土著人主动进攻或者背叛,征服者都极少激怒他们。相反,为了获取金银和传播基督教,征服者一直尽力与他们维持良好关系,并对皈依的土著人不轻易给予蔑称,而且对酋长子女多冠以尊称,以此来进一步拉拢土著社会上层,增强对整个土著社会的牵引力,从而为征服目标服务。
第五,命名体现出征服者的自我中心。用以宗教节日命名的拉撒路,取代原村落名坎佩切,用以统帅之名命名的格里哈尔瓦河,取代以酋长之名命名的塔巴斯科河,即便借用土著语音命名,而字母则是本民族的。一方面是由于双方语言文化的隔膜所致,在实际操作中,征服者只能借助自身的文化背景认识新大陆;另一方面,也是征服者自我中心的表现。这种自我中心的出现,既与当时文艺复兴促进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关[10],也与征服者强烈的宗教信念有关。在他们看来,新大陆是他们发财与传播天主教的地方,是他们获得名利的地方,是他们的个人主义得以伸张的地方,所以在命名中流露出主导倾向。
总之,影响命名内涵的几大因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探险与征服的目标、相对强大的军备优势、天主教文化观念以及相对缺乏的新大陆认知。若将这几大因素串联起来,便可发现,命名本身实际体现出探险者与征服者以自我为中心,凭借军事优势,将自身的活动目的以及充满地域色彩的文化观念融入新大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征服者一方面以灵活的命名方式为外在手段;另一方面以命名中所蕴含的丰富含义为内在支撑,在征服活动中发挥了众多基础性的作用。
三、命名的重要作用
首先,早期探险者将得来的地名标记于航海图上,为后续开展征服及殖民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导向与支撑。正如科尔特斯对蒙特苏马所说的,“那些人来探明路线、海域和港口,他们把一切探明,我们才能像现在这样,在他们之后前来”[8]230。这里说的他们即指早期探险者。由此可见,命名对于征服与殖民活动具有航海导向的意义。但是,对于“新大陆”的地理认知,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先前的偏差需要在后续探险及征服活动中加以改进。如在第二次探险过程中,船队驶进一条“很宽的河流”,由于司舵误将河两边的陆地看做岛屿,并将这片宽阔的水域视作分界线,因此,这片水域便被称作“界河口”,并被标记在海图上。但后续的探查表明,此处是一个良港,原先的岛屿实为陆地。
第二,由于命名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凝聚集体的意志,形成对某地或某人的一般性看法,使命名结果具备相当的权威性与参考性,从而对征服与殖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在首次探险活动中,探险队与土著人在波通昌村展开大战,损失惨重,该地由此获得“恶战海岸”的名称;到第二次探险活动时,由于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探险队在战斗中便没有陷入过分被动;到科尔特斯率队征服时,众人对此处的“恶战”印象演变成复仇心理,只是由于风向的原因,才未能靠岸大战一场。
第三,由于命名本身实际是区分自身与他者的过程,这对于探险者、征服者凝聚自身力量,区分外在的“敌人”与“朋友”,并在此基础上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具有重要意义。就地名来说,“洛佩卢西奥人”所在的村落便是科尔特斯需要拉拢的对象,而享有“恶战海岸”之名的波通昌村便成为科尔特斯想要复仇的对象;就人名来说,改信基督教并拥有教名的人要比其它的未改信基督教的人更受征服者的亲近与依靠,但在改宗的人当中,堂娜玛里娜是受尊敬与优待的对象,而“梅尔乔雷霍”则是受鄙视的对象。
第四,通过命名,早期的探险者及征服者构建起他们关于新大陆的众多认知支点,借助于这些支点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逐渐构建起一幅迥异于土著人的且服务于征服目的的“新大陆”文化景观图;并且,这些认知支点在日常谈话及域外通信中实际转变为信息交流的支点,表达、传播、协调征服队伍对阿兹特克社会的相关看法。比如,提及位于墨西哥城中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的大市场,征服者呈现的是一幅面积广大、人员众多、物品繁盛、井然有序的景象,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感叹道:“我们兵士中有些人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到过君士坦丁堡,走遍意大利和罗马;他们说,面积如此宽广、布局如此合理、人众如此之多、管理得如此井然有序的市场,他们尚未见到过。”④并且,通过科尔特斯的书信,征服者将此种印象传递给了当时西班牙的国王查理五世[8]101-105。
第五,通过命名,早期探险者及征服者将西班牙文化特别是宗教与语言文化,传播到阿兹特克“帝国”,实现军事征服与文化征服的同步。科尔特斯等人利用军事优势,把握历史契机,不但趁机捣毁了一些村落或城镇的宗教设施,而且尽可能强令土著上层人士改信耶稣,拥有教名,以此对当地社会产生示范效应,进而打破原有的土著信仰,传播基督教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变迁,源自征服时期的某些名称,实际成为带有鲜明价值判断的文化符号。例如,尽管有学者为科尔特斯的情人兼翻译马林切“鸣冤”,认为她当时的所作所为只是保存性命、忠诚地履行职责,但在墨西哥独立后,不少人将她的名字视作叛徒的同义词[11]。
总之,在探险与征服活动中,命名具有航海导向、经验指导、辨别敌友、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五大作用,对探险及征服活动不断产生基础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命名作为系统性征服活动的一部分,其作用的发挥,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附性。探险及征服活动需要将新大陆纳入逐渐兴起的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及文化体系中,而命名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渗透到探险及征服活动的各个领域,发挥独立作用。但是,必须和探险及征服活动的方方面面相结合,才能展现出自身的价值,哪怕是一枝用于绘制航海图的笔,它都难以离开,更遑论它对征服目的、策略及技术等方面的依赖。因此,只有将命名置于整个探险及征服活动之中,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作用。
结语
1492年内弗里哈的名言——“语言总是帝国的伴侣”呈递在西班牙王室面前;1521年科尔特斯率众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从此原有的墨西卡人势力范围转而成为王室统治下的新西班牙殖民地。在上述探险及征服活动中,一群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征服者,凭借正确的政治及军事战略,依靠相对强大的军事技术,怀揣着发财梦与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使命,背井离乡来到阿兹特克“帝国”。而在他们与当地土著人的利益冲突与观念碰撞中,命名在不断上演,从而使众多的历史信息遗留在命名之中。
虽然命名的方式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共同点都强调天主教因素;虽然命名的内涵丰富多彩,但核心在于欧洲的中心主义;虽然命名的作用广泛深入,但关键在于服务征服活动。从方式到内涵再到作用,围绕着命名,在层层递进中折射出一条不对等的主客体关系。代表西方文明的探险者及征服者掌握命名的主导权,而代表土著文明的阿兹特克人则处于被命名的客体位置。命名中所暗含的这种不对等关系,既是历史上征服进程的缩影,也是后世西方霸权的源头,而其中所暗含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更是值得警惕与关注,其实质与19世纪以来兴起的欧洲中心论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彰显了欧洲强国的话语霸权,且有意或无意宣扬欧洲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是西方人看世界的结果”[12]。
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倒塌声中,在旧帝国的废墟上,一个崭新的西班牙帝国正在兴起。在新旧帝国的交替中,作为旧“帝国”的伴侣,原有的纳瓦特尔语正处于衰退的边缘;而新帝国的“宠儿”卡斯蒂利亚语即将迎来自己的天地,且在命名中已露端倪。命名本身不仅是征服历史的映照者,还是西方霸权的昭示者。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文化利器,它也是征服进程中无处不在的参与者,它没像“春雨”那样,滋养阿兹特克社会的万物;反像“秋风”一般,四散开来,席卷整个疆土,在促使旧“帝国”走向灭亡的同时,也成为新兴帝国的前哨与标志,并且作为新兴帝国的文化印记,一直留存至今。
注释
① 下面正文中涉及的地名及人名的西班牙文,可查阅《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书后所附的《人名译名表》及《地名译名表》,第670-684页。
② 值得注意的是,除叫堂娜玛里娜外,此人姓名还有多种写法及含义。参见Rosa María Grillo,El Mito de un Nombre:Malinche,Malinalli,Malintzin,Mitologías Hoy,2011(4),15-26.
③ 也有国外学者注意到长官的个人主义如何凌驾于征服队伍的集体意识之上。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50-151页。
④ 需注意的是,由于音译的关系,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将现行译法“特拉特洛尔科”称作“塔特卢尔科”。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第240页,第244页。
[1] Antonio de Nebrija.Gramática sobre la lengua castellana,edición,estudio y notas de Carmen Lozano,y Paginae nebrissenses,al cuidado de Felipe González Vega[M]. Madrid:Real Academia Española;Barcelona:Galaxia Gutenberg-Círculo de Lectores,2011:3-11.
[2] 瓦尔特·米尼奥罗.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M]. 魏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48-50,60.
[3] 普忠良. 官方语言政策的选择:从本土语言到殖民语言——秘鲁语言政策的历史与现状问题研究[J]. 世界民族,1999(3):56-66.
[4]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M].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413-414,694-702.
[5]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M]. 章璐,等译. 维舟,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6] 李博. 拉美印第安土著社会被快速征服原因研究综述[J].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0(9):229-312.
[7] 戴尔·布朗,主编.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M]. 万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5.
[8]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 征服新西班牙信史[M]. 江禾,林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 Hernades Cortes,Anthony Pagden trans.Hernades Cortes:Letters from Mexico[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何新,译. 马香雪,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9-183.
[11] 本杰明·吉恩、凯斯·海恩斯. 拉丁美洲史(1900年以前)[M]. 孙洪波,王晓红,郑新广,译. 张家哲,译校.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98.
[12] 马克垚. 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J]. 历史研究. 2006(3):12.
Language was an Imperial Companion:Nomination Analysis During the Conquest of Spanish Empire
WANG Yan-xin
(Faculty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In 1492,the Spanish linguist Nebrija put forward one important idea that language was an imperial companion. As an important expression means of language,nominat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during the conquest of Spanish Empire. The reason was that the flexible ways of nomination were seen to be the important external means,while the abundant meanings of nomination were the internal suppor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factors,the seemingly meaningless nominations in fact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navigational orientation,experience guidance,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iends and enemies,inform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ffusion,which were beneficial to the spread of conquest. Studying this theme helps not only to reveal the origin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but also to reflect on the way of thinking of Eurocentrism.
cultural conquest,Eurocentrism,Spanish empire,nomination,Aztec
K731.3
A
1672-4860(2019)06-0001-06
2019-09-01
王延鑫(1991-),男,汉族,山东邹平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拉丁美洲早期史、拉美移民史。
本文是南开大学中央专项资金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与拉丁美洲”(编号:631929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