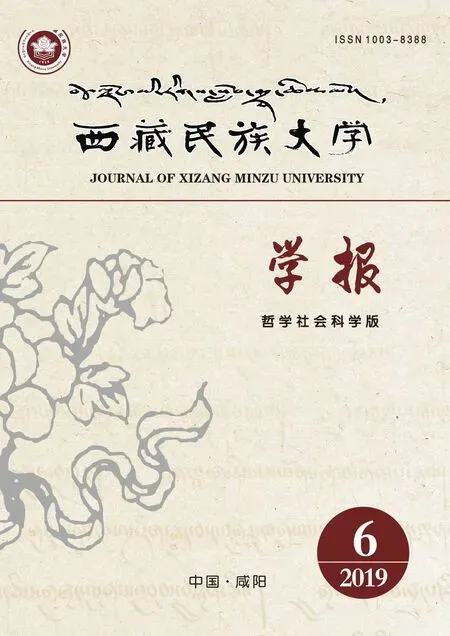新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70年(续)
木仕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三、阿尔泰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一)突厥语族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等文字,并用这些文字记录了大量各方面的文献,是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史的文献依据。
1、突厥文及其文献研究
突厥文是公元7-10世纪突厥、回鹘、黠嘎斯等族使用的文字,又称鄂尔浑-叶尼塞文(Orqon-Yenisey Script)、突厥如尼文(rune)。通行于鄂尔浑河、叶尼塞流域以及今中国新疆、甘肃境内的若干地方。1889年,俄国人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带领考察队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根据这两通石碑,丹麦的语言学家汤姆逊(V.Thomsen)解读了古代突厥文。俄国的拉德洛夫(W.W.Radloff),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Von.Gabain)都曾对突厥碑铭做过研究。国内最早对突厥碑铭进行译释的学者首推韩儒林先生,1949年前韩儒林的《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6期,1935年)、《突厥文芘伽可汗碑译注》(《禹贡》第6卷6期,1936年),《突厥文暾欲谷碑译文》(《禹贡》第6卷7期,1936年),《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翻译)(《禹贡》第7卷1期,1937年)。岑仲勉的《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6卷第l、2合期1937年),1958年,岑仲勉又据英文译本改译了韩儒林所译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王静如的《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1938年第7卷第1、2期合刊),冯家昇的《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1963年第3辑)对古突厥文刻题记进行了研究。耿世民的《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湾新丰出版公司1994年),《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探讨了突厥、回鹘的历史、碑铭的发现和解读情况,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古代突厥语法等,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九块碑铭以及《占卜书》做了全新的译释,提供了可靠的译本。此外,对突厥文碑铭的研究现做专门评述的论文有:耿世民的《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情况》(《图书评介》1980年第4期)。陈宗振的《突厥文及其文献》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突厥文的重要著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库尔班·外力的《吐鲁番出土公元五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文物》1981年第1期)。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从文学角度谈及部分古代突厥文碑铭及其文学价值。李经纬的《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对《苏吉碑》作了汉译和注释。林幹的《古突厥文碑铭札记》(《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突厥碑铭中的若干语词的释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克由木霍加、吐尔逊阿尤甫、斯拉菲尔等编译的《古代维吾尔文献选》(维文版)(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对《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磨延啜碑》进行了转写、维吾尔文翻译和注释。
耿昇译勒内·吉罗的《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1]对《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作了深入考证。牛汝辰、牛汝极的《古代突厥文〈翁金碑〉译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对发现于蒙古国的《翁金碑》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译释。张铁山的《我国古代突厥文文献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设想》(《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在评析突厥文文献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该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若干设想。牛汝极的《突厥文起源新探》(《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认为古突厥文从象形和契刻符号发展而来。赵永红的《古代突厥文〈占卜书〉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杨富学的《古代突厥文〈台斯碑〉译释》(《语言与翻译》1994年第4期)则对具体文献做了译释。芮传明的《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突厥文碑铭研究的新著。艾娣雅·买买提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古俗寻绎》(《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阿力肯·阿吾哈力的《突厥如尼文字溯源》(《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对突厥如尼文字的起源提出了新见。耿世民的《若干古代突厥词的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4期)、《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姆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丹麦学者汤姆森与古代突厥文的解读》(《民族语文》2006年第6期)论及突厥文碑铭的发现与研究现状。通论性的有戴良佐编著的《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收录了汉文碑铭210通(方),书中收录的20通元碑,反映了高昌畏吾儿人在内地的业绩。
2、回鹘文及其文献
回鹘人采用粟特文字母创制的文字,属音素文字类型,主要通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及中亚楚河流域。留存至今的回鹘文书写的碑铭和文献有《九姓回鹘可汗碑》《弥勒会见记》《福乐智慧》《金光明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高昌馆杂字》《高昌馆来文》等。
研究论著有耿世民的《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维吾尔族古代史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冯家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2,1953年)。胡振华、黄润华整理的《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胡振华、黄润华整理的《高昌馆杂字——明代汉文回鹘文分类词汇》(民族出版社1984年)。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经纬、鞠尚怡、颜秀萍著《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编著《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邓浩、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牛汝极的《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张铁山的《突厥语族文献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阿不里克木·亚森的《吐鲁番回鹘文世俗文书语言结构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①的译注与研究成为回鹘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出现了多个文种的译注本。耿世民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是关于古代维吾尔族原始佛教剧本(也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剧本,属公元8世纪)的研究,有功于戏剧史的追溯。张铁山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一、二)[2],为莫高窟新发现回鹘文献译释成果。
敦煌回鹘文木活字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也是20世纪90年代回鹘文字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1014枚,年代在12世纪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早于古腾堡使用金属活字。史金波、雅森·吾守尔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中,雅森·吾守尔执笔的《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整合多学科的视角,证明回鹘文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历程中的中介类型活字。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证明了在中国内地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就已经传播到西夏和回鹘地区,彻底改写了活字印刷术历史进程,确立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文明史地位。
3、察合台文及其文献
察合台文是突厥语诸民族和蒙古人使用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音素型拼音文字,14-20世纪通行于新疆和中亚以及印度北部地区。察合台文文献主要收藏在新疆。目前已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主要有:《拉失德史》《中亚蒙兀儿史》《成吉思汗传》《伊米德史》《安宁史》《布格拉汗列王传》《新史记》《乐师传》《巴布尔传》《和卓传》《突厥世系》《阿帕克霍加传》《和卓依斯哈克传》等近60本。
宝文安汉译的《苏图克·布格拉汗传》(《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6辑)、马维汉汉译的《艾卜·纳色尔萨曼尼传》系察合台文手抄本文献。察合台文《纳扎里诗集》《布格拉汗列王传》《和卓传》等都有汉文全译本。察合台文契约文书有陈国光在《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的基础上编辑的《民国时期南疆地区部分契约文书编目》,李进新的《近代新疆维吾尔族契约资料评介》,王东平的《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年》等。金玉萍的《清季吐鲁番地区的租佃契约关系——吐鲁番厅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研究》(《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对清朝光绪年间吐鲁番地区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作了研究。
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始于《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收入的314件文书包括契约及非契约性的文书,是研究清代南疆地区的维吾尔社会必备文献,弥补了汉文文献的不足。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整理、张宏超翻译《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收纳瓦依诗共260首,对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清史编撰项目编译的察合台文献的代表性成果有苗普生译注的《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将原文为察合台文或波斯文的五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年史》《和卓传》《大和卓传》《伊米德史》和《塔兰奇史》作了译注,对研究16-20世纪初新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蒙古语族文字文献研究
蒙古语族的文字符号系统的创制使用与蒙古帝国的崛起密不可分,还关系到蒙古族与回鹘、藏族、粟特等诸多民族之间的文字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
1、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研究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研究主要以文献整理,转写,注释为主。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是《也松格碑》时间约为1224年年末或1225年年初。回鹘式蒙古语及其文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道布编纂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古文版,民族出版社1983年),汇集了国内外先后刊布的13-16世纪回鹘式蒙古文文献22份,还介绍了蒙古文字概况和13-16世纪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整理研究情况。其他代表性成果有: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回鹘式蒙古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代表性论著有嘎日迪的《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研究》(蒙古文版,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中古蒙古语研究》(蒙古文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中古蒙古语研究》(汉文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系对13-16世纪回鹘式蒙古文音写蒙古语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关中期蒙古语的概括性论著。哈斯巴根的《中世纪蒙古语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蒙古语历史及文献语言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也是这一时期的回鹘式蒙古语及文献研究的代表性著作②。
宝力高的《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对蒙古文佛教文献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从版本学角度分类阐释了蒙古文佛教文献的载体、写本和刻本、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雕版刊行、版本特点以及内容等,是回鹘式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的代表作。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是对《蒙古源流》作科学整理和研究,经过校订的原文拉丁音转写等内容。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同时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或者不足之处,对不少问题有创见。
2、八思巴文及其文献研究
八思巴字堪称元代通字方案,可拼写不同民族的语言。现存八思巴字文献,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碑铭各有二十余通。八思巴字对译汉语资料有助于重建元代汉语的音韵系统,也可用以考求汉语北方官话的形成史。罗常培、蔡美彪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新版)即是八思巴文献的集成,研究元代汉语的重要成果。蔡美彪著《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主要是对八思巴字音写蒙古语碑文的考释,以及八思巴字音写蒙汉语及其他语言的文物的考释。蔡美彪著《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华书局2017年)所收录的元代白话碑的碑文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白话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白话口语状况,为研究元代汉语史必备资料。
照那斯图的《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资料辑存》(文物出版社1977年)收录印蜕95方,有重要参考价值。照那斯图此后出版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1990,1991年)两部重要专著,与薛磊合作出版了《元国书官印汇释》(民族出版社2011年)。照那斯图、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年)为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研究者提供了校勘本。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篆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是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系统之作。照那斯图、宣德五的《训民正音和八思巴字关系探究——正因字母来源揭示》(《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认为“训民正音”字母表的来源是八思巴字,备受瞩目。
3、托忒蒙古文及其文献研究
托忒蒙古文,是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文字。托忒文献包括人物传、法典、外交文书、祭地书、纪实文学、地图、世系谱等。M·乌兰所著的《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对托忒文历史文献作了系统介绍研究,探讨托忒文文献与卫拉特史方面的关系。特别指出,以往的学者们主要是对国外藏托忒文刻本进行研究,无视中国藏托忒文刻本及其载体类别。研究表明中国藏托忒文文献刻版类别最丰富,但研究落后于国外。通论式的著作有王大方、张文芳编著的《草原金石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全书通过对蒙古草原地区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元朝时期的石碑和印章等金石类文物的考察、拍照、拓印与研究,丰富了元朝时期蒙古族地区的历史史料。
(三)满-通古斯语族文字文献研究
满-通古斯语族的文字文献的创制与辽、金两个王朝的兴盛有关。契丹文字的创制受汉字的影响。契丹文分大字和小字,有表意和表音的性质区分。由于契丹文与女真文已经死亡,存世的文献有限,目前对契丹文与女真文的解读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仍在艰辛的探索中。契丹语言的语言系属,有的学者主张应归蒙古语族;有的则主张纳入满-通古斯语族。本篇为了叙述方便,暂归入满-通古斯语族。
1、女真文及其文献研究
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记录女真语,使用流行时间从12世纪20年代至15世纪中叶,女真语言文字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明朝编纂的《女真译语》。现存女真大字石刻共计十二件③,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的《女真语言文字考》出版标志着女真语文学的创设。自19世纪至20世纪末,在中国、朝鲜及今俄罗斯境内发现各类型的女真文文献30余件。金光平、金启孮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专号》1964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文字的专著。金启孮著《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收录女真字1737个,堪称女真文字研究的百科全书。金启孮、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大辞典》(日本明善堂2003年),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总数达到1300多字,区分了女真文意字和音字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脉络,并将其与满洲-通古斯诸语言作了比较研究。
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的《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1983年)对女真语的语音作了构拟并对女真语的语法作了新的探讨。乌拉熙春的《明代的女真人——从女真译语到永宁寺记碑》[3]讨论了《女真译语》和由汉文、蒙古文、女真文所写的三体碑文《永宁寺记碑》的两种残留的女真文资料,对15世纪的女真文从文字、音韵、语法等方面进行新的解读。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郡女真大字石刻》和《北青女真大字碑》的研究成果有乌拉熙春、吉本道雅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对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大字残页的综合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字书研究》(日本风雅社2001年);对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松香堂2009年)和刘凤翥等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中西书局2019年)。
2、契丹文及其文献研究④
契丹文是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统称,一般认为契丹大字于辽太祖神册五年(920),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系表意文字。契丹小字的创制晚于契丹大字,由太祖弟迭剌创制,系拼音文字。
1922年6月21日,辽兴宗皇帝及其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在辽庆陵被发现,引发契丹文字考释的一时风气。1925年日本的羽田亨所撰《契丹文字的新资料》(《史林》1925年第10卷第1号)发表视作契丹文字研究的肇始,该文区分了女真文和契丹文的界限,限于资料,契丹文解读仍在探索中。1930年代,处在对契丹字字义的推测阶段,代表人物有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等。具体成果为罗福成《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号,1933年),《兴宗皇帝哀册文释文》(《满洲学报》第2号,1933年)。王静如的《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契丹国字再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1935年)为契丹文研究的创始之作。《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考古》1973年第5期)则使契丹文的研究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厉鼎煃著(署名天德)《契丹国书略说》(仁声印刷所,1934年)、《热河辽碑二种考》(《大学杂志》第1卷第5期,1933年)、《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也是当时较突出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为:分清大小字的区别、了解小字的拼写构造、书写方法、推测一些字的意义。受制于研究方法,可信的仅七十余条。1939以来发现的契丹大字的9篇资料的拓片影印件和相关汉文碑刻均收录于清格尔泰等编撰的《契丹小字研究》[4]中。
1950年代,探索拼读法,构拟字音成为研究工作的主流。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为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劲旅。如山路广明1956年的《契丹制字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契丹文字的读音问题。村山七郎1951年3月在《言语研究》上以《契丹字解读方法》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契丹字来源于突厥文字的观点。长田夏树于1951年刊布《契丹文字解读之可能性》,对契丹字进行了系统的统计研究。爱宕松男于1956发表《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和《契丹文字鱼符、玉盏、铜镜铭文的解读》,主张契丹语和蒙古语完全相同,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原字还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字母和字头。1960年代苏联及欧洲诸国学者也开始全新的契丹文研究。如:鲁道夫、沙夫库诺夫、达斯今;法国的安比斯,德国的门格斯、弗兰克、道弗尔,匈牙利的李盖提、卡拉等为代表。
1970年代中国学者为了改变契丹文字研究停滞的局面,1975年9月清格尔泰、陈乃雄、刘凤翥、于宝林、邢复礼等人共同组织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契丹小字进行了一系列攻关式的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关于契丹小字研究》[5],初拟了一百个字的音值,最终成果题为《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问世。小组的研究以音义结合、重视汉文史籍中用汉字记录的契丹语材料,参照亲属语言的语音语法现象的研究范式见长,部分拟音内容和语词释读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有进展,具体如:构拟出110多个原字的读音,释读了三百多条词语,并对24种附加成分的音义作了讨论。
1980年代,出土了众多契丹小字的文献。18方契丹小字墓志铭的拓片影印件以及摹本均收录于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中。目前已确认且包括重复出现的契丹小字的总字数已突破3万5千字。契丹文字研究小组1985年专著《契丹小字研究》发表后,契丹文研究成果迭出,如:即实的《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刘凤翥的《遍访契丹文话拓碑》(华艺出版社2004年),乌拉熙春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和《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陈乃雄和包联群的《契丹小字研究论文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吴英喆、杨虎嫩的《契丹小字的新资料:萧敌鲁和耶律详稳墓志考释》,[6]吴英喆的《契丹小字新发现资料释读问题》(东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等。吴英喆认为契丹文研究界逐步掌握了契丹小字中存在的若干规律,如:(1)元音和谐律:清格尔泰首次提出契丹语中存在元音和谐律的观点。代表论文为《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2期)(2)“数”的和谐:高路加的《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8年第2期)中,提出契丹小字中基数词作定语时,被限定语常常采用复数形式(但也有单数的)的观点。(3)“性”语法范畴:吴英喆的《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观点。(4)父子连名现象:刘浦江和康鹏在《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期)认为在契丹族的历史上存在“父子连名制”。(5)元音附加法:吴英喆的《契丹小字拼读方法探索》(《蒙古学集刊》2006年3期)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元音附加法”的观点。(6)入声韵尾:吴英喆的《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蒙古学集刊》2006年第4期)认为辽代汉语借词中入声韵尾并没有完全消失。
刘浦江领衔编纂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厘定了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纠正了前人的若干错误。刘凤翥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涵盖了迄今为止最新的契丹语文研究成果和最全的契丹文研究资料,分:契丹文字研究史;契丹文字新研究;契丹文字资料诸篇。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的《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是继《契丹小字研究》之后总结国内外契丹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契丹文大小字性质各异,尚未彻底破译。契丹字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分析型的汉字与粘着型的阿尔泰语类型之间的契合路径,也利于了解汉字传播史的轨迹。
3、满文及其文献研究
满文文献研究历史悠久。清朝一直坚持对满文文献的装订分类存档。清乾隆年间就开始对《满文老档》进行整理、编纂出《无圈点字书》,堪称为清代满文文献整理的先河。清末有张玉泉、李德启的《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满文书籍联合目录》。1969年台北故宫影印出版十册《旧满洲档》满文文献。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整理出版《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2册)、《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为满文文献整理的重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的《盛京刑部原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三册)。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收录海峡两岸收藏的满文档案4297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的《雍正朝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收录海峡两岸收藏的满文档案5434件,文献均系首次翻译刊布。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史料选译》(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备受关注。
1980年代以来,满文古籍《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八旗文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熙朝雅颂集》得到整理和刊布,《满汉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的问世使清史和满语研究更上层楼。
关于满文文献的刊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全283册)出版问世,其内容丰富,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吴元丰主编的《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辑录北京7个单位所存满文和满、蒙、汉、藏等多体文字合璧的碑刻拓片,共计764种,比《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多出85种,代表着新的进步。
四、印欧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中国境内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⑤的文字文献都是古代的死文字及文献,但关乎东西交通、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一直是丝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吐火罗语文献、粟特文献的研究一直是印欧语言学界的重要研究论题。
(一)吐火罗文及其文献(焉耆-龟兹文文献)研究
吐火罗语是20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种死语言,1890年发现第一份吐火罗文书写的手稿。吐火罗文的文献以佛教内容为主,也包含了寺院经营档案、商旅通关文件、医学和巫术的报告等。季羡林1943年在德国发表了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利用包括汉文在内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46年回国之后,因资料缺乏,中断了三十年,中间只有冯承钧汉译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和列维(S.Levi)著的《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65年)问世。197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从1981年起季羡林又得以重新研究。季羡林的研究确认1974年在一处佛教遗址发现的残破的古代文书是用吐火罗文写的剧本《弥勒会见记》。1993年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⑥出版;1998年,季羡林在德国出版《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结束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历史。季羡林还发表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新博本76YQ1·1(两页一张)译释》(《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继季羡林之后,我国继续从事严格意义的吐火罗语文献研究的学者仅台湾女学者庆昭蓉一人而已。庆昭蓉的《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等出土胡汉文字资料为经,传世史籍与佛教典籍为纬,分析6-8世纪龟兹的历史特征,概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出土与收藏情况,并介绍近年国外吐火罗语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引述不少海外所藏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世俗文书残片的录文与翻译作为论证根据,吸收了一部分古代龟兹地区境内现存石窟题记的最新调查成果。相关最新的成果还有庆昭蓉的《从吐火罗B语词汇看龟兹畜牧业》(《文物》2013年第3期)、《从龟兹语通行许可证看入唐前后之西域交通》(《西域文史》第8辑,2013年)。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唐研究》(第二十卷)发表《苏巴什石窟现存龟兹语及其他婆罗迷文字题记内容简报》,对法国探险队20世纪初发现的有关题记的照片以及在法国吐火罗语专家walter couv⁃reur,georges-Jean pinault对该题记介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三方合作项目“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的调查与研究”对现存题记做新调查,并与Pinault的《库车地区诸遗址》(Sito divers de la re⁃gion de Koutcha,Paris,College de France,1987)出版的四道题记勘合,分前言、转写体例、题记内容、现存题记的文献与历史价值、结语五部分,仔细勘定了所录共49行横列婆罗迷文字,共计47道题记的原文内容,堪为最新成果。
中国学者认为,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定名是有问题的,主张称为焉耆-龟兹文文献⑦,如王静如的《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⑧等文论证了“吐火罗语”实际上就是“焉耆语”和“龟兹语”,季羡林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如是主张⑨。
(二)粟特文及其文献研究
粟特文字母系阿拉美字母的分支。现存的粟特语文献的写作年代集中于8-11世纪,多数是从穆格山、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目前我国学者对粟特语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在外国学者释读基础上进行的。龚方震的《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黄振华的《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程越的《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陈海涛的《敦煌粟特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均对粟特文文献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伊不拉音·穆提依的《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7]概述了粟特人活动和粟特语的演变。王叔凯的《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传播》(《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期)也论及此专题。其他讨论文书的典型成果如:王冀青的《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和陈国灿的《敦煌所出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1985年)都讨论了二号信札的译文及写作年代,观点各异。林梅村的《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从考古地层和信件文义分析,提出此前两位学者讨论的文书信撰于202年。林梅村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文书记载的女奴买卖问题。1984年马小鹤在《公元8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1984年)一文中,诠译若干粟特语、阿拉伯语文书,阐明了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经历和8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林梅村的《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利用汉文史料对碑文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了新的解释,称碑文的作者是在突厥为官的粟特侨民。
柳洪亮的《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收录了吉田丰的《粟特文考释》以及吉田丰对柏孜克里克摩尼教粟特文书信的格式所做的研究,吉田丰认为其书信格式一方面与《古代书简》(4世纪初)和穆格山文书(8世纪初)相似,并与同时代的回鹘文书信也有相同之处。美国学者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苏银梅译,《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毕波的《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期)提供了粟特文古信札的汉译版。马小鹤《摩尼教“五种大”新考》(《史林》2009年第3期)据粟特文文书Ml78对摩尼教教义作了研究。《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收录的马小鹤《粟特文“tinpi”(肉身)考》(中华书局2005年)对新发现的发现的三件粟特文作了研究。上述成果为中国学者研究粟特文文献和译述国外学者粟特研究论著的代表性成果。
(三)于阗文及其文献研究
于阗文是古代于阗塞种人使用的文字,又称于阗塞文。于阗文是继佉卢文之后,在于阗一带流行于5-10世纪的文字系统。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语言。于阗文文献以佛经居多,也有少量社会经济文书、官方文书等。英国学者贝利研究于阗文堪为集大成者,其著《于阗文文献》《于阗文佛教文献》《于阗文字典》为代表性成果。
中国学者的典型成果有林梅村的《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段晴的《于阗佛教古卷》(中西书局2013年)是对于阗语、梵语原始写卷,结合汉文文献,进行文本分析的新成果。段晴、张志清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中西书局2013年)整理、诠释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来自新疆和田的梵文、佉卢文文书。段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中西书局2015年)对国图所藏西域文书中部分于阗语卷的释读与研究,主要内容涵盖了国图所藏于阗语典籍、案牍等,反映了古代于阗国的社会、生活等多角度的情况,是目前中国学者整理翻译研究于阗文文献的典型成果。
(四)佉卢文及其文献研究
佉卢文是梵文Kharos.t.hi一词的简称,全称“佉卢虱底文”,又名“佉卢书”“佉楼书”,该名出于古代佛经译本,意为“驴唇”,故有时也称“驴唇文”。“佉卢文”仅作为一种文字符号,而用这种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佉卢语”。新疆发现的佉卢文资料大约为东汉时期的居多。新疆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约700余件佉卢文文书,内容涉及社会文化诸方面。佉卢文书载体类型多样,大多为古鄯善国的文献。
1965年王广智译出巴罗(T.Burrow)著的《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 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所1965年)。中国境内发现的佉卢文文书的全面汉译和研究首推林梅村所著《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该书根据文书的年代、形式和内容重新做出细致的分类,找出其间的联系,与不同地点出土文书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尼雅绿洲的社会生活实况,为尼雅佉卢文书研究的起点。
林梅村对佉卢文钱币、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的成果有:《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再论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述论》(《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汉佉二体钱铭文解诂》(《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1988年第8期),《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洛阳所出东汉佉卢文井阑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合刊),《新疆营盘古墓出土的一封佉卢文书信》(《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尼雅南城外96A07房址出土佉卢文》(《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佉卢文书译文》[8](P263-282),《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的流散与收藏》(《考古》1992年第1期),《新疆佉卢文书释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新疆佉卢文书的语言》(《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新发现的几件佉卢文书》(《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此外,还有段晴、才洛太的《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中西书局2016年)。上述的论著为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佉卢文文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五、南岛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中国的南岛语诸族群主要分布在台湾岛上,历史上这些族群都没有创制文字系统,自然没有文献传统,大抵视为无文字社会的典型。17世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统治台湾时期,即明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八年(1662)⑩,荷兰神职人员为了配合殖民者推行政务,管理台湾土著社区,兼传教为目的,教导现今台南新市乡一带的原住民西拉雅族群所在的社区新港社,教当地西拉雅族群民众用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作为书写、阅读、学习新港语的文字符号,传教士利用拉丁字母编纂原住民语的字典,开启了使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书写新港语的新传统。
1630年新港社原住民集体接受基督教信仰。1636年,荷兰人在新港社开办了第一所传教性质的学校,同时教授西拉雅族群信众用拉丁字母书写西拉雅语言。由此开始了用新港社区西拉雅语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传教士和社区民众除了用拉丁字母转写、书写口语外,也编辑了拉丁字母书写的西拉雅语言基督教教义问答、祈祷文等作为教材。顺次编辑了各种字典、教义书,如新港语的《马太福音》《虎尾垄语词典》等,成为后来语言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的书面文献依据。
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总督揆一向郑成功缴械投降,荷兰人于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荷兰人统治台湾38年,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统治烙印。仅以新港文书为例,现存最早新港文书的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最晚的是清嘉庆十八年(1813),距荷兰人离开台湾已有150年了,也就是说,荷兰投降退出台湾后,新港等社仍继续使用荷兰人所创制的拉丁字母书写系统来书写土著族群语言的契约文书。
明清易代,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地方流官为了便于地方行政和征收赋税的需要,依旧允许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社会经济文书,1813年新港文书堪为明证。这些用以书写西拉雅等族群语言的书写符号记录土著族群社会的社会经济文书和社会历史文书,被后人称之为“新港文”或“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其内容主要涉及原住民与汉人因土地关系订定的土地租借、买卖与借贷等方面的契约文书,民间的俗称“番仔契”或“番字契”,现今统称为“新港文书”。从现存的新港文书所使用语言和文字符号的类型来看,既有用拉丁字母拼音字书写的新港语单语文书,也有用汉字与拉丁字母拼音字对照书写的双语文书。
自然灾害救助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等特点以及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等现状使得我国承担巨灾损失的主要力量是政府。灾害发生后,我国灾害救助主要采取中央财政拨款无偿救济灾民的模式,根据具体的受灾情况由国家财政对灾区的损失进行相应的补偿。但是,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比重偏低(见表1),难以有效补偿灾害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另外,此类行为是一种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来实施救助的行为,强调的是社会公平,难以实现较高的补偿效率,单一的政府救灾体制机制不能满足灾害损失后受灾体可持续发展的需要[1]。
现今存世的新港文书,是19世纪台湾开港后,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以及日治时期日本学者等陆续采集而得的文献资料。1928年,今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在台北正式成立,设有“语言学研究室”。属于该研究室的日本学者小川尚义也在台南新港社一带采集这批“新港文书”。1931年由村上直次郎将这些古文书编纂译注出版,书名称为《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台北捷幼出版社1995年),该书收录了109件的“番仔契”,其中有87件为新港社(新港文书),包括21件的汉番对照;另外有卓猴社有3件(卓猴文书)、麻豆社16件(麻豆文书)、大武垄社1件(大武垅文书)、下淡水社1件(下淡水文书)、茄藤社1件(茄藤文书)。关于这批社会文书所属的确切年代,最早的一件是1683年的麻豆文书,最晚的一件是第21号新港文书,年代是1813年,贯穿17-19世纪台湾历史。
20世纪初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村上直次郎整理时以新港社契字最多,统称为新港文书。“新港文书”堪称台湾最早出现的非汉字文字符号系统,也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系统。“新港文书”也是西洋人在台湾岛首次传教的文献证据。现存的新港文书有140多件左右,是研究台湾土著族群文化、台湾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鉴于语言学者在20世纪初叶采集台湾土著民族语言材料时土著民语言已经处在濒危中,1930年代日治时期,新港社区的西拉雅语逐渐失去使用功能后失传,目前能识读新港文书的学者甚少。
1945年后迄今,有关的论著主要有村上直次郎编《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李壬癸的《新发现十五件新港文书的初步解读》(《台湾史研究》,2002年第9期),陈秋坤的《大岗山地区古契约文书的历史意义》[9],翁佳音、吴国圣《新港文书典契的解读与格式》[10]等。典型的专著有李壬癸《新港文书研究》(《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39,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10年)。
六、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七十年的成就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研究工作,注重对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范围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搜集到了大量各民族古文字文献,无论是文字文献的类型还是数量都有超乎以往的发现和收获,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的学者。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止或倒退状态外,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保护都处于平稳的发展进程。
由国家民委领导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进展顺利。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修复保护有专门的依托部门和机构,为民族文献的修复保护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从中央到各省市古籍保护领导机构健全,各有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密切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得以确立。国家专门出台相关政策并加大经费投入,已经精准摸清从全国各级收藏机构收藏的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类型和数量以及保护现状的家底。
少数民族古籍善本再造工程,分多个批次覆盖各民族古文字文献,十分有利于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研究保护传承。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不断趋于合理,涌现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大家,如季羡林、王静如、冯家昇、傅懋勣、马学良、耿世民、王尧、巴桑旺堆、东嘎·洛桑赤列、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张公瑾、李范文、史金波、雅森·吾守尔、刘凤翥、清格尔泰、金启孮、亦邻真、照那斯图、道布、蔡美彪等堪为各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其中耿世民先生获德国洪堡基金会颁发的《国际知名学者奖》及世界阿尔泰学界最高奖项PLAC金奖,季羡林获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王静如、李范文先后获得法国儒莲奖。
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不断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1、《中国西藏元代官方档案》(2013)其中4份圣旨是八思巴文官方档案原件。2、纳西东巴古籍文献(2003)涉及海内外收藏的三万余册纳西东巴经典。3、清代内阁秘本档中一组24件全满文有关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文献(1999)。2008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确定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各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翻译、整理、研究有条不紊得以开展;民族古文字文献方面的数字化和国际编码、中华字库等也在积极推进中。
2011年中国社科院设立十五项绝学及其负责人,绝学项目涉及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文种和负责人为:西夏文(史金波)、八思巴字(照那斯图)、契丹文字(刘凤翥)、女真文(孙伯君)、纳西东巴文(木仕华)、古藏文(东主才让)。国家社科基金开始设置绝学研究的资助项目,成为21世纪初的新发展趋势。
民族古文字文献整理研究现状十分喜人。需要进一步对已经刊布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开展系统细致的校勘、释义、注译、版本比较等研究,以数字化的技术,及时建立民族古文字文献文本及语音视频数据库,为民族古文字文献保护研究提供原始权威的基础资料,推动学术资料利用方式和研究手段的更新。海外收藏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回归成为最近十年的最重要的内容,涉及古藏文文献、西夏文献、纳西东巴经典、敦煌文献等中外合作顺次展开。国际合作超乎以往任何时代。另外,鉴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与丝绸之路历史有关的境外文字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研究和释读也得到空前的重视。
总之,70年的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均有进展,尤其是藏文文献、西夏文文献、黑水城多民族文字文献、蒙古文文献、突厥语族文献、印欧语系文献、纳西东巴文等文种及其文献研究依旧保持了上扬的趋势,论著作数量繁多。此外,佉卢文文献研究、粟特文文献、吐火罗文献、于阗文文献成为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而成为新的热点和亮点。“新清史”的热络使满文文献研究得到重视。相较而言,南方有文字文献传统的彝文文献、水书文献等则注重于探讨数字化、输入规范、文献刊布、保护策略等较多,对文字文献的本体研究较少。从整体的学术水准而言,印欧语系文字文献研究、藏文文献研究、突厥文献的研究水平,国际化程度较高,研究精深、范式严谨,古今中外相融一体,已经实现了中外学界的对接。西夏文献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草书文献的释读和佛教经典的对译和对勘研究,作者队伍随着文献刊布数量的增加而壮大。相对而言,南方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则有较大的局限性,语文学意义的研究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对国外学界的研究进展关注较少,研究范式尚未实现规范化。有的文字文献虽然研究论著众多,但研究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方法论都有待完善,大都以模仿汉文文献的研究范式为主,远未形成切合具体文字文献的研究译注范式。
70年来,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对学术研究的进步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其间所阐发的多元多学科的价值也必将在全新的视野中得到深入的体现。结合“一带一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方法,无论是以往研究过的古代民族文字文献,还是新近发现的民族文字文献材料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知识生产更新、学术进步不可偏废的重要研究领域,系统全面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各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事业任重道远,前途未可限量。
[注释]
①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有维吾尔文版(3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1984年;汉文版:3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乌兹别克文、土耳其文。
②此外,蒙古国学者D·Tumurtogoo的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s(XIII-XVI Centuries),2006年,台北刊行,也是这一时期回鹘式蒙古文文献集成的重要代表。
③其中十一件属金代、一件属明代。
④本节契丹文及其研究史分期、代表型学者及其著作的回顾主要参考了清格尔泰等著《契丹小字再研究》第一章概述部分,特此说明。
⑤中国塔吉克族的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塔吉克族是中国唯一使用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但文字普遍使用维吾尔文字。
⑥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又收入季羡林的《季羡林文集》第2卷《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收入季羡林的《季羡林文集》第2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⑦除了张广达、耿世民的《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考证汉文“唆里迷”和回鹘文Sulmi/Solmi都指“焉耆”时,曾介绍了吐火罗语命名的争论并有所贡献外,几无进步。
⑧《中德学志》1943年第5卷第1、2期合刊。王静如还发表过有关吐火罗语文文献的论文:“Arsi and Yan-Chi,Tokhri and Yüeh-Shih”,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9),1944年)《重论ārsi,ārgi与焉夷、焉耆》(《史学集刊》第五辑,1947年),另为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撰写过《〈吐火罗语考〉序》(中华书局1957年)。
⑨但季羡林终其一生,就一直用“吐火罗语”一词指称这两种语言,参见季羡林所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吐火罗语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90页。
⑩这段时间恰恰为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的生卒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