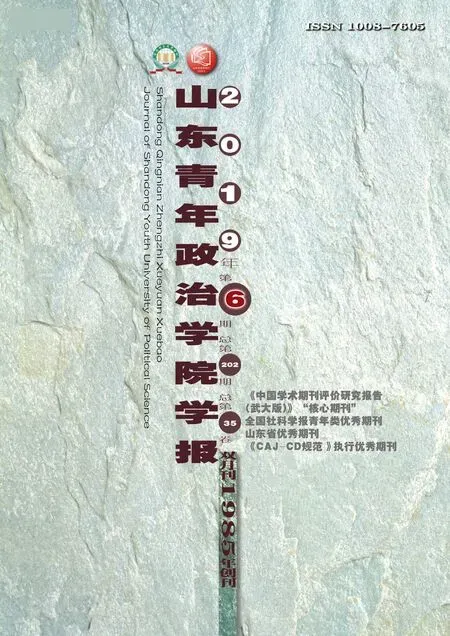创意写作学视域下创作方法论问题研究
葛红兵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创意写作学到底应该研究些什么问题?这并不是没有歧义的。以创意还是以写作为根本研究对象?以人的创造性实现为言说核心的写作学还是以写作为言说核心的创意学?这些问题依然需要学术界不断地通过研究加以阐明。判定学科对象的终极依据是它的实践及实践的实现形式,创作是创意写作学指认的根本对象创意实践的实现形式,创意写作学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都要落实到创作方法论上,不同的文学本体观和研究进路会带来不同的创作方法论,创意写作学和传统写作学在这一问题上是有不同的思考的。网络小说诞生以来,当代小说的主流样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等新小说创作方法下诞生的一系列小说类型已经成了小说创作的主导形式,当代文艺理论面对这种状况是失语的,网络小说已经诞生了其经典作品,但我们尚没有一种理论能解释这些作品,创意写作学的诞生,为培养这些作家提供了高校教育教学模式,同时也能为这些作家的创作提供理论阐释,创意写作学理论的丰富性让我们可以从其创意本体论出发提出创作方法论、批评论等一系列理论模型,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小说创作新现象。
一
在创意写作学看来,创作主体是通过创意实践来实现自我为创作者的。事实上,对于创意于人作为美学实践主体的意义,创意写作学有更为根本的看法,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创意是人作为主体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人作为审美主体的活动也自然于此自我认知统一,人只有把自己领受为创意者时,他才可能真正领受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其为基本原则来追求其主体性的自我完成,写作由此被理解为主体对其创意本质的一种领受和实现活动,一种被本质地包含于主体生命的内在实践。
由是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将写作学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写作活动现象描述为基础的现象写作学阶段,此时,写作尚未被本体性地从生产劳动活动中区别出来,它常常被当作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或者其副产品来加以认识;第二阶段,以写作活动的艺术性分析为基础的实践写作学阶段,这时写作被当作有别于生产劳动的精神活动。但是,此时这种区分依然是非常原始的,生产性文本活动和欣赏性文本活动并未得到严格区分,写作活动的精神性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技艺”;第三阶段,创意写作学阶段,写作被当作一种创意性活动,一种本质于人的生命主体的实践活动,对它的内在意识性的认识上升到了这样一种层面:它被用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根据和本质是什么?”
巴门尼德作为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认识到“思维”对于世界本质意义的哲学家,他说:“能被思维者和存在者是同一的”[1],他深刻地指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巴门尼德这里,思维是同时作为理性精神实践和感性精神实践而存在的,这种对于思维认识的浑然性,一方面显示了其原始精神哲学的古希腊朴素哲学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后”精神哲学的先见意蕴——他以人的精神性思维活动为依据直接断言了人的本质,当这种认识,由其同时代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从另一种角度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时,我们则更能理解这种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思维的先在性和本体性的指认。具体阐述创意思维在人的思维体系中的位置和分量,并非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实际上是反对把思维和对象二分进而又把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二分的,这会让我们堕入精神哲学和实践哲学都不能避免的形而上学窠臼。本文在此试图重点阐明的是,我们可以由此得到我们对创意实践的第一个层面的认识:人的创意活动与世界也是同一的,或者,我们可以进而言之,人的创意思维的内在性勾带出、勾带着并进而同一于世界的外在性[2]。这一点实际上很早就由巴门尼德和普罗泰戈拉等在古希腊时期阐明,尽管它们是原始哲学性的论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们的奠基意义,回到古希腊源头,体验其思想的当代性甚至未来性,常常是思想者最愉悦的而又能获得最大启发的事体。
拥有了上述认识,可以说,我们对创意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认识起点,但是,这仍旧是不够的。进一步的认识是,人在上述过程中让世界人化,人是因此而生活在人化的世界中,其结果是什么呢?是人本身也在“人化”着,我们要说的是,创意不仅仅与世界的外在性同一,也在不断地反向锻造着主体自身。就这一点而言,笛卡尔甚至这样认为:“由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实体的全部本质或者本性是思想,它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需要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不存在,心灵也不失其为心灵。”[3]在笛卡尔看来,人本质上是非物质性的思维体。让我们再来看看尼采的论断,尼采的论断更为直接,尼采说:“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换言之,在尼采看来,肉体先就是创造性的,之后,它才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并与创造性精神同一。[4]所以,人“不是一个坐在这世界舞台前的看客,相反,‘我'被卷入作用和反作用中。”“在愉悦和痛苦中、在恐惧和希望中、在无法移易的痛苦和不安的重负中、在出人意料地降临的狂喜中所经验到的、在我们之内并围绕着我们的活生生的力量”[5]。我们可以沿着哲学史上那些巨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线来对此进行继续梳理,如果说,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还是需要一个“上帝”来弥合的话,那么,到柏格森这里,思维的绵延性就变成了不需要上帝在场的“生命冲动”,“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存在就是变化,变化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无限的自我创造”。[6]
“创意”对于人来说是本体意义上的,它包含了两个本体论意义层面:人是创造性地思维着的,人是思维着的创造者。以此为本体论视域,创意写作学能看到什么呢?
二
人是创造性地思维着的。对于创意写作者而言,创造性地思维着,最重要的方面,表现为对世界的时间先后关系的把握,我们能够在思维中把握世界的先后秩序,什么是在先的,什么是在后的,我们用它来结构生活的先后链条,这种结构能力并不是机械的,而是创造性的。创意写作者是用因果结构来理解先后关系的,如果不能理解这种先后次序的事理逻辑关联、情感逻辑关联,我们实际上就不能对之进行再现,我们在思维中对世界的事件的连续性再现,是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和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创造性地思维着,意味着,我们理解这个链条的各种意义,首先是对事件先后作出事理逻辑因果的解释,“巫师”念咒在先,“下雨”在后,常常这种事件的先后要被赋予逻辑上的因果——巫师念咒导致下雨——来加以理解和阐释,所有的这种再现都要或多或少地基于这种从时间先后到事理因果的转化;其次,创意写作者还常常深入到情感逻辑之中,对之作情感逻辑的演绎,“妈妈叫我去医院看病”,“我去看病”,在这个先后次序的事件序列里,创意写作者的阐释多数是基于情感逻辑的“妈妈爱我/我爱妈妈”,这种情感逻辑解释了上述先后事件的合理性;最后,作为创造性地思维着的“创意”,它还不仅仅是基于解释的需求,还基于创造自我对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甚至在思维中让世界整体性显身的要求,创造者创造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模式并让“世界”在其中“诞生”,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世界观。
创意写作者用他的笔创造“世界”,伟大的创意写作者不是零零碎碎地创造世界的破碎图景,而是要创造出世界的完整拼图,这个拼图由表面的事件先后序列组成,但是,本质上却是对世界整体的“精神”意义上的再现,它展示的是创意写作者的“世界观”,它不是简单地是其所是地看世界,而是让自己作为创造者显身于世界中,让世界创意化,成为他的世界,进而整体性地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图景。由此,我们得到了创意写作学对于创意的三个维度的认识:它的基础维度是再现,这种再现是在创意写作者对外部世界的事件序列的把握中形成的,它的较高的维度是对事理逻辑和情感逻辑的创造,它创造了事件系列的意义图景,而在最高的维度,这种创意则是“世界观”,它创造了世界的意义,并让主体成为显身于意义中的创造性地思维着的“创造者”。
人是思维着的创造者。对于创意写作者而言,创作者脱胎于本体创造者这个事实是通过这样的工作而表现出来的,他用他的笔创作作品——他从事的是直接的精神创造工作,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认证自己为“世内创造者”,这是我们以往的文艺学和创作方法论遮蔽的一个事实,而这一事件恰恰是最关键的。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说人是一个主观的反映者或者说一个客观的反映者,这些都是对的,人是主客观统一的反映者,但这一一般原理运用于创意写作学,却需要更加深入的中介概念,无疑,创意是责无旁贷的也是唯一可以承担这一功能的概念。回到本文的话题,创意,在这里,作为方法,它有其特殊性吗?或者说,这种创作创造有其特殊规律吗?李泽厚认为是有的,他的根据来源于心理学,他说,“巴普洛夫曾根据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相互关系中的不同特点,把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分为三种类型:艺术型、分析型和中间型”,“艺术型的人在思维过程中,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占较突出的地位。”,他说,“这些人善于想象”,实际的意思,这里的“想象”一词我们可以把它和“创意”等同,这些人更加善于“创意创造”[7],这种创意思维的特性是什么呢?李泽厚借用伊凡诺夫的观点,讲道,“艺术的实质恰恰可以规定为这样一种认识形式:从现实现象的具体感性面貌中再现现实的现象。”[8]笔者并不同意李泽厚把文艺认识事物的方式和科学思维对立起来并命名为形象思维的看法,当巴普洛夫说,多数人的思维是中间型的时,实际上就已经宣布了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区分高级神经活动为三种类型是难的或者说区分艺术型和分析型是难的,笔者也的确认为,将这种思维命名为形象思维,进而把它和逻辑思维并列为“都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人的认识的理性阶段”[9]是不恰当的,它看起来是抬高了创意思维,实际上是贬低了和取消了创意思维,取消了创意思维在创意写作学中的本体论地位,所谓形象思维是用形象而不是用概念来思维的,认为作家在创意创作思维的过程中永远是不离开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的,是不进行概念的抽象和概括的,等等,这些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没有心理学证据的假说。一切都还要回归到更加本源的“人是思维着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论断上来:创作实践是本然于人是思维着的创造者这一人的本体论实践的,如果说,它有什么基于创意创作的特性,那么,这种特性正是这种“本然性”,创意创作活动,人的创意写作活动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创造活动,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创意写作活动对于人的创造性本质来说更加本然的了,创意写作要在这种人的本性的自由实现的层面呈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就方法论而言,也要在这个维度上展开自己的讨论。
三
现在,我们来讨论创意写作学的创作方法论问题可能会有更多新的看法。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以人的创意实践为基础,而不是直接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来讨论创作问题,这是创意写作学视域对文艺学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不仅仅表现在对文学本体论的探讨上,单单抽象地讨论创意本体论文学观是不够的,创意本体论文学观必须落实在作家论、读者论、创作论、接受论、批评论、文学史论、文学产业论等方方面面,而其中,最核心的无疑是创作论。
从创意本体论出发,创作实践乃是人的创造性实践也即世界人化实践的内部问题,创作创造在这里并不直接和客体世界接壤,它根源于人的创造性本体而终止于这种创造性本体勾画出来的“作品”世界。因此,它是一种与生产实践很不一样的精神“虚践”。在此,我们可以对创意虚践作一个限定:在其内部过程上,它是知、情、意的国度,它是对世界的事理逻辑的表现以及对这种逻辑的情感的、世界观(信仰)层面的赋意,这当然就是个体的、主观精神的,在其外在的层面,它是对个体共同体所构成的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领受,它让创作者体验到客观精神,这是一种个体主观精神的外化,具有客观性。但是,显然,它跟我们过去强调的客观世界的客观性不一样,它依然居于个体的精神虚践之内。
创意本体论的文学创作方法论,也因此,尽管它在本质上是反映世界的因而具有“符合”“真实”的秉性,但是,正如杜夫海纳所说:“表现的真实性之所以不以再现的准确性为尺度,就是因为表现并不揭示科学所认识的那种客观化的宇宙,而是主体性所感受到的一个世界的真理。它所说的是一个为了人的世界,一个从内部看到的世界,那种不能复制的世界……一个内心经验过的世界,一个只有情感才能使我们进入的不可模仿的世界。”[10]它的真实性不是外在写实性,而是表现论的创意创作主体内心体验的世界的真实性,一种符合创造者内在精神要求的更深刻、更直观地把人的灵魂的永恒本质也即创意地思维着的创造者的本质揭示出来的真实。他凭借主观精神进行内心体验,并将这种体验的结果化为一种激情,他舍弃细枝末节的真实性,追求深层“幻象”构成世界创意内在性,除了内在的创意激情,他不想受到任何外部束缚,也不想受制于任何他者,创意创作方法论的核心依据是且仅仅是:他是思维着的创造者和创造着的思维者。这种创意本体论的文学创作在方法论上不受“真实”的左右,也不受客观世界“善”的伦理学左右,就如爱尔维修所说,“这些感情固然应当被当作无穷错误的种子,却也是我们文化的源泉。虽然它们使我们陷入迷惘,却只有它们才能给予我们前进的必要力量,只有它们才能使我们摆脱那种随时准备拖住我们灵魂的全部能力的惯性和惰性”[11],如果它一定要遵循一种善,那么它遵循的唯一善的根据来自其自体[12]。
创意本体论的创作方法不是按照世界的是其所是来临摹,也不是按照世界的可能形象来想象,而是按照创造思维着的主体的内在创意原则来创造世界。例如,穿越小说,一个当代人可以带着他的当代物理学和化学知识穿越到古代去,它可能是不可理解的可能是荒诞的。例如,异大陆小说,它把自己完全假设在一个非现实的反人类经验的异世界里,它可能是神话性的。此外,修真小说,一个人可以通过修炼一步步达到仙的非人境界……这些都会被作家创意出来,这种创意如果说,它一定有什么原则,那么,文学的历史性比较原则也许可以说是其一,它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学表现要素,人物图谱、情节图谱、社会历史背景图谱,等等,进行细致的分析,进而进行综合的创新设计,它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落入这些窠臼,它对自己的世界观和情感状态进行深刻的反省,深怕自己成为一个人云亦云者……。要知道,创意创作论的核心是主体的创造性生成,除此别无其他。
正如索尔尼仁琴所言:“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13]当代文学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滋养呢?以一种精神的高蹈来倾听内心的风暴,以一种赎罪的感情来领受创造者的使命,以一种受难的信仰来迎接牺牲的洗礼,它是人类的心灵之眼,拒绝沉溺于细碎的描摹,它是大地的流泪之泉,拒绝接受物质的诱惑,它以创造者自居,高举创意之火,寻求作为创意创造者的自我完成,它在一个物化的世界里寻求精神自由为文学的苏醒呼号。这一切都需要某种理论先行,一种有勇气的理论,一种无限拥抱人的创造者本体的理论。
创意写作学的诞生在中国经历了从少数几所高校的实验性尝试到数百所高校的教改实践,它在质疑中前行,不断践行着自己培养作家和培育作品的使命,它是一场浩浩荡荡的高教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种理论视域的革命性创新,它曾经在高校教改过程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它也一定会在理论创新中展现其理论话语的革新力量。
——《当代写作学40年(1980—2020)》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