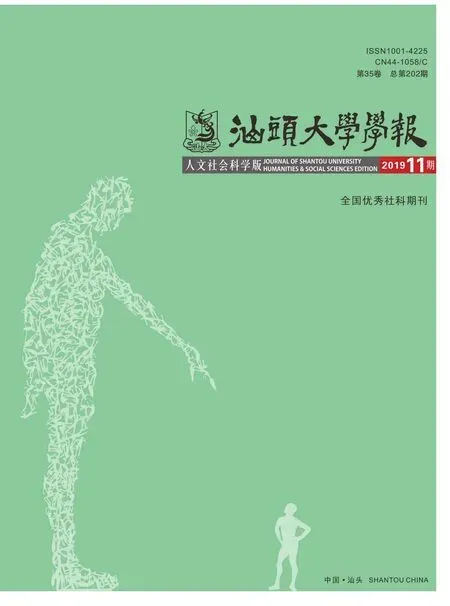在“补残”与“出世”之间
——论《老残游记》一集与二集的对话关系
谢博远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夏志清先生称《老残游记》为“中国的第一本政治小说”。[1]447的确,《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的官场文化批判,以及浸透着家国忧思的民间疾苦书写,都是考察晚清政治社会的独特文学景观,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然而,对刘鹗写作于1907年的续作《老残游记·二集》①《老残游记》共20 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 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1907 年,刘鹗开始创作《老残游记·二集》(共9 回)。下文将《老残游记·一集》简称为《一集》,将《老残游记·二集》简称为《二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不够充分。综合以往研究来看,针对《一集》的研究大多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解读,对《二集》的研究则多从禅理哲学着眼。两头入手,各自侧重。而笔者认为,将二者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解读,研究两个文本之间的潜在关系,有利于我们理解作者的思想和心态转变及其背后成因。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尚较缺乏。
综合两个文本来看,《一集》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游医老残的游历见闻,刻画了一幅官场黑暗,民不聊生的末世帝国“浮世绘”;《二集》讲述了老残和友人德慧生于山间小庙邂逅尼姑逸云并与其谈佛论禅的故事,最后以老残游历阴曹地府,并飞升“极乐世界”而告终。诚然,《一集》多写社会百态,《二集》则颇涉佛理禅道;前者的叙事场景囊括江湖市井,后者则聚焦于寺庙与阴曹;前者之老残摇铃救世,欲以己身补缀残局,后者之老残谈佛论禅,欲求自身之超脱自在。两者颇为迥异,似乎存在着一种思想的断裂。而笔者认为,《一集》和《二集》之间视域的切换,主人翁老残心态的转变,以及两者思想的异质,实质上正是围绕着如何在“千年变局”和“末世残局”的时代语境中调适自我而展开的一场对话。
一、身世与家国——明清小说中个体生命与群体秩序的“对话背景”
有学者认为,从《三国演义》的朝堂和沙场,到《西游记》《水浒传》的道路和战场,再到《金瓶梅》《红楼梦》的闺阁和花园,明清小说的题材呈现出时空关系逐渐“私人化”的微妙历程。[2]49笔者认为,在明清小说题材“私人化”的演化表层中,实质不断涌现着一股身世与家国之间,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群体秩序的维护之间的微妙张力:《三国演义》赞赏忠君爱民,家国为重的德性,崇尚开疆拓土,沙场鏖兵的功业,却也在水镜庄的闲适,卧龙岗的平淡,玉泉山的超脱中生发出一种对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的思考,更对儒家正统伦理在历史现实中的惨淡结局表示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悲幻感;《水浒传》描绘一百零八好汉张扬反叛的生命力,却又安排了好汉们在宋江“忠君报国”儒家正统伦理的指引下,被葬送在昏君奸臣手里的悲惨结局——最终葬送忠义的,恰是效忠的对象,这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巨大荒谬,也生成了一种对正统伦理的强烈批判力。当封妻荫子的美梦翻成泡影,而再入空门的鲁智深和急流勇退的燕青等在个体生命的完满中实现超脱时,不禁使人感到“热肠愤气一时俱消,并英雄忠义等字都应扫却”;《西游记》描绘孙悟空张扬凌厉的生命力,叙写他与代表正统伦理的天庭的激烈对决,也表现了个体生命无限止扩展的欲望被克服的过程——在“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取经路上通过克服心魔,最终使心猿归正,心境安宁。它既是对生命力量的热情礼赞,又是对个体欲望的可贵超越;《金瓶梅》通过揭露晚明道德败坏,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个人私欲无休止扩张时出现的道德决堤和社会在颠覆正统伦理、张扬生命个性之时出现的巨大思想混乱;《红楼梦》则极写一种超拔流俗,睥睨伦常,纯美高贵的生命美学,建构起一个与正统伦理相对立的“有情世界”。在这些身世与家国,群体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对话中,个体生命意识逐渐凸显——在《红楼梦》中,一种顺适个体生命自由,强调个体意志和人格独立,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达到了最强音。
《老残游记》延续了这种对话,却又在晚清末世残局的特定环境下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小说家的思考——清朝刚刚遭受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洗劫,维新无望,千年变局已至,国家和民族正值危急存亡之秋。文变染乎世情,沉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使得一代文人从个人情感的缠绵中挣脱出来,开始了沉重而深刻的社会书写。于是我们看到,在《一集》中,以往那股执着而耀眼,炽热而真诚的个体生命意识收敛了光芒,而又重新镀上了一股家国情怀的色彩。在“棋局已残,吾人将老”的身世家国书写中,他时时以老残的主体感受映照晚清社会的千姿百态,“棋局已残”,观棋者也是一种“吾人将老”的心态。其实此时的刘鹗不过四十左右,篇中的“老残”也只三十多岁,只是时局的颓废,维新救国理想的凋零,使他已有将老之感。《老残游记》开篇便“哭”:“棋局已残,吾人已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这哭中有“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3]6老残的哭,是一种将个体生命体验熔铸于家国忧患的悲怆。“吾人将老”的漂泊伶仃、老而无依和“棋局已残”的末世悲叹无比沉重地交织在老残的旅程之中。
在中国传统士人强调个体依附于群体的儒家伦理体系内,群体秩序的崩溃会直接导致个体价值的丧失,造成人生的极大痛苦和不自由。《二集》正是在为这样的痛苦束缚寻求一种解脱之道,它避开了《一集》惨痛的社会书写,淡化了沉重的家国忧患,反而时时于谈佛论禅之中显露出“破除执念”的佛理智慧,旨在引导个体生命走向心灵的超脱与自由。正是晚清社会的剧烈流变使得《二集》中的老残试图抛开家国的羁绊,隐遁于荒山小庙,游历于阴曹地府,上升至极乐世界,最后达成了个体生命的超脱。从“补残”到“出世”,《老残游记》无疑潜藏着一种群体秩序和个体生命自由之间的对话关系。
二、从国民到隐士——老残心态的转变
(一)《一集》中的老残形象
老残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独特的文人形象:一方面,他心怀“补残”的志向,意欲以毕生之所学,补天下之残,补棋局之残。他不是迂腐的道学先生,他颇通治水之道,也有着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一集》第一回中他治好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奇病,而后者正是水患严重的黄河的象征。在游历江湖的过程中,他眼见玉贤、刚弼等酷吏刚愎自用、草菅人命,不由得怒发冲冠,“恨不得将其杀掉,放出心头之恨”。之后更是为桩桩冤假错案四处奔走,力求还原真相,为冤民洗脱冤屈。一次,他眼见北斗,便起岁月流逝,国家忧患,百事俱废之叹——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3]47就连在梦中,他眼见大船将覆(象征岌岌可危的满清朝),也不顾个人身家性命,欲以向盘,纪限仪等西洋科学,救助朝廷和苍生。在《老残游记自评》中,刘鹗评道——正是因为“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1]74,故而老残只能“摇串铃先醒其睡”。在老残身上,无疑有着中国传统文人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担当和责任感。
而另一方面,他又跳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人的传统轨迹。在老残身上,我们感觉到,他跟中国典型仕人代表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他对官场的边缘心态。他不但不肯做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官场的失望。张官保爱惜其才,想举荐他做官,他连夜遁走。在第六回申东造劝说他做官的时候,他反诘道,“难道做官就有济于世道了吗?”并提出了“有才之人做官为害更甚”的颠覆性观点,认为有济世之才者难免陷于“急于做大官”的功利心理,所以为政绩哪怕伤天害理之事也要做,故而“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在老残看来,进入官场反而实现不了他“补残”的志愿,却会堕落成荼毒百姓的恶官。他对权力和官场有着明显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他不肯进入所谓正统的权力中心,而只愿充当一个“游者”,游走于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以“若即若离”的姿态为民奔波,为民请命,实现心中“补残”的意愿。
总的来说,老残胸怀家国,心忧民众,为冤民四处奔走,只身闯公堂,虽身系游医,但却有那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者的影子。他有着强烈的“大我”意识,有着“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老残是一个“民”而非“仕”,他始终自觉地保持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作为具有家国意识的知识分子,《一集》中的老残其实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现代“国民”的特质。
(二)《二集》中的老残形象
《二集》与《一集》的叙事场景明显不同,它首先对《一集》老残的视域作了缩窄性的转换,将《一集》囊括江湖市井的社会广角切换成寺庙和“地狱”(这两个场所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一集》二十四回老残的足迹遍布济南城、曹州府、东昌府、齐东县等地点,而《二集》的九回名义为游泰山,实质上将叙述重点放在逸云顿悟和老残游历地狱的描述上。如此,人之“游”由此变成了心之“游”。摇铃补残,江湖行义的入世故事由此变成了内心的自省、修炼、顿悟和解脱的心路历程。
在《一集》中,老残看到的是国势颓危,酷吏专横,民生疾苦;在《二集》中,老残对国事避而不谈,却对禅义佛理颇有见解。在第一回中,当好友德慧生为日本觊觎东三省,大敌当前而朝贵却毫不关心而愤然时,老残也只是“点头会意”,并不多作评论,这与《一集》中那个为酷吏残害百姓而咬牙切齿,眼见北斗便起家国兴亡之叹的老残相比,心态上是何其迥异。紧接着,老残和德慧生的话题过渡到了三教义理。当老残“只要虚心静气,自然会有看到地狱的一天”的话在篇末得到验证,老残果然得以游历地狱,飞升大道时,这仿佛是一篇只谈心性,无关家国的隐士文字。
其实,从《二集》的开篇便可看出,这里的感情基调已由《一集》的“身世家国之感情”转换为“人生如梦”的空幻与悲叹:
若百年后之我,且不知其归于何所,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更无叙述此情境之我而叙述之矣。是以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3]166
哀此生之须臾,觉人生之空幻,“人生如梦”的感情书写其实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母题。当文人骚客以宇宙之恒常朗照有限之个体之时,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悲幻和渴望超越个体限度的焦虑油然而生。《红楼梦》中,当贾宝玉听完黛玉悲吟葬花词之后,联想到诸姐妹和自身终会有“无可寻觅之时”,感叹唯有“逃大造,出尘网”,方可“解释这段悲伤”。《二集》中的老残,也正是在那种末世乱局的剧烈流变中感悟到人生如梦,一切都是瞬息而逝,“必随风驰云卷、雷奔电激以去”。这种虚无和悲幻使得个体不得不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诉诸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安顿。这种寄托和安顿,便是《二集》中俯拾皆是的关乎破除执着,获得内心安宁的佛理,是篇末那个承载着美好希望的极乐世界,指向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和超越。
于是我们看到,从《一集》到《二集》,追求“大我”的实现变成了追求“小我”的超脱,心怀补残之志的国民变成了避世悠游的隐士。从《一集》的摇铃行医以醒世救世,到《二集》的谈佛论禅以救心救己,老残无疑在一种末世心态的自我调适中走向了隐遁,并在隐遁中实现了自我的超脱。
三、“大公社会”的政治想象和“自我解脱”的宗教精神——从玙姑和逸云思想的“异质性”谈起
玙姑和逸云分别是《一集》和《二集》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在《老残游记》中,叙事主线始终安排在老残“游者”的视线之内,写的是“眼见之实”。而玙姑在桃花山上的论道和逸云在尼姑庵里的说法却与全文的写实风格迥异,显示出浓厚的哲理思辨性。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上文论及的老残从国民到隐士的心态转变所反映的,正是玙姑和逸云象征的两种处世哲学——一者是作者借玙姑之口,建构的儒家“大公”理想社会模型;一者是通过逸云之“说法”表达的佛家寻求“解脱”的超脱思想。
(一)玙姑的社会理想
《老残游记》对官场弊病的揭露,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官场小说“清官”和“贪官”二元对立的程式化书写。王德威称其“扭转公式化描写,重新塑造读者认知取向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新道德视景”[4]66。这就使得批判的高度上升到制度层面。面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老残直言,有才之人做官危害更大,因为“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官愈大,害愈甚!”更是力揭清官之恶,使人耳目一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3]78在作者看来,诸如玉贤、刚弼等清官之恶,根源也在“贪”,不过赃官贪财贪利,而清官贪名罢了。而清官之名正是使其通往更接近权力中心的最有效的敲门砖。有才之人急于做官,而且急于做大官,也是源于心中一股对名利的贪欲。而所谓的道学正统的最可笑之处,正在于一方面扼杀个人的私欲,另一方面又把为名为利,谋私为己的官员装扮成一群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道德楷模。
然而,《老残游记》是不是反对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呢?在小说的第九回,作者借玙姑之口,表达了其思想立场:
“孔子说:‘好德如好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3]70
由此,可知作者并不否定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认为是汉儒“拘守章句,反遗大旨”,宋儒扼杀人欲,“自欺欺人,不诚极矣”,这才使得孔孟儒学遭到了歪曲。在玙姑看来,人的欲望是真实存在,需要被尊重的。但是“发乎情”之外,还要“止乎礼义”,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
玙姑还认为,三教“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惟儒教公到极处。”在玙姑看来,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大公”,而三教之中又属儒教公到极处,最能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可见,在玙姑看来,尊重个体欲望是前提,但群体秩序的维护,群体价值的实现才是其最终目标。要在尊重个体生命,承认人欲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这就使得《一集》中“公”与“私”之间充满了辩证关系。因为真正的“大公”要在充分承认个体之“私”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否则,只能陷入像宋儒那般“自欺欺人”的境地,并滋生更多的以“公”之名谋私利的官场败类。在被作者赋予了“桃花源”意义的桃花山上,作者建构起这样一个道德乌托邦,它尊重每个人满足自己情欲的权利,但也为每个个体划定了道德准则——要行善、好公。这样的社会也正如第十回中黄龙子和玙姑合奏的那首海水天风曲一样——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3]75
海水天风曲的妙处,正在于各人演奏时各有不同韵律,而却偏能相辅相协,而不是互相干扰,这造就了一种韵律的和谐美妙。“和而不同”是音乐演奏的至高境界,也是社会组织之理想形态的隐喻。和而不同的社会,既强调群体的和谐和秩序,又尊重了个体的差异。
不过,需要明白,尊重个体之“私”的落脚点是要指向“大公”,“和而不同”首先关注到的是整体的和谐,群体秩序的维护才是儒家正统伦理的最终目的。由此可知,《老残游记》并不否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在第一回的梦境里,老残曾明确地指出那艘处于危难之中的大船(隐喻清廷)“驾驶的人并未曾错”,他并不认为是这套儒家伦理体系出了问题。它反而以鲜明的立场,厘清汉儒和宋儒对先秦儒家义理的歪曲,倡导重塑以先秦孔孟时代儒学为典范的儒家伦理体系。它倡导的是在尊重个体生命的前提下,崇尚群体价值的“大公”“和而不同”的理想社会组织形态和伦理价值体系。
(二)逸云的超脱思想
如果说《一集》是在一种身世之感情和家国之感情的沉重交织中建构起一种“人人好公”的理想儒家伦理体系的话,那么《二集》则是在晚清国之将亡,势之必颓的巨大痛苦中避开了《一集》建构的儒家伦理体系的笼罩,力求个体生命的超脱和自由。因为在中国传统士人强调个体依附于群体的儒家伦理体系内,家国的沉沦,群体价值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个体价值的丧失,造成了一种焦虑乃至痛苦。而更大的痛苦在于个体看到了自身的无能为力,国势已颓,无力回天,只能深叹“无才可去补苍天”。
从《一集》玙姑对“大公”社会的推崇到《二集》逸云谈佛论禅,追求解脱,两者构成了一种关乎生命价值的对话:人生短短百年,究竟是将自身的生命体验熔铸于家国安危忧患,依附于群体价值的实现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在有限的生命限度内,超越世俗观念,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超越——知其不可为而求解脱呢?
《二集》无疑选择了后者,在第一回中老残和德慧生的谈话中,已然显示出“名相雅相皆是虚妄,不可执着”的超拔观了。老残认为,把个“俗”字当做毒药,把个“雅”字当做珍宝,实际上不过想借此讨人家的尊敬。这种念头,其实正是大俗的表现。于是德慧生感叹道:“这话也实在说得有理。佛经说人不可以着相,我们总算着了雅相,是要输他一筹哩?”[3]168第五回,作者再次借逸云之口,指出男女之别乃至人相和我相不过是表面上一层虚妄的浮相而已。“《金刚经》云:‘无人相,无我相。’世间万事皆坏在有人相我相”。过往的种种情欲烦恼,不过是于自己女相之一念上生出来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便可清净自在了。[3]197
《二集》在破除对“相”的执念的基础上,更追求一种行云流水,任意东西的超脱和自由。在斗姥宫里,逸云谈及她把自己分作两个人,一个叫住世的逸云,“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一个叫出世的逸云,乐于“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3]199这里的住世之逸云和出世之逸云,又何尝不是住世之老残和出世之老残呢?在逸云看来,拘泥于佛理教规并不是真正超凡入圣的表现,陪酒和搂抱并不能成为她追求佛理的阻碍,只要认真修行便好。甚至环境污浊、尼姑留长发、吃肉边菜、女子被迫失身、男子放诞不羁(如赤龙子)等等,都不妨碍一个人修心成佛。所以作者写逸云,其实也正是在写老残——漂泊江湖,食人间烟火的老残,则不啻为一住世之老残;游离权力,超凡入圣的老残,则直是一出世之老残也。而三教圣人的智慧,日月天地的把戏不再是用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手段,而是个体完成生命价值和愉悦的一种精神寄托。所以我们看到,在《一集》中闪现的那种对群体价值的崇尚和体认在这里已经变为一种超拔的生命意识——破除对“相”的执着,达臻心灵的超脱和自由。用《老残游记》中引佛经的话说,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在这里,“无所住”代表着一种逍遥超脱的状态,代表着一种破孽化痴,消除执念,寻求个体生命解脱的佛教精神。这种“小我”的超脱精神无疑消解了《一集》中那种对“大我”价值的建构和追求。
总之,老残在前后二集中心态的转变,实际上正是玙姑和逸云象征的两种处世哲学在现实层面上的投射。《一集》中的老残摇铃行医,为民请命,志在补残,是对玙姑“大公社会”政治理想的践行;《二集》中的老残谈佛论禅,隐身荒庙,飞升极乐,也正是逸云“自我解脱”宗教精神的投影。就这个意义来说,《一集》是一篇政治书,它借玙姑之口,建构起一套“大公社会”的儒家正统伦理体系;《二集》则是一部禅理书,反映的正是一步步破除执念,由内省走向顿悟,最后虚心静气,明心见性,最终得以游历阴曹,飞升大道的心灵历程。《一集》宣扬的“大公”儒家正统伦理取向和《二集》追求“自我解脱”的出世精神,构成了一种鲜活的对话关系。
四、说不完的游者,消不尽的寸草心——对话的深层脉络
整部《二集》,极写一种平淡显豁,超脱自由的生命美学。这与《一集》所呈现出来的儒家正统伦理似乎存在一种思想的断裂。其实,两篇之间的关系是裂而未断:《一集》以梦始,《二集》以梦终。《一集》启首之梦,是家国忧患而未能救之梦,《二集》终了之梦,是游历幽冥而最终超脱之梦。二梦连接的老残心理转变过程,正类似于中国传统文人“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两种因时因境而变的处世原则和价值取向。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一集》与《二集》,“补残”与“出世”之关系乃是对话而非对立,既云对话,则二者必有所不同而又不尽不同。《老残游记》前后篇在“群体价值—个体价值”的对话中,还隐含着两者互相渗透的深层脉络。
(一)《一集》的“边缘心态”与《二集》的出世精神
首先,《二集》中体现的出世超脱精神,是《一集》中“边缘心态”发展延续和作者写作心态改变的综合结果,其转变有着其内在逻辑链条和外部动因。
《一集》借玙姑之口建构了一个崇尚“大公”的儒家正统伦理体系,而老残“补残之举”实质可视为对其价值取向的践行。然而,我们不要忘了,老残与玙姑,包括黄龙子都是有着边缘心态的一类人。一个“游”字,已道尽老残“边缘者”角色的定位——一种游离、流动、不固定,没有归宿的游者心态。老残身负实学,却只愿作一个游者,游离于权力中心,在远离社会中心的位置上观察与思考,进行着他那行侠仗义的工作。虽意欲“补残”,但他也明知其实这样的举动纵然救得了一二性命,也与大局无补。而玙姑和黄龙子,则是彻彻底底的社会变革的旁观者,甚至反对者。可以说,《二集》那种“知其不可为而求己身解脱”的出世精神,正是《一集》之中老残边缘心态的承续和发展。
其次,从创作心态看,据刘厚泽《刘鹗及〈老残游记〉》中对刘鹗生平的介绍,刘鹗在1902 年(《一集》写作时间)之后将精力转向发展民族工商业,欲以实业救国,如纺织、钢铁、电车、自来水、化工、轮船等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事业均以失败告终[1]13这其中包括时人对他兴办工商谋取私利的指责、列强对中国的侵占和“北拳南革”的兴盛。山河破碎,身世浮沉,让刘鹗更看到了国运衰微而自身渺小。“无材可去补苍天”是刘鹗这一阶段的心理写照。事业坎坷,国势已颓,身世与家国的剧烈流变使刘鹗在《二集》发出“人生如梦耳”的嗟叹,并在其结局安排了一个老残在梦中超脱入圣的结局,至此,老残完成了对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悲幻痛苦的寂灭。
(二)《二集》的现实映射
在《二集》中,是否真的全是玄奥的宗教书写和表达,不涉及社会现实的影射呢?其中是否残存着《一集》中那种家国情怀呢?作为刘鹗的心灵映射,老残最终“超凡入圣”,获得了个体生命的超脱和自由。然而,刘鹗是不是也获得了这种解脱了呢?
看看《二集》中逸云对于“住世”和“出世”的理解。她认为,拘泥于佛理教规并不是真正超凡入圣的表现,只要诚心所至便是佛。这种自心即佛的宗教观可以视为现实当中作者晚年的心理写照。对于此点,早有学者关注。[5]刘鹗秉持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主张,热衷于兴办工商业,实现其“富国养民”的愿望,但却遭到很多人对其贪图利欲的指责,其中甚至包括太谷学派的同仁黄葆年。然而正如刘鹗本人在给黄葆年的书信中所坚称的一样[1]299,称自己与其他同仁所做的,是“殊途而同归”,工商钱粮的世俗之事并不妨碍其超凡入圣、为国为民的心态。而且,小说在第八回游历地府的时候,借阎王之口说出“口过,毁人名誉乃是阴间大罪,要受极大恶刑”,这可视为其对那些恶意指责的回应。如此,逸云“住世出世互不挂碍”形象,正表达了刘鹗对自己清白之心的辩护。而地府中的情形,正映射了人心险恶、流言可畏的现实世界。
《二集》中消解了名相之执念、情欲之执念,却只字不提家国之执念,作者是否真的同老残一样,心无挂碍,达到了真正的逍遥呢?小说的最后一回,老残在折公朋友家看到了一首诗:
野火难消寸草心,百年荏苒到如今。
墙根蚯蚓吹残笛,屋角鸦枭弄好音。
有酒有花春寂寂,无风无雨昼沉沉。
闲来曳杖秋郊外,重迭寒云万里深。[3]235
野火难消寸草心,这也许是刘鹗一生最好的写照。刘鹗一生心怀“教养天下”的理想,意欲以西方之科学振兴已面临覆灭的清廷,欲救大船的小舟却被大船上的几百个人“骂为汉奸,用力乱砸,打得粉碎”(《一集》第一回中的梦境)。百年荏苒的事业道路和无可救药的国势就如野火,却烧不尽刘鹗心怀家国的寸草心。在刘鹗生命的最后几年,其依然奋战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兴建车站,置办实业,直至被构陷流放,不幸病亡的生命尽头。[1]14
也许《二集》篇末的超凡入圣,解脱自由只是刘鹗试图挣脱家国沉沦之痛苦的一个美梦。超脱的出世精神,也只是刘鹗精神寄托和内心安顿的一种建构。消不尽的寸草心,褪不去的家国忧患使得其无法完成痛苦的寂灭,难达内心真正的超脱和自由。故而《二集》的超脱出世,可视为刘鹗对现实中沉浸于家国忧患的痛苦,欲求解脱而不得的一种补偿。
因而,在《一集》“棋局已残,吾人将老”的身世家国书写中,暗含着老残作为游者的边缘心态;在《二集》玄奥而超脱的宗教世界里,潜藏着对现实状态的映射。《一集》的边缘心态衍化为《二集》的出世精神,《二集》的解脱结局又折射出《一集》中挥之不去的家国忧患。这种互相渗透的深层脉络,使得“群体价值-个体价值”的对话更加富有张力。
刘鹗延续了明清小说关于身世与家国,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潜在对话,又把这种对话放置于晚清国家、民族和文化遭受沉重危机的现实语境中,使其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思考充满了时代性和沉重感。
《一集》和《二集》,前者以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伦理,追求群体价值的实现;后者则以“知其不可为而求解脱”的出世精神,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超脱。前者将身世之感情熔铸于家国之感情中,当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现实遭遇残酷结局时,一种不可抑止的悲怆和绝望便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后者将个体价值超越于群体价值之上,面对无限宇宙和有限人生的异质,面对“人生如梦”的悲幻,破除重重痴障,消解种种执念,最终完成了对痛苦的寂灭,达臻了生命的自由。前者照见刘鹗真实的内心,更照见晚清一代文人在帝国末世、残局穷途之时的悲愤与绝望;后者折射其超脱的理想,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建构和安顿。故而,《一集》乃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二集》乃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两者构成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对话关系:《一集》是对《二集》的诠释和注解,为我们读懂《二集》的出世精神提供了一种前置的背景;《二集》是对《一集》的衍化和升华,为《一集》续写了一种理想化的结局——沉重的家国忧思从而获得了一个解脱的出口。在两者的颉颃中,我们得以窥见作者在末世残局的历史语境下的焦虑情绪和自我调适。
其实,如若把视线从《老残游记》延展到晚清小说,便不难发现,这种沉重的末世情绪被广泛地投射在晚清小说的书写中。这种末世情绪来自西方政治势力、科学技术、文化价值对传统秩序、文化体系的冲击而生的前所未有的混乱感和危机感——当往昔坚固而笃定的儒家文化信仰遭受质疑,面临崩溃,各类思潮奔突激荡,在混沌喧哗中,如何建构一种确定的主体认知?这反映到文学中,便是晚清小说中彷徨焦虑的末路意识和伤感悲慨的悲剧情绪。
面对末世残局,《品花宝鉴》《花月痕》等“狭邪小说”吟哦风月,表现一种在绝望中寻求心灵麻醉的末世狂欢,以欲望的释放来麻痹不知前路在何方的个体彷徨和焦虑;《文明小史》以变革中的中国为背景,表现在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扭曲和错位以及作者对文化冲突中的“我”的认知;《新石头记》则逆转彼时的中外强弱关系,试图在“中华盛世”的乌托邦式社会愿景中寻回民族自信。而《老残游记》中,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目睹心中信仰的价值体系逐渐式微,在“大我”和“小我”的主体认知中挣扎,徘徊……末世情绪的书写尽管众声喧哗,可我们总能看到一群从盛世迷梦中醒来的晚清文人,面对来势汹汹的危机冲击,在错乱复杂的文化洪流中试图找寻自我、调适自我的痛苦历程,以及他们无数次地突围却总是看到“此路不通”的焦灼、无奈和愤懑。这也是一种对话,一种末世残局中各种思潮激荡奔突,混沌喧哗却蕴含着可能性的对话。刘鹗和他的同行者在百年前写下的,是对这个时代的永恒应答,更是历史深处永不逝去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