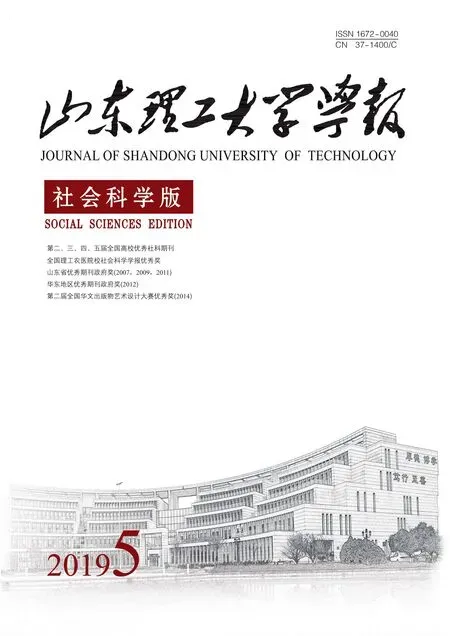家庭与政治文化的传递探析
石艳玲,王 青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一、引言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稳定需要很多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成功与否无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具体而言,亦即政府要将其所主张的政治文化真正传递到每个公民那里,让公民接受。这就需要了解政治文化通过哪些渠道影响公民。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政治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机构是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就我国来说,政府对学校和大众传媒重视较多,党和政府的一些施政政策首先通过大众传媒向广大群众即时播报,然后经过整理,编入教材传达给学生。
除此之外,我国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也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但是家庭在传递政治文化中的作用还没有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尚属空缺。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进行相关尝试研究,以期为学者和政府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般说来,家庭传递政治文化的形式有四种:一是直接的灌输。父母向子女直接传输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文化;二是榜样的认同。父母没有明确向子女灌输政治文化,但父母的言传身教也会间接地影响着子女;三是家庭的社会环境。每个人的出生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社会背景的设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父母的社会地位、父母所受的教育、所居住的地区等都对子女的政治态度有着明显的影响;四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也会影响着他将来走向社会时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理解政治和社会。出于叙述的方便,我们将第一种和第二种形式合并起来论述。
二、直接灌输和榜样
在家庭中,父母会把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态度直接灌输给子女。以美国为例,一些政治态度的获得即是来自于父母的直接教授。譬如忠诚的情感、对政府象征(国旗、自由女神)的尊重、一个公民被期盼的行为(尤其是守法)。而且,家庭也传递不同的观点,如对某个发生事件采取的态度[1]23。
但是在家庭中,对政治的探讨并不是生活的中心,因此子女对政治文化的吸取更多的并不是直接灌输,而是来自于父母的榜样力量。父母提供了可供儿童模仿的榜样,儿童多对自己父母的政治观点认同。戴维斯(James C. Davis,1969)认为“父亲是政治人物的原型,由此开启了儿童的政治权威的看法”。家庭提供了由儿童向成年人转变的主要方式,几乎所有的政治性格都是在家庭中决定的。儿童在满足自己需求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认同,而他的需求完全依赖于父母的供给,对家庭的依赖强化了与家庭的政治观点保持一致的趋势[1]23。
儿童对父母政治认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儿童对父母所喜爱的政党的认同。詹宁斯(M. Kent Jennings )和尼米(Richard G. Niemi,1969)对父母向孩子传递的政治价值进行了研究。他们以美国97所公立和非公立学校的1669名二年级学生为对象,采访了三分之一的父亲,三分之一的母亲,剩下的皆是对父母都采访。调查发现在政党认同方面子女受父母的影响较大。59%的学生在较广的类别上(都认同同一个政党,只是强弱程度有所差异)与父母相同,只有7%差别较大(父母强烈认同民主党,孩子则强烈认同共和党,或者相反)[1]23。
有的学者则认为,父母向子女传递政治取向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纽康伯(Newcomb,1969)指出父母向孩子传递政治态度确实存在,但却发生在很小的范围内[1]23。所谓很小的范围,主要指政党认同方面。尽管他们否认父母对子女其他政治取向的影响,但都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政党认同方面的影响较大。坎迪(Cundy,1969)认为父母在政党认同问题上,比同辈群体要有优势。他们首先认同父母,然后再是朋友和其他人[1]23。总之,不管学者作何争论,但都承认父母对于子女的政党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家庭所设定的社会环境
大的社会环境对人的政治社会化也有影响,不同的社会环境个体的政治取向也会有所差别。对于儿童来说,家庭往往是环境影响的中介。海曼(Herbert H. Hyman,1969)认为对事件的解释需要成年人的介入,这样减少了儿童直接面对现实。通常情况下,父母构建了儿童的世界观。父母的介入成为弱化社会变迁的因素。年幼儿童几乎与大的环境绝缘,他们不关注经济和经济的条件。譬如失业家庭的孩子,没有证据显示失业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而大学生之前的学生更容易变化,也在于他们这时已经脱离了家庭[2]69-70。
家庭的社会环境对儿童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儿童的政治理想化特征。所谓理想化,指儿童正面的评价、看待政治领导。海斯(Robert D. Hess)和 伊斯顿(David Easton,1960)对12000名2至8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持续五年的研究,他们发现儿童有关总统的形象都是高度正面的,多数儿童认为,与一般人相比,总统工作要更加努力、诚实、有知识和为人喜爱、是一个好人[3]636-637。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1960)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在1958年1月和3月对659名纽黑文四年级(9岁)到八年级(13岁)的学生,主要采取调查表的形式,然后加少量的访谈。他发现儿童在回答谁是最重要的人时,四年级学生把总统和市长排在了其他人物(医生、警察局长、法官、学校老师、宗教领袖、学校校长)之前。71%儿童认为总统“很好”,儿童倾向于把政治领导者描述为“帮助的”“关心的”和“保护的”人[4]936-940。为什么儿童的政治社会化具有理想化的特征?格林斯坦认为,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机构,父母和老师可能对政治提出激烈批评,但他们向儿童传输时则把激烈的观点软化或裹以糖衣[4]941。也就是说父母和教师承担了过滤器的作用,具体到家庭来说,父母把恶的东西挡在了家庭之外,从而导致了儿童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是正面的。海斯和伊斯顿的解释基本相同。美国的父母“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保护儿童以免于接触政治生活的现实。……他们感到让儿童常常感受到政治的丑恶和有争议的一面是不合适的”[5]243-245。
除了父母有意或无意地对社会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进行筛选外,父母本身的一些属性对子女的政治文化也有所影响。譬如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政治态度受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普卢策(Eric Plutzer,2002)研究发现,年轻人第一次成为合格的选民时,父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很大程度决定年轻人投谁。这种惯性仍然在以后的选举中会持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会将他们的优势传给子女,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子女的阶级偏见[6]54。
四、家庭人际关系经历
家庭中子女间的互动,以及父母的关系影响了对于他们的政治人格、政治态度也有所影响。海曼(1969)论证了家庭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积极参与政治者很有可能有一个积极的父亲或母亲或兄弟姐妹[7]66。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对子女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父母培养孩子的方式;二是子女的出生次序导致了子女相互间以及与父母不同的关系,从而影响了他们未来的政治取向。
(一)父母的培养方式
父母培养孩子的方式,按照鲍姆瑞德(Baumrind,1971)的说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放纵的(Permissive)、威权的(authoritarian)和权威的(authoritative)[8]2。放纵的方式就是容忍孩子所做的一切,对孩子的行为不加干涉。威权的方式对孩子采取极端专制的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来培养子女,以命令的方式教育方式,从不征求子女自身的意见。而权威的方式处于两种之间,是一种健康的培养方式,既不放纵子女,同时也对子女的一切都横加干涉,教育子女时尊重子女的意见,对子女产生的问题采取说服的方式。
父母对孩子政治人格、政治态度的影响与培养方式密切相关。麦科比(Maccoby,1954)发现一个父母对子女控制越严格,孩子越有反叛的冲动。相反,对待子女既不是采取自由放任也不是采取威权主义的方式对待孩子,采取说服而不是命令的强制方式,这种情况下亲子间的政治价值最有可能一致[9]41。
家庭的培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政治人格
家庭培养方式与政治人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戴维斯(James C. Davis,1965)认为“家庭在构建个体的政治性格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源于它作为人的基本的、先天的需求满足的主要源泉和所在的角色。”他认为家庭提供了由儿童向成年人转变的主要方式,几乎所有的政治性格都是在家庭中决定的[10]10。
现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父母对子女的威权的培养方式是子女威权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形成的重要因素。关于这种威权主义类型的人,霍克海默在为阿多尔诺等所著的《威权主义人格》作序言时指出:“他是被启蒙过的,同时又是迷信的;为自己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而自豪;却又害怕与他人有所不同;自负于自己的独立性,却又倾向于盲目地屈从于权力和权威。”[11]67可以说,这类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现代民主观念的洗礼,但却迷信、盲从权威,自我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有关威权主义人格的起源,《威权主义人格》的作者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了威权主义人格的童年起源,威权主义人格的培养与家庭的偏见有关。强调在威权主义家庭,与之相伴随的是情感的困难,威权主义的父母不能毫无保留地向他们的孩子表达情感。出生在这样家庭中的孩子恐惧父母的权威。同时,由于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孩子又是很难独立的,缺乏自信。孩子缺乏安全感,从而使他想依从于权威获得安全。这里的权威既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父母的代替物,如政治领导。但孩子在潜意识里又对父母产生敌意和仇恨,但这种仇恨和敌意囿于社会的规范,不可能指向自己的父母,于是其他外集团就成为他们转移仇恨的对象。这种形成了对内集团的盲目服从和对外集团的暴力的对抗[12]353。后来,《威权主义人格》作者之一桑福德(Sanford,1998)对此又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他在访谈的基础上断言,多数的威权主义者有一个统治性的父亲(或者强悍的母亲),而在非威权主义家庭里,母亲的影响是更重要的,或者父母之间是伙伴或平等关系[12]370。
除了《威权主义人格》的作者外,其他学者也有着类似的论述。哈里斯(Dale B. Harris,1950)等通过对5—6年级学生的偏见调查,以及对他们的母亲培养孩子的方式的调查,发现有偏见的儿童的母亲的特征是期望儿童迅速和毫无疑问地服从。无偏见的儿童的父母很少赞成打孩子或通过羞辱的方式训练孩子。儿童的偏见与父母的复杂的态度密切相关,包括威权主义控制处理的方式和缺少对于儿童的“恼人的价值”的仁爱与宽容[13]172-180。
2.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指在政治活动中对他人所做事件和所做承诺的信赖。政治信任与否最早源自于父母的培养方式。
戴维斯谈到了亲子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儿童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儿童在家庭中基本需求的被剥夺将会导致儿童对政治的冷漠。而且儿童对父母的偏离,将会导致他们倾向于对政治的偏离。同样,父母的过度保护也会导致子女对政治的不信任。父母把家庭作为保护之地,使儿童免受外在的威胁,其后果就是不参与政治活动,对政体产生敌意。按照戴维斯的逻辑,如果父母对子女冷漠,将会导致子女政治上的不信任;而如果父母对子女过于保护,则导致子女对父母的信任,而对政治上的不信任。总之,父母不正常的培养方式最终都会导致子女将来对政治的不信任[10]16-17。
父母的过度保护与政治不信任在平纳(Frank Pinner,1965)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他采用调查表的形式对法国、比例时和荷兰的中学和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以探讨过度保护与政治疏离和政治不信任之间的关系。所谓过度保护指父母限制儿童与家庭之外接触,十分焦虑地关心孩子的智力和情感的成长。而政治疏离指相信政党是无用的和分裂的,政治人是不道德的。政治不信任指政治是冲突的、寻求妥协和威胁性的,政治人从内心来说根本就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他研究发现,比利时的年青人受到父母过多的保护,法国次之,而荷兰的年青人拥有更多自由。与此相联系,比利时和法国的年青人表现出更多的对政治的不信任和疏离。父母的过多保护在于他们把外部世界描绘成敌意的和凶险的[14]58-60。
白鲁恂(Lucian W. Pye,1962)对缅甸的家庭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家庭是缅甸儿童生活的核心和保护自己以免受外来威胁之地。衡量个体最终品格的就是对父母忠诚和做对父母有益的事。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做让父母痛苦和使父母不高兴的事。这种做法最终就会使孩子服从于任何形式的权力,形成消极和服从性的态度。儿童一出生,母亲几近溺爱,世界属于儿童,家庭满足他的所有要求,驱除所有的挫折,这就为非理性和近乎强迫的乐观的感觉提供了基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表现出了另一面,有时出乎意料地冷漠、远离儿童和对儿童不感兴趣,这就使儿童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对于他来说,人与人之间是危险的和不确定的[15]182-185。
3.自尊
自尊是一种由自我评价所引起的自爱、自我尊重,并期望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自尊要求人们自己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而这种人格的独立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的心理基础。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应该做到平等待人,这就要求人们尊重他人的同时,也需要自我尊重,以及他人对自己的尊重。
家庭不同的培养方式导致了子女是低自尊还是高自尊。库珀施密斯(Coopersmith,1967)对10—12岁男孩的研究中,也发现高自尊与父母的训练相关。高自尊的人所生长的家庭环境是接纳(acceptance)的,具有明确的规则的尊重,以及看来有效率的、镇静的、有竞争力的个体,培养个体具有独立和创造性的行为的能力。在高自尊者的家庭中,相信和渴望成功。相反,在低自尊的家庭中,孩子所遇到的是拒绝、不尊重和失败[16]249-250。
布瑞(John R. Buri,1988)等采用问题调查的方式对230名大学生的自尊与父母的培养方式进行了研究。调查表包括自尊调查表和父母权威调查表及一个人口统计表。调查结果发现,父母对孩子自尊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于培养的类型。威权的养育方式导致低自尊,权威的培养方式形成高自尊。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培养方式的影响[17]280-282。
(二)家庭中出生的次序
子女在家庭中出生的次序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家庭中地位也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了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活。
纽曼(Joan Newman)和泰勒(Alan Taylor,1994)对1988年美国在位的45位男性州长和澳大利亚自1901年以来的男性总理的研究中,发现家庭中的长子更有可能成为政治领导者,而处于中间的孩子则很少可能成为政治领导者[18]435。
斯坦伯格(Blema S. Steinberg,2001)对1960年以来世界上出现的41位女总统或女总理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像男性领导人一样,长女身份的领导者在这些领导人的比例偏高[19]89。安迪维格(Rudy B. Andeweg)和范登柏格(Steef B. Van Den Berg,2003)的研究范围更为宽泛,对领导者的考察不限于男女,也不限于长子(女)和中间子女的比较,而是加入了独生子女和最小的子女。他们通过对荷兰1200名地方和中央的官员的研究,验证了以前学者的结论:长子(女)更有可能成为领导,中间的子女的占比例较少。同时他们又发现,独生子女成为领导的比例也较高,而最后一个孩子成为领导的比较小[20]612。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安迪维格和范登柏格从两个角度对此作了解释。一是亲子关系的角度。子女出生的顺序不同,在家庭中享受到的资源也有所不同。第一个出生的孩子,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还没有经验,给予了他(她)更多的关注,较多的智力投入,同时对他(她)抱有了较高的政治期望。这种高期望和带有焦虑的关注使长子(女)产生了自卑,从而促使他(她)以后依靠追求权力来克服自己的自卑。以后的孩子每一个出生资源都会减少,而且后面的孩子因父母经验的增加而变得平静,因此,对他们也关注不多。二是兄弟姐妹的角度。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弟弟妹妹更多承担了指导角色,从而积累了一些领导经验,而且在兄弟姐妹的竞争中因有较多的经验而占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因弟弟妹妹的出生,自己独自享受父母之爱的机会没有了,内心受到了创伤,这种创伤也需要以后追求权力来补偿。尽管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对于将来人们的政治参与都有重要的影响,但从独生子女成为领导的比例较高来看,父母的影响明显超过了兄弟姐妹的影响[20]607。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家庭在政治文化的传递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传递的价值重要。家庭传递了一个公民培养所需要的重要的价值。譬如,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政党认同,政治信任、自尊,以及以后的政治参与。其二,传递的形式多样,而且以非直接的传递为主。传递的形式包括了直接的灌输和榜样的认同,家庭所设置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中人际关系的互动。其中,除了直接的灌输外,其他都属于非直接的传递。其三,传递的效果好。由于家庭中对政治文化的传递大多是非直接的、无意的,它不是强迫的,人们对这种形式传递的政治文化很少抵触心理,因此这种传递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能够深入影响到人们的灵魂中。同时,由于家庭中的政治文化传递是在人们尚处于童年时期,对政治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一旦接触这些知识,就很难抹去,往往能够影响到人的一生。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多数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得出的,因此有些结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子女的出生次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与目前中国独生子女占多数的国情不相符合,政党认同结论的得出也与西方政党轮替执政的制度相关。不过有些结论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譬如父母对于子女忠诚于国家观念的培养,家庭设定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不同政治态度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培养方式对人们的人格、政治信任和自尊的影响。这些结论都应该引起中国学者和政府的关注,中国学者们应结合我国国情再进一步进行研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与政治文化的传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