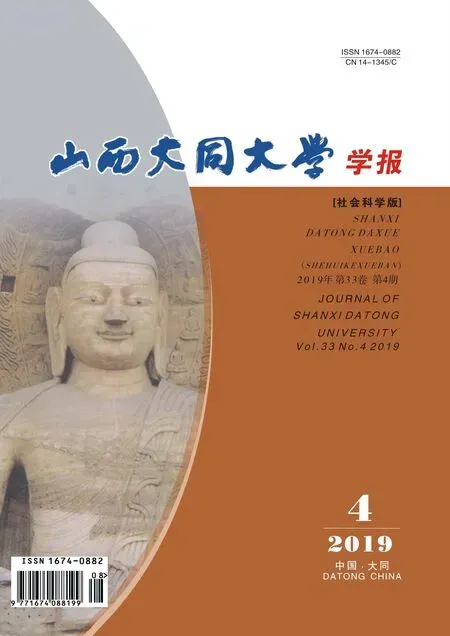日本无赖派作家的反讽叙事艺术
——以太宰治的《维荣之妻》为例
任江辉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言
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坛上出现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特殊文学派别“无赖派”。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大多呈现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真实现象,描绘了“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政治混乱、经济颓废、民众生活凋敝,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状态,社会思潮发生根本变化”[1]的景象,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太宰治就是该文学派别的代表性作家,其被尊称为“昭和文学的金字塔”。其文学造诣极高,文学艺术表现张力极强,叙事手法丰富多样,其中反讽叙事艺术是其文学创作的一大重要特色。在采用反讽叙事的时候,太宰治时常将叙事话语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进行错位,将叙事者的叙事话语与作者内在观点进行背离,通过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叙事对立和冲突,以一种蕴含否定和嘲讽的艺术修辞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特点在其《维荣之妻》的作品中表现得一览无余。该作品以女性的独白体作为叙事方式,从叙事情节到叙事话语,从叙事人物到叙事主题,反讽叙事艺术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叙事情节的反讽
叙事情节的反讽是指故事情节的矛盾化并置,将情节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展现出来,体现了一种叙事的相悖,让读者阅读后产生一种反讽的美学效果。在《维荣之妻》中叙事情节的反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叙事情节的反常态。反常态的叙事情节是反讽叙事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以直观性和具体性的艺术手法推动着反讽叙事艺术的呈现。在作品中,作为丈夫的“大谷”平时对家庭和孩子漠不关心,但是这一天“大谷”喝得酩酊大醉后回到家里,还破天荒地询问孩子的病情。 此外,作为外表斯文的知名诗人“大谷”在居酒屋老板上门讨债时,完全不顾自己的脸面和名声,一反常态突然亮出大型折叠刀以示吓唬。这些叙事情节的反常态凸显了作品的反讽意味,以一种突如其来的形式增强了讽刺的效果。其二,叙事情节的特异性。叙事情节的特异性是反讽叙事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特异性”的内涵将故事情节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反转,引导着叙事情节向前发展,进而出现反讽意味的彰显。面对“居酒屋老板的倾述其丈夫‘大谷’多次忽悠,赊欠酒钱不还,并将其居酒屋的酒几乎喝光”这一事实,按照常理,作为妻子的“佐知”会马上表示歉意,然而此时妻子“佐知”并没有直接道歉,相反忍不住笑出声来。再者,知道自己丈夫“大谷”在外面多次出轨,与不同女性鬼混后,一般来说,妻子“佐知”会顺理成章地表示愤怒和抗争。但是,此时的佐知并没有生气,反而为了偿还丈夫“大谷”的债务,在居酒屋打工还债。这些叙事情节“特异性”的导入,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反讽力度,拓宽了叙事手法的张力。其三,叙事情节的巧合性。叙事艺术的巧合性往往蕴含着反讽的特质,拓展了反讽叙事的宽度,加大了反讽叙事的深度。在叙事情节中,居酒屋平时存放的现金不多,由于年关将近,还款较多,当天居酒屋存放的现金到达“五千日元”,这一数目对于当时的居酒屋来说是个巨款。老板娘把这笔巨款存放在抽屉时,刚好被正在喝酒的“大谷”看见,“大谷”突然起身抢走巨款。这一叙事情节的巧合性将平时被老板视为“名门望族之后”的大谷形象撕得粉碎。而更为巧合的是,一般情况下应该马上报警的居酒屋老板却觉得“大谷”是熟人,报警对“大谷”太残酷。如此一来,叙事情节才出现了居酒屋老板向妻子倾述“大谷”在外酗酒和出轨的种种劣迹。种种叙事情节的巧合性不但增进了叙事内容的趣味性,而且加深了反讽效果的浓度和色彩。
此外,叙事情节的反讽艺术还体现在其叙事情节的反常态、特异性和巧合性,更体现在叙事相悖上。所谓叙事相悖就是将不同甚至相反的叙事内容进行并置,从而突出了叙事情节的矛盾性,加大叙事内容的差异性,呈现一种反讽的美学效果。在《维荣之妻》中,妻子“佐知”对丈夫“大谷”在外面出轨、酗酒、偷钱等种种事情,都是在“佐知”与居酒屋老板夫妇的交谈中并置进来的,将丈夫“大谷”的酗酒享乐和妻子的逆来顺受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体现出来,形成了一种叙事情节上的相悖,增强了反讽的意味和深度。
三、叙事话语的反讽
叙事话语的反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的载体,也是形成文学作品叙事风格的主要途径之一。“反讽作为修辞学的一个概念,不同于明喻、暗喻等修辞方法,反讽表达的是与所说出来的话语相反的语意或引导读者不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方法。”[2]在《维荣之妻》中,叙事话语的反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品中叙事者以一种正话反说的艺术形式,让话语表面的真实性看似合理,其实背后蕴含着与此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意味。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维荣之妻》的语言层面中,比如:面对妻子“佐知”应允以打工抵债后,居酒屋老板嘲讽地说道:“是吗?太太,没想到你也成了‘阿轻’啦(在日语中‘阿轻’意味着替夫还债卖身为妓的女人)。”又如:妻子“佐知”在以打工抵债后的语言表达,“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这样呢,我很幸福啊。女人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而面对丈夫“大谷”放荡不羁、推卸责任的说辞,妻子“佐知”只是淡淡地说道:“是不是人面兽心的畜生都无所谓,我们只要活着就好。”这些语言层面的显性话语,看似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交流对话,其实凸显了话语者内心的虚伪,体现了话语者心理的无奈。作品通过这种反讽的艺术手法将孤独和落寞的社会生态展现出来。
除了上述显性的语言表达以外,叙事话语的反讽还表现在文学作品叙述者利用叙事话语来表达一种隐性的反讽效果。如:作者借助于居酒屋老板的口述,得知一位叫“阿秋”的女子与“大谷”相识后,为“大谷”尊贵的身份所倾倒,替“大谷”还债,后来生活发生突变最终沦为乞丐。这一叙述话语既是对“大谷”表面风光的嘲讽,也暗示了妻子“佐知”命运结局的悲惨。在“得知丈夫“大谷”偷钱被追到家里来的经过后,作品叙述妻子“佐知”的心情时,用了“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忍不住笑了出来,突然想起丈夫诗词中的‘文明的结果就是大笑’,大概它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情吧”。[3](P188-189)这种心情的叙述话语,将滑稽和无助捆绑在一起,将冷幽默和可笑有机融合在一起,既是对丈夫“大谷”无赖行径的抨击,又是对当时(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生态的反讽。另外,在叙述居酒屋客人群体的时候,作者还运用了对比的反讽修辞手法。妻子“佐知”观察到喝酒的客人全都是犯过罪的人群,相比之下,吃喝嫖赌的丈夫“大谷”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人。这些特殊的反讽叙事话语蕴含着妻子“佐知”对丈夫逆来顺受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颓废和人性的黑暗。
不论是显性的语言表达,还是隐性的叙述话语,在《维荣之妻》这一作品中,反讽的叙事话语在体现叙事内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的同时,都蕴含着话语的矛盾性和滑稽性,不仅建构了整个故事系统的框架,而且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就是说,太宰治在《维荣之妻》中以反讽的叙事话语,“通过以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文学创作方式进行,抛弃道义和人情的虚伪面具,凸显颓废的人生哲学和虚无主义理念,在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中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从而对战争时期的封建伦理、陈旧道德进行反叛”。[4]
四、叙事人物的反讽
叙事人物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活动主体,也是文学作品内涵和思想的主要载体。也就是说,“叙事人物既是叙事中的符号,更是具有叙事生命力的表现者,和作家一起讲述故事,他们的行为和功能是故事叙述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在叙事中的种种功能性作用,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人物的多种可能性。”[5]在《维荣之妻》中,太宰治笔下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十分丰满,但是通过反讽的叙事艺术,也使得叙事情节中的人物刻画显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也就是说,在小说《维荣之妻》中,太宰治并没有特意花费大量的笔墨对人物进行渲染,而是通过人物的隐性反讽和对比反讽来诠释人物的性格和特点。这种颇具特色的艺术反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对人物形象的符号性命名。 在文学作品的命名上,太宰治采用《维荣之妻》,有其叙事手法的特意性,也彰显了其艺术思维的巧妙性。“维荣”一词源自法国,其英文名叫“Francois Villon”,中文翻译为“弗朗索瓦·维荣”(有的翻译成“维庸”或“维扬”),是法国十五世纪的著名诗人和近代诗歌创作的先驱,他虽然才华横溢,但是曾杀过人,当过强盗,过着入狱、流浪和逃亡的荒唐生活。因此,“维荣”这一称呼成为才华出众却放荡不羁、颓废、堕落的代名词。而太宰治有意识地利用法国这一知名诗人作为男主人公“大谷”的代称,蕴含着特殊的反讽意味同时,彰显了男主人公颓废堕落的性格特征。
其二,对女性的叙述。在《维荣之妻》中主要叙述了妻子“佐知”、居酒屋老板娘、阿秋、神秘漂亮夫人、卖酒的贵妇等。作为妻子的“佐知”,有两重身份,作为母亲,她在家里悉心照看孩子,勤于家务事,就连到居酒屋打工还债时也没放弃照顾小孩,而是背着小孩去上班打工,可以说是个勤劳的母亲。作为“妻子”,她对丈夫尽心尽力,逆来顺受,甚至在发现丈夫“大谷”在外拖欠酒钱、偷抢巨款的时候,没有生气发怒,反而挺身而出替夫还债,可以说是个贤惠的妻子。但是,“佐知”在被两位居酒屋客人玷污后,表现出若无其事、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只觉得能活着就够了。这种前后处事的不同态度,对比鲜明,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而尽心经营小店的居酒屋老板娘,在新宿酒馆当女招待、并替大谷还债的阿秋,外表体面却贩卖假酒给居酒屋的贵妇,这些女性虽身份和行为各有特色,但是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她们都坚持工作。这与日本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观念完全不一样,突破了传统日本女性被禁锢在家庭内部的束缚,是对日本传统家庭道德的一种深刻反讽。
其三,对男性的叙述。首先,对男性的论述,最典型的莫过于“大谷”。“大谷”身份尊贵,出身名门望族,是日本四国大名的后裔。曾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是位大学者和知名诗人。但是身份高贵的“大谷”却对家庭毫不负责,对妻子漠不关心,整天在外沾花惹草、酗酒、淫乱、欠债、盗窃。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与其高贵的身份和高学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混乱和人心的颓废。其次,是居酒屋喝酒的男人们。这些男人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有的是罪犯,有的甚至是对“佐知”进行过性侵犯的客人。这些男人们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精神颓废,内心烦闷,常常借酒浇愁以发泄内心的迷茫。相对于勤劳持家、外出工作的日本女性来说,这些男性无所事事,酗酒度日,毫无家庭责任感。两种人物形象对比,将反讽的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体来说,在《维荣之妻》中,太宰治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并不是十分突出,但是通过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通过人物性格的描绘和人物语言的阐释,将反讽的意境渲染得十分到位和得体。
五、叙事母题的反讽
叙事母题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和叙事单位,是构成文学作品整体的有意义线索。有学者认为“母题是客观的叙事成分,也是基本的叙事单位。它可以是情节成分,也可以是人物角色和情节背景,但都是基本的叙事成分,反复出现在各种叙事作品里,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蕴。”[6]《维荣之妻》中蕴含的母题主要包括家庭、道德、战争等内涵。这些母题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而且大大增加其文学的反讽色彩。
其一,家庭母题。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叙事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场域之一。日本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男主内女主外”,而在《维荣之妻》中,丈夫“大谷”对家庭漠不关心,不负责任,一直生活在“家庭之外”,他在外酗酒、淫乱、偷钱、欠债,显然没有承担其他作为家庭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丈夫“大谷”不能挣钱抚养家眷,整天游手好闲,还自得其乐。表面上看好似悠然自得、毫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内心充满焦虑,对生活迷茫,反讽意象十分明显。这种反讽的意象犹如作者太宰治个人的生活写照,对此,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这样评论到:“《维荣之妻》是混杂着作家对家庭生活的赎罪感与歉然感的作品。”[7]另一方面,妻子“佐知”在尽心扶持家庭圆满的同时,为了替夫还债,毅然决然地来到“家庭”之外,打工挣钱。可见,“对于妻子佐知而言,她对家庭从开始的精神寄托转变成麻木的漠视。在家庭内佐知演绎着妻子与母亲的角色,然而在家庭外她周旋于椿屋(居酒屋)客人之间,由传统女性觉醒成为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8]这一家庭的剧变颠覆了日本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观念,形成了强烈的思想反差,暗示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转型,增添了极大的反讽效果。
其二,道德母题。道德是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正常有序发展的重要准则。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变迁,道德标准也随之变化。在《维荣之妻》中,丈夫“大谷”在外出轨淫乱,与新宿女招待阿秋、神秘贵妇人、居酒屋老板娘、居酒屋年轻女服务员等均有非分之情,这与他作为有妇之夫的身份形成了极大的反讽意味,显然丈夫“大谷”的行为不检点是对家庭道德伦理的无视。其次,出身名门贵族,拥有高学历和高名气的诗人“大谷”在日常生活中耍赖欠债甚至公然偷钱,这一身份与行为之间的极大反差,渲染了“大谷”对社会道德的茫然。而妻子“佐知”面对丈夫的出轨行为竟然感到麻木,两次被居酒屋客人玷污却毫无反抗之意,只觉得“这样就是生活,能够活着就好”。佐知对道德伦理的漠然使读者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对当时道德规范的崩盘给予极大的嘲讽。再者,外表光鲜亮丽的贵妇竟然将掺水的假酒卖给居酒屋,而居酒屋的老板也公开违法销售从黑市购进来的酒类,这些尔虞我诈的勾当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存在。显然,这些行为“既没有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非标准”[9],是道德的沦丧和伦理的解体。这一反讽的叙事手法和自我戏谑的艺术创作,映射出太宰治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嘲讽,和企图建立崭新的社会伦理体系的期望。
其三,战争母题。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粮食配给数量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现象无法控制,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伤兵、妓女、流氓、小偷、强盗、失业者、流浪汉、投机商人充斥街头”[10](P57),社会呈现一幅颓废破败景象。作为书写该时期社会现象的太宰治,其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会涉及到战争的状况,或显性或隐性地描绘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在《维荣之妻》中,战争母题的体现并不是显性的,更多呈现为隐性特征。在阐释居酒屋这一叙事空间的时候,就谈到居酒屋由于战争的影响濒临停业,由于老板夫妇的坚守才得以勉强经营。而且由于战争的影响,酒类大多通过黑市取得,销售假酒等投机现象层出不穷。再者,居酒屋的客人中也有人在谈论着纸张的黑市交易。从这些侧面可以看出战争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显然,由于战争的影响,日本社会经济凋敝,乘机投机倒把的商业行为屡见不鲜。再者,来居酒屋喝酒的客人中,大多是受到战争影响的颓废堕落人物。有罪犯,无所事事的底层人物,酒店的女招待,失业者和流浪汉,等等。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济不景气,这些经济上较困难的人只能到“椿屋”这种狭小邋遢的居酒屋借酒浇愁。从居酒屋的经营状况到居酒屋的客人群体可以看出,《维荣之妻》所体现的战争母题是隐性的。作品只是从叙事空间和场域中的侧面来反映战争的巨大影响,并以反讽的意味衬托出战争扭曲了人性这一事实。
六、结语
反讽叙事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叙事艺术的一种手法。作品以不同价值观的对立,将叙事话语的表里相悖,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凸显了太宰治的叙事艺术张力,表达了太宰治的思想主张和价值理念。在其《维荣之妻》中,作者不仅将叙事情节的矛盾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彰显其反讽的意味,而且将叙事话语的显性和隐性融入到叙事情节中,增添了反讽的色彩。同时,作者还将不同叙事人物形象的巧妙构思和身份对立,加大了反讽的效果。进而,作者还将家庭、道德、战争等叙事母题进行精心糅合,丰富了反讽的内涵。无论从叙事的形式到叙事的内容,还是从叙事的现象到叙事的本质,作品均呈现了一种悖立的矛盾性。作者在语言表达和文本意图上树立了一种背离的状态,以反讽、否定的委婉修辞艺术地表现出来,鲜明地表达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内涵。因此,要客观准确地理解太宰治的反讽叙事艺术,应紧扣当时社会的历史语境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真正把握其反讽叙事的艺术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