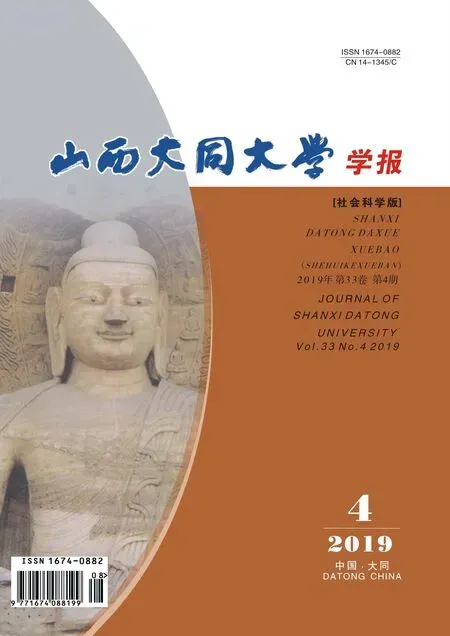论元代文人与僧人关系的新变
相 文,韩震军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元以前文人与僧人之关系
自魏晋时期佛学东传至直至两宋时期,在文人与僧人交往活动中,文人大多居于主导地位,僧人居于次要位置(本文所用“文人”概念,泛指有文化的读书人,如“名士”“儒士”“理学家”等都属于“文人”范畴。“诗僧”也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但本文为突出比对性,故将“诗僧”归属于“僧人”群体)。在这样不对等的交往关系中,文人对待僧人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方外之友、统释入儒、鄙视排斥这三种情况。
(一)方外之友 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佛学初传,僧人意在借名士之地位以传教,而谈玄名士又多觉老庄及佛学本无二致,因而名士、释子共入一流。当时文人如王羲之、谢安、许询等多与僧人交游往来,或谈经,或讲玄,关系融洽,共同推动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二者友好往来是当时的主旋律,但在具体交往时,士人还是有身份的优越感,如: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1](P193-194)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有一部分文人对出入朱门大户的僧人持轻视态度,文人优越感十足:你一个僧人怎么能像我一样出入达官贵人之宅?
唐时,佛学鼎盛,蔚为大观,禅宗的出现,标示着印传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宋时,禅宗思想已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主流信仰。在这样的背景下,僧人群体逐步扩大,甚至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诗僧。这些诗僧文化素养高深,具有高雅情趣,与文人之间的关系较普通僧人更为密切。盛唐“诗佛”王维,与僧人交往颇多,曾师事道光禅师,“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2](P752)中唐诗人白居易也有过游寺、访僧、研经的经历,“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悠游终老。盖唐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3](P1407)北宋诗人苏轼,“与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为方外之交。”[4](P283)唐宋文人与僧人交游,甚至与僧人成为方外之友,不仅是因为这个时代佛教昌盛,而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一,文人治天下的儒家理想与四处碰壁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让他们需要借助佛家思想来排遣心中的抑郁之情,需要远离名利场的僧人来净化自己的心灵。其二,僧人绝妙的才艺、高雅的情趣,使得文人仰慕那些具有高人之风的名僧。其三,僧人刻意与名士文人交游,以扬名天下,传播佛法。陆游有云:“宋兴,诗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长吉,宋文安之于凌云惟则,欧阳文忠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东都秘演,苏翰林之于西湖道潜,徐师川之于庐山祖可,盖不可殚纪。”[5](卷29)
(二)统释入儒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处于发展阶段,儒家思想仍是主流。唐至五代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佛家思想成为时代的新宠。一方面,儒家思想受到佛道两家的冲击;另一方面,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纷起,纲常伦理失序。面对这一形势,一大批儒士提倡“道统”,试图振兴儒家,重整社会秩序。这群儒士对待僧人的态度主要是:反对僧人,统释入儒。
韩愈认为“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6](P92),批评佛老思想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6](P2662)的排佛建议。反佛运动在宋代进一步发展。欧阳修认为佛教对政教有害无益,批评僧人不讲孝道,灭绝人性。但他反对如韩愈那般暴力的禁止佛教,主张补阙修废,立足于礼义之本,“……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此自然之势也。”[7](P199-200)欧阳修之后,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以理学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和修养论等批判佛教,使得宋代儒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这群儒士、理学家与僧人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在学术上,他们批判佛学,反对僧人;在生活中,他们却与僧人交游,如韩愈“不读浮屠书,亦不作浮屠文字,然于大颠、高闲、文畅之属,健羡丁宁,累书珍重。”[8]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隐含的真正目的是“统释入儒”:“人固有儒其名而墨其行者,问其名则是,构其行则非,可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其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与之游乎?扬子云称:‘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吾取以为法。”[6](P1582)
(三)排斥鄙夷 还有一部分文人是完全排斥僧人,他们对僧人热衷名利,参与科考表示鄙夷,认为僧人不得做官。如:
梁相张策尝为僧,返俗应举,亚台鄙之。或曰:“刘轲、蔡京,得非僧乎?”亚台曰:“刘、蔡辈虽作僧,未为人知,翻然贡艺,有何不可?张策衣冠子弟,无故出家,不能参禅访道,抗迹尘外,乃于御帘前进诗,希望恩泽。如此行止,岂掩人口。某十度知举,十度斥之。”[9](P1824-1825)
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衣冠子弟出身由僧返俗而应举的,像张策那样,却要受到排斥。”[10](P200)僧人热衷功名的,大多没有好的结局:
灵澈一游都下,飞语流贬;广宣两入红楼,得罪遣归;贯休在荆州幕,为成递放黔中;修睦赴伪吴之辟,与朱谨同及于祸;齐己附明宗,东宫谈诗,与官僚高辇善,几不保首矣。[11](P302-303)
到宋代,政府还下令禁止僧人参加科举,“颇闻有僧道还俗赴举者,此辈不能专一科教,可验操履,他日在官,必非廉洁之士。……当下诏戒之。”[12](P214)由此可知,文人与僧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科举是文人的特权。
概而言之,虽然有不少文人与僧人交游,甚至成为方外之友,但这并非是这个时代文人的普遍行为。统释入儒和排斥鄙夷,是元代以前文人对待僧人的主流态度。
二、元代文人与僧人关系之新变
元时,文人与僧人的关系出现了新变。以文人为主导的不对等关系下的交往模式逐步消失,以文人、僧人在平等关系下的新型交往模式成为主流。在这种新型平等关系下,文人出入佛学、与僧人交游的人数日众;文人为振兴儒家道统而排佛的现象消失;文人对待僧人结交权贵、追求功名的态度由鄙视排斥变为羡慕投附。下面将从普遍性、平等性两个方面考察文人与僧人关系的新变之处。
(一)儒释交游的普遍性 元代文人与僧人的交游活动在文人群体中具有普遍性。翻检《全元文》,无论是以理学扬名的理学家,如“北许南吴”(许衡与吴澄)、姚枢、姚燧等;还是以诗文著称的文学家,如闫复、程钜夫、袁桷、虞集、揭傒斯、欧阳玄、黄溍等;或是官位显达如“暇日游戏艺事,诗律则雅而不俗,字画遒而不媚。中书李公孟、张公珪、翰林李公谦、刘公赓、赵公孟頫、集贤宋公渤、李公衍、王公约,皆方外交也”[13](第30册,P248),他们的作品中,塔铭、寺碑记、僧人传等有关僧人的文章数量都很多。从时间上看,元初的忽必烈藩府文人群、元中后期的馆阁文人群等都与僧人交游密切;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东南扬州、杭州为中心还是以北方大都为中心的文人雅集活动中,都能发现僧人的身影。如北方的雪堂雅集中的雪堂上人,“雪堂上人禅悦余暇,乐从贤士夫游。诸公亦赏其爽朗不凡,略去藩篱,与同形迹,以道义定交,文雅相接”[13](第6册,P196);南方的玉山雅集中的释良琦,“玉山草堂中诸词客每有倡和,必琦为发端,诸公雅推重之。”[14](卷3)
由此可见,中唐以来儒士反对佛教以振兴儒家的传统已经消失,元代很多重要文人都与僧人有或深或浅的交情,“以余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数十人 ”[13](第41册,P298),与僧人交往已经成为整个文人群体的共同行为。
(二)儒释交游的平等性 元代文人与僧人的交游活动在主客体关系上具有平等性。其一,儒释在雅集唱和中的平等性。元以前雅集活动都是以文人为中心,即组织者、参与者都是文人;但是到了元代,雅集活动却变成文人与僧人共同参与,甚至出现了以僧人为中心、由僧人组织诗社雅集唱和的现象,用以宣传佛法的莲社也大量出现。“粹上人由天台绝海泝江,历参浙水西诸名山,而雅喜与贤士大夫游,声称藉甚。……搢绅先生闻其行,争为歌诗以伟之……”[13](第50册,P226-227)再如著名的雪堂雅集,就是僧人雪堂上人在天庆寺组织的一次雅集活动。由此可见,僧人在与文人的交往中已经居于对等甚至中心地位。其二,儒释在功名追求上的平等性。文人不再鄙夷僧人为官,甚至出现很多文人投附高僧,以期能被引进推荐的现象。此外,僧人为官下场不好的现象消失,很多僧人,如刘秉忠、不忽木、杨琏真加等居于高位。
三、元代文人与僧人关系出现新变的原因
崛起于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吸收先进汉文化,用汉法治汉人;另一方面又竭力保持蒙古族的民族传统,保证蒙古民族的特权。因此,“元王朝在统治方针与政策制定理念方面都体现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游牧特质与农耕文化交错共存的特征。”[15](P6)文人与僧人的关系在元代发生新变,最根本上的原因在于元代统治者采取了与前朝截然不同的政策。富有蒙古族特色的宗教政策和用人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僧人与文人身份地位,促使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此外,在异族第一次全面统治中原的特殊背景下,元代文人产生了前代文人所未曾体会过的独特复杂心态,也是文人与僧人关系发生新变的重要原因。
(一)元代宗教政策的变化 宗教信仰在蒙古族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元代统治者在制定宗教政策时,自然而然的对宗教抱有亲近的态度。有元一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都给予保护支持,但也有偏重,藏传萨迦派在所有宗教中地位最为显赫。“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16](第15册,P4517)元代皇室信仰藏传萨迦派佛教,其领袖被称为“帝师”,还设置宣政院主管藏传佛教事务。
亲近佛教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元以前僧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一些有名望的高僧,在政治上,位高权重,结交朝廷重臣,掌握着一定的仕进渠道;在经济上,广建寺庙,占有大量土地,收入殷实;在文化上,凭借佛教是国教的特殊地位,具有一定的话语阐释权。僧人地位的提升是文人与僧人的关系得以产生新变的前提。政治上的优势,使得文人不得不以平等的关系与僧人交往;经济上的优势,使得僧人有能力自己主办雅会集宴,成为诗会的主导者;文化上的优势,使得佛教文化成为强势文化,能够冲击渗透儒学,使得文人深受佛学的影响。
(二)元代用人政策的变化 元代统治者重道轻文,重视实用之学,轻视辞章之学。忽必烈曾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17](P230)“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18](P3746)在这种重视实用、轻视辞章的用人思想指导下,元初几十年未开科举。元仁宗时,虽重开科举,却仍以重实用为指导思想取士,“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16](第7册,P2018)此外,元代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19](P729)在这种官制下,汉人和南人大多只能充任属员。
重道轻文影响下的科举时行时辍,蒙古人才能为百官之长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文人仕进之路变得狭窄,地位下降,阶级优势丧失。九儒十丐之说,虽是误传,却反应了“儒户的实际处境,远逊于同时代的僧、道户,和以前各朝士人享受的待遇,更难以相提并论”的状况。[20](P3)
文人阶层地位的下降,使他们丧失了对僧人的控制力。政治上,文人丧失了以儒家理念制定管理僧人的僧官制度的管理权;经济上,文人丧失了经济支撑,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卖弄文艺;文化上,文人丧失了话语权,学术舆论不再以文人独尊。阶层地位的下降,还导致了文人群体的分流:一部分文人选择避世隐居;一部分文人顺时而变,以经济、实用之策追求功名;一部分文人虽亦向往功名,但空有辞赋之学而无用,只能沦落下层,成为所谓的“书会才人”。以姚枢、姚燧、许衡、吴澄等为代表的文人,批判继承宋代理学思想,去除理学中空谈的心性义理之辩,转而注重实务的经世致用之理,以拯救生民为己任,将说理之学应用于政治实践,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成为馆阁文人。他们为了顺应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僧人往来,改变了自中唐以来儒士排斥佛教的传统。以“书会才人”为代表的文人,虽然有不为世用的愤激之情,但并未放弃寻找出仕的机会,投附结交位高权重的僧人,成为他们攀登“官梯”的绝好途经。
概而言之,元代用人政策所造成的文人地位下降,是文人与僧人关系发生新变的根源所在。文人分流后,馆阁文人的数量虽然在整个文人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他们身居要职,为普通文人所羡慕,他们的行为态度对文人群体具有引导示范的作用,馆阁文人对待僧人态度的改变是新变得以发生的关键。下层文人数量众多,是文人的主体部分,他们对待僧人态度的转变既是对上层文人的呼应,又是自身追求功名的需要,这就使得新变得以持续和扩大。因此,下层文人对待僧人态度的转变是新变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三)元代文人心态的变化 蒙古族统治下的文人,拥有远异于前代文人的复杂心态,这也是文人与僧人关系在元代得以发生新变的重要原因。
遗民文人心怀故国,严守华夷之别,拒绝出仕异族政权。面对天下战乱纷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处境,他们“视天下无可为,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13](第1册,P669)“盖兵乱已极,衣冠之流,铅椠之士,逃于其类而为之,非佛氏之为教或当然也”,[13](第12册,P135)或避世山林,或遁入空门。一大批文人由儒入释,文人与僧人有了共同的文化背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释之间的隔阂,使得文人与僧人的交往更加平等,关系更加持久。
出仕文人心态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作为汉族士人,出仕异族,在世人眼中是“失节”的表现,会遭到亲友们的鄙视谴责;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也并非真正信任汉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疏远之臣’……因而处处小心,而且不敢担任会招致怨恨的重要职务”,[21]出仕文人既没有隐居文人那样彻底拒绝官位的决心,又不能对家族亲友的非议听而不闻。外部的谴责和内心的自责,使得他们的心灵无以依附,时常处于痛苦之中。在这种特殊的心态下,出仕文人需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受蒙古统治者重视的佛教自然而然地走进他们的心灵。“季代儒者谈浮屠氏学十八九,而未见浮屠谈吾儒者”,[13](第41册,P291)他们亲近佛教,与僧人交游唱和,用以淡化内心的痛苦,获得心灵的安宁。以赵孟頫为例,大宋王孙的身世与仕于蒙古的经历,让他心灵饱受折磨。同乡好友钱选不耻于他仕于异族仇敌,“至元间,子昂征入,功名赫赫,诸人皆依附取官。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诗画以老。”[22](P91)“缅怀老尊宿,燕坐毗庐峰。尘缘苦未断,无由往相从。一宿返归掉,回望但青葱。”[23](P554)赵孟頫通过书画等方式与中峰明本、笑隐大诉等僧人交游往来,以“吏隐”的生活态度来排遣内心的矛盾痛苦。出仕文人因消解复杂心态的需要而出入佛学,使得儒释之间的交往具有更为深厚的现实基础。
四、余论
元代统治者的宗教、用人政策的变化,文人的独特而复杂的心理变化,造成了文人与僧人关系的新变:儒释之间平等交游成为贯穿时代的普遍现象。这一新变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首先,儒释思想上的相互渗透,使得文人禅意化,僧人文人化(俗化)。其次,大量文人由儒如佛,增加了僧人中的文化人分量,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再次,元代主流文学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佛教书写,使得元代文学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