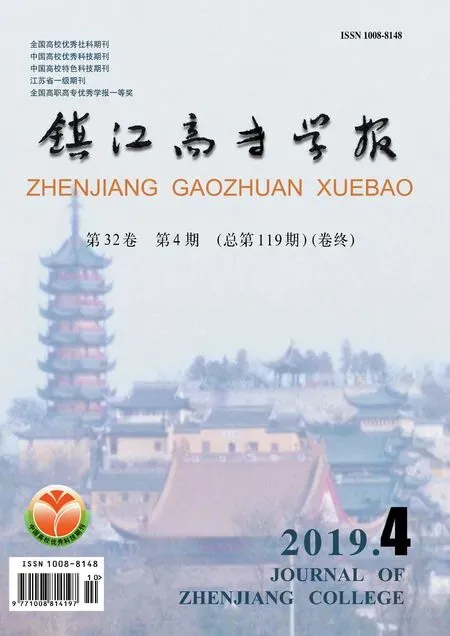论书法“墨韵”美
曹 斌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系,四川 广元 628017)
魏晋时期,文学艺术以“韵”为审美标准,如“体韵”“雅韵”“风韵”等,体现绵密、轻盈、轻柔之形态内容。王羲之谓:“点画之间皆有意。”黄庭坚说:“凡书画当先观其韵。”杨慎在《墨池琐录》云:“书法以韵相胜。”谢赫《六法》指出,“气韵”除了“生动”之外,还要“骨法用笔”。古人认为“中锋笔圆则气厚”。清布颜图说:“气韵出于墨,生动出于笔。”书法创作中,“韵”主要体现在用笔、用墨、结字、章法的生动变化中。“墨韵”是书法“韵”的重要因素。通过用笔的提按、使转、疾速产生墨韵美,通过浓墨、淡墨、枯墨、润墨的变化产生意蕴美。
1 文化内蕴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制作的墨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墨。秦墨呈圆柱颗粒状,颜色纯黑。早在殷商时期,先民们便用朱色或黑色矿物颜料在陶器上绘制纹饰。考古发现,殷商出土的陶片上的“祀”字,墨色黝黑,起止露锋,笔画富有弹性,用笔纯熟。许慎《说文解字》云:“墨,书墨也。从土从黑,黑亦声。莫北切。”[1]454《考工记》载:“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黑”属于北方正色系,这和传统的“尚黑”有关。《礼记·檀弓》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2]28先秦历代对色彩的认识是从“黑”到“白”再到“赤”。现代考古发现,原始社会大量“黑陶”、部分彩陶上“黑”色纹饰是先民们以“黑”为美的见证。
以“黑”为美,犹如点睛。顾长康画人点睛可“传神”。《人物志·九征》谓:“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苏轼《仇池笔记》说:“今世论墨,惟取其光而不黑,是为弃墨。黑而不光,索然无神气,亦复安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儿目睛,乃佳。”[3]79
早期书法中,墨的“黑”与甲骨、青铜、竹简、木牍、绢帛等载体(包括后来的白色宣纸)暗含阴阳之理。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苏轼《送参廖师》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静”才能体会“动”之妙,墨之黑才能体现白色宣纸之空,“空”才能纳万境于胸。
至春秋时期,墨色由单一的“黑亮如漆”变为丰富多彩。书法中,墨色既有“浓黑”,又有“淡润”。张彦远主张“运墨五色俱”。王维、苏轼、董其昌以诗道禅,艺入禅境,以无色之墨凝练人生的诠释。朱良志认为:“墨色就是不着色,以无色貌净天下之色。”[3]95
2 影响因素
书法也称“线条艺术”“抽象艺术”“表现艺术”,包括笔法、结构、章法、墨法。若“用墨”是书法的“血”“肉”,“用笔”则是书法的“筋”“骨”。康有为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4]146墨的变化、墨韵的形成、意境的生成离不开笔之运用。当代人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书法是有创造、有个性的,既悠扬,又抒情,通过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产生如同音乐旋律一般的“有意味的形式”。
用笔是产生墨韵美的前提。朱和羹《临池心解》云:“字法本于笔,成于墨。笔实则墨沉,笔浮则墨漂。”[5]738浓墨、淡墨、润墨、枯墨的灵“活”使用,通过提按、使转、迅疾等用笔变化,显示书法的自然美,体现“韵味”。首先,提按则墨韵流畅。运用手腕带动笔尖通过提按、衄措的复合动作,将偏侧的笔锋收归画中。书写时,下笔即迅速将笔毫提起,锋尖已入画,保证墨汁从锋尖均匀地注入纸张。笔毫下按,与纸的接触面增大,笔肚上的墨容易下注,如隶书等较厚重线条的书写。提得起、稳得住是提按的关键。“提”要恰到好处,以锋收归画中为度。“提”是腕中的一种感觉,将笔锋提起,笔身保持直立状,注墨均匀,点画丰实饱满,墨韵流畅。其次,使转则墨韵沉着。转折时用笔贵在圆劲、力润,具有弹性的曲线美。转折时,依靠手腕协调配合,保持中锋用笔。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云:“转折需暗过,暗过处,又要留处行,行处留,乃得真诀。”[5]733最后,用笔疾速则墨韵变化多端。用笔迅疾使墨色变化多端,达到“飞白”的效果,墨韵十足。
书体不同,墨韵不同。《笔阵图》云:“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飏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5]23篆书圆润婉转、章草古朴洒落、八分方劲峻利、飞白枯润自然,体现了笔韵变化。行草、篆隶重浓墨,以显示笔力遒劲。李之仪《姑溪集》称:“东坡研墨几如糊方染笔。”楷书用墨不浓,稍加点水,以保证枯中有润。行书蘸墨量多于楷书,但浓度略低,墨色层次变化多。狂草是综合性用墨,酣畅淋漓,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枯中有润,燥中有湿,笔势迅疾,墨虽枯,但有神采,如颜真卿、董其昌用墨。
书写载体不同,如简牍、绢帛、熟纸、半生熟纸、生宣纸的性能、质地不同,墨韵效果不同。而宋代以后的文人,因性情、用水、用墨习惯不同,将墨韵变化推向了时代巅峰。
3 表现
3.1 浓墨的神采美
行草、篆隶中常用浓墨,秦汉简牍也以浓墨为主。浓墨,墨色浓,黑白对比强烈,用笔有力度,精神气十足。殷商至两汉时期,书写以实用为主,墨色以“黑亮如漆”为标准。简牍质地不同,会出现氤氲的墨色效果和率意的枯墨,是“书佐”无意而为之。孙过庭《书谱》谓:“带燥方润,将浓遂枯。”[6]89魏晋至隋唐,用墨已朝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苏轼认为,用好浓墨可以“传神”“抒怀”。苏轼的书法墨彩清莹,神韵十足,“如小儿目睛”。欧阳询认为“墨绝浓必滞锋毫”。书法创作时,笔毫完全发开,饱蘸墨汁,则意欲圆融、流丽活泼。刘墉用墨以浓用拙,笔笔浓墨,人称“浓墨宰相”,如《小楷七言诗》中“已”“混”“生”等字。墨气浓厚,墨色厚泽,浓墨漆黑如糊,为清代碑学书家的墨韵特征,如金农《篆书临峄山碑》、伊秉绶《隶书立轴》等。有浓必有淡,浓淡变化甚为微妙。如米芾手札、吴昌硕临《石鼓文》常出现中黑边枯之笔,甚至飞白现象。
3.2 淡墨的恬淡美
生宣纸具有渗化作用,淡墨有时更能表达书法的“气韵”。杜甫诗云:“元气淋漓障犹湿。”淡墨的使用讲究方法,否则“墨淡则伤神采”[6]2。《临池管见》云:“浓欲其活,淡欲其华,活与华,非墨宽不可。”[5]720笔毫铺开,笔尖点入砚池,如用篙点水,墨从笔尖吸入,笔酣畅,墨饱满。书写时,墨从笔尖出,墨湿润而笔毫凝聚。董其昌倡导“墨气”,一生求“淡”,其意有二:书法常用淡墨,淡不腻笔,以求流畅、淡雅;意境求“淡”,“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他认为“淡”与绘画“气韵”一样,“必由天骨”。“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董其昌认为:“诗文书画,老而淡。”王摩诘的画使用淡墨渲染,有别于北宗的轮廓勾勒,由淡而生“韵”。他将此理运用于书法创作,意境“虚静、恬淡”。王文治继承了董其昌的淡墨法,以淡墨为主,间以浓墨变化。
3.3 枯墨的沉稳美
行草书创作中,常出现“飞白”“枯笔”“渴笔”现象,墨韵独特。
“飞白”,在笔画书写时,笔毫中墨尽而丝丝露白的痕迹,能够表现迅疾的笔势。张怀瓘《书断》记载:“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7]102
“枯笔”,笔毫中所含浓墨书写完后,笔毫与纸面摩擦产生的笔触,以中锋用笔为前提,笔力强劲,笔势迅疾,虽笔干墨枯,但有神采气韵。李日华《评书帖》认为,“刷字”出自“飞白运帚”,若运笔“迅疾,中含枯润”,则有“天成之妙”。“枯笔”,在行草中表现气势的酣畅、墨色的沉稳,如米芾的刷字;在隶书中表现线条的厚重。
“渴笔”,笔毫中墨已尽,在宣纸上“挤”出墨。中锋运笔,行笔速度稍慢,笔力迅疾,气势酣畅。《祭侄文稿》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米芾《虹县诗》中“满船”渴笔取势,“书画”则浓墨重书;“明月”又是“渴笔”,彰显古拙老辣、墨色沉稳的墨韵美。
3.4 润墨的韵味美
蒋骥言:“用墨,润则有肉,燥则有骨。”用墨间杂枯涩,润燥相宜。若太枯、太燥,如草木枯萎,缺乏生气。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用墨需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也。”[5]542要墨韵滋润,须控制用墨水分和运笔速度。“水太渍,则肉散。”运笔,力要稳,要提得起笔,否则便成死墨。
华琳在《南宗抉秘》中提出,墨分五色,即“黑”“浓”“干”“湿”“淡”。好的作品必是多种墨色综合运用。苏轼喜用浓墨,但其墨色变化微妙。浓中微淡,锋藏于墨,没有太淡或太枯,体现了儒家的中和美。米芾《致彦和国士帖》浓淡结合,枯湿相宜,是多种墨色运用的经典之作。第1行“芾”字起笔浓墨,书至“经”字再蘸浓墨;到第2行“胜”字,墨已枯,“山”字再蘸浓墨;第4行“给”“一”字开始,墨稍淡,直到“交”字,墨已枯;第5行“也”字复用浓墨;“本欲来日送”开始,笔毫中墨已变枯,书写速度明显放慢,墨从笔毫中“挤”出,在纸上“擦”出一种效果;“耳”字末笔换锋直下,此时,锋已散,好在巧妙地补了一笔。
4 意蕴美
“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8]27以笔墨的外在形式表现书家的内心体验。书法既是“形学”,又是“心学”[9]139。“形”指书法外在结构、用笔、用墨、章法构成的形式美,“心”指书法家内在学问、修养。意蕴是书法的“灵魂”,以笔韵、墨韵构成作品的“神韵”。王僧虔《笔意赞》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5]62创作必须把意蕴与物象结合起来,做到蕴以象尽,象以蕴而神,即“意中有境,境中有意”。
“墨韵”的变化给书法创作带来无穷魅力。浓墨的使用在于“传神”,但要注意“浓不凝滞”,意欲圆融、流丽活泼才能表现“韵”的神采。淡墨的使用,要结合“用水”之法及宣纸的性能,“淡不浮薄”,方能展现虚静、恬淡的书法意境。枯墨的使用,注意笔势迅疾,以体现线条的厚重感与沉稳美。润墨的使用因墨色的润而极富韵味美。书法用笔、用墨变化产生墨韵美。李嗣真评价王羲之书法“阴阳寒暑,四时调畅”“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张怀瓘谓:“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复本谓也。书复于本,上则注于自然,次则归于篆籀。”[7]259苏轼崇尚自然,注重主观情感作用,追求创作心态自由。“笔秃千管,墨破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追求“意”的畅达不羁,反对“法”的束手束脚。书法以自然美为审美目标,追求中和美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