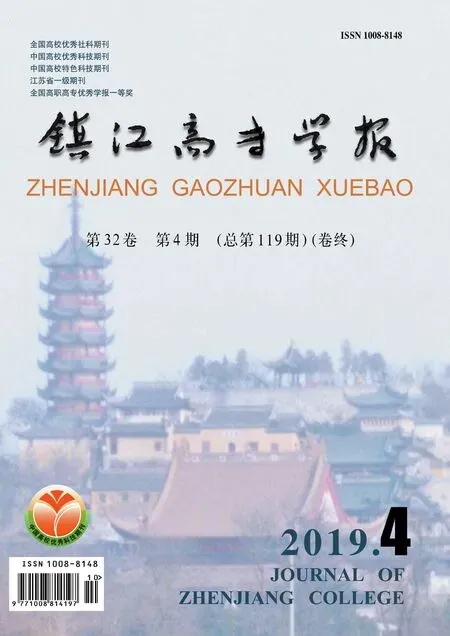论赛珍珠作品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以《生命与爱》和《结发妻》为例
李晓华,张 雅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4020)
赛珍珠81年丰富的人生经历具有中西结合的特点,这也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赛珍珠的前半生在中国度过,《结发妻》是她早年以中国人为题材写成的著名短篇小说,《生命与爱》是她回美国后,于晚年写就的以美国人为题材的经典短篇小说。就目前国内赛珍珠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研究而言,大多从其中国题材作品角度进行探究,将其外国题材作品与中国题材作品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为数甚少。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互动在国与国之间已成为常态,深入研究赛珍珠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不仅具有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最早于1725年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阐发。杨须爱将这一思想理论进行了归纳,肯定了其积极性的一面,如“文化是由特定社会的所有行为模式构成,是人类心理的产物,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和价值标准”“民族是文化的实体,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1]。姚君伟分析了赛珍珠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作品,认为赛珍珠是“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者”[2]。笔者在姚君伟的论证基础上,将赛珍珠早年和晚年的两个代表短篇进行对比,探究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在文中的体现,明晰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行为背后的文化差异性和赛珍珠传达的存异求和、天下一家的理想。
1 理性坚定、保守固执的“旧”人与激进开放、盲目乐观的“新”人
《结发妻》中,渊的父亲是个笃信孔子儒家文化的商人,从唐朝以来“重冠冕”的传统观念使得其“对于自己的儿子并无奢望,只想他出去做一个大官”[3]28。他不赞同渊的全盘西化,告诫渊“最好一面还是熟读四书,一面到洋学堂去求学”[3]29。此言表现出赛珍珠具有建立在中西文化基础上的辩证思维。
渊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虽说在家里有一定的话语权,却不敢违背家庭的最高权威——渊的父亲。渊的母亲亲自为儿子挑选门当户对的妻子,以儿子自选的妻子为异类,否定儿子的西学成果,由此可看出她既看不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无法获取知识的贫苦大众,同样也无视和否定积极向西方学习新知识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妇道思想已内化成其人格的一部分。
结发妻自从父母死后,便“埋葬在婆家”[3]23,她在老宅守了7年活寡,数载光阴在侍奉公婆、管教子女、操持家务等忙碌中如梦般挨过,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来,竟等来一纸休书。无奈与痛苦中,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能保证灵位进入婆家祠堂。结发妻自尽的横梁在风水上是形煞。赛珍珠在这里借“横梁”象征渊与结发妻注定的悲剧婚姻,同时,也象征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新”“旧”文化的阻隔。辜鸿铭在谈到中国妇女的婚姻生活时曾说过,“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事实上,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4]65。结发妻的形象令人联想到赛珍珠的《东风·西风》中的桂兰。与之相比,结发妻这个形象在当时更为普遍,所以结发妻只有一个代称。桂兰在青少年时代的命运虽与结发妻相似,但所幸的是,她的丈夫在国外习得的家庭文化更为人性化,其丈夫的态度与渊对待结发妻的态度完全不同。结发妻与《生命与爱》中的葛莱辛也存在某种相似性。结发妻在婚后10年间,思想如葛莱辛一般固执而守旧,两人对新文化都有着本能的排斥,在旧文化中寻找出路方面都表现得异常坚定。结发妻离开学校时冷静而执着,决定以死了结时又是异常决绝。葛莱辛在毁掉玩偶屋前也表现得异常平静。这些特质,若从固守旧文化方面来看,是难以改变的人性缺点;若从与新文化存异求和方面来看,它们又都会变为盲目求新者所不具备的优点。
《生命与爱》里的葛莱辛和《结发妻》里的渊的父母、结发妻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旧”人的典型,因文化差异而各有不同表现。渊的父亲虽保守,在文化上亦有包容的一面;葛莱辛则表现出更专制的一面。葛莱辛擅于积累财富,终身未婚,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偶得玩偶屋后,他曾短暂享受过作为玩偶们的天父所带来的权力上的满足感,但在发现圣母的存在后,内心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一神论思想促使他毁灭了玩偶屋,但终究他也没能得到上帝的任何启示,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孤独与绝望。
作为被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渊和他自选的未婚妻显然并非绝对正面的人物。两人是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留学生的典型,然而他们在摒弃传统旧文化后,却为新文化所束缚而不自知。渊坚决地对父亲说“四书今已无用”[3]21。渊接触了“新”文化,就摈弃了“旧”文化:丢掉毛笔,改用外国金笔,拒绝再读四书,拒绝与结发妻沟通和同房,单方面对她发出指令,单方面提出离婚等。科学知识、西方宗教文化、军国主义等等一系列思想在他脆弱的心灵里混杂。我们在渊的身上也能看到葛莱辛的影子。葛莱辛在玩偶屋里对玩偶们发号施令,稍有不从,非打即骂。渊留学归家后对结发妻的冷漠与疏离也是一种冷暴力的表现。渊受了7年新文化的熏陶,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彻底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很显然,渊表现出的这种“新”并不被赛珍珠所认可。
真正的“新”体现在玩偶屋里的玩偶们身上,体现在渊的儿女身上,尤其是渊的女儿秀兰身上。《结发妻》中的一双儿女形象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他们象征着赛珍珠所期待的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光明未来。未被缠足的女儿,强烈渴望进新学堂,“若不让我去,我就去死”[3]46。儿子虽恃宠而骄,活泼顽劣,却对新兴科技表现出极大兴趣,当父亲告诉他可以带他去坐火车、轮船、飞机时,他开心得忘乎所以。玩偶屋里的老夫人领着大小不一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依靠,互为独立,过着赛珍珠理想化的中美文化完美融合的家庭生活。玩偶们在伪善的“慈父”葛莱辛统治下,丧失了民主和自由,偶尔违抗就会招来葛莱辛一顿打骂。但摇篮里的婴儿是新生命和希望的象征,如同《东风·西风》中桂兰哥哥和美国嫂子的爱情结晶一般,融合了中西文化特征,体现了赛珍珠存异求和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
赛珍珠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她以比较客观的创作态度塑造了众多不同年龄、性别和国籍的人物,又在主观情感上以中国为母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好感,表现出在文化思想上、在秉持情感上更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
2 在旧文化中寻求出路的“旧”爱与在新文化中迷失自我的“新”爱
《结发妻》中的渊并未爱过结发妻,在他看来,结发妻不过是为他的家族延续后代的“我儿的妈”[3]8罢了。结发妻性格内敛,对渊沉默而顺从。因为封建礼法的限制,她竭力克制情感。赛珍珠通过刻画结发妻的眉毛和耳根的微妙变化表现出她的心路历程,令人印象深刻。结发妻想到渊是她的主,“忽然感到羞涩,耳根渐渐地绯红”[3]9,听到宾客预祝渊连生贵子,“耳根下面的血流又加高热度了”[3]12,当她放弃了接受新知的机会,试图在她所认可和熟悉的旧文化和旧体制内寻求躲避新文化的猛烈冲击的避风港时,她用着近乎绝望的语气抽噎着说“我再也不能离开这里了”,听说渊要休妻另娶,且要赶走她、带走她的儿女之后,“她两次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双眉在眼上耸动”[3]68。面对这一切变故,她无计可施,只能被迫以死抗争。
渊的“新”爱是跟他一起留过洋的女同学。他爱她,也迫切希望父母能接纳她;渊的女同学勇敢地冲破了传统包办婚姻的牢笼,憧憬于自主选择的新的婚姻生活。然而渊彻底抛弃旧传统,全盘西化,最终能否与“新”爱有个圆满结局不得可知,渊的女同学自主选择的在封建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渊能否给她完美的婚姻生活,这是个当时激进而盲目的热血青年们来不及深思的时代问题。
渊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及希望得一“智识之妻”陪伴他,为他料理家务与教育孩子,他认为这就是新时代妻与丈夫的“并立平等”。渊所憧憬的完美婚姻不过是赛珍珠父母、赛珍珠与第一任丈夫婚姻的翻版,与民主和平等相悖的婚姻显然并不为赛珍珠所推崇,她理想的大家庭是《生命与爱》里的玩偶屋。自从有了玩偶屋,葛莱辛很快抛弃了其他收藏品,葛莱辛“发觉这就是他一生中所寻求的东西。这儿——一个真正的家和家属,还有听从他的孩子们”[5]56。但顽固的“一神论”思想还是使他追随了他的上帝,也使他亲手毁灭了精神乐园。郭清香曾引用《圣经》中耶稣的一段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掉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6]153。玩偶屋里的女性形象是基督的受害者,耶稣不仅以神的权威占据她们的心灵,还以男性的优越控制了她们的个性。我们从文本后面圣母“脸上显著温和的表情”可以读出,玩偶屋里的女性的觉醒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妇女身上产生了一种不可压抑的独立感和表达自我的欲望”[7]。但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独裁者的统治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固化,玩偶屋中女性的女性意识不可能成为一种能真正对抗男性权势的力量。
《结发妻》从渊被动择“旧”爱到主动寻“新”爱再到“旧”爱自毁结束。渊有权自主选择新的妻子,赛珍珠借渊的父亲之口提出了较折中的解决方法,渊的父亲曾寄给渊一封信,“今且允吾爱女随余等而居,为汝抚育子女,切勿令知其已遭离异为要。余绝不以此言告伊,居此世外桃源中,伊亦无庸知矣”[3]65。《生命与爱》中的葛莱辛是从主动择“新”爱到无意发现宿敌再到主动毁“新”爱终结,只因为葛莱辛无法理性地面对异文化,做不到存异求和,无法容忍文化共存。两部小说共同说明了最适合爱存活的是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环境。
3 源远流长的“旧”思想与继往开来的“新”思想的激烈碰撞至理性融合
赛珍珠的父亲是保守的基督教徒,母亲是虔诚的清教徒,“每天上午,赛珍珠会在母亲的安排下阅读美国的教科书,而一到下午,父母又给她请了一位中国老秀才做家庭教师”[8]24。终其一生,赛珍珠都习惯从中西方两种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赛珍珠接受的并非只是儒家思想,对中国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她晚年仍清楚地记得:“孔先生细心地讲授了道家学说……他拥护两者的结合。他说:‘让你的行为是儒家的,让你的情感和思想是道家的。’”[9]60赛珍珠的一生的确遵循了先生的教诲,“学会以自己的方式去随我所愿,自由而又创造性地感受”[9]61。
渊抛下父母妻儿,离开祖宅外出留学,也彻底抛弃了中国传统“旧”思想。渊重新找了一个跟他有相同“新”思想的良伴,并回到祖宅欲与结发妻离婚。结发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思想的迅猛冲击,无勇气和能力抛弃固有的“旧”思想。赛珍珠对于渊这种非旧即新做法的态度,通过渊的父亲给渊的信表达了出来,“设汝必如汝意,则任此可怜弱息随余等终其余年,即不为汝妇,亦为余辈女也。余等爱之不稍变”[3]64。渊的旧式父亲尚能体恤儿媳娘家父母双亡、家宅钱财也被娘家兄弟们悉数瓜分,而渊却变得如此冷血和不近人情。渊只谈民主平等自由,抛弃孝悌忠信,失去了本性。在《生命与爱》中,葛莱辛的冷血和不近人情则体现在禁止约翰和玛丽夫妻俩亲吻,让老祖母外出工作来谋生活,打翻摇篮,对躺在地上两天的婴儿不闻不问。赛珍珠深刻揭露了中国和美国两个家庭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自私,对已婚女性的尴尬境地给予深切同情。
葛莱辛也是一个丧失自然性的人。起初,玩偶屋看似在慢慢治愈他的异化、病态的人性,赛珍珠借玩偶们传递了“新思想”,诸如“人性中有神性的光辉,人的生命有着神的高贵”[6]153,248、建立中美文化融合的大家庭等。但顽固的“一神论”思想又使葛莱辛自我否定,直至作出丧失理性的举动。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称葛莱辛有一个太窄的心灵,只可容纳他的上帝,威廉·詹姆士把它称作“奉神病状态”。确乎,只有在遵循自然纯真本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人类社会才会走向真正的幸福与和谐;反之,如果人类迷失了本性,那么无论社会多么文明、科技多么发达,人类社会依然会长期处于一种无谓的争斗状态,永远不得安宁。
赛珍珠曾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家庭,她认为中国传统大家庭原本的、未染上摩登味的生活是怡情宜居和自然的,是纯粹中国的。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如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联系得那样紧密,这是赛珍珠推崇中国式家庭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个一心追求‘上帝事业’、不顾家庭的典型传教士,这给赛珍珠造成了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父爱的缺失”[7]54。从《结发妻》与《生命与爱》中,我们可看出,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理性有着由衷的赞美和推崇。赛珍珠在《生命与爱》中对玩偶屋进行了理想化的建构。她舍弃了《结发妻》里的老父亲首位制,取而代之的是老夫人为一家之尊。中国封建传统家庭强调长幼尊卑、强调夫权,美国家庭更注重平等、自由和个性独立。玩偶们组成的家庭是赛珍珠心目中中西合璧的理想家庭的代表,一家子黄头发蓝眼睛的老老少少以老夫人为中心,既和谐地居住在一起,又相对独立地分隔于不同的房间,充分体现出赛珍珠是一位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者。
4 东方“旧”信仰的和谐包容与西方“新”宗教的专一难容
《结发妻》中,渊的父亲是孔子的信徒,渊的母亲是终身吃素、从不杀生的虔诚佛教徒。面对渊母亲的信仰,父亲只是平和地对待,“信你的神罢,不过你在怎样的季候里去求怎样的东西,我相信你是容易办到的”[3]11。这句话充满了先秦的实践理性精神。自南北朝以后,儒佛道互相攻讦辩论,在唐代三者逐渐协调共生。赛珍珠接受了普通中国民众的宗教立场,认为“每一种宗教都是混杂在迷信和虚假中的真实和善良,宗教只不过是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信念和行为而创造的”[10]152。
渊有不同于父母的另一种信仰,他“信仰那新奇的战舰、犀利的炮火、精锐的陆军……”[3]30。渊留洋7年,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在基督教文化中,教会提倡“禁欲”,对于男女关系强调“要节制”,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夫妻生活应是为了传宗接代,婚姻中夫妻关系以男人为主、女人为辅。所以渊才会在回家第一晚即对结发妻说“现在我们免了这种形式罢,不但今晚”[3]14。渊所期待的不过是能为他料理新家、替他教育子女的伴侣,这与赛珍珠父亲对赛珍珠母亲的态度何其相似。
相比于渊,渊的父亲对待异国文化的态度要更加理性,他劝告渊既要学习他国文化也需熟读本国经典。渊的父亲深感忧虑,“我的孙儿将来大了会不懂得孝悌忠信”[3]32。渊的父亲的劝告体现了赛珍珠一直坚持的多元文化观,赛珍珠认为多元文化观是中国文化中最可贵的精神。
《生命与爱》中的宗教文化冲突更加明显和激烈。异质宗教互不相容,同源异派间的冲突也一样激烈。当葛莱辛意识到自己握有绝对的权力时,他就从“父亲变成了天父,醉心于他自己全能的力量”[5]61,野蛮而残忍地滥用“神权”。葛莱辛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赛珍珠对轻视妻子和患有“厌女症”的父亲的控诉与不满。葛莱辛效仿上帝对“新”人进行最后的审判。做完这一切后,“葛莱辛却先走到窗外去,他看着天空,已是黎明时模糊的淡蓝色。在他不停地盯视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5]64。作者暗示葛莱辛试图找到上帝的启示,却徒劳无获。通过描写葛莱辛对异教徒的敌视和仇恨,赛珍珠表达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怨愤与惋惜。新旧文化的冲突和不相容使得葛莱辛始终无法真正融入玩偶屋那个理想家庭。
《结发妻》里渊的父亲对渊的母亲代表的佛家文化体现出一种包容的态度,这与葛莱辛的狭隘形成了鲜明对照。赛珍珠曾说过:“……我既不属于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或许是它们两者,有时也不完全只是它们两者,我不是一名无神论者。”[11]257赛珍珠的基本宗教立场是基督教的立场,但是,因为受到儒家、道家等中国宗教思想的影响,她的宗教思想更加圆融、开放,特别是更强调回归人性。赛珍珠的生活经历“使她逐渐领悟到对待不同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坚持平等态度的重要性,以及反对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要求另一种文化这一行事方式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赛珍珠的跨文化、跨国界的实际生活促使她逐步确立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这是她的文化精神之源”[12]25。
5 结束语
渊全盘舍弃中国传统文化,老父亲对西方文化既觉新奇又畏缩不前,葛莱辛对圣母仇恨难容,玩偶屋式的理想大家庭制难以在美国立足,究其根源,这些都是新旧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悲剧。赛珍珠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应该彼此尊重、彼此融合,“爱”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恨是要付出代价的,相比之下,爱的代价要低得多”[13]116。赛珍珠善于以敏锐的眼光考察不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相互碰撞或相互冲突的,从而探讨人们如何通过“爱”进行沟通。读者从作者笔下的人物看到了持不同文化观的人对待文化差异所持的迥异态度。更为难得的是,两部小说展现了中美两种文化在家庭婚姻方面的独特性,也让人们看到了赛珍珠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朱希祥说过:“全球意识一方面要求注意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即各民族加强文化之间的联系,实行互补互渗;另一方面,又要求文化的多样化,要求各民族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以求全球文化丰富多彩、五光十色。”[14]43《生命与爱》最后一句颇具意味,“从这广大的空间,那遮住了天空的半边的,是一只巨大的、敏捷的、有力量的、复仇的手狠狠地击向着他”[5]64。在《结发妻》中,作者以结发妻自杀的代价启示读者,死是“旧”的终点,亦是“新”的起点。作者借这些艺术处理表达了自身观点:与其互相敌视,互相攻击,最后两败俱伤,不如采取存异求和的相处方式。赛珍珠推崇天下一家的理念,通过叙述两个家庭的文化冲突悲剧,探讨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空间和平共处的问题。作为一名“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者”[2],赛珍珠主张不论“新”与“旧”,在不同时空都只是相对概念,每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理解,共同为天下一家的理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