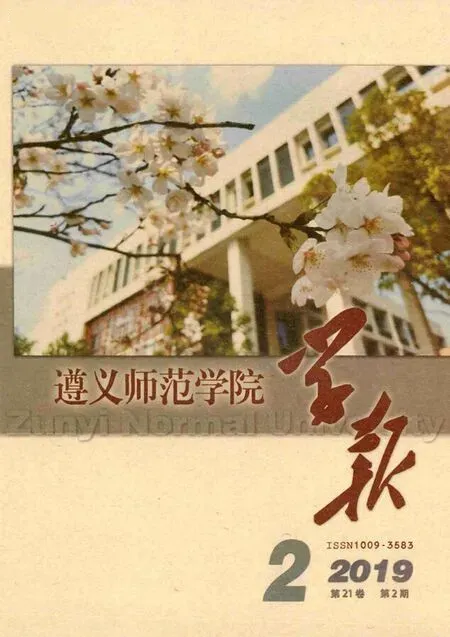审美人类学视角下仡佬族民歌研究
简 澈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 563006)
随着美学的发展和美学的研究视域得以不断扩大,从抽象的美学理论探究到具体文化现象审美的关注,是近些年来美学发展的趋势。美学家也逐渐从书斋走向田野,走向人民群众当中,探究其鲜活的民族文化当中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象等,由此逐渐形成审美人类学。对于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王杰等学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一是将美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考察审美现象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和特殊之处;二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较研究、整体研究、深入阐释文化细节的研究方法为主,广泛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美学从传统的单纯抽象思辨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三是使美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和阐释基础,具有解决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新生的审美问题的能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获得突破与创新。”[1]本文即试图借助人类学的方法对仡佬族的民歌进行分析研究,以探析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
仡佬族民族语言为仡佬语,属汉藏语系,也是中国众多无文字民族之一。在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仡佬凭借着口耳相传,积淀了异彩纷呈的传统文化,包括神话、宗教信仰、祭祀活动等等,其中仡佬的民歌因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得以较为完善地保存。“出门就爬坡,开口就唱歌,要问唱什么?处处皆是歌”,这首歌谣充分展示了民歌在仡佬族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民歌因为与生活相关,所以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其中所反映的审美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表现的是一种历史过程,“审美活动中一切现象及对其的思考,都是人类生存的产物,它们的展示形态、分类,命名与阐释,都随着生存的整体历史而发展,有历史的延续性,也有历史的差异性。”[2]P11-12
一、仡佬族民歌概况
通过对仡佬族民歌的梳理和田野调查的材料整理,可以发现仡佬族的民歌类型多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要围绕着日常生活展开,既有对于生产劳动的反映,如号子,打闹歌等,也有对于节日、仪式等方面的表达,如山歌、情歌、说福事等;既有关于仡佬族族源的神话,也有关于爱情、酒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前人学者对仡佬族民歌的分类非常多样化,本文借鉴前人分类的成果,从民歌内容的视角将仡佬族民歌分为劳动歌(包括号子、盘歌、打闹歌和苦歌等)、情歌、仪式歌(包括哭嫁歌、茶酒歌、丧葬歌等)三类。
(一)劳动歌
人类正是通过劳动而不断创造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许多的艺术都与劳动相关,在文学起源的各种流派当中,就有主张文学起源于劳动的“杭育杭育”派。作为山地农耕民族的仡佬族,也在世代的劳作当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民歌内容。仡佬族民歌主要包括劳动号子、薅草秧歌、采茶歌、砍柴歌等。
劳动号子是为了集体劳动时统一节奏、统一步伐、鼓舞干劲时所唱的民歌,主要表现于重型的体力活,包括采石,伐木等方面,如石工号子《桃子花溜子红》;薅草秧歌又称打闹歌,顾名思义,在劳动当中以歌唱的方式来凑热闹,以缓解劳动中的单调与疲乏。这类民歌有说有唱,以生活趣事、生产知识或典故为题材,重在增加劳作当中的趣味性和表达丰收的喜悦之情,如《高山画眉叫得乖》。除了劳作的热闹和丰收的喜悦,仡佬人对社会的不公和压迫感受也很深刻,口头传唱的《苦歌》即是典型代表,有一段为“石旮旯来石旮旯,石旮旯住的是仡家。石旮旯地仡家种,粮食收进地主家。仡佬头上两把刀,租子重来利息高。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细细蚂蚱平地飞,仡人少了仡人亏。仡人少了无处靠,东逃西散不成堆。”[3]
(二)情歌
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通过爱情使两性之间的结合,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得以延续,也促使不同群体之间通过婚姻手段结成联姻而编织起社会关系网络。与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比,仡佬族在爱情方面的表达与追求更为大胆和自由,或直抒胸臆,或借物传情。情歌是中国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与民族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社会对婚姻爱情控制较为严厉的地区,情歌以哀婉为主,而在仡佬族等爱情较为自由的地区,情歌以欢快为主。《仡佬族古歌》里面收录的《泡桐歌·夫妻游天》,通过讲述一对情人从相知到相恋的过程,表达仡佬族对自由爱情的赞美;《柑子树开白花》则直白地表达了仡佬族小伙对情姐的爱意。
(三)仪式歌
仪式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就现在所知的世界上的任何人群,都存在着特定的仪式。仪式一般被分为两大类:针对社会危难的强制仪式和针对个人的过渡仪式。仡佬族人民在历史上和现今的各种传统仪式性场域,都会演唱相应的歌曲,最主要包括傩戏、哭嫁歌、祭祖、酬神和酒歌等。最为典型的仪式歌当属丧葬歌。仡佬族的丧葬歌有着地域性的差异,但核心内容相似,包括“追溯天地初开,兄妹开亲,引种稻谷的神话传说,描述亡者灵魂跟随雄鸡指路、与祖先相聚,以及管理者为亡者祷祝、祭祀的内容”。[4]丧葬类的民歌相较于其它类型的民歌,从格式、韵律到内容都较为固定,与具有即兴创作特色的山歌和情歌有着明显的区别。
如果说以上的各种类型的仡佬族民歌都是集体性的创作的话,花灯调则主要是民间花灯艺人独自创作的歌谣,既包括歌舞合一的也包括对唱和群唱。
二、内容审美
仡佬民歌是仡佬族人民审美意识的活化石,通过对这些民歌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仡佬族人民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即美之所在。胡洁娜将仡佬族的审美总结为以勤劳为美、以智慧为美、以健壮为美。[5]笔者在此基础上认为,仡佬族民歌的审美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勤劳与乐观之美、快乐与忧愁之美、崇敬祖先与自然之美。
勤劳与乐观之美。“仡佬仡佬,开荒辟草”,作为最早繁衍于黔北地区的民族,为贵州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劳作在其生活当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劳动歌曲。通过这些歌曲,可以发现仡佬族的勤劳努力和在艰苦环境下的乐观精神。《采茶调》中唱道“四月采茶茶叶长,当门有个牧羊郎,牧得羊来秧又老,栽得秧来麦又黄”《栽秧歌》里面唱道:“大田栽秧先栽角,妹妹下田脱光脚,过路哥哥不要笑,丈夫小了莫奈何。”前者表现的是从采茶到麦熟这半年时间的农忙情景,后者则表现了在辛苦劳动当中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些民歌,纯粹是为了舒缓单调的劳动工作而唱的,如《扯谎歌》中唱道:“太阳出来(么悠悠)照半坡(呀么扯长扯呀),听我那个唱个(呀儿哟)扯谎(哩)歌(呀么索扬索),扯根葛藤(么悠悠)三抱大(呀么扯长扯呀),吊起那个太阳(呀儿哟)往上(哩)拖(呀么索扬索),半天云里(么悠悠)搭灶头(呀么扯长扯呀),抓把那个星宿(呀儿哟)下油(哩)锅(呀么索扬索);玉皇气的(么悠悠)吹胡子(呀么扯长扯呀),牛郎那个乐得(呀儿哟)笑呵呵(呀么索扬索)。”用葛藤吊太阳,在半天云里搭灶头,通过夸张的手法,将自然和生活事物联系起来,让闻者忍俊不禁。
快乐与忧愁之美。关于仡佬族的婚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比较自由,男女青年以歌为媒,以树石为证,从而结成良好姻缘;二是认为受汉族影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产物,如向零等认为,“古时,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仡佬族人与相邻的其他族人之间发生通婚关系——大部分地区仡佬族青年男女婚姻全由父母包办——黔北地区仡佬族婚前要哭嫁三天,直至上轿发亲。”[6]P154这两种观念在民歌当中都能找到证据。《情姐下河洗衣裳》中唱道:“情姐下河(哎)洗衣裳(啰),双脚踩在(哎)石梁梁(哎),手拿棒槌(哎)朝天打(啰),双眼观看(舍)少年郎,棒槌打在(哎)妹拇指(啰),痛就痛在(哎)郎心上(哎)。”而在哭嫁歌中则唱道:“做人媳妇做人难,歪风细雨要上山。落雨不得干衣服,天晴不得汗水干。”通过对情歌与哭嫁歌的比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仡佬族女性在情意绵绵的爱情、复杂的婆媳关系和艰苦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景的衬托,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新娘自己,通过对将来生活艰难困苦的预测,以突出父母亲和亲戚朋友对自己的关心或大家对新娘的关爱,烘托出难以别离之情。所以说,这种忧愁与其说是对未来生活艰苦与不确定性的哭诉与忧愁,还不如说是对家人的依恋与感谢。
崇敬祖先与自然。仡佬族在历史过程中,对给予他们生命的祖先和滋养他们成长的自然万物都抱以崇敬之情。黔北地区,生产生活方面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三月三,仡佬族最隆重的节日里,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祖先和山神树神等。在民歌方面,《泡桐歌》记载:“田土本是祖先开,收新祭祖本应该;田边地角都收到,男男女女一齐来;吃新祭祖要扫寨,扫除瘟疫和虫灾;五谷丰登六畜旺,清洁平安到材来。”[3]
三、形式审美
仡佬族民歌在形式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调式、旋律和节奏等方面。当然,作为集体创作的民歌,也有许多并未参照特定的旋律和调式,而是兴之所至对情感的抒发,节奏非常自由,如《民歌好唱难起头》。巴托克也说:“农民音乐实际上是活动在人类下意识中的自然力量所转化产生的结果,这是用最经济的形式和方法来表达乐思的典型范例。”[7]P45
从调式上看,仡佬族民歌以五声中的徵声羽声调式为主,如《情姐下河洗衣裳》《无情的哥哥穿草鞋》。在旋律方面,大跳音程是黔北仡佬族民歌当中非常重要的旋律特征,具体表现在纯四度、小六度在仡佬族民歌当中的反复出现。“道真县仡佬族民歌在旋律结构上,受地方民歌和其它民间文化的影响,大量运用跳进音程,形成了欢快跳跃、粗犷豪放的旋律特点。”[8]如以五声羽调式为主的《望郎歌》:“初一晨早(舍)去望郎(噢喂),扎双新鞋(舍伊哟)送(噢)小郎(噢)。”[9]P18
节奏、节拍没有固定性,表达上非常自由。灵活多变、不规律,适合于表现民歌的即兴创作、氛围与情感。对于节拍与音乐表现力之间的关系,张新林有过专门的论述:“二拍子的强弱规律有着行进的律动,最适合表现活泼、雄壮、热烈、刚健、欢庆的情景和场面。三拍子的强弱规律有着旋转、摇曳的律动,适合表现有舞蹈性质的轻巧、优美、诙谐、田园、安详的气氛和情感的乐曲。四拍子的强弱规律比起前两种来说就更具有抒情性,适宜于表现优雅、舒缓、雄伟、庄严、悲伤、温柔等多种情感的乐曲。”[10]仡佬民歌以二拍子为主,每句字数不限,以四字句和七字句等交替出现为主。
仡佬族民歌的另一大特点是装饰音或者说衬词的大量使用,在一些民歌里面,实词和衬词的数量旗鼓相当,如《桃子花,溜溜红》唱道:“桃子花哎溜溜红哎,哎呀扬喊咗哦来;要把那石哎王才,吆喊咗哦喂;撬走哟开哟喂,桃子花溜溜红哦;桃子花哎溜溜红哎,哎呀扬喊咗哦来。”在这一民歌中,衬词如“哎、喂、哟、啰”等,字数占了半数以上,两句表意的歌词中间,就夹杂着一句装饰音,这些衬词任意选取,不拘泥于形式,以达意为主。
四、意象审美
意象是指表意之象,即通过一些具象化的客观物体来表达其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民歌审美意象的以象表意特点,决定了创作手法上必然是以实显虚,以自然实境来显示创作主体的思想灵境,以自然景象的神姿妙态来表现创作主体的精神风采。”[11]在民歌的创作当中,创作主体往往会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与所描写的景物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种由虚和实两者结合所呈现出来的意象和意境是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仡佬族民歌所表现的情感虽然比较直白大胆,但不代表不采用相关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在情歌方面,比如“比”和“兴”的手法就经常被采用,通过物品的地方性意义用来含蓄地表达彼此之间的感情,如“女唱:马桑树儿发青苔,郎来给妹收低歹。妹藏绣楼纳鞋底,收完低歹送郎鞋。男唱:马桑树儿发青苔,低歹黄了收进来。收完低歹穿鞋去,秋来给妹种低歹。”[12]P92这里面的马桑树儿和鞋垫就是表达爱情的意象。
五、小结
仡佬族民歌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仡佬族的社会历史记忆,也是其价值观念和意识的载体。通过美学的视角,结合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对仡佬族的民歌进行研究,能够有效地将历史与现实、物质文化与无形文化、自然环境与意识观念等结合起来,有利于更加深入和完整地分析民歌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义。
——以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双坑村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