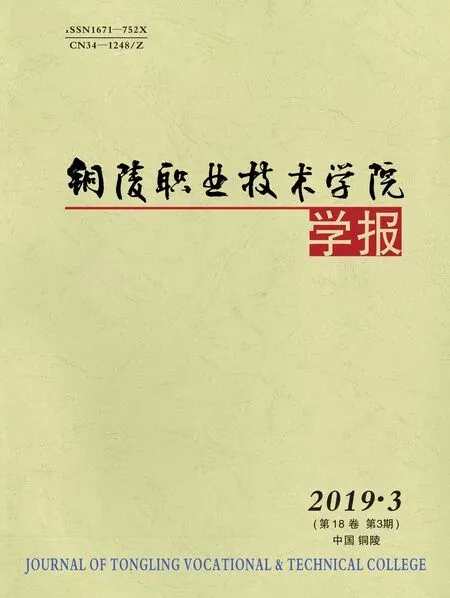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
——论王家新诗歌中“雪”的意象
罗敏仪
(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之一,王家新至今仍坚持诗歌创作与翻译。一方面,王家新诗歌中精湛的技艺与精神品质使得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家;而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关于“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中,王家新激烈的言辞与锋利的批判使他处在风口浪尖位置。王家新认为,无论作家创作多么向往历史中的自由,但仍然受到当下政治生活的影响,最终仍要回到这种我们注定要承受的汉语的现实中来。[1]在诗歌日益私人化的话语言说趋势下,王家新诗歌则呈现强烈的分化,公共意识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成了王家新诗歌的特质。正如臧棣所评价的那样,1989年以后王家新的写作走到了中国诗歌写作的最前面,肩负着当代诗歌严峻的时代意识与潮流。[2]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越来越摒弃了诗歌自身以外他律的意义与目的,诗歌成为自身精神需求的存在。在王家新的诗歌中,“雪”在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具备同时代不合时宜的隐喻,这是理解王家新诗学问题的关键,并以此为路径,来探寻中国同时代诗人群像的精神谱系。纵观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我们可以发现,“雪”这一意象在1980-2000年之间大多是以自身的诗歌创作出现,而在2000年之后,“雪”的呈现多于他翻译的一大批俄国诗歌之中。通读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与翻译诗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王家新诗歌背后诗学的转变与自身的精神历程与“雪”的书写变化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王家新自身的诗歌创作以上世纪90年代为界限,前后诗歌内在的艺术表现力和意义的表达都有明显的变化。本文以时空为线索,对王家新诗歌中“雪”的意象背后隐含的诗艺转变做了三个概括:一是故乡与“北方”的记忆;二是呼吸西方诗人的文学传统;三是在历史与“梯子”中,找到诗歌语言的词根,从而进行诗人自我身份的定位与确认。
一、练习曲:故乡与“北方”的记忆
王家新将自己的诗按照时间界限分为三个阶段 :练 习 曲 (1979-1989)、转 变 (1989-1999)、来 临(2000-至今)。这可谓是诗人对自身诗艺的概括性归结,而诗歌中“雪”的意象的书写也正是其中明显的关键词所在。
练习曲(1979-1989)是王家新开始诗歌创作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是诗人摸索探寻诗歌艺术的重要阶段,正如诗人自己的定位上世纪80年代属于其诗歌练习期,而内心有更宏大的诗歌理想,便需要内心的沉潜。[3]王家新在诗歌练习期中对“雪”的表达是具有明显的出生地特征的。诗人于1957年出生在湖北丹江口,确切地说,是鄂西北人,处在湖北西北部偏僻山区,贫穷且寒冷,冬天里常常是冰天雪地。根据诗人自身回忆,“也正是这样的寒冷,至今仍在我的体内燃烧。”[4]童年的贫寒与冰天雪地环境相互映照,构成了诗人生命历程最初的底色。诗人生在武当山下,直到20岁上大学之前都没有出过山区,也正是对外面未知世界的向往,当上大学走出故乡看到心心念念的世界顿觉失望后于是写就了他的成名作《在山的那边》。一定程度上而言,出生地的“雪”呈现的地域性影响了王家新的性格与精神特质,那团燃烧的火便是王家新对诗歌创作的热爱与探索如何成为一个诗人所付出的努力。因此,“雪”在王家新诗歌练习期充当着由一个人的角色走向诗人身份的内在精神动力,是诗人在压抑与屈辱的青少年物质生活中最初开始诗歌创作的精神慰藉,正如王家新本人说过他诗中一再出现的雪的意象最早来自童年记忆。与“雪”相关的词语如冬日、北方、风、雨、寒气等呈现的意象联想痕迹,除去修辞化的诗歌语言需求,故乡“雪”的记忆在王家新探寻诗歌艺术道路中,由八十年代的诗歌语言艺术的呈现,到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开始内化为诗人的精神追求与象征,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
《雪意·中国画(组诗)》(1984)中的“雪”意象表达意思有两层:其一,是诗人所处在的具体自然环境特征,是古往今来经典的抒发情感、发人深思的载体;其二,“雪”具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与灵魂寄托,“雪”地上走过的人使得诗人 “灵魂又返回自身”,“雪”是诗人安身立命灵魂回归本心的警醒鞭策。更让人惊奇的是,“雪”带来的是世界的宁静与清晰,具有净化污浊尘世喧嚣的功能,洗涤人的心灵“画出光的呼吸”。“光的呼吸”在这里寓意有二:其一是希望与光明的乐观之意;其二更是代表诗歌创作路上的引路灯,而持灯的使者便是 “雪地上嚓嚓走过的人”,这带给王家新的是与自身灵魂之间的对话与自我的叩问,时刻守护自己的灵魂不离内心的那片纯净圣土。
从自然景象进入到精神事件,从下雪到万物的生长,从身处的地理环境到诗人的精神内部,在王家新的生命中“雪”似乎成了某种生命编码,是主观世界联结客观事物之间的一个路径,沟通了诗人的精神升华与现实遭遇。而 “冬天的精神”将我们包围,“我”与“雪”的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如果说在《什么地方》(1988)中仍未过多言说“雪”带给诗人精神品质的重要性,而在《北方札记》(1988)中则表现得一览无遗。这是以“北方”为题的诗篇,而“北方”在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中是寓意深刻的。诗中与“雪”联合在一起的死亡、寂静、寒冷与茫茫,我们很难想象死与“雪”之间的相关性,而“使一个从不恐惧的人,开始发慌,使一个在地里劳作了一生的人,最终如一张悬置的犁”,正是这无休无止的大雪造成了劳动人民的恐慌,大雪落下来天灾造成人祸,人民对粮食与庄稼的关心,对全家人食不果腹的忧虑。看似纯白美好的“雪”,造成的却是死亡,这无疑呈现了诗人王家新对人类命运强烈的使命感与承担感,读起来痛苦沉重与震颤,而末句中的“我们”取代了“我”,是诗人从诗歌私人化到诗歌公共性,诗歌承担历史与时代责任的明显标志,“我们”表明“我”与芸芸众生的灵魂是平等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类苦难勇于承担的姿态,而“雪下的土地”正是诗人的现实关怀与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依托下的个体生命崇高的同情。而也正是这样的诗歌创作体验,王家新在90年代后的诗歌明显地具有知识分子心灵成长史的意味。
诗人从1988年开始,诗歌中便开始多次出现“冬天的精神”与“北方”等词汇。诗人于1985年5月从一个湖北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诗人所处自然环境的变化便导致了诗歌意象的转变。因此,从1988年之后,王家新在诗歌中关于“雪”意象的书写由故乡湖北转移到了“北方”,所蕴含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正如诗人所言,“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换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5]湖北丹江口的地域特征与青少年生活的寒冷与贫苦,奠定了王家新生命灰色深沉的生命底色,从湖北到北京,北方严寒的气候与政治文化中心,“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使得诗人“呼吸”到自己所渴望的东西;《诗刊》工作原因使得诗人更加接近诗歌本身,与更多的诗人有交往,如北岛、多多、欧阳江河、顾城、西川、杨炼等,1987年夏,山海关举办了一场青春诗会通过诗人之间的交流,王家新感受到了可以提升当时诗坛诗人精神事物的存在,预示着诗歌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欧阳江河也正是在那时那地写下了名篇 《玻璃工厂》,而1989年3月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给了当时一批诗人精神上的震撼、自责与思考,多多在朗诵会上说出他对海子之死的愧疚,骆一禾整理海子遗稿期间死于脑溢血,生命定格在28岁,正如他悼念海子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而王家新更是写出了《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其中的沉痛、黑暗的物质都在敲打着诗人的心灵。曾经热闹喧哗的朋友都四处散开了,诗人在西单白庙胡同老房子里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 《日瓦戈医生》、《安全通行证》等,也正是那黑暗处生长出来的向上的精神力量让诗人明白了自身被赋予诗歌创作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内心的绞痛,苦难的承受,个体与时代的命运,都让王家新沉思。如果说“雪”所承载的诗歌精神血脉的迸发与勇敢在诗人的八十年代处在懵懂萌芽阶段,在90年代之后,在诗歌中便是蓬勃发展与加强。而青少年生活与历史事件密不可分,其中的沉思与诗歌精神追求,更是在具有个人划时代意义的诗篇《帕斯捷尔纳克》(1990)发表后使得其中的要素得以确立,是诗人心灵容器贮藏沉潜的实现。
二、转变:呼吸西方诗人的文学传统
上世纪九十年代于王家新而言,是具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伴随着《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表更是具有指标性质。1992年王家新远赴西欧游学,诗艺泥土养分的汲取也产生了空间上的转移,从故乡到西方,诗歌精神与自身的地理空间相互融合,从个体化的记忆经验渗透到广阔的时代语境。远离故土的王家新,面对非汉语的生活环境,诗歌创作内心蒙上了更浓厚的孤独、彷徨与沉重感,对母语诗歌写作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加诸植根于西方遭受了“暴风雪”的诗人们给了王家新深切体验到自身存在与诗歌所要承担的命运。我们会发现,一个诗人对另一些诗人的呼唤,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与文章中毫无掩饰地追随与召唤“那些高贵的名字”,这些名字大都是在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中“放逐、牺牲、见证”的作家诗人,与其说王家新借用西方资源这把“梯子”,倒不如说是他召唤的“那些高贵的名字”来到王家新心中发出声音给他的诗歌创作灵感迸发积攒力量。正如洪子诚提及到的,王家新的艺术和精神谱系中不断由“寒冷”和“雪”所链接的是一批经受了历史与生命寒冷与大雪创作出不朽作品的诗人,如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阿甘本、策兰、凯尔泰斯等。[6]诚然,王家新在致敬西方诗人中,将他们的诗歌技艺与个人生存环境的时代与历史相结合,化为王家新独具个人化的诗艺。
《帕斯捷尔纳克》(1990)中“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成为诗人与人悖论式痛苦的概括,更是帕斯捷尔纳克与王家新共同的悲剧。“几千里风雪”一方面表示空间地理位置的距离,从俄罗斯到北京;另一方面,时间上穿越风雪而来的是两个灵魂之间的呼喊和召唤。“疯狂的风雪”代表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时代动荡中所遭受到的巨大苦难,承担着时代给予共同的生活和命运,是精神漂泊中的对生存现实的认知与沉默。而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所呈现的精神姿态鞭策诗人的灵魂,在寒气、冬日与黑暗中的苦难中关怀自己的土地与人民,而这不仅是痛苦,更是最崇高的幸福,是“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诗人“需要用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这里的“冰雪”更是象征那些“放逐、牺牲、见证”的“高贵的名字”,是忠实于自己决不妥协的生命,关注祖国的命运,而这也是诗人毕生所追求的独立生命姿态与历史意识。反观王家新八十年代创作的诗歌,则是由相对纯粹的抒情增加了些“黑暗与灰色”的悲剧成分,积极向上的力量似乎远去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冬天里的诗人遭受着民族与时代带来的惨重命运,而“雪”带来的是一次次的历史事件中,个体精神意志的增长与消解,此起彼伏的精神矛盾冲突。王家新在诗歌中完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与历史苦难的承受,而这也正是王家新与帕斯捷尔纳克处在共同的生活命运与精神困境中的言说结果,王家新找到了异质环境下的帕斯捷尔纳克,跨越了时空之后完成的对话。“冰雪”是王家新诗歌中表达当下生存现实的认知与承受的理想勇气与面对磨难后自我辨认的见证。
而与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人同一精神谱系上的还有茨维塔耶娃,王家新多年来的写作与生活中都有“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诗人的指引,激励王家新不断地往前走到他心中理想的诗歌艺术。”[7]遭受过疯狂风雪打击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前后经历的历史性事件,他们的诗人身份被视为俄罗斯的苦难与希望,这样的诗歌直撞王家新的心灵,战栗不已。不仅如此,在多年译介策兰的诗歌中,王家新更是有着内心的深深触动。遭遇过暴风雪重击的策兰,是犹太民族苦难和历史浩劫的见证者,但却拒绝苦难写诗,而是将一切内化为深刻的声音。这更是与王家新青少年的生活与时代事件息息相关。王家新经历过“文革”,因为父母“出身问题”与策兰有相似的精神向度,自小便经历了生活的贫寒、压抑、苦难和黑暗,翻译策兰在王家新的精神向度中不仅是是经历、身份、心灵上的认同,更是得益于照亮我们自己所盲目忍受的生活,并一再撕开我们自身的创伤……[8]从一个诗人到了另一个诗人,是诗人对孤独、苦难、挣扎,对另一个诗人的命运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方能进入他的精神内核解剖达到心灵上的契合。
你可以充满信心地
用雪来款待我:
每当我与桑树并肩
缓缓穿过夏季,
它最嫩的叶片
尖叫。
——《雪的款待》(2002)策兰著,王家新译
王家新于1997-1998年开始翻译策兰,这一首诗出自策兰晚年于1967年出版《换气》诗集中的第一首诗《你可以》。“雪”为自然意象,更是生命的隐喻。而经历了奥斯维辛刻骨体验的策兰,“雪”没有因为季节更迭而消逝,相反,它穿越了时空的限制与夏季的桑树呈现在我们眼前,冬日与夏天,雪的款待更意味着命运的馈赠,叶片尖叫更是将视觉感受转换为听觉体验,这令人惊奇,尖叫有着对生的渴望。而“雪”在这里似乎并不意味着消极的死亡,我认为更多的是,即便生存艰难,却有着向死而生迸发出的微弱向上的光芒。在策兰的诗歌中不难遇到 “雪”的书写,而王家新的诗歌词根中“雪”也是其中的一个,王家新在通过翻译策兰诗歌过程中不断地进入到策兰那沉默、断裂、痛苦的词语之中,去感受他从生活中生长起来的词根,从而进入到穿过苦难历史见证的诗歌。这便是王家在90年代诗歌创作与翻译中“雪”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追求,触碰到那些“高贵的名字”后呼吸到西方诗人中伟大的文学传统达到诗歌创作上的契合,而这也正是王家新在追寻诗歌语言的词根故乡来临前的沉默与承受。
三、来临:追寻诗歌语言的词根故乡
王家新以西方资源为路径,在呼吸西方诗人的文学传统时,从诗人的痛苦写作中追寻到了诗歌语言词根的存在。准确来说,比2000年稍早些年,王家新便在诗歌中体现到了“雪”与词根的关系。《布罗茨基之死》(1996)是诗人在布罗茨基去世2个月后所作之诗,满怀悲痛与震动。布罗茨基对中国诗人影响深远,正是那“持久不化的雪冠”,这是布罗茨基代表的西方诗人带来深刻的精神经历,是一种和我们深刻相关的死亡、抗争与流亡。而死亡带来的“一阵词的黑暗”,这便是死亡带来的痛苦,才能进入这黑暗的词。
《布罗茨基之死》作为一个先声,同年王家新还有另外一首关于“雪”的诗为《尤金,雪》(1996)。 诗歌创作中,一切流于表面的创作理由与动机都不能成为诗歌本身,惟有“雪降带来的寂静”。雪降带来寂静实际上是一条连接表面与本质的通道,这有别于其他的寂静,这是更具有力量让诗歌自身与人自身往内走。深夜写作的人必须在大雪之前找到创作的词根,这使得“雪”与“词根”之间是对应的宿命般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紧绷的张力,是生命与哲学境界沉思的结果。正如王家新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有触及了这样的‘言说之根’,诗或思才走向我们。一个诗人的写作才有了它的真实可靠性。”[9]跋涉这个词表示了要找到词根与进入语言自身的难度,写作是丰富的痛苦。“永不封冻的窗户”,在诗人看来,是艺术本身。窗户中看到的是“雪,雪,雪”,反复强调“雪”正是表达了诗人找到了诗歌的词根时候的喜悦,这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欢欣,是诗歌语言与生命存在的缘由。海德格尔“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语言是存在进入的路径,是现实与时代的关系,“词根”正是从诗人全部的一切中生长出来的产物。王家新自80年代末去国外以来便关注“词”的问题,其中有对母语的认识,也有对土地的爱。诗歌的创作,本身就是寻找语言词根故乡的过程,正如诗人讲到,“‘词’也有它自身的家乡。诗人所做的,不过是通过他的‘走’,即通过一种不懈的语言的劳作,使词语本身望到它那神话般的家乡——而那,才是我们生命的本源。为此,我们不得不在词中跋涉。”[10]“词语”与“精神”之间有一个向度,是相互吸收最终达到统一的诗歌。诗歌的语言,便是一个诗人心灵的表达。而语言的难度,就是伴随着漫长的艰苦的反思与心灵的觉醒带来的产物,是易卜生的铭言 “写作,就犹如对我们自己做出判决。”“雪”所链接起来的那一批诗人所坚持的文学传统与独立的时代姿态便给了王家新诗歌创作天启般的感悟。不可否认的是,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借用了“梯子”的作用,其中诗歌的翻译更是一定意义上将寻找语言的故乡作为自身诗艺的追求。正如夏尔所言那般“我们只借那些可以加倍归还的东西”,对翻译诗歌的召唤正是源于语言自身不满足的需求,为了达到其中的唯一性。王家新一直强调诗歌创作中的“还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到故土,实现地理位置上的“还乡”。于一定意义上而言,这是“生命的还乡”,是听从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听从灵魂中深沉渴望中指引,摆脱了现世中糖衣的遮蔽,找到世界的本原与生命的本真状态,实现生命长途中自我精神的挣扎与成长。诗歌创作通过“语言的还乡”方能实现“生命的还乡”,从现实生活的经验中找到语言的“词根”,在永不停歇的荒诞生活中无限地循环往复。“雪”作为王家新由生活经验进入精神本原的路径,既是“生命的还乡”的理想状态与崇高追求,更是“语言的还乡”中跋涉寻找词根的结果,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品质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而实现的。
再一次获得对生活的确信,就像一个在冰雪中用力跺脚的人,在温暖自己后,又大步向更远处的雪走去。
——《变暗的镜子》节选十八(1999-2000)
诗歌的诞生是诗人内心绞痛与时代历史的融合,一生的写作便是毕生的痛苦的集结,在痛苦的冰雪中用力跺脚使自己有继续撕开痛苦的力量,“更远处的雪”隐喻着印记在王家新精神族谱中那些“牺牲、放逐与见证”的名字与灵魂,他们象征着诗歌的姿态与最本质的东西。为了达到那样的高度,王家新此生便是“苦役犯”般的存在,这是王家新自我身份的确认,诗人需要艰辛、深入的创作,面对时代与历史疯狂的浪潮,王家新认为诗人需保持良知与勇气,个体凝视历史深处找到语言词根的故乡审视诗歌艺术本身,而唯有那些如策兰般处在“他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下”言说的诗人才能找到诗歌的立身之地,这便注定诗人要“像苦役犯一样完成这一生的写作”,通过潜入到历史记忆的与词根的深处方能感知与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当他像苦役犯一样完成这一生的写作,我想他将走出屋子,对着远方这样喃喃自语地说:孩子,现在,我可以感受到温暖的阳光了,我可以听到从你的花园里传来你的女儿的笑声了……”
——《变暗的镜子》节选二十(1999-2000)
我一辈子都是这样一个苦役犯。
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
——《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回忆录》(2016)
王家新作为当代重要的诗人之一,诗歌中“雪”意象的书写是诗歌语言的词根,并因此将一系列其他的词联结在一起,构成诗人内在的诗歌追求。“雪”是寒冷、纯白、光亮与冬日等解读,但在王家新的记忆与生命相关的黑暗、苦难、贫寒与压抑的底色下,“雪”成了他诗歌艺术品质提升与自我灵魂洗礼的证明。一个坚持独立思想的诗人用诗歌揭示了诗、思与时代的关系,王家新作为同时代人,便是用诗歌不合时宜地征引历史中试图建立起回归当下的方式,通过脱节于时代中其他私人化诗歌写作的浪潮或保持独立知识分子的承担历史苦难的姿态而附着于时代的联系,这样方能清晰地看时代,沉思诗歌与诗人的真正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