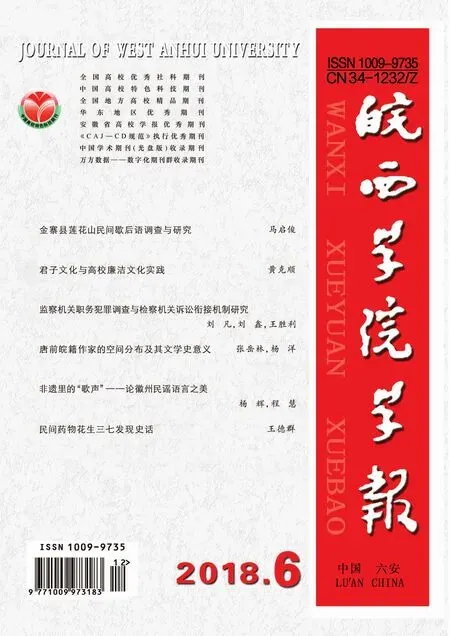试论吴景旭的词
韩路路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吴景旭(1611—1695?),字旦生,号仁山,浙江归安人,明诸生。吴景旭是归安前丘吴氏家族的房支,吴氏家族世居归安前丘,是当地的著姓望族,吴景旭从小便博学诸家,工于诗文;入清后,无意于仕途,投身于诗文创作,入同岑社,是双溪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留下了《历代诗话》八十卷、《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后附《南山堂填词》一卷,《续订诗》五卷、《三订诗》四卷、《乐府》一卷。关于吴景旭的生卒年,山西大学的邱红霞在她的《吴景旭的文学活动与诗学思想研究》这篇文章中指出:“《三订诗》中的《乙亥元日至元夕无日不雨雪,聊作歌以排闷》及《八十五戏作》,可见诗人至少活到了八十五岁以后,因此卒年应在1695年之后,具体时间无法确定。”[1]
目前学界对吴景旭的关注大多集中于他的《历代诗话》,有关他诗词的研究,没有专门的著作或期刊论文。吴景旭有867首诗和一部《历代诗话》著作,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和写作风格,源于吴景旭特殊的遗民身份,以及他转益多师善于学习的态度,也使得其诗词创作方面有着独特的意蕴和价值。词是吴景旭创作的一部分,本文欲从其词的研究窥视吴景旭创作上的特点。除此之外,对于吴词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更全面的发掘遗民词人群体的创作情况;另一方面,吴景旭与广陵词派、西泠十子等流派的成员往来甚密、交往颇深,在吴词中也多次写到他与友人的宴集、交游之事,这些词作也在不同方面显示出多个流派的风格特色,因此,研究吴词也是对清初词坛创作特色探索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成因三个方面对其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吴景旭词的题材内容
吴景旭有《南山堂填词》一卷,共50首,收录在《全清词·顺康卷》。其词多是一些生活实感的记录,以及无奈悲凉之情的抒发;在他的词中所体现出来的真性情和真实感与他主情的思想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作家是一个学识广博、兼容并包的学者;从题材而言,吴景旭的词可分为咏物词、记事词、抒怀词三类。
(一)咏物词
吴景旭的咏物词共计9首,占其总数的18%。这些咏物的对象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白秋海棠、寒冬腊梅、牡丹、金鱼、宋磁、宣炉等等;文人们借咏物有所寄托是常见之事,吴景旭也多是借咏物以抒怀。以这首《梅花引·腊梅》为例[2](P710):
立闲房,倚明窗。谁裊金丝这样黄。倩蜂忙,倩蜂忙。疑向密脾,偷来深处香。好将宫女涂鸭色,重添春睡飞花额。点新妆,点新妆。无限远山,似偏生夕阳。
开头两句,首先点明了地点和词人的状态,闲来无事,倚坐在明亮的窗前,放眼观去是蜜蜂飞来飞去的正在采集梅花蜜的景象;上阕热闹、明亮的场景,下阕一转进入静寂、暗淡的基调,也开始了作者内心的联想,“宫女点新妆”意味着有“新主”进驻宫殿,夕阳则象征着“旧主”的时代已从作者的记忆中渐渐逝去。吴景旭亲历明清易代,在这首词中非常含蓄地把自己的思乡怀古之情表达出来了,名为咏物实则抒情。
清初,高压政策之下,文人们被打击迫害,让他们不敢直接表露心声,因此借咏物以抒怀成了这一时期文人们特殊的表达方式,再有一首《雨中花·秋葵带雨》[2](P707):
红雨虽非春陌,犹簇几堆秋色。休道君家,向阳门第,变做淋漓客。一朵水欺娇又匿,强似落花狼藉。奈幼妇愁多,面儿黄瘦,把泪痕轻拭。
这首词整体都透露着凄凉悲伤的情调,上阕“红雨”“秋色”两种意象尽显悲凉之景,此处“红雨”乃是落花之意,引自唐·李贺的《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下一句写雨中秋葵变做淋漓之客,此处也是词人的人生写照;下阕写雨打秋葵的狼藉之色,之后又将秋葵拟人化,索性将词人满腔愁苦、凄凉之情全赋予这朵秋葵,“幼妇愁多,面儿黄瘦,把泪痕轻拭”,吴景旭入清之后,绝意仕途,一心归隐,对清朝的排斥之情和思念故国的悲苦之情,让他饱受折磨,内心的抑郁无法言说,只能独自流泪,自我排遣。
诸如此类的咏物之词在吴景旭的词中不胜枚举,吴景旭很善于将感情隐匿于意象之中,虽是含蓄的表达,却将感情宣泄到了极致;吴景旭能把感情发挥的恰到好处,还在于他高水平的咏物方式,《花草蒙拾》中,王士禛说:“程村尝云:‘咏物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用意’二语可谓简尽。”[3](P683)吴词中的景物无不神形具备,“一朵啼痕血蘸”,写海棠花的娇艳;“窃红深紫各争新。被谁勾住,才吐芳魂”,写盛放的牡丹;“正群游处,惊作电,避如风”,写出金鱼在水中之灵动。只有景物描写的形神具备,才能更加生动形象的把作者所赋予的人之情态表露无遗。对于身处高压政策下的遗民词人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抒发真实的情感。
(二)记事词
吴景旭的记事词共17首,占总数的34%。吴景旭生活在朝代更替的乱世,入清后,他便绝意仕途,积极参加诗社雅集等活动,专心于文学创作,在他的这些记事词里,多次记录当时与友人交游、对弈等雅事;吴景旭的记事词名为记事实则抒情,如他的这首《解蹀躞·忆园次太守灯舫宴游》[2](P711):
且莫仙□琪树,叠作空中架。但连群舫溯回卜清夜。看取碧浪湖边,映浮千点星火,疑真疑假。燃灯者。原是祈年村社。不妨传杯斝。其时太守开筵尽名下。有人拈得诗云,客应比乱山多,岂虚言也。
这首词是对昔日与园次太守宴游场景的回忆。吴景旭与吴绮是多年好友,此时吴绮已被罢官多年,吴绮在任湖州太守三年间,经常高朋满座,诗酒唱和,雅集宴游,当时吴景旭的南山堂也常是友人们欢聚的地方,吴景旭还有诗《家梅村祭酒,宋既庭、徐建庵两名宿南山堂》,记录当时的事情,说明吴景旭对当时的挚友之交倍感珍惜,此种闲适快活的日子,是随着吴绮被罢官而终止的。此词“客应比乱山多”之句,乃是化用吴伟业《家园次罢官吴兴有感》之句:“官随残梦短,客比乱山多”[4](卷一,P12),这是吴伟业为吴绮丢官抱不平所作,前面一句不难理解,后面一句源自于吴绮罢官后填的一首小令《茅山逢故人·醉题》云:“满月乱山无数,一片寒潮来去。故业何存?故人何在?故乡何处?《离骚》一卷长怀,莫向西风空诉。才子无时,美人无对,英雄无路”,道出了他罢官之后的不平之情,词中所说“乱山”,是访客的比喻,以此点明了吴绮丢官的原因。这里的“访客”大都是吴景旭多年好友,吴绮罢官后,他们这些往日里诗酒言欢的朋友也都各散天涯了。此词吴景旭借以表达对往日故友以及昔日相聚之欢愉的怀念和感慨。
再有一首《沁园春·重修赵松雪三石》[2](P715):
赵孟頫,字松雪,是元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吴景旭在赵孟頫别业建南山堂,此词源于重修别业有感而发,词的上阕对赵松雪别业往日景象的描述,“当年贵胄,迷花洞窗”与下阕“柴门外,藕满孤汀”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作者内心凄凉的落差感,昔日的风光景象已不在,剩下的只有眼前的孤独和悲凉。入清后,吴景旭作为遗民的身份带给他的心灵创伤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在这首词中,暗含着吴景旭对早年故国生活的追念,也借此抒发当下孤寂生活的苦闷之情。吴景旭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作家,生活中小场景小事件都能成为他吟咏的对象,在他的记事词里,还记录了像洗砚、卖花、嘲友人买姬等等这样的生活琐事。然而,这些看似是对生活琐事的记录,却也都是作者心灵的慰藉和感情的寄托。
遗民身份使吴景旭这样的一群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以诗存史,以词记事,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身经两朝的凄凉悲苦,对现世的排斥和无奈影响着他们内心的思索。
(三)抒怀词
吴景旭的抒怀词共有24首,占总数的48%。吴景旭是身经两朝的遗民,这样的一批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现世的排斥和无奈之感,内心的凄凉悲苦以及自我的排遣,在吴景旭的词里都有所表现,这一类的作品,首选他的《虞美人》十首。如《虞美人》[2](P709):
其六:
夜闻骓逝朝何处。不道乌翔树。忽逢骤雨打荷新。认作怒声喑咤废千人。身经七十余争战。败落空嗟怨。妾当二十四番风。此亦天之亡我乱飘红。
其七:
上林请苑犹遭械。给粟功难贷。无双国士更休夸。我自甘心为伍米囊花。逢人说项徒酸哽。满地胭脂冷。大王意气奈虞何。赢得月寒人静叹声多。
吴景旭的这十首《虞美人》词,均是以借项刘之争的事情作为抒发情感的寄托,以虞美人草自喻来诉说自己身经两朝的处境和遭遇;他把已亡的明朝比作项羽,把清朝比作刘邦,把自己比作虞姬,通过“刘项”之争,来表达自己对于明清易代的抗争,“身经七十余争战”一句,能让读者体会出,入清后,他是经过艰难的挣扎才得以接受这个悲惨的现实。
吴景旭仅有的50首词,这一类家国之感慨的词就占了10首;不得不让人想到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遗民身份。这是大环境下,一类人所共有的情感状态。遗民身份是这一群同时代文人们之间的一层微妙关系,在他们的交往中,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这些文人喜欢集会结社,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来抒发他们独有的特殊情感,这也是吴景旭在文学活动中的一种诉求。
二、吴景旭词的艺术特征
吴景旭是明末遗民,受明词格调,以及清初声势浩大的广陵词派提倡尊体和主情意识的影响,词风含蓄隐约;入清后,受制于清朝的高压政策,许多文人因“文字狱”受到迫害,导致他们在诗文创作上都不敢直抒胸臆;只能在艺术上寻求委婉含蓄的手法,或选词造句之精炼,或使事用典之隐晦,或语言之俗中见雅。
(一)练字、炼句之一字之妙
“练字”是一代又一代文人所得之经验,一句之中“字”的妙处,体现的不仅仅是修辞之美,更有意境之传神,自然之动态的表达;用字之准确,可以开阔读者的想象,让词中之境更形象地呈现在脑海里。
吴景旭练字有两则妙处,首先是“一字能言词境”:如《减字木兰花·同余子澹心泛碧浪湖》中“一川平绿,撑出柳塘弯个曲”,“平绿”比“平野、平川”之妙就在于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绿”是一个有生命的字,绿草、绿树、绿荫、绿水等等都是鲜活的画面。“弯”是一个动词,真实的画面必将是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平绿”“弯”字一出,一副青山绿水间,撑一支长篙泛舟湖中的画面映入脑海。
“经年作词赋,何用拟相如。眷怀裒所积,筐箧有尺书。遂无金石声,聊用托贱躯”[5](卷二,P22),吴景旭练字妙处之二在于“一字能摹情态”,吴景旭选词造句多注重表现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如《玉珑璁·夏兴》[2](P711):
山头睹,溪头俯。从篁越样阑干舞。风宜作,雨宜作。满天涼散,弥天晴阁。乐、乐、乐。昨时暑,今时愈。一炉烟裊沉香煮。茶宜瀹,人宜瀹。意中朋友,眼前评驳。谑,谑,谑。
此词第一句中“睹”“俯”,俯首抬头间景象全出,此词上下两阕分别写了夏季雨天和晴天的两种乐事,上阕“风宜作,雨宜作”,写夏天雷雨过后的凉爽之乐,与下阕“茶宜瀹,人宜瀹”,写今日里煮茶会友的乐事相呼应,“作”“瀹”两字分别把“风雨”“茶、人”的状态和情境表达出来了,“乐、乐、乐”与“谑、谑、谑”把诗人的情致表露无遗。一字能出语境、一字能摹情态,“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6](P1)。“练字”可以体现出作家的性情志向和人生体验。吴景旭能以一字之妙,描摹出心之所向、情之所感。
吴景旭“练字”之工还在于对叠字的锤炼上,如他的《行香子·金鱼》中“日色瞳瞳”“树影重重”“池水溶溶。”严羽说:“下字贵响,造语贵圆”[7](P118),“瞳瞳”“重重”“溶溶”皆为句眼,叠字音节的重复,音律和谐圆融。语句的浑然天成全在于选字造句的精准,不仅能把意思表达出来,还要在结构和意蕴上妥帖恰当。
(二)用典之字无虚发、点铁成金
用典即所谓“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8](卷十九,P186),吴景旭词用典之巧妙在于字无虚发,点铁成金。试举一例《南乡子·秋闺》[2](P710):
妆罢拂豪犀。好把红蓝掩昨啼。记得木瓜新粉渍,谁知。梦断眉峰冷翠微。芍药自从离。寄杀文无总不归。刚在百虫声里坐,堪奇。又报寒更第一鸡。
“拂豪犀”出自《豪犀·汉典》诗:“侧钗移袖拂豪犀”;“芍药”“文无”出自晋·崔豹的《古今注·问答释义》:“芍药亦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亦犹相招召,赠之以文无。文无名当归也”,这是一首写闺中怨情的词,一个女子早起化了妆,把昨夜的泪痕遮掩,夜深人静时坐思归人,出神处,梦里梦断天长。在一首词中就用了两种典故,“拂豪犀”,是词人以诗句点化入词,提高了语境,此外,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作者借用典故之意委婉地将一个闺中思妇的情态描述出来了。
除此之外,还有《蝶恋花·题四美人图》中“扇底流萤,偷过东家壁”,是化用了杜牧《秋夕》中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词人又再一次以诗句入词,借此来表现画中美人的孤寂无聊之态。《虞美人》其三中“草草同朝槿”,出自五代·张正见的《白头吟》:“颜如花落槿,鬓似雪飘蓬”,词人以此表达对虞姬红颜薄命的感慨。吴景旭用典之字无虚发与他选词炼句的精准总是能把词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木槿”之花朝开夕落,花期只有一个白天,与“竟使故家乔木骂无端”句中高大且生命力长久的“乔木”形成对比;来表达作者由明入清的遭遇,早年短暂的美好转眼即逝,余生乐少苦多的生活却还要长远地过着,抒发了词人悲凉无奈的心情。
吴景旭所用之典或是自己人生际遇的写照,或是对世事变迁的感慨;如:《雨中花·秋葵带雨》中“红雨虽非春陌”,出自唐·李贺《将进酒》诗:“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红雨”即为落花之意,词人以此来感慨雨后落了一地的秋葵。《醉花阴·古意》中“说甚加餐饭”,出自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重行行》“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化用古诗句,表达的意思也更强烈了,“行人久未还,说甚加餐饭”;还有《虞美人》其五中“商山非有採芝人”,此典出自于秦末“四皓”隐商山採芝作歌,借此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心。这些“落花”“行人”等意象均是作者入清后触景感怀,悼古伤今的情感寄托,归隐是他最终的选择。
(三)雅俗并存的语言
吴景旭创作语言上的艺术性在于直用古语和反用古语,吴词中多处以诗句入词,使诗句得到了更加精准的阐释,如:“说甚加餐饭”(努力加餐饭),“扇底流萤”(轻罗小扇扑流萤),用的不着痕迹,与诗意浑融一体;且在直用古语的同时反用其意,不蹈袭窠臼,使表达更有新意,感情的抒发自然顺畅,有着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此外,吴景旭还常以诗韵入词、以曲家手眼填词,如他的《青玉案·手录苏黄二家诗》及《念奴娇·赠南粤归·用东坡赤壁韵》。吴景旭为避明词词曲相混的弊端,有着强烈的尊体和主情意识,不以曲韵为词韵。在选词造句上以通俗浅易的语言抒发真情实感,注重独抒性灵;“不贵浮华贵性灵,性灵一透自渊渟。纯施锦匹昌黎手,温李新声亦减零”[9]卷二-120,吴景旭非常重视体物之真切,感情之自然流露,如他的《前调·熊雪严宪长邀登风满楼弈棋》中“但取赢余才数子,何必多多益善。当局偏迷,旁观独醒,那话应喷饭。终须借酒,为公释此三战”,创作随意兴发,感情潇洒直接,口语化的形式,让语境更加真实可感。《江城梅花引·闺月》中“照也照也,照不见、谁最精灵”,《满江红·七夕》中“又何须、想盼到经年,真默矣”,《惜分钗·小集分咏作绣鞋》中“依稀么凤,倒挂收香。双,双”,随题命意的创作方式,加上浅近平易的语言表达出真切丰富的所见所感,以市井俗语入词,抒写性灵,实为俗中见雅。
三、吴景旭的词风成因
吴景旭的词大都是生活实感的抒发,感情真挚奔放,词中多用典故,语言以俗为雅。这种词风与以下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时代背景
吴景旭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期,这一时期明王朝逐渐恢复,走向开放,社会面貌一片欣欣向荣,此时的吴景旭正值少年时期,大明王朝的昌明盛世给他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但明神宗之后,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开始走向腐化;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在位期间,社会动荡,各地农民起义,日渐衰微的大明王朝逐步崩溃。吴景旭见证了明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无法挽回的局面让他感到既心痛又无奈。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变成遗民的事实,让吴景旭不禁感慨“自古儒冠,惯将人卖。心难逐。身难赎。”;顺治十一年至清康熙十年,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不仅从经济、政治上打压文人,思想上也控制他们,而且受“文字狱”的制约,文人们无法将内心的无奈,悲伤之情直接流露,只能借咏物抒情,以记事悼古伤今。“芍药自从离,寄杀文无总不归。”,故国已逝,往事不可追忆。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吴景旭此时早已改心易志,绝意仕途,走向归隐。
(二)人生经历
吴景旭是归安前丘吴氏大家族的房支,其祖父吴世治(1554—1626)字用卿,号文石,吴仕安之子。建平知县,南京兵马司指挥。吴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吴景旭少年便博学多才,工于诗文;吴词中使事用典,化用古语的艺术特点,难以摆脱所积之才学的影响,他早年的诗里记载了一些乱世飘零,民不聊生的境况;在他的词中,亦有一些表现人生巨变,身世浮沉之感的,如:“休道君家,向阳门第,变作淋漓客。一朵水欺娇又匿。强似落花狼藉”“诗空录,书空读。老天那管眉头蹙”。吴景旭经历了科场落第、故国灭亡、前朝遗民等大事变,这些都是他在词中所抒发悲凉苦闷之情的因素。入清以后,吴景旭作为前朝遗民,人生有此大变,心里的矛盾和无奈以及对现世的排斥,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词中,有《虞美人》十首是专门表现明清易代这个巨大的现实变化的,在这十首词中,词人以虞美人草自述的方式,运用比兴手法,言说“刘项之争”的事情,却将自己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最后用“商山採芝”的典故,说明了自己只想归隐山林的想法。
隐居之后,吴景旭积极参加文学活动,潜心治学,广泛交友,纵情于山水自然之间,悠然自得。
(三)文学活动
吴景旭是明诸生,入清后,隐居不仕,潜心治学。其所居莲花山庄更是文人名士常常雅集聚会的地方。吴景旭交友甚广,有同为遗民身份的吴伟业,余怀等等,也有新朝入仕的达官贵族。吴景旭是双溪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入同岑社,除此之外,他还跟其他诗社词派的成员关系密切,例如:广陵词派的吴绮、宗观等,西泠十子之沈谦、丁澎等。吴景旭非常热衷于参加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与其他文人名士的雅集宴游、读书讲学等文学活动;在他的词中,记录了多次与友人的交游活动,如:《前调·熊雪严宪长邀登风满楼弈棋》《祝英台近·家瑶如太守招游支硎》《解蹀躞·忆园次太守灯昉宴游》《踏莎行·同园次太守郭外观荷》《减字木兰花·同余子澹心泛碧浪湖》等等。在这些交游的过程中,也是文人们相互学习,技艺切磋的机会,吴景旭善于学习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得他在创作上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影响。清初,咏物词的审美主要关注在“物”上,以此为标准,受广陵词学理论影响的词人比较欣赏那些善于刻画物之情态的作品;吴景旭共有9首咏物词,为把所咏之物描写的形象逼真,并不是简单的死板的刻画一个物象,而是以不同的描写方式对景物进行刻画,不仅写形而且写神,最着意于突出景物的神态;《行香子·金鱼》中“见倏忽间,初是白,继而红。周身束管,毫无芒背,更拖开、三尾蓬松。易寻名件,难定浮踪。正群游处,惊作电,避如风”,把金鱼的形态、动作、细节等都描写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此外,吴景旭多以曲家手眼填词,且喜用“西泠十子”之沈谦词韵,源于广陵词派强烈的辩体意识,吴景旭不赞同以诗韵入词韵,他的一首《十二时·中秋纪虎丘》后注有:“词韵未有成式,用诗韵者,不分元与魂,不分卦画与怪坏,则倚声病其不协。用中原音韵者,支思分出齐微家麻,分出车遮,则必至于各押入声配;作三声,则必至于同押是直。以曲韵为词韵,不更大谬乎?沈去衿有割半分用之目仍照诗韵而区别之,平上去列为十四部,入声则为五部,有独用,有通用,既不失之滥觞,又不患于凌紊。园次太守梓行最为善本。去衿乃三十年前诗友,余作词用其韵,所从来旧矣。”[10](卷十,P97);“庾公清啸凭风月,谢守新题散绮霞。”[11](卷三十二,P374)是吴景旭称沈谦的诗词有庾信和谢朓之诗的清啸与清新自然的风格;沈谦以诗韵入词,多有创新之处,吴景旭认为“不失之滥觞,又不患于凌紊”,所以填词多用沈谦词韵,吴景旭的一卷词也是清新自然的风格。
综上所述,吴景旭的词在创作过程中深受他的生平经历和他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题材上,咏物、记事、抒情均是特定情况下心理反应的选择;艺术方面所追求的练字练句,使事用典,语言上的以俗为雅,清新自然的词风,符合明末清初整体创作上的共同追求。对于吴景旭创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具体的了解遗民群体的心理特征和创作追求,也能够反映出那个时期特殊条件下的创作环境;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深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