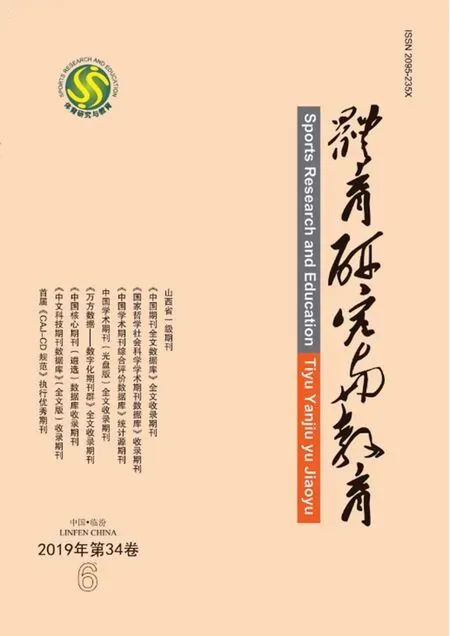身体在场:武术“会、对、巧、妙、绝”的主体性反思
杨国珍,段丽梅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澜先生指出“教育要实现生命自觉”[1],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赋予体育增强生命自觉的历史意义。然而,在体育教育中我国普遍存在“学生14年的体育必修课为何学不会一项运动技能”[2]的悖论,学校武术也不例外,学生“喜欢武术而不喜欢武术课”“学完忘光”的体育式武术教育常态往往置武术教育于尴尬境地[3]。研究认为“去本体化的无主体反思”是当前教育缺少生命气息的瓶颈[4]。学校体育应该从人学存在论角度更好地进行生命呵护[5]。对于武术传承而言,就是要回归身体进行主体表达[6]。“会、对、巧、妙、绝”曾是中国武术的集体无意识主体反思与生命认同记忆[7]。在当前学校武术表面繁荣与助力国脉传承[8]的现实反差面前,对武术传承中即将消失的“会、对、巧、妙、绝”现象进行分析,探寻生命教化的内在机理,将有助于学校武术教育改革与创新传承。
1 外在评价与概念认知:竞技武术与学校武术的发展瓶颈
竞技武术与学校武术都是科学认识论思维下的产物。追求武术的规范与标准,使武术趋向于外在评价与无我性的概念认知,最终导致其存在了发展瓶颈。
1.1 规范与标准:竞技武术与学校武术发展的双刃剑
近现代以来,武术发展走进了科学化发展的话语体系,竞技武术一举成为武术的代名词,学校武术顺理成章成为了简化版的竞技武术。从竞技武术的裁判法来看,无论是1996版的第七套竞赛规则,还是2002版的第八套竞赛规则,虽然在“切块打分”和“难度动作”方面进行了微调,使得比赛更加量化与可视化,但也同时造成武术纯粹的外在性评价。学校武术亦然,从学习内容来看,第一套国际竞赛套路和第二套国际竞赛套路都被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学校,考试打分虽然标准有所降低,但仍是遵循动作规范质量、演练水平和难度系数等外在性评价。既便是初级的武术套路教学,也主要是从动作是否熟练、有无错误动作、动作路线正确与否、动作外形是否标准等方面来评价。
在武术现代化发展初期,由于竞技武术与学校武术外在标准与规范的易操作与评价性,使武术得到迅速的普及与推广。但就竞技武术而言,虽然在裁判规则上已根据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宗旨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与创新,但仍被奥林匹克无情地一次次拒之门外。究其因,武术虽已非常量化,但其演练分值的非完全明朗化等仍是武术进奥的主要障碍,而与武术相似的柔道、跆拳道等,却能以稍改外形但仍不失真的简单实用反而捷足先登成为奥林匹克项目,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就学校武术而言,规范与标准化改革使得武术易于以班级制形式在学校广泛推广,然而武术从民国进入学校后的不温不火发展到至今被跆拳道严重挤压等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说与武术发展中泛化的规范与标准等量化追求息息相关。
1.2 去本体感知与无我反思:武术发展屏障的直接导火索
如果说规范与标准影响了武术的发展,那去本体感知与无我反思的概念认知就是导致武术发展屏障的直接导火索。柔道、跆拳道等国外武技在进行量化评价的外形改造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攻防技击的本质,再加上其文明礼仪等主体反思的教化内涵,使其自然发展成为广泛普及并受社会追捧的习练项目。社会上各种柔道与跆拳道馆如雨后春笋般开设,而学校武术教育传承却相对门庭冷落,鲜明的对比进行了无言的表证。
“花架子”常被认为是当前学校武术的代名词,“考完忘光”也是学校武术教育的异化常态。“花架子”的操化武术使得习练者犹如记忆套路的机器一般,长此以往,学生自然对武术敬而远之。有研究表明:从民国起,学校武术发展就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境地,民国时期学校武术就存在有课堂无内容的教学现实[9]。无内容是指将学生当客体对象进行身体缺席的武术教学,身体的缺席必然造成武术传承本体的抽离与习武主体的隐退。发生“学生喜欢武术而不喜欢武术课”,与跆拳道等外国武技挤压武术课堂等现象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了。失去本体感知与主体反思教化内涵的武术操演,对于竞技武术,尤其对于学校武术来讲,实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项目而已。
2 身体本体认知与主体经验反思:武术“会、对、巧、妙、绝”的新诠释
“会、对、巧、妙、绝”是以“六合”劲力习得为学习效果的传统武术评价标准,更是习武人自我功夫与境界提升的身体本体认知与主体经验反思。
2.1 “会”:齐整性劲力体知与主体对静态平衡的把控
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都有会不会练的说法。我们当前所说的会与不会,主要是强调动作规范下的熟练,是指能不能将所学动作熟练比划下来的意思,传统武术中也有这层含义。如形意名师李存义讲习武“学,很容易,一会就学会了,但能练下去就难了”[7]。此处的“会”,就是指动作的熟练。对于现代学校武术学习而言,会了再反复操练,能熟练演练。如果不是用于比赛,就算是高水平了。对于传统武术而言,武术入门常以较为简单的入门拳架与桩功为主。“会”除去会比划动作之外,还提出“会”的基本规定与要求,即“会”还指一种形规下(动作和顺)的劲整。
“要知拳真髓,首由站桩起”的“入门三年桩”是传统习武人共识的一种基本能力。此种能力在多种武术文献中皆能见到,如《少林拳术秘诀》云:“未习打,先练桩”。李存义《论站桩》中也有“若是诚意练习,总要勿求速效。一日不和顺,明日再站;一月不和顺,下月再站”等说法,并以“三害之病不可有”“九要规矩要真切”等力求达到“外在形式要和顺”[10]为标准的规范。此种规范并不止步于外形,而是要初步形成一种整体劲力化的身体结构,即传统武术所称之“六合”(外三合是手与足合、肘与膝和、肩与跨和手与肘合;外三合是内三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和、气与力合的前提与基础),其实质使身体整体为一。站桩是身体合一的重要与首要手段。站桩后身体的正确反应是像按弹簧一样,你推他、压他、拉他、托他到一定程度,他都会反弹回来,这才是站桩所应有的觉知[11]。所以站桩不是死站,而是要体会上下、左右、前后的身体整体性争力,能引导全身上下、左右、前后互相牵引而共争一个中心,习得一种以静态平衡为主的身体能力。
2.2 “对”:通贯性劲力体知与对动态平衡的把控
“对不对”“好不好”通常是我们判断习武之人功夫水平的基本评价。传统武术的“对”既有只针对外形动作进行粗略指点的知识教学,更是对力点、角度等拳劲规范的强调。形意拳名师尚云祥弟子韩愈口述指出:对于一般非入室弟子,师傅只会给你指出这个动作对了,那个动作错了等简单的问题;而对于入室弟子,“对”则是指一个人功夫的思辨力强,所以对动作要深究到皮肤筋腱一毫一厘的程度来帮助学徒体知劲力[12]。
由入门拳架与站桩获得的静态整劲只是探究劲力的开始,一分一厘调整身姿是为获得通贯性的动态劲力。这是一种徐徐贯通由静到动的劲力,使习武者能从动态动作上巩固与精确静态动作中获得的劲力,以最终达到肢体动作准确规范与劲力顺达。由静到动常采用“一通百通”的传承方法。大成拳名家王建中认为“学拳,先求一。一生万物,你做到一个,后面的自然都出来了”[13];太极名师杨禹廷认为“太极拳就两个势子,一阴一阳,一通百通”。对于一通百通,传统武术拳师各有各的实践。如对于初学者,形意名师尚云祥常询问学徒对哪个式子有感觉,然后继续往深里教[7];八卦名师王培生强调要克服日常行走以步带身的习惯;形意名师李仲轩采用打一厘米拳来“锻炼动势,摸清拳架的来龙去脉”[7]等。对此,大成拳名师王芗斋总结道:“拳本无法,有法也空,一法不立,无法不容”[14]。劲力贯通后,人体就能基本体知到身体的变化而进行适时性的调整,最终达到人体动态下的平衡。这也是武术与其他外国技击项目的不同之处。中国武术专注于自我重心不倒的平衡[15],其他武术则强调硬碰硬的实力,故格外强调动态平衡。
2.3 “巧”:敏感性劲力体知与即时性反应跟进
“既习艺,必试敌”。习武较力是武术传承中的常态现象。习武较力常要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形,所以形意名师尚云祥说“练武就是练一切”。如果说“对不对”的贯通劲力能使人保持限定条件下动态平衡的话,那么能敏感一切才是真正能活学固劲的前提与根本。武术习练要达到活学固劲,其实质是身体具备了应激反应能力,即武术就是习练对于一切的敏感性。李仲轩说“打拳就像约定好了一样,应着对方来用招。只有练拳对一切都敏感时,才能在比武中发挥出应有的功夫”[7]。习武人敏感性的主要体现就是对对方进攻的预判。攻防进退有方向,行动起来有节奏,才能在比试中少挨打。
武术不像西方格斗项目一样是压“桥”和造“桥”硬碰硬的实力对抗[16],而是强调以柔制刚之道。预判就是以柔制刚的一个重要环节。已故武术家蔡龙云先生曾讲“当别人已经出手了你再还击就迟了”,此即强调预判的重要性。形意拳名师李仲轩讲“比武关键是看对方给了你什么好处”[7]。预判不仅是了解人,还要对环境信息全息把控,这正是武术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关于方向,其实就是强调找准发力点。方向感的体认是习武关键。方向一乱满盘皆输;练武有了方向感才能对人对己有纲领[7]。习武到一定阶段,师傅常会通过不稳定的情形设置来提高习拳者的稳定性,以帮助其体认方向巩固劲力。武术攻防格斗体认方向的过程,也是体认在应激状态下身体找准发力点的能力积累过程。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形意拳大师薛颠所谓的“搁对地方”,收到较好的发力效果。关于节奏,传统习武人的练拳节奏,不是现在学校学生的口号式节奏,而是一种以意导气,以气催力的发力节奏。有了发力节奏,就不容易受别人牵制而能自由地发力与换劲,也就能在比试中占据主动地位,并越练越上瘾。“管他呢,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保持动态平衡。这是已故武术家蔡龙云先生对比试能取得成功的经验之谈。
2.4 “妙”:“身长”性劲力体知与实效明显的反击突破
传统武术强调的劲力是指六合整劲。形意名师李仲轩讲“得了六合明三节”(根节、中节、梢节的三节武术身体,使身体贯通为一个整体),即是讲六合能协调人体起力、导力、发力的三节身体为一体,用整个身子发力,而非仅仅局部的肢体之力,也就是真正改变人体用力的杠杆结构。形意拳师韩伯言认为“耍巧容易比长难”,“杠杆比对手长一截,就好控制他了。大拍子打小球,可杀可留,打出各种巧妙”[12]。意思即是讲,武术攻防技击之妙就是妙在身体三节能表现出整体为一的“长”上。为达到身体三节为一体的“长”,武术中常采用“三追三催活三节”“查缺补漏齐三节”“器械拓展促三节”“以头领身纠三节”[17]等方法,使习武人发力时能脚接地力、调控身体、力上拳头,不断生成“整中有长”的身体发力结构,真正发挥技击效果。
武术是攻防技击之道,强调“击必中,中必催”,靠的是虚实相间之力。虽然武术劲力有虚实之分,但要真正给对方造成致命性打击,还是要依赖于能够力上拳头的实力。武术中有“力不达梢实而仍虚之说”。就是讲只有力上拳头了,才能把整个身子的力量都用在拳头上,发挥出最大技击效果。当然如果习武人脚扣地不紧,不能利用地面的反作用力,也会大大影响力上拳头的发力效果。故而,习武人往往采用练“蹲墙功”等以根催稍的练习方法,提高习武者脚接地力的扣地能力。武术拳谚曰“万般准备一旦无,手招不如身招熟”。身子能自由调控是“全身重量上拳头的好法子”[7],武术强调能自由调控身子对劲力发挥的重要性。身子转换、起落等灵活了,才能起到上下连贯一体的枢纽作用,保证发力效果。
2.5 “绝”:意象性劲力体知与即拳即艺的游于艺
与一般性身体发力不同,武术强调用意不用力。不同拳种用“意”不同,比如太极的摸鱼,形意的捉虾,八卦的推磨等。武术练到最高境界是练拳意而非拳技。“意”最基本的要求是能辨别人、环境等各种现象信息的变化[7],引领身体达到发力最合理的理气结构。薛颠曰“一气贯通而谓之真合矣”[18]。只有身体达到发力最合理的气理化结构时,技术操作实践才能表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绝技。达此水平,习武人常常能做到有形也无形,无形有真形,随身所欲,举手即是[19]。实践操作中往往一个无形的动作能使人即刻完败,故而常常给人造成一种神秘化的认知与想象,也由此吸引了无数人对武术一见钟情,如形意拳名师尚云祥即是用强调起落动作“鹰捉”三指一划的摩挲劲震撼了李文彬,让他诚心于习武。
意象性的体知劲力时,习武人就不但能随心所欲,而且独具特色形成绝技,如半步崩拳的郭云深、双撞掌的程廷华等。正是有了如此高超的绝技,才使得他们在较技时能游于艺式地自由发挥拳技,以物对手、影子对手等方式达到“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特异化效果的双赢结局[20],并伴随酝酿了一种受世人青睐的“善养浩然之气”社会威望。习武人不但技艺独具特色,并且传承武术也别具一格。如尚云祥用“我教的是我这一套”启发学徒创新性传承,并以学徒能否创拳作为出师的标准[7],由此创拳往往成为一些习武人毕生的追求。
由上可知,武术人“会、对、巧、妙、绝”的习武历程,正是身体积累齐整劲力、贯通劲力、敏感劲力、身长劲力、意象劲力的体知历程,同时也是身体处理静态平衡、动态平衡、即时反应、即时反击、游于艺的主体认同过程。
3 身体在场的习武进阶及其教化俱进
武术术道融合、由术及道,以身体感知为前提的技能习得使生理身体主体性得到认同,也涵化了内隐于其中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培育主体教化,构成了武术由技术而教化的内化传承。
3.1 生理身体的劲力体知内隐了武术参与的主体认同
研究表明:能协调与掌控自己身体的人对体育参与有更多的积极性[21],体育身体的练习成就是体育参与与主体认同的中介变量[22]。体育如此,武术亦如此。武术人常将习武阶段划分为小乘、中乘、大乘,或明劲、暗劲、化劲等,就是对不同技术学习阶段身体不同体验认知与主体认同的侧面描述。习武人技术学习同时获得的身体本体认知与主体认同是一体两面的。身体本体感知的获得表面上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时间记录,其实是肢体之力到全身之劲的身体空间的重新部署[20],武术身体空间的内在逻辑是“六合明三节”。上文“会、对、巧、妙、绝”的习武历程就是一个静合、动合、力合、气合、意合的过程;也是身体由“整”到“长”,再到“整”“长”互促合三节的过程[17]。以上理论认知是以实践中“学虫子”的桩功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节奏感、“脚如犁行”的方向感等内在体验为前提,由此形成武术人能静态平衡、动态平衡、敏感反应、实效反击、游于拳技的主体认同。传统武术人以“有了节奏就会越练越上瘾”“有了方向才能对人对己有纲领”等的切身体验,内隐性地诠释了身体的内在本体认知与主体武术参与的相辅相成关系。
3.2 社会身体的交往体知移情了主体间性的主体认同
虽然武术传承常讲“未曾习武先习德”,但真正的武德认知却常常因为移情而发生于习武历程中,“会、对、巧、妙、绝”的习武渐进历程,同时也是武德由被动到主动的深化理解与实践的过程。中国武术传承强调模拟血缘的师徒如父子,这就隐喻了武术的师徒传承是以情为基调的教化过程。与以往文献武术传承拜师学艺“不传”“不教”以及各种门规等冷冰冰的记载不同,真实的武术传承不排除这些被动的武德教育过程,但更强调以习得身体长杠杆发力结构为前提的养练一体(门户药方等)、多元启示(生活近譬等)、教之比试(靶子陪练等)、拓展传承(游学指导等)、点到为止(较技时关爱对方生命的影子对手与物对手等)等人情逻辑,以照顾的以情达心方式[21]达到“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使对方移情。同时也以实践或展演拳技为前提的民事仲裁(技术符号为表征的调节纠纷等)、为国为民(小则维持社会秩序,解决门户之争,大则抗击列强侵略等)等大爱逻辑,以命运共同体的共存共融方式达到以责为格[22]使对方移情。武术传承中人情逻辑与大爱逻辑是对双方都有效的主体间性[23],以互利共生而教化育人。
3.3 心理身体的“静”“勇”体知涵化了精神气质的主体认同
武术“会、对、巧、妙、绝”的拳技进阶历程,也是习武者由好怒易斗、平息躁性、静养生性的情绪调控过程。中国文化“论心从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认为论心则应落实到情来讲[24]。在“会、对”阶段的习武初期,习武人往往刚刚学了皮毛,就以为自己身手了得,常有好斗争胜的欲望,侥幸胜了便会沾沾自喜,多数情况下会由于“怒则生暴而藏拙”[25],“惊则气乱而无神”[26]等心不控体而遭惨败。在此习武阶段,技术动作与情绪调控还基本没有吻合。武术拳谚云“未学打人,先习挨打”。学习攻防技击必须先经过预防挨打的应激习练。这是一个“克服浮燥、力求谨慎、追求平静”等以心合技的融合阶段。习武到“巧”甚至“妙”的阶段,能体知到武术动作本身就是情绪的外化,便会有“虚势则喜、着力则怒、过势则哀、逼门则乐”[27]等相伴相生的经验反思与主体内省。此时情绪就是动作,动作亦是情绪。孙禄堂说“武术可以变化人之精神气质”。刘奇兰拳论摘要有言“变化人之气质,得其中和而已”[7]。中和的本质就是以静为本的情绪弹性控制。调心古称“练神”或“存思”,即意拳名家王芗斋所讲“动作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动作”。
4 结语
在“会、对、巧、妙、绝”习武历程中,不同境界伴随着不同的本体体验感知与身在——身能的主体反思认知。主体反思源起于本体认知,不仅表现为生理身体方面如何使用身体发力,而且代偿社会身体隐喻人际交往、内化心理身体培育精神气质,如此又反哺于生理性的身体使用。这是习武人能习武上瘾的内在机制,也是武术教化育人的源泉与根基。这与体卫艺司王登峰司长所强调的“让学生学会1~2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要有面向人人的竞赛”讲话精神一致,与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所讲“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也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