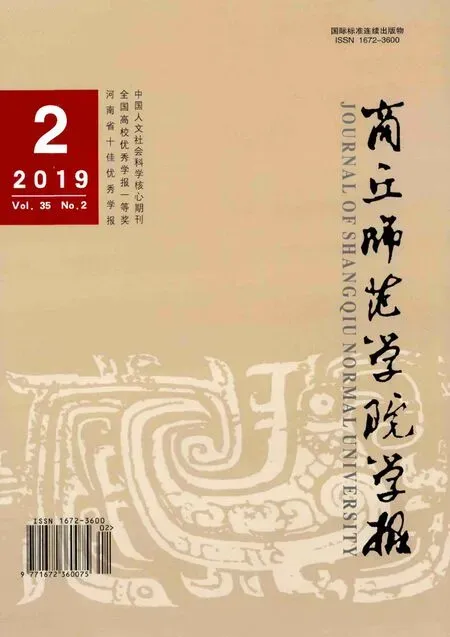春秋时期“刑加于大夫”事例类征
——以《左传》为中心
牛 钧 鹏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周代基于“亲亲”之谊,对犯罪的贵族用刑,会顾及情面[1]380。春秋时代随着礼崩乐坏、新旧观念交织,“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78的理念逐渐式微。为了达到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的目的,“常刑”或“九刑”,不仅施用于犯罪的庶人,也经常加诸违礼悖逆的统治阶层成员[3]386,其所受刑罚大致可归为死刑、肉刑和放逐刑。刑罚施加于大夫及以上的统治阶层成员,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政治效应。以《左传》为中心,分析春秋时期刑罚施用于各国统治阶层成员的事例,可作为了解春秋时期政治发展的一个切入口。
一、死刑
春秋时期死刑的形式、标准不一,但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目的相同,乃是大辟之刑。当王子、公子、卿、大夫的作为已经威胁或侵犯到君位、政治秩序及国人群体利益时,时常导致死刑的施行。此外,基于整饬军纪、排除异己及取悦外国等因素考量,统治阶层的成员遭受死刑也不在少数。
(一)刑加于弑君犯上者
弑君叛乱的罪行为天下人所厌恶,“贵族有篡位,弑君,弑父,及贵族自相争夺,残杀等危及国家秩序,扰害贵族全体安全的行为,不能为贵族全体所容忍而超过舆论的谴责程度时,常为贵族所放逐或杀戮”[4]204。
《左传》隐公四年记:“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其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5]35-38鲁隐公四年,卫国公子州吁弑杀卫桓公、篡位之举使他缺乏统治卫国的正当性,故而“未能和其民”。经由老臣石碏的设计,陈人将州吁及他的党羽石厚(石碏之子)扣留,卫人派右宰丑在陈国濮地杀了州吁,石碏也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到陈国杀了石厚。州吁因弑君篡位的罪行而伏诛;杀掉石厚,则是由于石碏身为宗族长老为避免石氏家族受到石厚党同弑君罪人的牵累,断尾求生以保全家族利益的权宜做法。这桩事例显示了“家族成员不孝由宗主决定并实施惩罚,国家并无任何异议,甚至予以支持”[6]25。
《左传》庄公十二年载:“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比及宋,手足皆见。宋人皆醢之。”[5]191-192鲁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杀宋闵公及仇牧、大宰督等人,立子游为君,其党羽南宫牛、猛获则帅师围亳,讨伐公子御说。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讨伐其弑君叛乱的罪行,南宫牛与子游皆被杀,猛获奔卫、南宫万出奔到陈国,但终被引渡回国处以醢刑(死刑的一种)。“公臣事君应忠贞无贰,若觊觎权位,弑君篡上,深为春秋时人所耻”[7]182。
(二)刑加于谋逆作乱者
春秋时期,社会对于篡逆之事,“如一国之君位背正统主义而被人篡立,则篡立者竟成为大逆不道,乱臣贼子,各国非惟不应予以承认,且有讨伐之义务”[8]105。
《左传》庄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载:“(周)惠王……取为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冬,立子颓。”“……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徧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5]212-217鲁庄公十九年,周王室五大夫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分别因为周惠王夺其地、收其秩之事而发动叛乱,以苏子为援,拥王子颓攻打周惠王,后来更借重卫、燕两国的军队攻打成周,立王子颓为周天子。次年,王子颓设享礼款待五大夫,郑厉公向虢公指出王子颓篡位叛乱的罪行。鲁庄公二十一年,郑厉公与虢公攻杀王子颓与五大夫。郑厉公的“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之言,反映了篡逆之事无法见容于春秋社会的事实。
《左传》僖公十年载:“丕郑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济矣。’冬,秦伯使泠至报、问,且召三子。郤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皆里、丕之党也。”[5]335-336鲁僖公十年,丕郑向秦穆公建言以重礼笼络吕甥、郤称、冀芮等人,意图推翻晋惠公夷吾、迎立重耳。但冀芮等人识破其计划,将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等人诛杀。对晋惠公而言,里克、丕郑之党的言行实属谋逆,已威胁到国君的权位和安全,必将其明正典刑。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吕、郤畏偪,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见之,以难告。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5]414-415鲁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返国即位,吕甥、郤芮等人预谋焚烧宫室、杀死晋文公,阴谋被寺人披揭发。晋文公在秦穆公的协助下得以平安脱险,并将谋逆之人处死。相对于晋惠公的强势作风,晋文公即位之初的权力基础较薄弱,必须依赖外国势力的介入才能平定叛逆、对作乱之人施行死刑。
(三)因巩固权位而施刑
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而滥用公权、侵害臣下使之遭受死刑乃至被夷族,不见得有什么正当性的理由,多是欲加之罪、便宜行事。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载:“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5]226-227,230,232晋国桓叔、庄伯的家族势力强盛威逼公室,令晋献公感到忧心。鲁庄公二十三年,在晋献公的授意之下,大夫士蒍开始展开一连串铲除桓、庄之族势力的行动。他先在群公子之间说富子的坏话,与群公子设计除去了富子;次年士蒍与群公子又合谋杀了游氏之二子;鲁庄公二十五年,士蒍又使群公子杀尽游氏之族,同年冬天,晋献公再包围聚城,杀尽群公子。这一连串的杀戮行动是晋君在自身权位受到威胁时,实施的反制措施。
缺乏实权的国君若想借由杀戮大夫来夺回权力,一旦功败垂成,面对掌权者可能的反扑威胁,国君不仅权位朝不保夕,就连性命也岌岌可危。《左传》桓公十五年载:“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夏,厉公出奔蔡。”[5]142郑厉公忧心于大夫祭仲专权,鲁桓公十五年,郑厉公派祭仲的女壻雍纠谋杀祭仲。不料事迹败露,雍纠被杀,郑厉公被迫出奔到蔡国。由此可见,死刑实施的成功与否,与统治者是否掌握实权有一定的关系。相对于晋献公透过士蒍有系统、有步骤地铲除威胁自身权位的异己,郑厉公的权力不像晋献公那样稳固,行动失败的话只得逃亡到其他诸侯国。
(四)因排除异己而施刑
春秋时期,政敌为私利而排除异己、蒙蔽国君,使死刑借由谮言而加于大夫之身者,不在少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子上……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大子商臣谮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5]504鲁僖公三十三年,晋国阳处父攻打蔡国,楚令尹子上前去救援,与晋军对峙于泜水。子上因为担心渡河会遭到晋军的袭击,于是率楚军后退三十里,其做法正好给了太子商臣诬告他的口实。指称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躲避晋军,使楚国蒙受耻辱,罪行深重,楚成王因之杀子上。太子商臣之所以要谮杀子上,是因为子上曾对楚成王说:“且是人也,蠭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5]513-514反对立商臣为太子。商臣对子上怀恨在心,成为太子后便伺机谮杀之。
《春秋经》成公八年载:“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成公八年亦载:“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5]836,838鲁成公八年,赵庄姬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将要发动叛乱,栾氏、郤氏都为她作证,赵同、赵括因而被杀,赵氏宗族亦被夷灭,仅赵武匿于公宫而得免。
(五)为伸张诉求而施刑
春秋时代,国人的政治自主性更为提升,不乏国人驱逐、杀死大臣甚至国君之情事[9]353-355。统治阶层的作为若不符国人的期待,则国人往往加以批判乃至举事、用刑。刑杀则是国人为达成政治目的、伸张诉求所采取的一种激烈手段。

《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5]1050郑国子孔执政专权独断,国人对此感到忧心,于是追究西宫之难与纯门战役的罪责,鲁襄公十九年甲辰,子展、子西率领国人攻杀子孔,子孔的家业也遭到瓜分。“公卿统治阶层平时的行动不能使国人十分满足,也会受到国人的批判……《左传》所叙述国人之向背是对公卿统治阶层的一项批判标准。”[10]866
《左传》哀公五年载:“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郑人恶而杀之。”[5]1631郑国下大夫驷秦富有而奢侈,常常将卿的车马服饰陈列在他的庭中,子思评论其“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5]1631,鲁哀公五年,郑人因为厌恶驷秦的作为而杀之。驷秦不守其位、僭越失度,国人难以容忍,成为实施死刑的参与者、主导者。
(六)因整饬军纪、追究败责而施刑
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861,军事为各国所重视,一旦军纪涣散、部队战败,主帅往往成为归罪的对象,常被施以死刑。《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5]356-367鲁僖公十五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陷在泥泞中不得出,向大夫庆郑呼救。庆郑非但不救援,反而批评国君不听从他的劝谏,致使晋惠公遭到秦国俘虏。待到秦国释放晋惠公回国,庆郑亦被刑杀。《国语·晋语三》记,庆郑所犯大罪在于“失次犯令”[11]317,而从其对蛾析说的话中可知,为人臣者在战役中“陷君于败”,罪行当处死,否则国家就会“失刑”。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5]470-472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战于城濮,晋国中军在沼泽地遇到大风,丢失了旗帜,祁瞒因此犯了军令,遭到司马处死,并遍告诸侯。晋军回师之际,舟之侨先行回国,后来亦遭受处死,并通报全国。先前攻曹之役后,颠颉因为不满晋文公赦免曹国僖负羁家族,愤而放火烧毁僖负羁的家,也遭受死刑,并使将士周知。晋文公将颠颉、祁瞒和舟之侨三个罪人处死而使人民顺服,君子因而称他“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不失赏、刑之谓也”[5]472。晋文公究责施刑,从而建立领导威信,对战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5]468城濮之战,楚师败绩,申、息的子弟多有伤亡,楚成王派人责备令尹子玉。子西与孙伯所讲“君其将以为戮”[5]468之语,亦点明楚成王将会追究主帅子玉的败战责任,子玉最后选择自杀。
《左传》昭公六年载:“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干谿。吴人败其师于房锺,获宫廐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5]1279-1280鲁昭公六年,楚灵王怕徐仪楚背叛,遣薳泄攻打徐国。吴人救徐,楚国令尹子荡因而率军攻打吴国,在房锺遭吴人击败。由于战败者死,但子荡并未负起战败的责任,却把罪过推给薳泄而将他处死。
(七)为取悦大国而施刑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常有之事,小国、弱国常基于外交因素考量,宁可舍弃统治阶层的成员、强加罪名致之于死,来取悦大国。
《左传》僖公十年载:“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里克)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矣。’伏剑而死。”[5]333鲁僖公十年,晋惠公在周王室与齐国的支持下顺利即位,他以将中大夫里克曾经弑杀奚齐、卓子二位国君及大夫荀息为由,赐死来讨好周王室和齐国。虽然里克认为这是“欲加之罪”的说辞,但在晋惠公掌控实权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以剑自杀。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5]452鲁僖公二十八年,晋国欲攻曹国而借道卫国,卫国不答应,晋国因而攻之,楚人前来救援卫国,未胜。鲁国本向楚国,派公子买在卫国驻守,但鲁僖公又畏惧晋国,只好杀死公子买,并安上驻守期限未满就擅离职守的罪名,来讨好晋国、哄骗楚人。可见,大国的态度足以影响他国死刑的施行。
二、肉刑
墨、劓、刖、宫以及鞭、扑在周代“九刑”中,都属肉刑。但据《国语·鲁语上》载臧文仲之言,鞭、扑乃“薄刑”[11]152,仅是带有惩戒、警惕性质的轻微责罚;而所谓的“肉刑”乃是会对受刑人身体造成永久伤害的墨刑、劓刑、刖刑和宫刑。肉刑除了使受刑者的身体受创伤而残废、行动不便之外,还会对受刑之人的宗族乃至国家产生相应的政治后果。
贵族一旦沦为刑余之人,便成为宗法社会中的边缘人,“刀斧之痛、伤残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身受肉刑意味着在民事关系上的死亡”[12]17-18。
《左传》成公十七年载:“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武子召庆克而谓之。庆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謪我。’夫人怒。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国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鲍国相施氏忠,故齐人取以为鲍氏后。”[5]898鲁成公十七年,鲍牵向国武子揭露庆克与齐灵公母声孟子私通之事,国武子告知庆克,庆克心生畏惧,反而鼓动声孟子向齐灵公进谗,指称:高无咎与鲍牵意图谋逆,将改立公子角为新君,国武子也知道这件事。鲍牵因而遭受刖刑。鲍牵被刖之后,齐人从鲁国召回鲍牵之弟鲍国作为鲍氏的继承人,此举反映了鲍牵因身受肉刑,已经失去了家族地位的继承权,其原本享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也因为受刖刑而遭剥夺。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亦载孙膑曾遭庞涓“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13]2163,其后齐威王欲以孙膑为将,孙膑却以“刑余之人不可”[13]2163为由推辞。因遭受肉刑而无法享有某些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事例,不仅在春秋时期存在,更延及战国时代。
肉刑“让刑人充任贱役,最初可能是一种恩惠性的权宜措施,它能使因肉刑而被社会抛弃的人得以生存”[12]17。但是,因其终身奴役的特征,刑余之人被迫终身充任贱役,任之为近侍,则存在着某种政治风险,尤其是杀身之祸。“刑人不在君侧”[5]1031,正是顾忌刑人心怀怨恨而谋害国君,因此不让他们接近国君。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5]1157鲁襄公二十九年,吴王余祭以越俘守卫宫门,却因此被弑身亡,故《公羊传》讲“近刑人则轻死之道也”[14]462-463。《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提到齐庄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贾举便为崔杼监视齐庄公以成弑君之事。由此看来,刑人接近国君,是很有可能对国君的安全造成威胁的。
而大夫及以上的统治阶层成员一旦受刑成为刑人,将遭受众人的鄙视,从春秋时期对待刑人的态度可见一斑。《左传》襄公十七年载:“齐人获臧坚,齐侯使夙沙卫唁之,且曰:‘无死。’坚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以杙抉其伤而死。”[5]1031鲁襄公十七年,齐国攻打鲁国,俘虏了鲁国大夫臧坚,齐灵公派宦官夙沙卫,赐他不死。齐灵公虽然赐臧坚不死,但却派受过宫刑的宦官去慰问他,臧坚觉得不受尊重而自杀。宦官虽不属大夫以上的统治阶层,但由此例可看出刑人的身份颇受鄙视。
三、放逐刑
“夫刑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周家之刑狱其钦恤明允固无异于唐虞也。”[15]13有周一代,在“明德慎罚”的政治理念影响下,主事者往往对贵族采取宽宥的处置,令犯罪者在流放地忏悔思过。《左传》中载有“放”“逐”之刑,“放”即流放之刑,“逐”则指驱逐出境之刑。“流宥五刑”[16]65,以流放之法来宽宥应处“五刑”之人。以维护政治安定看,放逐刑乃是具有宽容性质的政治惩罚。
《春秋经》宣公元年载:“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又《左传》宣公元年载:“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5]646,648鲁文公十二年的河曲之役,晋国大夫胥甲父和赵穿不肯将秦军逼迫到黄河边,秦军因而乘夜遁逃。鲁宣公元年,晋人惩处该战中不服从命令者,赵穿因为是赵盾之侧室及晋襄公之婿而豁免,大夫胥甲父则被流放到卫国。被流放之人身体不受损伤,生命也不会受到威胁,可以视为是一种权宜性的政治处置。
《左传》庄公六年载:“夏,卫侯入。放其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5]168鲁桓公十六年,卫国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被迫出奔到齐国。鲁庄公六年,齐襄公率诸侯之师伐卫,迎卫惠公复位。擅行废立,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处以死刑,但是公子黔牟却只流放到周,在罪行的惩处上显然获得了宽宥。
值得注意的是,施刑者能先行决定“放”刑执行的时间和地点。《春秋经》襄公二十九年载:“齐高止出奔北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5]1153,1167鲁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齐国大夫高止由于喜好生事以自居功,再加上专权,因而被公孙虿、公孙灶流放到北燕。这个事例记载了高止出国的日期,“乙未,出”,反映出高止有过动身前的准备,并非仓皇逃出齐国。
《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将行子南,子产咨于大叔。”[5]1211-1213鲁昭公元年,郑国公孙黑与游楚争妻,游楚误伤了公孙黑。子产认为,游楚年幼位卑,罪在其身,并指出他犯了不畏威、不听政、不尊贵、不事长、不养亲五条罪状,决定将游楚流放到吴国。“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将行子南”指出游楚将被流放的启程时间和目的地,可见流放的时间和地点是施刑者事先决定的。子晳族大势强,子产未能讨之,据子产谓国君“不女忍杀”“宥女以远”以观,游楚已受到宽容的对待,将其流放到吴国,可视为政治妥协的结果。
对于犯罪受刑或政治斗争的失利者而言,被“逐”出母国,出奔他国,不失为一种政治避难、寻求政治庇护的权宜做法[17]。《左传》襄公六年载:“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5]946宋国大夫华弱与乐辔经常彼此戏谑,又相互毁谤。鲁襄公六年,乐辔在朝廷上用弓套在华弱的脖子上像带枷一样,宋平公认为司马在朝廷上带枷是为不详,于是将华弱驱逐出境。同年夏,华弱出奔到鲁国。这一事例,未言明华弱出奔到鲁国的确切时日,“遂逐之”说明华弱可能是在施刑者决定后立即遭到驱逐出境,但是受驱逐者显然较被流放者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出奔的国家。
《左传》昭公六年载:“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5]1277-1278鲁昭公六年,宋国右师华合比欲求媚太子佐而将杀寺人柳,华亥与寺人柳勾结向宋平公告状,华合比因而遭到驱逐,出奔到卫国。华合比被驱逐,主因在于宋平公感受到自身的权位受到威胁,不能将华合比留在宋国以滋后患。立即驱逐他,其目的在于隔绝祸乱、防患未然。
《左传》定公十三年、十四年载:“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愬之曰:‘戍将为乱。’”“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5]1592,1594鲁定公十三年,卫灵公厌恶公叔戍,南子向灵公指控公叔戍将要发动叛乱。次年,公叔戍及他的党羽均遭到卫灵公驱逐出境,赵阳出奔至宋国,公叔戍出奔到鲁国。公叔戍遭驱逐的主因在于南子对他的指控,让早对公叔戍心生厌恶的卫灵公更加忌惮,将其驱逐出境,以免心中忧患。
值得注意的是,遭受驱逐出境的贵族仍有再次返国的机会。如《左传》宣公十年载:“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5]706齐国大夫崔杼受到齐惠公的宠信,高、国二氏都害怕他的逼迫,鲁宣公十年,齐惠公去世,高、国二氏乃将崔杼驱逐出境,崔杼出奔到卫国。据《左传》成公十七年云:“齐侯使崔杼为大夫。”[5]900可知,先前遭驱逐的崔杼当时已经重返齐国。
《左传》哀公十六年、十八年载:“卫侯占梦,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与卜人比……乃逐大叔遗,遗奔晋。”“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卫侯辄自齐复归,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5]1705,1713鲁哀公十六年,卫庄公蒯聩的宠臣因为向大叔遗求酒不成,便与卜人勾结,借卫庄公占梦之际谮言大叔遗将不利于君,大叔遗因而被驱逐出境。鲁哀公十八年,随着卫出公返国复位,大叔遗等原本遭卫庄公驱逐出境的人也得以归国官复原职。
四、结语
刑罚的原始机能在于把恶人驱逐出社会,在此一目的上,死刑、放逐刑和肉刑是相同的[12]18。春秋时期,施行死刑,或因维护政治秩序,或为贯彻私人意志而侵害人命。当大夫阶层成员威胁、侵犯国君个人权位或国人群体利益时,常被处以死刑;弑君、谋逆或僭越常制者,则会引起国君或国人的制裁;而统治者为巩固自身权势利益便宜行事,也会使大夫难逃死刑、家族遭夷灭的下场;大夫之间会因私人利害而蒙蔽国君、谮杀同僚,亦使死刑成为排除异己的政争手段;由于军事过失、追究败战责任或为取悦大国的原因,导致大夫阶层成员遭受死刑,也非偶然。统治阶层成员遭受肉刑除身体受创伤外,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往往遭到剥夺,从而沦为宗法社会中的边缘人;刑余之人虽因政治施恩而得以苟活,但却终身充任贱役,必须忍受地位卑贱所带来的羞辱和疑忌。放逐刑乃是具有宽容、隔离性质的政治惩罚,“放”刑将封建阶层成员流放远地,有达成政治妥协、宽宥犯罪者的用意;“逐”刑则将统治阶层的成员驱逐出国,意在消除政治祸患、防患未然,而遭到驱逐出境的大夫阶层成员可以选择出奔他国,也能因母国政治情势的改变而得以返国复位。以《左传》为中心,举春秋时期“刑加于大夫”的事例以类证,可知春秋时期刑罚往往取决于个人意志,与西周礼制原则多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面貌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