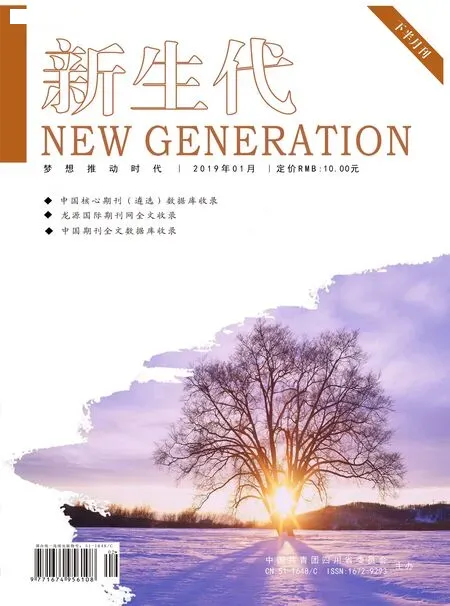曹魏复议肉刑之我见
曹楚炜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一、曹魏之前肉刑的发展及废立
对于肉刑的定义,古今不同。在古代,肉刑一般是指斩人肢体、毁人肌肤之刑,具体包括黥 (墨)、劓、刖(剕)、宫四大类,四者程度逐渐加深。除此之外学术界有另外一批学者认为肉刑为古代五刑,多出一刑为大辟(隋代之前死刑的统称)。笔者根据曹魏时期群臣复议肉刑的主要内容,采纳第一种说法,即黥、劓、刖、宫四大类。
关于肉刑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说起源于蚩尤苗人,《尚书·吕刑》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椓,刵,黥。”另外有一说言大禹开肉刑之滥觞,《汉书·刑法志》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无论肉刑起于蚩尤还是大禹,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以当今眼光看来,肉刑作为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刑罚,其实仍旧是氏族部落之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一种表现手段,它作为一种同态复仇的延续而被延用、保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对敌人只能采取剥夺生命的办法来维护本部落的安全,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古代死刑的肇始。在战争中,割损对方的身体甚至剥夺对方的生命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战俘奴隶的待遇,则将残损其身体以示其与本族人的区别,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墨、劓、刖、宫’刑的不同的执行方式。”由此可见,肉刑作为古代中国奴隶制时期的刑罚,它的适用范围一直都在不断扩大。汉文帝时期,缇萦救父,文帝深受触动,开始了对肉刑的第一次改革,并且颁布法令:“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汉景帝时期,肉刑又经过了两次下调,将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一百。肉刑被废一百余年之后,汉光武帝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复议肉刑事件,时任太中大夫的梁统与光禄勋杜林上书直议,言明政权初建之时应该去除苛政,才能使得百姓爱戴,刘秀采纳了二人的建议,本次复议肉刑无疾而终。在此之后,班固著《汉书》,其中专列《刑法志》,书中班固主张恢复之前的肉刑,并且系统地阐述了恢复肉刑的理由,这对曹魏时期主张恢复肉刑的大臣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班固《刑法志》仅为“一家之言”,没有进入当时统治者的视野,因此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很大波澜。
二、曹魏时期复议肉刑的高潮与平息
东汉末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百年未变的法律条文已经渐渐落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社会背景也对当时的刑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汉文帝时期被废除的肉刑再一次进入了曹魏君臣们的视线之中。曹魏时期对复议肉刑的大讨论共有五次,参与讨论的都是位高权重的核心人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传统法律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虽然是刑罚史上的一大进步,但也造就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第一,文帝时期颁布的新法令将之前的“斩右趾”之刑划归到了“弃市(死刑)”当中,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死刑的范围,在当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背景下,死刑犯人的增多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打击。第二,废除肉刑并不是文帝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由于淳于缇萦的忠孝有感而发,虽然颁布的新法律由张苍等人重新制定,但却造成了汉代律法中的一个重大失误:缺少了中间法。汉代之前肉刑作为死刑与生刑之间的一种刑罚,它的产生与演变具有着社会本身赋予的使命,肉刑的废除使得汉代刑罚出现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的现象,正如班固在《刑法志》中所说:“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奖惩失当,法律便会失去它存在的最根本的意义。
另外,武帝曹操的个人观念也是复议肉刑的一个关键原因。史书记载“魏武重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重赏深罚的法家思想一直被曹操所看中,五次讨论中的前两次都是曹操授意,恢复肉刑的目的昭然若揭。加之当时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儒家正统思想已经发生了动摇,乱世用重典使得法家思想有所抬头,正如《晋书·刑法志》中所说:“是时天下大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而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对于恢复肉刑以稳定社会制度这一举措,是持支持态度的。
最后,中国古代作为一个人治社会,国家的最终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在法律方面的表现就是刑法的使用都由皇帝一言而决,这就导致了肉刑废除的不彻底性,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时期施加在司马迁身上的宫刑。宫刑作为肉刑中的一种,在汉文帝废肉刑之后仍然大行其道,史书中也有许多以宫刑代替死刑的例子,《汉书·景帝纪》记载:“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除宫刑外,刖刑、膑刑也有过记载,而这些又为曹魏时期主张恢复肉刑的大臣们提供了事实依据。
曹魏时期对于肉刑的五次讨论的内容则是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恢复肉刑作为中间刑的地位,减少死刑的概率,最终目的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持此观点的主要人物是钟繇,他在《请复肉刑代死刑疏》中说道“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李胜也在《难夏侯太初肉刑论》中言“今有弱子,罪当大辟,问其慈父,必请以肉刑代之矣。慈父犹施之于弱子,况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腕;系蹄在足,则猛兽绝其蟠。盖毁支而全身者。夫一人哀泣,一堂为之不乐,此言杀戮之不当也,何事于肉刑之间哉?”持此论点者已经发现了汉文帝以来律法的不妥之处,此时提出的以肉刑代替死刑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的反对者显然提出了更好的解决方法,以王朗为首的反对派首先对钟繇复肉刑的初衷表示肯定:“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转而对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案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即劳役)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釱大骇耳之声。”王朗主张以劳役刑来代替肉刑成为新的中间刑,比之钟繇复肉刑更加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人民的易接受程度与可行性也更高,从而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被统治者所采纳。
第二是较之其他刑罚,肉刑的警示作用更强,而且去除肢体上的作恶部分,更能起到以刑止罪的作用。汉末天下大乱,军阀割据,长期的战乱与饥荒直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犯罪率的上升,主张恢复肉刑者认为肉刑可以有效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这一观点的拥护者主要有陈纪、陈群、李胜等人,陈群在《复肉刑议》中提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纪陈群父子的主张是“以刑止刑”,通过恢复肉刑来达到“永无淫放穿窬之奸”。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理想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抓住犯罪的本质其实是人的种种欲望,而不是手脚本身。以孔融、夏侯玄为首的反对者则认为肉刑是种毫无意义的刑罚,“夫死刑者,杀妖逆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于肉刑也。”夏侯玄的《论肉刑议》阐明了刑罚具有惩恶扬善的实际作用,与之前的陈群等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相比,观点显然更进一层,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他在《答李胜难肉刑论》中又提到“圣贤之治也。能使民迁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惩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惩戒则无刻截,刻截则不得反善矣。暴之取死,此自然也。伤人不改,纵暴滋多,杀之可也。伤人而能改悔,则岂须肉刑而后止哉!杀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断截之政,末俗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杀人无所,斫人有小疮。’故刖趾不可以报尸,而髡不足以偿伤。伤人一寸而断其支体,为罚已重,不厌众心也。”夏侯玄这段将肉刑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论述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时代背景下各家思想的碰撞与交流。
三、复议肉刑与各家思想的碰撞
曹魏时期肉刑的复议与当时诸子学说的复兴有着很大的关系,天下纷争正是各派学说重登历史舞台的绝佳时机,从当时各个大臣的言论与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儒法两家的对撞与儒家内部的自我整合与发展。
汉末法度废弛,纲纪败坏,汉代以来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儒家名教已经不足以应对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此时此刻,复议肉刑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对汉末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提出的批判,他们看到“肉刑之废,使得轻重无品,生罪入死,死罪得饶,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未至于死,髡笞则太轻,若无肉刑,无法惩治中罪,罪与罚两相名实不符。所以,肉刑之复,正是使罪罚之间,名实相符,又能治中罪,惩劝戒。”正因为在汉末天下崩坏之际,法家思想再次得到重视,连带着复肉刑之议再成为讨论焦点。但魏文帝之后,天下三分之势已为定局,社会秩序也已经开始恢复,休养生息、稳定局势成为了重中之重,武帝时期奉为圭臬的法家治国政策也渐渐被更为柔和的儒家思想所取代,对肉刑的复议虽然也多有探讨,但整体已成一边倒的态势,曹丕也下《议轻刑诏》言己“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复肉刑论是魏武帝时留下来未完成的讨论,文帝时由钟繇再提出,继续讨论下去。钟繇从汉代始,便习刑名之学,为刑名家。钟繇主复肉刑,实与其主刑名之学有关,也与当时从刑名之学来主张复肉刑相一致。钟繇刑名之学在曹操时方能得势,文、明二帝时则不管用。文、明二帝明白地倾向于不主张复肉刑,钟繇之议亦罢而不行。明帝时期钟繇与王朗的论辩结果也是“时仪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恢复肉刑成为了镜花水月。
而在复议肉刑的诸多辩论中,不仅仅是儒法两家的争端,儒家内部也借此机会进行了一番交锋与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论述中反复被提及的“法先王”思想与“仁”的思想的碰撞。上文提到肉刑的使用历史悠久,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而不衰,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法先王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先王之法不可变更”更是一柄锐利的武器,曹魏时期主张恢复肉刑者也是举起了这杆大旗,指责汉文帝废除肉刑不合古道,进而提出恢复肉刑的观点和主张。当他们在与以孔融、夏侯玄为首的“教化派”相遇时,便又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其实无论是“法先王”派还是“教化派”,都是借用了圣贤的言论来阐明自己的主张,颇有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演变与发展。
四、复议肉刑的余波与影响
曹魏时期这次规模宏大的复肉刑之议,推动了我国古代刑法理论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刑法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大作用。它针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所遗留下来的弊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其中王朗以劳役刑代替肉刑来作为中间刑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新的刑法体系的建立。另外夏侯玄等人主张的刑罚当以教化为主也指出了预防犯罪的根本方法是防患于未然的德化礼教,中国的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