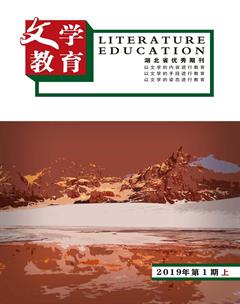论叶兆言小说的亲情书写
内容摘要:叶兆言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凡俗人生的生存意义和情感世界,在冷静的叙述中潜藏着对日常情感的思考与困惑。他打破了亲情社会的常规性和有序性,将亲情中不易察觉的异质因素真实地呈现出来:长辈畸形的爱禁锢着子女的自由;晚辈不堪重负只能选择毫无意义的“出走”;父亲在场儿女却依然沉迷于“寻父”的游戏;欲望撕裂禁忌通过“乱伦”向亲情社会宣战。叶兆言通过讲述一个个家庭故事,颠覆了传统的理想化亲情,暴露了亲情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变与脆弱。
关键词:叶兆言 亲情 “出走” “寻父” “乱伦”
中国是由一个个“亲情社会”组建而成的,里面包含着的骨肉之情、手足之情、天伦之乐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伦亲情。家族内部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天生就具有相濡以沫的血缘亲情。“血缘亲情是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最稳定,也是最能显示家庭人情美与人性美的情感关系”[1]亲情不是激情的偶然迸发,而是与生俱来、永不磨灭的,伴随着人类从出生到死去。作为人类情感的普遍性表达和社会最底层力量的不可抗拒性,亲情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至关重要。但是亲情本身联系着古老的生存方式,避免不了新事物与旧亲情的碰撞,所以亲情既有坚韧宽阔的一面,又有脆弱狭隘的一面。古往今来,作家们就对亲情呈现一种模糊的审美姿态。即使是鲁迅在《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对封建人伦道德进行过猛烈抨击,但是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出走”,实际上他在家履行“孝悌”,默默承认了母亲为他安排的媳妇朱安,在外对兄弟慈爱宽和,“他向往兄弟怡怡、永不分离的弟兄关系,若非突生变故,他会尽力维持大家庭的生活”[2],充分反映了魯迅矛盾的亲情观。此外,大部分作家都绕不过对亲情人伦的书写。余华的《现实一种》展现了祖孙、母子、夫妻和兄弟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令人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世界的残酷与丑恶。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写尽了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不可通约性,展现了彼此的猜忌与窥探,家庭之间的亲情被可怕的梦魇所替代。到九十年代,正常的人伦亲情开始回归,以亲情的本原面目还原了中国人的情感故事。
叶兆言于1980年开始写作,在他的大部分的作品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他关注的焦点。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潜藏着对生命的思考或困惑,道出住房、家庭、婚姻、金钱等关乎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借以表现纷纭复杂的生活形态及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3]。其中书写亲情的篇幅很多,本文主要展现出叶兆言小说中亲情书写的不同形态:禁锢的亲情,“出走”的情结,“寻父”的母题以及乱伦的禁忌都有所表现。在叶兆言的小说世界中,亲情不是亲人同聚一堂、其乐融融的温情状态,而是呈现出一片淡漠与苍凉的笔调。叶兆言以温和平静的姿态既呈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不可遏制的爱,也写出了晚辈不堪重负,因“爱”而“出走”;既展现了血缘亲情中非常规的不伦之恋,也连带出了爱的背后畸形的情感因素。夫妻、父子或母女,不再是互为生存的依托和见证,而成为相互摆脱不了的负担。叶兆言撕破了那个虚伪的亲情社会的面纱,暴露人性的隐秘与亲情的脆弱。通过讲述一个个家庭故事,颠覆了传统的理想化亲情,呈现出亲情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变。
一.无法言说的亲情桎梏
《半边营》是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中的一部小说,主要叙述的是在深宅大院中,久病在床的华太太对三个子女身心上造成的伤害。“叶兆言的《半边营》刻画一个年华老去的华夫人与她三个子女间的怨怼关系,摆明了是向张爱玲《金锁记》的敬礼之作。”[4]故事中的华夫人其实就是《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姊妹”。她常年昏睡在“一张半新不旧的大铜床上,严严实实罩着一条厚被子……”,子女们精心照料,处处迁就。然而性格专横的华太太“脾气一向与人为难,越把别人搞得下不了台越称心如意。”她嘲讽陪伴左右的长女斯馨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嫉妒二女儿嫁了个有钱有权的男人,把儿子阿米折磨得“刚三十岁的人,瘦的像只虾,满脸的疲倦,满眼睛的惶恐。”。她在儿子永远不成熟、女儿嫁不出去、儿媳重蹈覆辙的快感之中获得病态的满足感。“百善孝为先”的伦理和亲情的纽带强制性地将华太太栓在阿米和斯馨的身上,亲情的重担压着他们无法呼吸。华太太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制造了一个密封逼仄的囚笼,将儿女们圈养在里面,在施虐的快感中埋葬儿女们的青春年华和美满婚姻,上演一幕幕“亲情悲剧”。她罔顾子女的独立意志和爱情自由,所谓的亲情关怀演变成禁锢与被禁锢、施虐与受虐的畸形关系,而亲情在这个幽闭的空间中完全失去了温度,成为儿女们手脚上冰凉的镣铐。母爱的光辉已消失殆尽,温情脉脉的亲情被分解得支离破碎,人性的复杂与荒谬暴露得淋漓尽致。王富仁认为“严格说来,母亲对于儿女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观念中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他或她的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世界,一个他或她生存的伊甸园。”[5]而叶兆言笔下的母爱,却成为埋葬儿女青春和幸福的坟墓,“母爱神话”已然衍化成母爱异化的悲歌。
而在他的另一部小说《花影》中,妤小姐的父亲对她的关爱是从小教她抽鸦片和为她拒绝宅院外的一切新鲜事物,充分施展着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父权制逐渐演化为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在这个制度内的权利运行矢向是:年老的男性有权支配青年男性,男性有权支配女性。”[6]父权制在血缘关系体系中处于主导权,对子女的人生具有支配权。在家庭制度和人伦亲情中,父亲的权力应该被绝对肯定和拥护。因此在父亲管制下,童年生活中的绕膝之欢、天伦之乐都与她毫无干系。甄老太爷将妤小姐禁锢在一个逸乐淫猥的场所,却要求女儿严守规训,不能越防。密闭的生存空间和豪门“闺训”导致妤小姐没有任何机会接收外面的新事物,只能在父权的淫威下熬成老姑娘。而甄家大院本来就是一个类似于妓院的封闭式空间,除了父亲和哥哥,都是女人,小妾们言语上的性挑逗,还有淫声艳语都可能激发一个成年女性对于男性、对于正常的性的需求。然而除了那本能给她带来性启蒙的《金瓶梅》,妤小姐无处宣泄女性的烦恼和内心的性苦闷,所以她不得不压抑自己对于性的渴望,将所有的念想和疑问都埋在心底,直到自己成为甄家的继承人。父亲的去世给了她身心的最大自由,同时也唤醒了她潜藏已久的性意识。她开始对某种父权式的专断和既定的秩序产生本能的抗拒,大胆地向男权社会宣战。
王德威说“她是位最堕落最意外的‘新青年”[7]。虽然她有意识地反叛旧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将父亲曾经加之于身心的枷锁通通卸除,成为一位享受自由的“新”女性。但是她的武器是自己的“身体”,以自己的身体去诱使男性为她争风吃醋,满足她一直被宠溺的高傲。可以说,她一面在反抗父权制的禁锢,以自觉的意识去玩弄男性,为女性的王宫加砖添瓦;一面她又在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以父亲曾经统治甄府的方式来统治自己身边的男性世界,事实上,妤小姐只是依照父亲的模板重新建造了一个类似的世界,她一直活在自己营造的虚假的自由影像中。在这个影像中空虚和满足共存,善良和恶毒同在,显出暧昧不明的色彩。结局妤小姐瘫痪在轮椅上,怀甫成为男主人,甄府又恢复了男权统治的秩序,这说明妤小姐还是未能彻底摆脱父亲的影响。
此外,还有《陈小民的目光》中陈小民的母亲何萃芬,作为前组织部长的夫人,自以为“善于相夫教子有方”,却只会在儿女们的伤口上撒盐;《状元境》张二胡的母亲也是寡妇脾气,状元境有名的泼辣性子,对儿子和儿媳百般刁难,惹得整条街的人看笑话等等,这些变了质的人伦亲情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叶兆言以一个个悲痛的故事打破了长期以来亲情社会营造的假象,将母爱或父爱中的杂质通通倾倒出来,暴露在世人面前,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伦亲情。
二.意义缺席的“出走”之路
王富仁说“在最初的意义上,子女与母亲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但是子女的成长则意味着二者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子女的成长过程,但也是一个逐渐失去二者和谐关系的痛苦过程。”[8]在成长过程中,子女不仅从母亲怀抱中挣脱出来,进而可能与整个家庭发生分裂,走出家门寻找更大的自由天地,这就是贯穿现当代文学的“出走”情结。
叶兆言的《追月楼》曾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主要讲述了南京沦陷前后丁老先生一家的故事,是对巴金《家》的戏仿之作。“《追月楼》更直白简单一些,它其实就是一个当代人重写的《家》,表现了当代人对《家》的重新认识。”[9]其中仲祥“出走”的情节也是觉慧“出走”的翻版。然而与觉慧为打破封建家长专制、追求青年个性自由而愤然“出走”的意义不同,仲祥的走出家门,并非思想上有所新的追求,而是单相思的诱因使他稀里糊涂地参军报国。他不是陈旧的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也不是寻找新出路的先觉者,而是在潮流中被动地被裹挟前进的流浪儿。出走再归家是必然的结局,因为仲祥并不是《家》中最早的觉醒者觉慧,敢于冲出“狭小的笼”做最勇敢的叛逆者;也不是矛盾笔下的新女性梅行素,敢于从封建礼教的绳索中挣脱,走出自己的路。他的出走没有目的,不是为了拯救自己于封建牢笼,也不是为了在精神上获得重生,而是无目的无意义的一次出走。
小说中说到了家国存亡的危急时刻,仲祥仍沉迷于儿女私情,并且以参军报国为借口追逐男女之情。丁老先生是个开明的家长,十分赞成仲祥去前线做“义民”,并在临行前送给他《春秋三义正传》和《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代表着长辈对于他学业上的督促和理想上的支持,在亲情伦理秩序中,丁老先生没有阻碍子孙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们的爱与支持,竭尽一个家长的职责与情义。在丁家,仲祥并没有遇到不自由的婚姻或者大家长的专制等烦扰一代青年的家庭问题,相反,家庭给了他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其中寄寓了丁老先生的宠爱和希望。以家为中心组成了亲情社会不是一个专制王国,而是一个理想之地,虽然有小打小闹,却不存在仇恨和斗争等激进因素。但是仲祥却把这亲情之爱当成负担,认为爷爷老糊涂,不能理解自己单相思的痛苦心情。说明仲祥的出走其实也是对于亲情社会的“叛逃”,意在与丁老先生代表的旧伦理亲情一刀切断,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在这里,爱情已经战胜亲情后成为支配仲祥的唯一情感。“‘出走不仅仅是个行为,更是一种心态,是内心深处的叛逆与抉择,因而,完成了“走”的动作并不意味着真正地从陈旧腐朽中蜕变而获得新生。”[10]可以说,仲祥的“出走”情节展开的不是新与旧的矛盾,而是亲情与爱情的角逐。
在《没有玻璃的花房》中,当九岁的木木在发现父亲李道始和母亲林苏菲是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大义灭亲的革命激情。虽然房门被封,无家可归,但是木木仍然信心十足, “我决定离家出走,决定到大街上去流浪。流浪是与家庭割断联系的最好方式,木木要和李道始与林苏菲彻底决裂。”木木開始开始了自己的“出走”之路。孩童的出走比起成年人的出走感性色彩更加浓厚,但是透过孩子的心理,也可以折射出这一代人对待人伦亲情的心态。“孩子们自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缘亲情也不例外。”[11]懵懂的木木年龄虽小,却清楚地知道爱毛主席胜过父母亲,爱党和人民胜过自己的家人。木木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人,而父亲、母亲是反革命分子,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在人伦秩序中他已经从“儿子”的角色中脱离出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战士”。孩子时期天真的本性和对父母亲的依恋被阶级感情所替代,父母亲的崇高形象和温情脉脉也被解构,木木的“出走“其实代表着亲情纽带的彻底断裂、亲情社会的荒漠化。由此可见,文革时期的亲情遭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家庭人伦情感在阶级和革命面前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但木木的“出走”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游街队伍散尽之后是幽深的寂寞与悲哀,在被小混混欺骗之后,木木还是被寄养在另一个“家”,一个没有亲情维系的“家”。这次与成长于文革一代的孩子同步的“出走”过程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行为,因为即使木木走出家门,也不会被纳入真正的革命队伍之中,他所追逐的只是孩子们模仿成人世界的“革命游戏”。
“走出家庭、走出亲情包围,这本来应该是向着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宽厚的情感境界走去。[12]然而,叶兆言笔下的人物出走并不是出于反封建、反专制的时代精神,也不是处于追求梦想、提升境界的价值实现,出走只是一次无意义的旅程,最终还是以“丧家之犬”的面目回归家庭。满怀激情的“出发”与无法抵达预设目的的“结果”构成了一组反讽,希望和失望的交织,展示了人在时代面前的被动状态,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叶兆言对“出走”情结的再写,无疑是向传统的宏大叙事主题提出了挑战的宣言。
三.啼笑皆非的“寻父”之旅
“父亲”这个符号在不同为文化语境中具有多层次的文化意味,而且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亲生父亲。“需要父亲”这一基本的精神需求便驱策着每个孩子自小就心存对理想父亲的本能渴盼。[13]在现实生活中,父亲是严峻的纪律和原则,是理性和权威,体现着人类的社会原则。当父亲缺席的时候,人伦秩序就会失去一定的规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寻父”的想法。“‘寻父则主要是由于生存无奈的焦虑、灵魂无‘力的失落和人格意志的稚弱所导致的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对某种卡里斯玛(Christmas)式所在(人物符码或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的期待和呼唤”。[14]叶兆言小说也不能避免对“寻父”主题的书写。
《去雅典的鞋子》中的丽娜和《青春无价》中的来生都是在进行一场啼笑皆非的“寻父”之旅。丽娜本身的父亲是居焕真,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小时候的丽娜总是沉浸在同龄人对父亲的赞美和期待之中,然而当一家人聚齐之后矛盾日渐突出。母亲的谣言和自杀更是一个不解之谜,在丽娜和父亲之间添了一堵无形的墙。丽娜偶然间看到智仁勇的名字,浮想联翩的她以为这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此便沉迷于寻找亲生父亲的旅途。《青春无价》写的是“我”的朋友来生,偶然间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来海峰在台湾,开始编造一个个关于父亲的神话,并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寻父的道路。但当亲生父亲真正回大陆之后,他意识到现实中的父亲根本看不起自己,最后在幻想中杀死了父亲,寻父之旅至此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丽娜和来生并不是在“无父”的状态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形式上他们两人都有父亲。为什么还是在不断地“寻父”呢?这正是叶兆言对庸常人生的审视和思考的结果。“‘寻父,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母题,它昭示着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时做出的本能选择———向父亲寻求庇佑。”[15]叶兆言指出当代人虽然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物质生活,然而精神上始终处于无法安定的焦虑之中。自我身份的模糊和精神上的空虚驱使着他们去寻找理想中的“父亲”,寻找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青春无价》中的来生物质生活穷困,母亲是一条街上最穷困潦倒的女工,继父是个拉三轮车的车夫,视来生为家里的“拖油瓶”。物质上的清贫落魄,精神上父爱的缺失,导致来生心里产生深深的自卑感。持续出现的女朋友说明爱情并不能安慰他失落的情感,他需要的是“父亲”。血缘关系的断裂、缺失父爱的痛楚,加之经济上的窘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需求驱使他去寻找父亲。这个父亲是他心中建构的父亲,身份崇高而又温情脉脉的“理想中的父亲”。然而,亲情链条的重新接合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个神话中的父亲、来生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的理想父亲并不存在。现实中的来海峰只是一个自私虚伪、贪恋女色、毫无人情味的陌生人,从未在事业上帮助来生,在感情上弥补亏欠的父爱,他对来生的冷淡和嫌弃,与来生对他的崇拜和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完全解构了“理想中的父亲”形象。“与子辈理想中高大神圣的父亲形象相比,真实的父亲往往显得弱小、狠琐,……”[16]来生在一次次的希望和失望中,终于放弃了对理想父亲的找寻。就如叙述者所说,“来生寻找父亲的故事,也许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永远也不要找到什么父亲。寻找本身是一个最美好的故事。”《去雅典的鞋子》中的丽娜更是在寻找自己身世中完成了一次“寻父”之旅。在亲生父亲在场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寻找并不存在的亲生父亲,展现了现代人的情感荒谬和精神的无所归依。但是,与来生不同的是,丽娜并没有找到自己所谓的亲生父亲,因为居焕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虽然用科学证明了自己的身世,但是在丽娜的心中,永远不会放弃“寻父”的念头,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
叶兆言笔下的“寻父”并不是寻根文学寻找民族精神之根和传统文化之根,不是对历史的拷问和和挑衅,而是寻找当代生活中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根基。父亲不是善与美的象征,不是历史与文化的代言人,而是当代人的情感价值导向。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价值导向,会产生无法确认自我身份的焦虑,“寻父”让漂泊在世俗欲望之中的年轻人能够证实自己的身份,找到自我的定位与生存的意义,实现心灵困境的突围。所以,对理想父亲永不停歇的找寻是人类永远的情结,也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地蔓延的原因。
四.欲望放纵的“不伦之恋”
乱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它一直被视为文明形态和民族文化中的禁忌和罪恶。特别在中国,乱伦禁忌是作为一种严格的伦理规范,因为乱伦破坏了古老的伦理常规。“一方面是人类本能的乱伦欲望,一方面是人类文明的乱伦禁忌,本能和禁忌既对立分明又纠扯不清,文学作品正是以审美的模糊性而成为这种特定的集体深层意识的艺术转译方式。”[17]作家们正是通过文字给乱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从曹雪芹的《红楼梦》、曹禺的《雷雨》到陈忠实的《白鹿原》使“乱伦”逐渐衍变成一个“原型”故事。
叶兆言的长篇小说《走进夜晚》就是一部主要写乱伦主题的叙事文本。马文在继女蕾蕾十二岁的时候连哄带骗,强迫蕾蕾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当蕾蕾懂得男女之事后,为了自己的未来开始抵抗马文对她的侵犯,但马文在刺激下的罪恶欲望更加猖狂。“慈父的面具已经不复存在,温情的面纱也已经揭去,他对蕾蕾的所有要求,都以她是否让他满足欲望为准绳。”等到亲生女儿蒂蒂长大后,马文又企图强暴蒂蒂被家人及时制止,家人无奈只能结束他的生命,以此遏制住罪恶的根源。在《花影》中,妤小姐二十七年都身在甄府大院,父亲和哥哥日日夜夜寻欢作乐,自己却不得不遵循豪门“闺训”,在小妾们的淫声浪语中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父亲去世后,妤小姐开始报复男权,将院里的女人全部换成男人,任意驱使和践踏他们的尊严。身心的极大自由使长期被压抑的性欲突然爆发,与暗恋自己的堂兄怀甫一拍即合,迷失在不为人知的乱伦之中。在《苏珊的微笑中》,蘇珊在换工作时如鱼得水,因为她是省长洪叔叔的地下情人。洪叔叔本是母亲的同学,年轻时候觊觎母亲。苏珊长大之后,洪叔叔开始盯住苏珊。位高权重的他以帮助她苏珊为由,占有了她,成为苏珊的靠山。
“欲望是人人都有的,也是构成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欲望不被控制就会产生破坏的力量。原罪始于欲望,欲望诱发原罪。”[18]妤小姐在父亲的禁令下,无从接触其他男人,只能将自己的欲望一点点压制下去,她是情感压抑者。而父亲的去世激活了她的性欲,她通过堂弟怀甫的乱伦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在征服男人的快感中弥补逝去的青春。而马文就是主体发起者,他是欲望的化身,在情欲的驱使下极端追求欲望的发泄,企图染指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满足病态心理。他通过乱伦毁了女儿的童年、婚姻和未来,简直就是家人口中的“禽兽”。不管是侵犯女儿的马文,还是与堂哥苟合的妤小姐,都任由泛滥的情欲冲破理性的阀门,超出道德的底线,将自己沉醉在欲望的大潮中,将传统的人伦亲情践踏在脚下。叶兆言通过乱伦传达出现代人的人性存在和生命方式,管窥出了人性被情欲所主宰后的悲哀和对生命的质疑,以毫无节制的性欲望和超出道德的不伦之恋向亲情社会的常规性和有序性发起了进攻,再现了欲望放纵的生命悲歌。
五.结语
与叶兆言同时期的作家苏童、余华等人都写过亲情中的暴力或温存,但是叶兆言既不书写极端的暴力和死亡,也不过度渲染亲情的温暖,而是在客观的叙述中,在平静的铺陈中,缓缓道出亲情本身的缺陷和生命的不完美。叶兆言敢于面对人的日常情感,敢于正视平庸之恶,在细缝处发现人的脆弱与情感的异变。“文学不是大道理,文学有时候就是非常细腻的内心力量,这种东西很善良很美 ,但是你发现文学往往就是从这些小的地方组成。”[19]叶兆言善于以小见大,由浅及深,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人的生存本质。他透过亲情这个隙缝察觉出蛰伏在历史真实背后的市民阶层的另一种真实生活,伦理秩序的颤动,人性欲望的膨胀,不可言说的压抑,都通过亲情这个不易察觉的视角暴露出来。叙事者以旁观者的角度窥探着亲情社会的命运,刻骨铭心的爱与不可遏制的激情都急于冲出理性的大门,奔涌而去。亲情呈现的其乐融融、和和睦睦,而是施虐与被虐、桎梏与逃离的病态,叶兆言将长期遮蔽人类双眼的面纱撕裂,将亲情的缺陷通通暴露出来。在缓缓的叙说中解构着传统的亲情观,凸显现代人的人性裂变与情感脆弱。
注 释
[1]方华蓉.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恩仇悖离主题[J].小说评论,2012(04)
[2]阎浩岗.鲁迅的亲情观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
[3]徐兆淮,丁帆.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寻觅自我——叶兆言和他的新写实小说探微[J].小说评论,1990(06)
[4]王德威.艳歌行——小说“小说”[J].读书,1998(01)
[5]王富仁.母爱·父爱·友爱──中国现代文学三母题谈[J].云梦学刊,1995(02)
[6]杨经建.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J].文艺评论,2005(05)
[7]王德威.艳歌行——小说“小说”[J].读书,1998(01)
[8]王富仁.母爱·父愛·友爱──中国现代文学三母题谈[J].云梦学刊,1995(02)
[9]周新民.叶兆言.写作,就是反模仿——叶兆言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03)
[10]张玲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情结[J].文史哲,1999(06)
[11]孟繁兵.血缘亲情关系的扭曲和异化——文革小说中的血缘亲情解析[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12]李万武.“江心无岛”:亲情寓言──评孙春平长篇小说《江心无岛》[J].小说评论,2001(03)
[13]马丽蓉.孤行者的“寻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
[14]杨经建.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J].文艺评论,2005(05)
[15]李莎.寻父·审父·弑父——论苏童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J].当代文坛,2014(03)
[16]张艳玲.新时期小说的“寻父”主题[D].陕西师范大学,2007
[17]杨经建.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乱伦”叙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06)
[18]宫立江.人类意识之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7
[19]刘莉娜.叶兆言:作家,以及写作之家[J].上海采风,2011,(7)
(作者介绍:黄菊,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