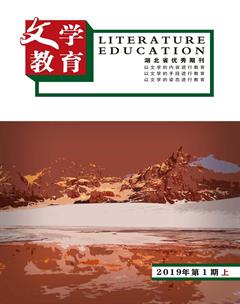宝贝儿,带我飞
孙睿
一
米乐把油画颜料甩到他老婆脸上后,他老婆也甩了脸子,不到十分钟便拉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留下米乐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这十分钟里,他老婆所做的事儿不是告诉米乐冲牛奶水温多少、晚上用哪种纸尿裤,她只管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完全不顾米乐在照顾孩子上毫无经验,还重重地把门撞上。
好在孩子没受影响,不为关门声所动,憨憨地睡着,浑然不知自己的父母刚刚为了她都动手了。米乐作为湖南人的女婿,终于体会到湘南女人的麻辣爽利,对那首叫《辣妹子》的歌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
米乐并没觉得当妈的突然离家是多大个事儿,他从容地坐在画布前,拿起笔,发现调色盘里的颜料少了,想起来刚才有一部分用在离家那位女性的脸上了,于是又往盘里挤了点儿,准备工作。
米乐的职业是画家,一个职业画家。但是他现在准备画幅商品画,已经两年多没卖出一幅作品了,他得生活。
画到一半,孩子突然醒了,哭。米乐放下笔,跑到孩子那屋,拍她。
“又做梦了,没事儿,爸爸在。”以前孩子妈就这么应对。
“妈妈呢?”孩子回到现实,大哭变抽泣。往常这种时刻都是妈妈在。
“不知道,睡觉。”米乐拍着孩子。
“妈妈拍。”孩子不习惯米乐。
“没妈妈,就有爸爸,闭眼。”米乐给孩子的上下眼皮捏在一起。
“拍这儿。”孩子指了指屁股的位置。
米乐照着这个部位轻轻拍着,一会儿,孩子睡着了。
米乐离开床边,画了半宿,然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睡在画布旁边的那张简易床上,而是蹑手蹑脚躺在孩子旁边。这是有了孩子后,他第一次睡这屋。米乐家是一居室,客厅就是米乐的工作室,摆满了画画的东西,没有沙发和电视。唯一的一间卧室在有孩子以前,是米乐和孩子他妈睡,有了孩子,就成了孩子和孩子妈的,米乐很少再进去。
此时,米乐躺在这张可以称之为床的床上,躺在孩子身边,觉得那个女人走了,自己有了睡这儿的机会,真挺舒服的。
二
米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的,眼睛突然就睁开,看见一张宛如朝阳的脸----孩子正笑呵呵地看着他,俯着身,双手扒开米乐的眼睛。
“爸爸起床!”
孩子刚会说话,声音奶奶的,发音并不标准。即便被抠醒,米乐也不忍发作,只睡了三个小时,他还是起来了。
“妈妈呢?”孩子对家庭人口突然少了三分之一很在意。
米乐也往客厅看,看孩子妈是否冷静了一宿后回来了。客厅确实和米乐临睡的时候不一样了,遍地孩子的玩具。
“妈妈去哪儿了?”孩子光着脚,脚底板一层黑土,显然米乐睡觉的时候,她自己已经在地上跑来跑去玩半天了。
“上班去了。”
“去哪儿上班?什么时候回来?”作为一个父母都不上班的两岁孩子,对上班这事有点理解不了。
“下班就回来了。”米乐随便给孩子打开一个电动玩具,“你先自己玩会儿,爸爸去上厕所。”
有了孩子,米乐对自己的称谓已经从“我”水到渠成地按人物关系转变为“爸爸”。
米乐像每个早晨一样,褪掉裤子,毫无顾忌地坐在马桶上,随之而来的是不同于以往的一阵局部剧痛。
“我去!”米乐起身回头一看,马桶里插着一把刷子,刷子把儿正顽皮地向上挺立着,刚刚米乐一屁股坐在这上面,肛部火辣辣的痛感遍及全身。
除了孩子,不会是别人干的。
孩子妈每天早上都要刷一下马桶。小时候在水边长大,每天都看大人在河边刷马桶,觉得好玩,也帮大人刷,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关于刷马桶这事儿,米乐和孩子他妈还有过讨论。米乐说你们刷马桶洗衣服洗菜都在那条河里,可苦了那条河了。孩子妈说,那我看你在我家也没少吃没少拉呀。
孩子每天看她妈拿着刷子和马桶互動,像她妈小时候迅速捕捉到这一生活细节一样,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岁便拿起刷子,准确地放进马桶里,造成米乐屎意全无,周身爽辣。
孩子笑着跑掉,有种新学的本领得到赞赏的满足。米乐追出去,故意追不上,孩子绕着客厅,蹒跚地跑着,成了做游戏。
跑着跑着,米乐觉得不对劲,顺着余光往昨晚的那张画看去,它立在地上,靠着墙,已经不是他睡觉前的那样了,上面被涂得乱七八糟,仿佛北京的地铁线路图。孩子在一旁得意地看着米乐,传递着“油漆未干”的信息,同时也在等待米乐对她改造过的这幅“杰作”予以褒奖。
半年前米乐特意找来纸笔,鼓励孩子在上面涂抹,但是孩子尚未具备此能力。米乐这半年多没画过一幅画,孩子这半年里学会了走和跑,随时可以来到米乐的画前,拿起笔……是米乐自己没把画放好,哪怕是放在架子上,没戳在地上,孩子也不会够到,加上孩子妈平日二十四小时看护着,孩子但凡有摘破坏的苗头,就被拦住,现在孩子没人管,能可劲儿造了。
米乐体会到了孩子妈的重要性。她已经离家十个小时了,没有任何信儿。米乐发过去微信视频邀请,想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顺便看看脸上的油料还在不在,但视频被拒绝。米乐又打过去电话,被挂断。
什么意思?米乐发过去文字信息。
半天没回信。这就代表着可能什么意思都有。
米乐最不愿意猜女人的心思,迄今为止,他生活里的最大心思都在画画上,尽管半年多没画一幅,那是他太走心了,不愿意随便画画。
看着那幅被二度创作的画,除了重画,别无选择。孩子却没事儿人似的,说她饿了。
米乐回忆着孩子妈的流程,从桌上的铁桶里出几勺米粉,装在已经倒了热水的塑料碗里,搅拌。均匀后,米乐尝了尝,不烫,还挺甜,怪不得小孩爱吃。米乐把孩子抱进儿童餐椅里,用小桌板卡住她,摆上那碗米粉,忙乱的早上终于得以安宁。
安宁仅局限于孩子吃饭时嘴被占着提不出别的要求这会儿工夫。吃完之后,米乐的时间就不再是自己的,完全被孩子所控。先陪着过了会儿家家,又被要求放儿歌,手机上网搜了几段,放的同时还被拉着一起跳舞,冒充各种动植物,一直玩到手机没电。孩子又说,该去滑滑梯了。
米乐被孩子领着,到了小区里的儿童乐园。孩子轻车熟路爬上梯子,依次从每个能滑下来的地方滑下。立春刚过,天气干燥,孩子的头发因滑梯摩擦的静电一根根支棱起来,小小的身躯,像顶着一脑袋挂面,乐此不疲地爬上滑下。
米乐就呆呆地在一旁看着。
眼前孩子在玩滑梯,不远处是他位于一楼的家,更是画室,被改造过的全玻璃外墙正扎眼儿地从楼体伸出来。发誓不画商业画的他,昨晚刚刚在玻璃房里完成了一幅香道会所订制的画,此时付钱的人正在来这的路上。但是今天他并不能让对方心满意足地拿走这张画,因为在滑梯上玩的那家伙,早上改变了这张画的样子。拿不走这张画,付钱的人就不会付钱,又到月初了,画室的房贷还没着落。
生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刻呢?
三
米乐今年三十一,来北京十七年了。二00一年到北京上美院附中,二00四年考上中央美院,毕业后就成了北漂。漂着漂着,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跟北京有了瓜葛。
二00八年美院毕业那年,米乐去潘家园买画具,当时那里已经不仅仅是古玩市场,更是美术用品和工艺品市场,价格低廉,尤其适合穷学生和穷老外。
米乐的老家是西安的,他在地摊儿上看到一幅老照片,黑白的影像上,是一对夫妻在西安古城楼门前的合影。那对夫妻米乐并不认识,但是他俩在城墙前的样貌,瞬间激发了米乐的创作灵感。他买下这张照片,回学校开始创作自己的毕业作品。
照片是“过去”拍的,黑白影调,梅花边儿的相纸,城墙底下的冰棍摊儿以及无意路过入画的大二八自行车,四寸的面积里无不显示着“过去”的气息。尤其是那对夫妻脸上的笑容,那是“过去”才能看到的笑容,阳光里也弥漫着一股“过去”的味道。然而这种“过去”,在米乐看来,具有一种无限可能的未来感,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那两个人虽然一本正经地站在城楼前,却俨然是在城楼前飞。
米乐为这幅毕业作品取名《笑脸》。
四寸的照片被米乐画成了一百四十寸的油画,摆在学校二00八届毕业生作品展里。适逢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北京各画廊为了迎合即将拥入北京的大量热爱艺术的老外,提前备货,去各美术院校选购。于是米乐的这张《笑脸》从毕业展上撤下来后,直接搬进798的一家画廊。画廊开出条件,每月给米乐一笔生活费,米乐需保证十年内每年独家供给画廊五幅以上以“笑脸”为题的画作。老板觉得“笑脸”可以作为一个长久命题,一直画下去,他负责包装“笑脸”,让笑脸不仅绽放在北京的美术界,也绽放在全世界。
米乐不想离开宿舍后去住地下室,他需要一个阳光充足的空间来画画,加上每月的生活费,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不愿意再向西安的父母伸手了。况且米乐恋爱了,在即将走出校园的时候,有了女朋友,两人也需要独立空间。这些都成了米乐和画廊签不签的考虑因素。
最终,当然是签了。有了生活保障,在宋庄租了平房。米乐学的是油画,签画廊或许是最对得起这个专业的出路,其他同学早就转行去设计公司上班或者去美术考前辅导班当老师去了。
邹市明为中国队夺得第五十枚金牌那天,米乐的第一幅“笑脸”被法国人买走。法国人喜欢这幅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很美好”。
老板让米乐照这路子画下去,把笑脸背后的场景换成中国其他名胜古迹,让中国人的笑脸出现在大江南北。米乐尝试了,但是背景前的笑脸,却总“不够美好”。那种美好是真实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没有了人物基础,米乐画出来不像,放大到一百寸以上的画布上,尤为突出。
米乐需要不同的笑脸,不同背后又要有相同之处,那是一种混杂着腼腆、羞涩和希望的笑。这种笑用文字好描述,但出现在脸上, 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脸为基础。人长什么样不是想出来的,是这个人就该长这样,每一道皱纹、每一颗牙齿、每一寸头发出现在那里都是有道理的,或者说,真的脸在真的笑,才有这效果。
于是米乐去各种旧货市场淘老照片,前后统共淘了一鞋盒。给鞋盒里的笑脸充当背景的是黄山、张家界、北戴河、黄鹤楼甚至个人家新买的冰箱电视机摩托车。在宋庄的房子里,米乐反复研究这些照片。似乎那个年代的人拍照时都这样笑。这是一种被镜头关注的惊慌吗,怕泄露内心的秘密?这秘密是幸福吗,毕竟这种笑看上去如此美好。人类是一种多么可爱的生物,表现幸福时都这么羞涩。米乐意识到,这就是《笑脸》这个命题的意义---含糊不清的美好。
米乐照着这个感觉画下去。第二幅画完,画廊老板拍了照片发给第一个购买的法国人,法国人立即打来订金,并让米乐接着画第三幅。
这时米乐清晰地觉察到,自己画出来的虽是笑脸,本质上却是在画飞翔。在那种笑脸里,人是飞起来的。这个题材正好满足米乐这时期的内心,此刻的他渴望飞翔,画出来得心应手。人类也需要飞翔,所以画被顺利买走。
一飞就是三年,直到女朋友大学毕业。女朋友是三年前米乐在毕业作品展时认识的,当时米乐需要把《笑脸》拍下来留作资料,就去摄影系找人,同届的摄影系同学没时间,早都出去接活了,连大二的都出去干兼职了,只有大一的在学校准备期末考试,反正拍清楚了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米乐就找了大一的学生。是个女生,帮师兄干活儿是校内传统,义不容辞。
女生也喜欢这张《笑脸》,跟米乐聊起创作动机,从天亮聊到天黑。热爱艺术的青年男女,一旦谈起恋爱,也有火一样的热情。那几天,他们从高更聊到布列松,从齐白石聊到杜可风,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聊到杜斯图里卡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望京的中央美院的女生宿舍聊到米乐在宋庄的画室,两人一起飞。一个陕西人,一个湖南人,聊到一起的同时也吃到了一起,都爱吃辣的。这位女生,就是后来被米乐甩了一臉颜料,离家出走的孩子她妈。
女生毕业后,去了广告公司。和米乐住宋庄上下班太远,决定在公司附近找房子。米乐也不太喜欢宋庄那个环境了,总有人打着艺术的名义来找他喝酒,因为他们知道米乐又卖画了。不是米乐不愿意请他们吃饭,是他们只会吃饭,米乐没见过他们画出一幅像点儿样的东西,只是以画家的名义安心地浪费着时光。这三年里,米乐把鞋盒里的二十张笑脸变成了二十幅画,为自己继续留在北京打下坚实基础。
米乐和女生看了四环边上的一处房子,一楼的一居室,只有六十平方米,看上去有一百平方米,客厅的落地窗外被业主加盖了个阳光房,和客厅打通,面积充裕,光线充足,太适合画画了。
中介说房东出国了,房子交给他们代理,又租又卖,建议米乐买下来,租金和贷款月供差不多,北京的房价已是开弓之箭不会回头,早买一天早赚一天。米乐一眼就看上这房子,他对北京房价没有判断,只是喜欢这个铺满阳光的客厅,看着就想架起画板,抡开膀子画点什么。
中介算了首付和月供,照这三年的卖画情况看,米乐刚好能承受。他的画慢慢还会涨价,后面的日子应该会更好过。米乐唯一担心的是那个阳光房,不在房本面积里,属临时建筑,如果日后拆了,这房子将对米乐毫无意义,他看中的恰恰就是这块面积。中介说这个阳光房已经盖了三年,至今物业还让它存在着,说明就是合法的。当初整个小区只剩这套房没卖出去,因为太靠小区边缘,离围墙也近,又是一楼,看着就不安全。为了清仓,开发商和物业承诺日后可以在窗外加盖一个阳光房,这才卖掉。现在出售的不仅有房本上的面积和阳光房,还有物业对阳光房终身合法的承诺。米乐特意去物业求证,属实,便买下。
女朋友每天从这里起床,走着去公司上班,只需十五分钟。米乐每天从这里起床,喝咖啡,晒太阳,构思下一幅画。
不知不觉又过了三年。三年很快,无非就是米乐又画了十几张画,女朋友工作转正,拿了三年年终奖换了一个更好的相机而已,比学校里的那三年还快。要不是女生突然发现自己怀孕,在给肚子里的孩子做打算时,都没意识到已经毕业三年了。
怎么办?米乐放下画笔,坐在玻璃房里思考着。
要不结婚吧?两人一拍即合。一个陕西人和一个湖南人,组成了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家庭。也没办婚礼,艺术青年觉得这事儿忒傻,双方家长都来了北京,操着各自的地方普通话,边唠家常边吃了顿饭。新婚夫妇觉得家长们的口味和口音都很难凑到一起,及时结束了家庭宴会。来不及改口,双方家长已经踏上归途。年轻的艺术家夫妇,办事就是这么麻利,坚决不与人间俗事过多纠缠。
十个月后,孩子出生,女孩。孩子妈全职在家,孩子爸画画养家。孩子妈倒还好,喂奶、换尿布都是人生第一次,干得有声有色。孩子爸不是第一次画画,却画不出来了,觉得家里乱,灵感全无。这也是他们没让父母过来帮着带孩子和请阿姨的原因,地方儿有限,多一个人眼前晃,米乐就觉得晕。
晕是表面现象,内里是孩子的突然出生给了米乐一个措手不及。他感觉自己不是之前那个人了。虽然孩子不怎么用他管,他也确实没插手,但心里无法对这个孩子视而不见。以前他敢幻想,自由,夜里喝点儿酒,想想明天要画的东西,感觉自己在飞翔。现在喝完酒,刚想起飞,总有一个孩子像秤砣一样在后面拽着他。孩子带来的麻烦、琐碎,不是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
为了甩开秤砣,他就多喝点儿,喝到天亮,看着窗外的雾霾,盘算的却是该给孩子那屋配个空气净化器了。米乐学会怕了,那种勇往直前的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飞不起来了。
米乐画了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张画,遭到退画。画商说,你画的笑脸,怎么像在哭?不光画商这样说,以前买画的那个法国人看完也是这种评价,觉得画上的人,笑得很苦涩。米乐又画了一幅,得到的意见是:这张更苦。
米乐打印出一张以前的画,和新画的两幅摆在一起,细细端详,确实不一样了。以前画的那种笑,是人物原型在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里,经作者之手,笑成了那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是米乐主观加工后的浪漫产物。现在米乐人生中那种含糊不清的美好不见了,失去了浪漫的能力,生活因孩子的出现而写实,天时地利人和都缺。他没有再询问曾经的艺术伙伴对此事的态度,她正忙着给孩子收拾刚刚拉在床上的屎。
米乐觉得自己需要调整,决定出去上班,换个环境,找回原来的心境。和画廊的十年合同还没结束,老板也知道米乐的问题所在,同意米乐缓两年。
米乐去了一家动画公司当视觉总监。上了半年班,发现自己是创作型的,无法服务于人,艺术上的妥协让自己难过。于是辞职,闲在家里,既然《笑脸》系列画不成,就构思新作。
首先萌生出的想法是《苦脸》,符合心境,能画出神韵。米乐试着画了一张,把人物的脸画得微微起泡,像苦瓜的皮,强颜欢笑着,苦中作乐,他觉得这更是多数人的表情。
画商看完很不满意,说艺术作品甭管是荒诞的还是浪漫的,得给人力量,不能太苦,这么大一幅挂墙上,要么像太阳一样发光,要么像月亮一样宁静,不能像朵乌云,让人压抑。这些虚的先放一边儿不管,首先一眼看过去,脸上都是疙瘩,不美。
是不美。但现阶段米乐就喜欢批判现实主义。人生本来就没那么美。
米乐不听劝,又画了第二幅。两幅挂一起,更压抑了。画商都不愿意进屋了。
米乐就这么渗着,思考着到底该画什么,一年又过去了。以前的积蓄都还了房贷,接下来的月供没着落,米乐不得已,接了给会所画装饰画的活儿。
承包人是米乐的大学同学,头脑清晰,知道自己不是画画的料,大三就去装饰公司上班,外号钱串子。当年大家都觉得钱串子丢了油画系的脸,即便向金钱投降,也应该等毕业后再说。米乐刚毕业就被画廊签,在同学看来,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九年后钱串子成了装修公司老板,佼佼者开始给钱串子打工,这个故事太不励志了,考美院的时候没人会这么想,从美院毕业,人过三十,每个人都觉得这很正常。
前后的落差,加上近两年在作品上的郁郁不得志,米乐脾气见长。他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画画以外,昨天就是他刚拿起画笔,老婆便冲他抱怨,他只是想阻止老婆再说下去,却变成甩了她一脸。
老婆的抱怨也忍了很久,米乐父母刚刚和他们在北京过了春节,其间发生一些儿媳妇看不惯的事情。憋到元宵节,公公婆婆终于走了,儿媳妇不吐不快,首先指出的就是米乐他爸居然让孩子坐床上拉屎—一当然是把幼儿马桶放在床上,让孩子拉在马桶里。但是明明可以放在地上,拉屎都上床,以后还不无法无天,这就是隔代家长愚昧無知只会溺爱的教育方式。经过这两年的磨炼,米乐老婆已经从一名懂摄影的文艺少女,变成深谙现代教育理念名副其实的孩子妈。
米乐也觉得孩子爷爷做得不对,下回不这样就完了,没必要展开论述。陕西的辣和湖南的辣终归不是一种辣。孩子妈生完孩子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拼命通过说话来弥补自已失去的。有时候看着这张喋喋不休的脸,米乐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小心点儿,非要让对面这位女性怀孕,生下孩子呢。而且孩子生下来后,被她妈一口一个“宝贝儿”地叫着,可这“宝贝儿”没一点儿宝贝的意思,都是麻烦。
昨晚在“宝贝儿”睡后,这张脸上的嘴又像永动机一样开始工作,米乐一挥手,示意别说了,结果甩到脸上。永动机停了,留给米乐一个后脑勺,走掉。
现在和“宝贝儿”才相处一个早上,米乐有点理解“永动机”了。他抬眼望去,钱串子韩总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正向他这边走来。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季,米乐来到北京,考美院附中,从此就留在了北京,是为了现在这刻吗?
如果不是,下一刻怎么改变?
但显然这种想法是奢侈的,现在米乐更应该想的是如何不让孩子哭。不远处,他的“宝贝儿”和别人的“宝贝儿”正因为玩滑梯排没排队打起来了。
四
“没事儿,你要是有俩孩子,这种事儿更会习惯。”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韩总看着被毁的那张画,只是笑笑。
“我再给你画一张。”米乐看着一旁没事儿人似的孩子。
韩总说不用了,客户对之前的那套设计不满意,全部推翻重来,但钱照付。画用不到了,韩总更不需要把实情告诉米乐了,原本这幅画是打算挂在香馆卫生间的。现在客户觉得无论是闻香室,还是拉屎撒尿室,都应该低调内敛,想走日本茶道路线,冲着“和敬清寂”去。韩总要去日本考察,叫米乐这个高才生起去,帮他参谋参谋。
“孩子怎么办?”这成了米乐现阶段干什么都要先考虑的事儿。
“带着。”
米乐觉得现在让他带孩子出国,不太现实。韩总说一看米乐平时就不管孩子,怯场,也无知,带孩子出去玩,是最省事的方式,外面那么多好玩的,孩子不会缠着你,等于找了保姆。
米乐抱着试试看散散心的态度答应了。先给孩子妈发了信息,说他要带孩子去趟日本,问孩子妈去不去,并不是为了让她接管孩子,这两年她看孩子辛苦,想带她出去玩一圈,她以前说过去京都的打算。
米乐给孩子妈在手机里存的名字叫“一辈子”,可是“一辈子”依然不回信,打过去电话还是被挂。米乐心中自嘲,要不要改名“半途而废”。他准备了父女二人出行的东西,奶瓶、纸尿裤、儿童餐具、小饼干、腰凳、折叠婴儿伞车、能随身携带的玩具等。还对孩子和自已进行了培訓,对自己的培训是熟悉孩子的脾气秉性和生理规律,对孩子的培训是树立爸爸的威严感,让孩子知道了有一种惩罚方式叫“打屁股”,会很疼,如果不听话,就得被打屁股,并编了一段顺口溜哄孩子睡觉:爸爸揍我是为我好,我挨揍,能进步,三天不揍就难受。
一切就绪,父女二人拉着手,走出家门。
飞机起飞前,一切都好。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越来越快,呼啸着将窗外的景象甩在身后时,孩子被吓哭了。从未经历过这么快的速度,安全感全无。哭声盖过了发动机和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空姐走来,问是否需要帮忙。这时飞机忽悠一下,轻盈地拔离地面,孩子突然不哭了,一双黑黑的眼球呆呆地看着窗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看,飞起来了,有翅膀就能飞。米乐指着窗外从机身一侧伸出的机翼说。
孩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像第一次认识这个世界。
五
孩子嘴壮,不挑食,吃完拉面还能喝半碗面汤。米乐每天出门前给包里装满吃的,就能让孩子度过愉快的一天。有奶便是娘这话没错,孩子在日本这么多天,都没问妈妈怎么没来。
推着孩子,米乐和韩同学走访了京都多处香艺和茶道馆,还去了金阁寺清水寺等历史古迹和京都国立博物馆,充分领略日范儿美学和美食。韩同学说,日后那家香馆无论是想改成饭馆还是酒馆,此趟京都之行,让他都有办法应对。
临回国的前一天,赶上京都每月一次的二手货集市,韩同学拉着米乐去淘宝。集市在东寺,离住地不远,去的路上有很多杂货小店铺,其中一家门口挂着一对羽毛翅膀,孩子看到,指着翅膀:飞,飞,飞!
对,翅膀,和飞机的一样。
爸爸,我有翅膀吗?
咱们是人,人都没有翅膀。米乐推着孩子走过了那家店铺。
集市挺热闹,人多,东西也多。韩同学淘了一大堆旧货,有老的,也有半新不老的,准备带回去自己别墅装修的时候用。日本之行收获颇丰,韩同学说吃顿饭庆祝一下,想吃饺子,找了半天没找到能吃饺子的地方,最后进了一家鳗鱼料理馆子。但是孩子之前听说吃饺子,就做好了吃饺子的准备,当端上来的是黑乎乎的鳗鱼段而不是白花花的饺子的时候,不干了,又哭又闹。
这是妈妈离开后孩子第一次耍性子,因为吃。好在鳗鱼汁泡饭的味道还算鲜美,米乐强硬地盛了一勺塞进孩子嘴里,她不哭了。眼前的滋味虽然和饺子不一样,也不失为美味,一勺接一勺吃了下去。可出了餐馆时,还不忘:“那晚上再吃饺子吧!”
这次出门住的是日式家庭旅馆,韩同学为了方便米乐带孩子,生活不局促。房间里有电磁炉,能自己烧水煮面,韩同学热心,买回来速冻饺子,说日本的最后一个晚上,不能让孩子失望。
饺子熟了,给孩子的盛进小碗里,仨人坐在榻榻米上吃起来。韩同学还买来拌海藻芥末章鱼,开了一瓶山崎威士忌,两个大人喝了起来。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米乐喝美了自然会聊他的艺术抱负,韩同学喝美了自然会聊他的商业抱负。韩同学总想纠正米乐自上学以来的错误概念,没有所谓的纯艺术,一切艺术最终都会和资本搅和在一起,若没有商业买卖,艺术根本开展不下去。米乐说资本家那边怎么想的他不知道,但是他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是有纯艺术这么一回事儿的,虽然画被资本们买了又卖,但是在每幅画抬出画室前,它对于米乐的意义,是钱所带不来的。韩同学已微醺,气势上要压米乐一头,说米乐幼稚,一口一个艺术,画最终被挂在咖啡馆还是洗脚房,是买单的人说了算,并告诉米乐,他的那幅画险些就被挂进卫生间。
米乐不说话了,之前意气风发的表情和挥斥方遒的气势没了。喝了一口酒,一扭头,看见孩子正抠开饺子皮,光吃馅儿,旁边已经一片饺子皮儿。
皮儿也吃了。米乐说。
你就让她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吧,皮儿怪硬的。韩同学护着孩子。
把皮儿也吃了。米乐又说了一遍。
才两岁,别管她。韩同学端起酒杯。
孩子因为有人撑腰,把掏出来的馅儿放进嘴里,熟练地把皮儿扔到旁边那堆皮儿里,然后准备拿下一个饺子。
不吃皮儿,馅儿也别吃。米乐拦住孩子伸向饺子的手。
小孩都这样……
都这样不行!米乐这才转头,冲向韩同学。
韩同学的话被米乐突然打断,似乎明白了什么,放下酒杯,识趣地起身,叮嘱孩子:听你爸话。同时开导米乐:一个孩子,不至于,快乐教育。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
屋里三人变成两人。孩子觉察到气氛有变,不再嬉皮笑脸,紧张地看着米乐。米乐也看着她,不说话。空气凝固。
孩子试探着向饺子伸出手。
连皮儿一起吃。米乐允许孩子又拿走一个饺子。
孩子直直地看着米乐,却仍然抠开皮儿,取出馅儿放进嘴里。
米乐指了指皮儿。
孩子含着馅儿,不敢嚼。两人对视着。
又是孩子绷不住了,突然笑了。好像在说:爸爸你别闹了,让我踏实吃完。
米乐一点不迎合,更严肃了,传递出:不把皮儿吃了,这事儿没完。
孩子看着米乐板着的面孔,突然害怕了。
米乐不需要孩子怕他,他需要孩子懂事儿懂规矩,比如画不能挂在卫生间。米乐拿起刚刚那个饺子皮儿,递到孩子嘴边:吃了。
孩子紧紧闭着嘴,似乎不吃皮儿是一种真理,需要坚持。
米乐只好把皮儿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双手挡住嘴,就是不吃,冷冷地看着米乐。
米乐的手垂在孩子面前,捏着饺子皮儿,等孩子自己收场。
两人僵持着。
片刻,孩子手从嘴边挪开,拿过米乐手里的饺子皮儿,放在被扔掉的那一堆饺子皮儿里。似乎想以这样一种方式将此事告一段落。
米乐照着孩子的屁股就拍了一下。
孩子没有意识到这是米乐在打她,并没有哭。米乐也觉得这巴掌隔着裤子打上去不足以对孩子产生威慑效果,紧接着扒掉孩子裤子,露出两嘟屁股肉,打了上去。
这回手和屁股有了接触,摩擦感传来,算是实实在在地“打着了”。
孩子先是一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脸憋得通红,因为疼,哇的一声,哭了。
米乐没有打第二下,也没有安抚孩子,只是给她提上裤子,任她继续哭。
米乐转身,收拾刚才的一堆饺子皮儿。
现在你想吃也晚了,没有改正机会了。米乐说完把饺子皮儿统统扔进垃圾桶,透出无限失望。
哇!孩子哭得更凶。跑过来,抱住米乐的腿:爸爸别扔,我吃!
说着,孩子捡起一个掉在地上的皮儿,放进嘴里,一边嚼一边说:爸爸揍我是为我好,我挨揍,能进步……米乐听不下去了,说可以不吃了,吐出来,但是孩子把手里剩下的都塞进嘴里,流着眼泪说:坏爸爸,我不扔,我吃!
又是一声---哇!这回声源来自喉咙以下。哭得太凶,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连同之前的馅儿。黏稠的一团。
小手伸向呕吐物,还要捡起来:我吃,我都吃了……
米乐眼圈红了,抱起孩子,紧紧搂着。
孩子抽噎不停,米乐后悔不迭:以后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孩子喃喃着:我不对,我挨揍,能进步……
米乐把脸紧紧贴在孩子的脸上,她的脸像发了烧,滚烫。
米乐倾尽全身力量抱着孩子,孩子并不重,米乐有股劲儿使不出来。就抱着孩子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高高举起,连说带逗,哄孩子开心。这样玩了半天,当又一次把孩子举过头顶的时候,米乐说了一句:飞,你也能飞。
孩子就本能地伸出双手,上下挥动,真的像翅膀一样。瞬间,脸上有了笑容,像一朵盛开的无畏风雨的花。
米乐就一直举着孩子,让她在自己的头顶上飞,肆意绽放。飞翔的时候,就忘了皮儿和馅儿,忘了一切。
玩累了,弥补过失,米乐又打开电视,让孩子看了会儿动画片,平时他都禁止孩子看,费眼睛。动画片是日语的,米乐看不懂,但孩子懂,安静地坐在电视对面,目不转睛,好像之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米乐在一旁欣赏地看着孩子,悄悄退到门外,以最快的速度跑出旅店,他还记得白天的那对翅膀在哪家店里。
六
回国的路上,孩子一直背着翅膀。多数时间米乐跟在后面,保护着翅膀。
到了家,孩子妈还是没回来。坚定了米乐自己带好孩子的决心。
米乐像欠了孩子什么似的,尽一切可能,让孩子高兴。他愿意看到孩子的笑。
孩子也特愿意配合,米乐安排的所有“活动”,孩子都积极参加,比如烫脚。暖气停了,天儿还冷,孩子脚总是凉的,米乐觉得让孩子小脚热乎着入睡是一个父亲负不负责任的体现,脚暖和着睡觉关乎幸福指数。他自己有燙脚的习惯,十几年前住平房考美院附中以及大学毕业在宋庄的那段时间,晚上冷得睡不着,就烧一盆热水,把脚往里一放,别提多舒服了。
孩子被米乐带动两次后,迅速染上这一癖好。每当夜幕降临,就自已拎出一大一小两只塑料盆,摆好小板凳:爸爸用大盆儿,我用小盆儿。等待米乐倒入热水,把脚没入水里搅动,玩水。水温降下来后,会像模像样地说出一句:再给我兑点儿热的。
烫完脚,米乐会举着孩子在头顶上飞会儿,将一天的快乐推向高潮,然后讲一段故事,陪孩子入睡。
不再有坐在玻璃房里思考的时间,米乐习惯了每晚睡在孩子身边,但没有忘掉买这套房子的初衷。脚越热,画画的心越不会凉。半夜因为照顾孩子醒来,米乐会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思索自己画画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