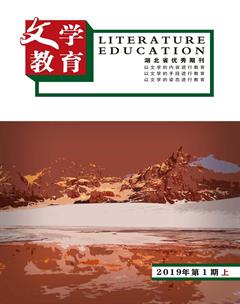重建人和土地关系的叙事
周新民:你只上过中等师范学校,接受的是中等专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的文学教育完全不能和高等学校相提并论,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你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关仁山: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像苏童、余华、迟子建、格非、毕飞宇,他们都是经历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昌黎师范学校上学。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喜欢文学,在阅览室读文学作品。当时学校办了一个校刊叫“碣石文艺”,我就当了学校文学社的社长。就这个时候培养了我的对文学的热爱之情。
中师毕业以后,我就去当老师了,文学离咱们远了。教书以后我还是不甘心,教了半年书,我就写文章,搞文艺创作了。写了一篇散文在县文化馆发表之后,我就跟领导提想到文化馆工作。最初,文化馆不缺人,然后给我放到一个镇的文化站。在文化站就那么干了一年多。我当老师的时候,教美术,还兼管语文。学校比较杂的学校,我管这两科。后来到了文化馆,给我分配的也不是专业创作这块,是跟美术有关系,是美术组的。后来就跟领导提说还是喜欢文学,又一番周折我才进了创作室。我没有经历过中文专业的系统训练,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全凭热情以及对文学的热爱。
周新民:你的“雪莲湾系列”小说就以关注当下社会现实而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九月还乡》《大雪无乡》被看做是“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潮流的经典作品,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
關仁山:关注现实生活,而且还写传统与现实的冲撞、文化的冲撞、人性的冲撞,是我一贯的文学追求。九十年代初期,我在渤海湾渔村体验生活,创作了《苦雪》、《红旱船》、《蓝脉》等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
进入1994年,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和乡镇企业问题非常突出了。我故乡唐山乡镇企业走到一个严峻关口了,必须得股份制改造,我的《大雪无乡》是最早反映股份制改造小说。在这之前,先锋文学探索到了一个阶段,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作家掀起的“新写实”文学已经风靡一时。“新写实”小说虽然把对人的关注引导到人生的本真状态。但是,更广阔层面的人民大众生活,缺乏相应的文学的表达。就在这时被雷达老师命名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应运而生。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我的《大雪无乡》等作品集中发表。这些作品直面中国当下最基层工厂、乡镇,以文学的方式反映中国当时最为广大老百姓关注的、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时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周新民: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文学潮流的评价的确出现了分歧。不过,对于你个人而言,《九月还乡》《大雪无乡》是你文学创作的巨大飞跃。《太极地》《闰年灯》和《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作品,虽然都是关注农村的社会现实。相比较而言,你觉得在叙事手法和所关注的问题上,《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和《太极地》《闰年灯》有何不同?
关仁山:像《九月还乡》、《破产》这一批作品,那一年发表有七八个中篇吧。最响的是《九月还乡》和《大雪无乡》这两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大雪无乡》《九月还乡》更有特色。例如,我在写股份制改革的《大雪无乡》中在塑造了一个文学形象潘老五。潘老五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他一手遮天,驾驭乡土,功过参半。但是,对于潘老五的塑造还有些遗憾,还没有把他做到极致,特别是没有很好挖掘他的灵魂,遗憾地与这个有可能成为“这一个”的典型的人物失之交臂。这个人物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老子打的天下,乡镇企业是我的天下,老子说了算”的观念特别严重,忽视人民的利益。那个是一个疯狂的时代。那时候鼓励胆子大一点,富得快一点。是时代的大环境给了这种人物以平台,同时也展示了其劣根性与人性的龌龊。潘老五已经成为时代前进的阻力。我发现了这个典型人物,遗憾的没能很好挖掘到他的灵魂深处。
《九月还乡》中的九月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农村的姑娘上城卖淫的现象特别严重,但是没有文学作品敢涉及,我是比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九月还乡》当时给了《十月》这个杂志定了头条。然后《小说选刊》转载了,《新华文摘》也转载了。这九月人物耐人寻味,她到城里打工,最后沦为卖淫的妓女,她用卖淫的钱伤痕累累地回到故乡,在家乡美丽的土地上耕种棉花,开垦荒地。九月的形象呢,当时是富有争议的。九月从过去罪恶的泥沼中挣扎出来,故乡温暖的土地抚慰着她受伤的灵魂。有人认为她身上有新农民的元素。她想当了一个农场主,历尽艰辛,被人冷眼想看。这一形象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孩由沦落而升华,从田野的劳动中重新找到了她一度失去的做人的价值。九月的命运也折射出改革催生了人的巨变这一重大命题。
周新民:九月身上是充满挣扎的,包括人性的温暖和现实的无奈,读来让人心酸。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到你的《九月还乡》中的九月,折射了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文学反映城乡关系的巨变。高加林是很纯粹很简单,他一心要脱离土地,要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因此,《人生》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与冲突中展开情节。但是,到了《九月还乡》,就不能以简单的城乡冲突来表达九月们的命运了。你是怎么看待“九月”她们的命运的。
关仁山:《九月还乡》中九月这个人物,带着满身伤痕,带着内心的疼痛回来了。她在棉花田里哭泣,她有自责的东西。她为啥说她回来做手术去骗他这个淳朴的恋人双根呢。做手术,回来跟双根成家,她内心里是向往美好的,但是由于现实的残酷,她要生存,必须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碾碎。她要突破她底线的东西,她要生存。人进行生存的挣扎,要站住脚跟,就要不择手段了。如果说再往前走,高加林就是这么个人物了。但是高加林还不能往前走,当时刚改革开放嘛,他还突破不了时代和文化上的道德的约束。高加林心灵受伤之后还得回到黄土高原,他得回到故乡的热土自己疗伤。
而九月就不同了,她突破底线,她挑战道德。山西的评论家段崇轩写评论时,提到我这个九月的形象,认为是新农民的代表。九月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而且她还有了商业意识、法律意识。她身上开始具有现代文明的商业意识、自醒意识。她开垦荒地,把产品推向城市。她做最糟糕的是罪恶的原始积累,挣更多的钱,为了以后再来买回更多的东西。这让我们心痛,也让我们思考。
周新民:九月这个人物身上实在有太多东西了,她的历史内涵很丰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我们看到所谓的农村转型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也反映了了中国商人的原始积累是“带血的”、突破了道德底线。从美学意义上来讲,九月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多重性。她既不安于现状,要往外走。但是,她又缺乏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各种素质;然而,当她回到农村时,又倍感尴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了。《九月还乡》实际上这里面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该怎么进行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九月还乡》很有前瞻性。到了今天,农村青年他也面临这个问题。当前,二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出现。你怎样看待新农民的命运?
关仁山:现在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原名《归来》)。但是我现在换成什么写法了呢?我写一个农民回了乡村吧,他不能适应乡村,融不进乡村;在城市呢,他融不进城市,成了没有身份的人。在这种双重纠结中,他必须得归来,灵魂得归来,身体得归来。这是一个“双重归来”的主题。
我写了这个农民的老家——大雪灾中的一个绝望群体。这个村里支书、村长都已经进城了,就一个小组长在管着村。村里十几口人全是在外打工致残的,还有些年老的空巢老人和小孩。这些绝望的人在大雪灾里被政府给遗忘了。救灾也没考虑他们,屯里就认为这村没人了。恰恰这个农民惦念在这个村子里的这些亲人,所以他回来了。他本来是照看照看他们,救救灾带点吃的。结果一个人自杀了,临前他开了一个会议必须绝地重生。他必须带村子里的人活下去。我就写这个农民,在城里打拼接近半成功的一个农民又回到了这个家园,他还是被迫拽回来的。
这个绝望的群体经过六年的奋斗,干出了让城里都羡慕的事情。光伏发电,苹果不打农药,还卖成了四十五块钱一个苹果定制给佛堂。他做的是前瞻的,很商业的东西,还包括这个电商销售。他宣传村里的所有产品,废物变宝。如果没有他,这些残疾人他们看到的只能是废物。只有有了见识的人,他才可能有这个意识,变废为宝。而他的妻子呢,在城里办证,想在北京买套房融进城市。但是这个过程艰难。我写了他的妻子不断地要融进城市,又不断被打回来再融进去,打回来再融进去的历程。我感觉在城市是归来,在农村也是归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你都融不进去,但必须得融进去的“归来”。这个过程中它很艰难的。
周新民:你的小说围绕人和土地的关系来展开。人和土地的关系史也是中国农民命运的沉浮史。你的小说从《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到《天壤》、《平原上的舞蹈》,再到《红月亮照常升起》、《农民》,叙写了农民承包土地——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的历史过程。这些小说中你其实在思考一个命题:作为农民,最终还得回到土地上来。
关仁山:无论你多么恨土地,最后你找到自己的价值还得回土地上来。《金谷银山》写了这个恨土地的农民,在城里卖菜闯出半个天地,但是,还是融不进城市。这个在城市中很卑微的人,最后在救灾中照顾家人,帮助绝望中的人们活下来。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他一步一步融进了这乡村,尽管他不习惯这里的生活,甚至连空气都不习惯,但是他依然重新融进乡村自然,并保住了这一片绿水青山。
这个过程很难,他又种药材,又找种子。由于他本身就是个卖菜的,他非常反感转基因食物,反感吃外国粮食的种子。他们这个村子里有一种小麦的品种是老种子,但是这个老种子已经绝迹了。农民当时推广种子,不让吃老种子,也由于产量低,老种子就绝迹了。只有出嫁太行山老姑奶奶,带走了一包种子和一棵树。他老姑奶奶在太行山涉县,然后,他就追得到涉县。老姑奶奶也说老种子绝迹了,但是有一包种子在老姑爷坟里头,老姑爷喜欢把老种子带进坟墓。最后,他们把坟刨出来,做个仪式,拿羊、猪羊“领牲”,然后哭了三天三夜,把种子捧回来。之后,他们把这个村庄变成中国人的种子基地。尽管他跟孟山都的转基因不能抗衡,但是他这个精神的东西在这个小山村里面闪光了。
我是写一批绝望的人如何做出一些富有精神高度的事情来。转基因的种子不能再发芽,产完了以后还要再买,这是孟山都他们美国公司跟中国农业部造成的中国农民的尴尬。这个农民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有为了民族的高度,他认为这种子值錢。恰恰这样,他那条山成了种子基地了。谷子、大豆、小麦,中国的原始种子纯正的种子,从坟里起出来,再把它培育发芽。这里有象征色彩。
周新民:《麦河》是一部反映土地流转的长篇小说。土地流转是中国农村面临的最为主要问题之一,也是中国政府力推的重大政策。反映重大的社会政策问题的作品很容易出现概念化和匠化的不良倾向。我觉得《麦河》最了不起一点就是,能够把对现实社会的反映通过文化的视角增加一种厚度,使艺术形象更有张力,更饱满。你怎样看?
关仁山:我和雷达老师有过交流,后来我的《日头》出版之后,雷达老师说他还是更喜欢《麦河》。这两个作品风格不太一样。《麦河》瞎子弹唱乐亭大鼓,包括这条流淌着麦香的河流,雄鹰叼着一根麦穗飞翔,它有些美的东西,麦浪滚滚,大麦田上的舞蹈。《麦河》关于农民的未来,我们让老鹰虎子做了一些预见。大量农民会一步一步走进城市,乡村也会变好的。现在想来,大工业越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净土。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麦田里,让他们劳动、咏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没有路,也不愿放弃劳动和咏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脚步。我们富足了,都是土地付出的代价,一切物质的狂欢都会过去,我们最终不得不认真、不得不严肃地直面脚下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灵魂。我们说土地不朽,人的精神就会不朽。所以,我们有理由重塑今天的土地崇拜!雷达老师读过小说一语道破天机,他说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是土地,这是一部土地之书。
周新民:我明白你的思考。表面上看,你是在写中国农村土地流传这样一个重大政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但是,你是把土地流转这一社会性话题嫁接在“土地崇拜”这一文化母题之上,使土地流转这一社会性主题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根基。《麦河》之后,你创作了《日头》。《日头》是你的“农民三部曲”的压卷之作。你认为,《日头》和《天高地厚》《麦河》相比较,有哪些超越?《日头》中的两个人物形象金沐灶和权桑麻很有意义和价值,你能详细谈谈这两个人物形象么?
关仁山:“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的大量篇幅,都贯穿了作家关于农村未来发展前景的思考(鲍真、曹双羊等农村新人的实践)、乡村政治多元势力之间的戏剧性冲突(荣汉俊、权桑麻等权力者与新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农村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与实践(金沐灶的形象),这些都是“三部曲”的重头好戏,也是我认为这个艺术画卷中最亮眼的部分。《日头》我感觉文化的氛围更浓了。它塑造了权桑麻和金沐灶这两个典型形象。去年十一月,这个“农村三部曲”在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学术研讨会。陈思和教授就提到,尽管这个权桑麻形象不是独创,在《农民帝国》里也有过,但是在《日头》里面更突出了。
《日头》中权桑麻这个人物更立体了。他是个民间枭雄,很复杂的形象。权桑麻的形象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真实写照。这一人物形象的确立是作者直面农村社会现实中最要害问题的敏锐书写,也是探讨农民问题的作品中最大胆和最直接的“现实主义”。农民的问题决不是单一的问题。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桑麻这种投机钻营且胆量大的“积年老狐狸”反而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权利空间,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掌控者。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仅仅是道路宽敞、拥有钞票、住上高楼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而是应该尊重普通民众对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自由选择,是让农民活得有希望、有尊严、有精神追求的内在信仰的获得。
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是一个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的封闭体系,而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则是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只要这样的人还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果就会变味,老百姓就不会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果实。面对这样的体系与如此强大的利益格局,中国农村现代化若想取得成功,必然要解决制度的、人的以及文化上的种种问题。
金沐灶是与权桑麻相对立而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是民间一个思想文化探索者。金沐灶形象比权桑麻形象要更理想化一些。金沐灶他父亲在文革时期为了护一口大钟,一口血喷在钟上。大钟上有金刚经,他沾着他父亲的血把金刚经拓下来。这件事一下子改变了他人生的所有走向。金沐灶带着悲悯情怀,带着精神探索苦苦追寻给中国农民怎样过上好日子。虽然他是个失败者。但是,他追问和求索极为有价值。金沐灶这一人物形象的新意,更清晰地表现在思想境界的开阔与高远上。最初设计故事时我以为,写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后来发现金沐灶这一人物形象应该是超越复仇的,他应该突破了既定的故事格局,使小说成为一个讲述农村维权者、探索者的奋斗传奇。
周新民:你提到金沐灶这个形象,他是农民的维权者以及农民中的理想主义者,为摆脱农村贫困与苦难不断地寻找出路。你是怎么看待金沐灶这种失败的探索,或者说你是怎么看待探索农村建设这一重大问题的。
关仁山:金沐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探索,他对农民新生活的企盼,对未来的向往,农民生命的意义的思考,都是珍贵的。陈思和老师在那个会上给予高度肯定,他仰望星空的姿态让人感动,但是也有遗憾,他的探索没有结果。我们作家的任务没有完成,必须完成新乡村的一种重建。因为这样,作家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我感到壓力。有专家认为,农村政策调整和改革实践,必然带来极其复杂和惨烈的后果,观念上新与旧冲突,经济上得与失交替,伦理上的颠覆与蜕变,既是发展也是衰退,一切都在进一步退两步或者进两步退一步之间徘徊和挣扎。所以,农民的绝对贫困率的降低与幸福意识的丧失,几乎是同步产生的。这一切,都给以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一个沉重的挑战,来自现实的力量逼着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中国乡村现实是怎么一回事,不会再有传统的理想目标指示作家如何通过艺术形象来引导大家走金光大道,也不会再有梁生宝、萧长春这类理想人物来充当农村改革的当代英雄。这种人物到底还有没有?我在生活中发现这样的理想人物还是存在的。
只要走进农民的生活,就会有新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我现在写的这个新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又延续了这个金沐灶的探索。我找到了范小枪这样的一个新农民原型。《金谷银山》的任务是要重建。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民族文化被城市文化殖民、打得鸡零狗碎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农民英雄。《金谷银山》中的这个农民是在无意识中完成一个新乡村文化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建以及经济重建。这个重建既不是今天的文化的照搬,也不是历史文化的翻版。它是农民自己干起来的一、正在建设的文化。你说我们都在骂这个体制也好,骂农村贫苦也好,但是农村也就这样了,我们再骂也就这样了。我们前几部作品该批判也都批判了,以后需要文化重建。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武汉作协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