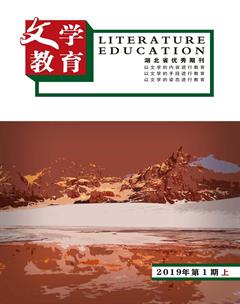风吹稻花十里香
周华诚
1
二禾君,好久不见,近来可好?你来信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也迫不及待地想与你分享。
春节前,村里在张罗一场“村晚”。谁的爹会拉二胡,谁的爷爷能吹个喇叭,还有那一群每天都在村头跳广场舞的大娘大婶,都拉到舞台上摆一摆。
舞台就搭在“稻作文化馆”边上。文化馆是请了中国美院团队设计的,硬件已基本完成。村民看了这个馆,都说建得好、上档次。村里人世世代代种田为生,没想到日常摸惯了的犁呀耙呀,风车呀草鞋呀,还能摆进文化馆。水稻界鼎鼎大名的科学家袁隆平,还给我们题了一块匾——四个大字“耕读传家”,还有一行小字“赠常山县五联村”。哎呀,这可是镇馆之宝!
二禾君,你应该猜到了,我依然是在老家种田。不知不觉,已然种到第四季。
我有时会想,如果没有那时突发奇想,回乡下来种这么一片水稻田,4年后的今天,我又会如何。当然,生活不是数学,无法用程式来计算;然我可以保证,我心里不会有一片辽阔的水稻田了。如今,这里的山林、茶园、涧谷、溪流、蛙鸣与蝶舞,都成了我内心的风景。
谈及水稻田的收获,其实,每一季都有很多快乐。种田本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种便有收,挥洒下汗水,一定会长出果实。农人千百年来依靠土地生活,形成自己的光阴节奏与行事思维。然而在大地上挥汗,自然是艰辛无比。我的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考上好学校,扔掉锄头耙子。这也是我整个少年时期的奋斗目标。
不过,二禾君,当我们从城市回来,重新俯下身耕作一小片稻田,早已跟传统意义上的农人有所区别了,或有人以“新农人”呼之,而我们从土地上收获的,又岂止是一捧稻谷。
好,二禾君,这是我的青春(如果我现在还有一点青春的话),它跟我父亲的青春,是不一样的了。
2
2013年冬天,我决定回到五联这个安静的小村庄,跟父亲一起种一小片水稻。我16岁离开家乡,村庄里的景象就在发生着变化,青壮年争先恐后去了城市打工,会种水稻的农民越来越少。我甚至担心“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牧童再也看不到了,“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的农人再也看不到了,“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风景也再也看不到了。
我并非是对逝去的田园牧歌作矫情的怀念,而是对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予以关注。时代滚滚向前,但仍然有一些东西,是不该被抛弃的——譬如,我们还是应该知道,饭从何来,衣从何来;我们还是应该知道,俯身向着大地辛勤劳作是何种滋味。即便有一天,科技进步到所有农事都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完成,我们也依然应该记住:辛苦是什么,汗水是什么;播种时的希冀是什么,收获时的喜悦是什么;以及,稻叶割在手上的痛与痒是什么,蜻蜓振翅飞舞,蝉声不息鸣唱又是什么……
于是,2014年春天,当我带着几十位城市的大人與孩子一起回到乡村,学着父亲的样子插秧时,我与父亲,这一辈人与上一辈人的情感与记忆,终于发生了联结,那仿佛是一种人生的延续,也是记忆的衔接。我忽然就理解了父亲的一生。我开始懂得了父亲与土地的情谊。我甚至开始觉得,父亲这样种田的一生,何尝不是成功的一生?
3
2016年的3月初,我去了一趟位于海南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南繁基地,找人打听沈希宏博士。有人说,沈博士一大早就到田里去了。这时候水稻开花,正是他最忙的时候,只要去田里找,他一准儿是在那里。
沈博士是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育种专家。在他的试验田里,常年种着几千到一万个品种的水稻。每年从春到秋,沈博士把这些水稻种下,让它们生长,使它们杂交,观察它们,研究它们,从中挑出觉得有用的那一株,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天在海南继续种下,让它们生长,使它们杂交,观察它们,研究它们……
周而复始,秋冬春夏。有时要过二十年三十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
南繁,堪称是中国种业的“硅谷”。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有一批南繁人在那里埋首忙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甜瓜大王吴明珠、玉米大王李登海、棉花专家郭三堆…这些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大多是从南繁走出来,并在这里,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农作物新品种。
好了,这样你就知道了:沈博士不过是成千上万南繁科学家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沈博士的家在杭州,但他在南繁的基地要待上两个月。二十年来,年年如此。
沈博士在杭州有试验田,在海南有试验田,在印度尼西亚也有试验田,因为热带地区冬天也可以种植水稻,一年当中,就可以多种几季。对于育种专家来说,好像这就是一个游戏,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游戏。
其实想想,也很残酷——就好像你有一个孩子,你盼着她快点长大,可是她越快长大,你就越快老去。有多少科学家,是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抛在了稻田里。
4
我走到田埂上去,想看看沈博士在干什么。沈博士手上夹着一个记录本,一边观察水稻,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有时,他就怔怔地望着水稻,半天不挪动脚步。时不时地,他还俯下身子,手抚稻叶,或摘下几粒稻花放到鼻边,脉脉含情又满怀期待。
沈博士是一个感性的人。他觉得水稻也有帅哥或美女,他觉得短圆米不好看,细长米才好看,他对水稻的研究,是为了培育更好看也更好吃的大米。
沈博士想要培育出一种叫做“长粳”的品种。原来的粳米都是短肥圆,只有南方的籼米是长粒形,但籼米又不如粳米好吃。所以,沈博士要培育长粒形的粳稻,并且在南方推广种植。
经过十多年的科研积累,沈博士田里所有的材料,都慢慢地带上了他的特征:清一色都是长粳系列。“长粳”的香米,“长粳”的软米,“长粳”的黑米,“长粳”的香糯,还有很多很多,暂时还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一个的代号。
越来越多的想法,带上对稻米的期许,沈博士构建了一个自己的小田园,一个自己的水稻世界。
在中国水稻研究所,每一位科学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有的人,研究了三十年的抗旱水稻;有的人,一辈子研究病虫害;有的人,一门心思研究稻田里的杂草;有的人,孜孜不倦于野生稻;还有的,则专注于水稻的基因——水稻有4万多个基因,随便哪一个基因,就可以让人埋头苦干几十年。
5
二禾君,我想告诉你,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的水稻田里發生了很多值得记录下来的新鲜事。
这一年,我们的水稻田采用了新品种——沈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一种长粒型的粳稻。秋天的时候,稻友们得以收获品质极佳的大米。它的口感超过了我父亲曾经种过的任何一种水稻。当时,这个品种还没有命名。其中参与水稻收割的一位稻友雅号“包公子”,擅长舞剑,行云流水,于是沈博士命名新品为“包公子”——乃传为一段佳话。
稻田收割时,我们在稻田里作了一项名为《TIME》的艺术活动。在广阔的稻田中间,只保留了600株水稻,人们来到田间走动,收割,脱粒,一个相机镜头就默默地记录这一切。水稻的生长,需要时间;人生的过程,也是时间。在这个活动中,大家静静体会时间的价值。
这一年,因为“父亲的水稻田”活动,许许多多有着共同志趣的朋友汇集起来,来到五联这个小村庄,还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
“稻谷两头尖,天天在嘴边,粒粒吞下肚,抵过活神仙!”稻谷收割的时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喝彩歌谣”的传承人曾令兵,也来到我们的稻田,为开镰喝彩。一句歌谣,一声众喝“好哇”,回荡在田野上,响亮在天地间。
彼时,三四十位稻友一起,站在沉甸甸的稻穗前留影。父亲,沈博士,我,还有那么多稻友,以及在稻田里风一样奔跑嬉戏的孩子们,所有人脸上都挂着笑。
二禾君,在这里,我领受了大自然赐予我的所有美好。我重新俯下身来,看见了许多细微的事物。我富有耐心地把它们写下来,想让乡村生活与大自然的美好,为更多人所认识:我写了《下田》,我写了《草木滋味》,还有一本《草木光阴》即将出版。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
二禾君,你大概不会明白,种田怎样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它让我的心思变得宁静澄澈。我曾在一篇文章《把秧安放进大地》中写道: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几句诗里,隐藏着插秧的技术要领。……低头和弯腰是与田野进行亲密接触的首要条件。弯腰使得人呈现一种躬耕于南阳的低微之态,低头是把视野变小,把世界观变成脚下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水,看见泥,看见水中有天,看见天上有云,看见水中有自己,也看见水中有蝌蚪……泥土微漾之间,一种契约已经生效:你在泥间盖上了指纹,每一株青秧都将携带着你的指纹生长。”
我记起沈博士写过的一句话:“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我乡。生命与种田,所求的也不过是一粒心安。”二禾君,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片水稻田。我们在那里挥洒汗水与欢笑,收获成功和喜悦。我们的青春,在这些广袤的田野之上,蓬勃生长。
(选自《浙江日报》201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