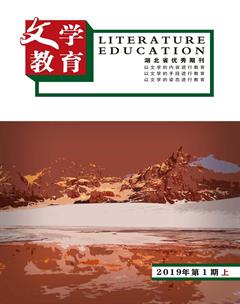在时间的纵深里,领受时代的开阔
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这说明具有时空意识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不经常“穿越”的人而言,这种意识可能在感官本能上已经隔膜;而对于一个经常“穿越”的人而言,这种意识则会在心灵中逐渐滋长。
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海洋文化沉淀出了西方人以空间型为主导的意识结构,农耕文化沉淀出了中国人以时间型为主导的意识结构。然而从杨克侧重表现时空意识的诗篇中,我们却并不能提炼出上述观点。在他有关时空观念的诗篇中,以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为主导的诗篇平分秋色,这反映出杨克的时空意识与传统有了变化。在这些诗篇中,《夏时制》和《1999年12月31日23点59分59秒》以时间意识为主导,前者写因人为的时间变动所带来的空间移位或者错乱,后者则以既是新旧年之交又是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个特殊时间点来细节性地凸显其对时空的精致打量。而《有关与无关》和《地球 苹果的两半》则以空间意识为主导,前者以时间轴中的某一时段为参照,力图展现不同空间中所发生的世界大事;后者则以十分形象的比喻,将两个空间进行既对立又统一的观照,尽管有历时性的叙述,但空间的意识占据了主导。杨克诗歌中时空意识及其观念的变化,个中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客观而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大背景导致了东西方不再是互相隔膜的世界,而科技的发展更是使遥远的空间在短暂的时间中变得不成问题(参阅《地球 苹果的两半》);主观而言,杨克的人生阅历,使他在承继以时间型为主导的文化意识结構的基础上,又触摸到了西方文化,具备了西方人的眼光,打开了全球性视野。其实,不论是以某个意识为主导的诗篇,还是意识互相合流的诗篇,杨克在其中都浑融了中西文化。他的这种时空观念与卞之琳诗中的时空关系多注重古老的中国意识(浑融儒道)有所不同。
有研究者认为,对时空的体验乃是人的内在生命觉醒的起点,同时也是艺术的起点。由于诗歌是人类艺术之一种,故而在诗歌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时空变换将使诗歌在内容和审美的形式上更加富于艺术性。中国的美学家向来喜欢探讨艺术中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以期藉此来发掘中国艺术所特有的个性与精神品格,而艺术家也希望凭靠此一技巧来使自己的艺术形式及其所蕴含的意趣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范例之中,杜甫和周邦彦在这方面的修为可谓已经登峰造极。杨克身为一位中国诗人,其诗歌艺术中应该说还是有无法抹去的“集体无意识”所留下来的“结构影子”。“所谓时空意识,不仅仅是指人们对时空的意识和把握,更是指一种以时间和空间思维特征为基础的感知、体验和思维的模式,它其实是一种生命感知形式,在文化传统的基因里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生命中。”(参阅程明震著《心灵之维:中国艺术时空意识论》)杨克的《际会依然是中国》,从章法而言是一首较为繁复的诗。他的感知形式,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宋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周词长于铺叙,并且擅长“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还善于增加并变化角度、层次。”(参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该诗以暴雨中朗读扎加耶夫斯基的《中国诗》为背景,调动一切元素进行交错穿插,诗歌的时空秩序一度回环。其时空序列之繁复,既体现在此诗本身与扎加耶夫斯基《中国诗》的层叠上,又体现在借助各种关联意象将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进行的交错上。比如,现在场景中的“暴雨”让人联想到“宋朝的屋檐”;诗歌通过“我”的视角关联起扎加耶夫斯基,并透过他的“蓝眼睛/看到故国诗人行船在江面上”。同时,诗中更细节化的想象也将现实中的国际空间(克拉科夫)转换到过去(宋代)的中国空间。诗的第三节也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结构,前半截通过想象将现在导向“未来”(扎加耶夫斯基的方向),同时以隐喻的方式将“未来”进行“味外化”处理。在最后,诗人仍意犹未尽,又将充满弹性的艺术时空进行了一次伸缩。
杨克诗歌的时空意识糅合了古今中外,既丰沛又精致。他对诗歌的时空感相当敏锐,让“在时间的纵深里/领受当下这个时代的开阔”变成了既定的事实。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