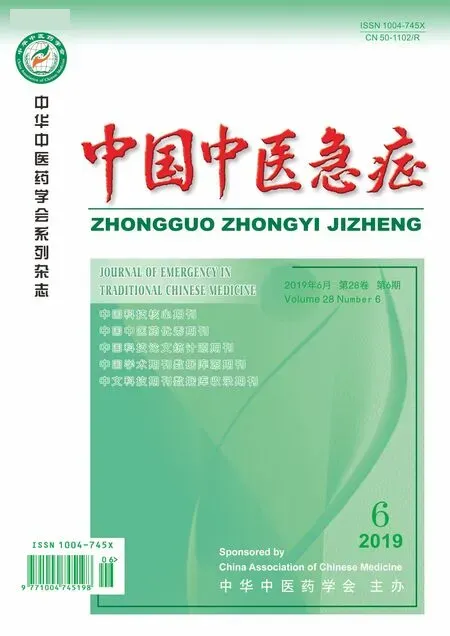从伏气学说探讨清瘟败毒饮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中的应用
蔡伟桐 吉训超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10405)
伏气学说属于温病理论之一,起源于《黄帝内经》,历代医家对其都有所探讨发展,并兴盛于明清时代,多用于指导临床治疗。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笔者临床实践发现本病临床表现及发病规律与伏邪致病发病机制有相似之处,现从伏气学说角度探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因病机及清瘟败毒饮的临床应用。
1 伏气学说的概况
伏气,又称为伏邪,是伏藏于机体内的邪气。伏气学说雏形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素问·金匮真言论》所提及“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1],均指出伏气为感受邪气之后,逾时而发,并成为后世伏气学说的理论依据。此后,晋代王叔和在《伤寒论·平脉法》中首次提及伏气之名,伏寒化温理论成形并成为主流学说。经过后世医家不断地总结完善,伏气学说理论体系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代表人物吴又可《温疫论》提出“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伏于膜原,发为温疫”[2]。清代刘吉人《伏邪新书》提出“夫伏气有伏燥、有伏寒、有伏风、有伏湿、有伏暑、有伏热”[3]。意味着伏邪种类扩大化,不再局限于伏寒化温,标志着伏气学说广义化,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指感受邪气,不即时发病,邪气潜伏于体内,或在外邪引动下,过时而发。
2 伏气学说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主要是由EB病毒原发性感染所致的一种急性增生性传染病。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多属“温病”“瘟疫”范畴,其发病主要是感受瘟疫时邪,邪犯肺胃,并按卫气营血规律传变,以气营两燔、热毒炽盛、痰热瘀结为基本病机。王艳认为EB病毒致病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能够长期潜伏在人体中,在人体免疫力下降时激活并增殖,免疫功能紊乱极有可能造成EB病毒的感染,或者被感染本身就存在免疫缺陷,在EB病毒的诱导下而表现出来[4]。这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1]。故多数患儿表现为轻症或隐性感染,年长儿症状较重。EB病毒作为温病邪气中的温毒之邪[5],潜伏于机体,发病符合伏邪致病的特点:邪气盛则即发,邪气弱则伏藏,正气盛则即发,正气虚则留邪。国内文献亦指出“EB病毒感染乃中医伏邪致病”[6],与上述论点不谋而合。
伏气又分外来邪气与内生邪气,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内生邪气的产生和致炎因子、免疫介质等内分泌物质的产生机制密切相关[7]。 国内研究表明[8-10],EB 病毒感染所致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其免疫功能紊乱程度与EB病毒感染量有关。何廉臣于《重订广温热论》中提及“凡伏气温热,皆是伏火。虽其初感受之气有伤寒、伤暑之不同,而潜伏既久,蕴酿蒸变,超时而发,无一不同归火化。中医所谓伏火症,即西医所谓内炎症也”[11]。因此,EB病毒引起的机体免疫紊乱为内生邪气,加之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潜伏日久便为伏火,也与“气有余便是火”理论相符。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发病初期即出现发热,咽喉红肿疼痛,乳蛾肿大,溃烂,颈部瘰疬等一派热毒炽盛的表现,为邪在肺卫之表证,但表证持续时间不长,即迅速出现皮疹显露、紫癜等热入营血,胁下痞块等痰热瘀血互结的表现。疾病后期表现为低热缠绵等阴伤气耗、余热未清之象。其临床表现与伏气邪说所言颇为符合。从传变规律看,笔者认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并非必然按卫气营血规律传变,从临床观察看,起病即表现为气血两燔之证亦不少见,可见皮疹及胁下痞块,如《黄帝内经》所言诸积,皆由初感外邪,伏而不觉,以致渐浸入内所成者,安可必谓其随感即病,而无伏邪耶。故气血两燔证发病可为伏邪外透,合并表邪发病。本病可从伏气角度分析:感受外来邪气(EB病毒),久伏机体,日久化热,内生伏火(免疫紊乱),正气日久渐虚,感受时邪,内外合邪,热毒炽盛,热入营血,炼津成痰,痰热瘀互结。因此,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发病机理与伏气学说密切相关。
3 清瘟败毒饮的应用
3.1 方药解析 清瘟败毒饮首见于《疫疹一得》,为清代余师愚所创。本方由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三方化裁而成,方药组成为:生地黄、黄连、黄芩、牡丹皮、石膏、栀子、甘草、竹叶、玄参、犀角、连翘、芍药、知母、桔梗。主治因疫毒邪气内侵脏腑,外窜肌表,气血两燔,表里俱盛的火热实证。余师愚认为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气薄,能解肌热,体沉性降,能泄实热”,故重用石膏入胃经以清十二经之热,配以知母、甘草、竹叶,效法白虎汤,大清气分之实热。黄连味苦,性寒,《本草求真》[12]载其“大泻心火实热”;黄芩功专“上行泻肺火”,两者合用以清心肺之火于上焦,栀子入心、肺、三焦经,善清心除烦;连翘味苦入心,长于清心火;黄芩、黄连、栀子、连翘同用,取黄连解毒汤之法,泻三焦之火毒,配以桔梗作“舟楫之剂”,载药上行,充分发挥解毒之功。犀角现为水牛角代替,两者功用类似,水牛角清热凉血解毒;生地黄甘,苦,寒,功专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神农本草经》[13]言其“逐血痹”;牡丹皮清热凉血,使血凉而不瘀,血活而不妄行;赤芍凉血化瘀;四药伍用,合为犀角地黄汤,佐以玄参“清血中之火”,共奏清热解毒、凉血散瘀之功。
3.2 临床应用理论依据 张锡纯认为“盖凡伏气化热窜入胃府,非重用石膏不解……其种种病因若皆由于伏气化热……投以白虎汤或投以白虎加人参汤,再因证加减,辅以各病当用之药,未有不随手奏效者”。又《伤寒序例》云“伏邪郁久而后发,发即大热大渴”,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气血两燔证,证候多表现为壮热烦渴等,属阳明气分证。明·陆九芝认为伏邪“藏于阳明”,白虎汤大清气分实热。柳宝诒《温热逢源》强调“治伏气温病,当步步顾护阴液”[14],认为伏气郁热内耗,易伤阴液,白虎汤还具有清热生津之效,故清瘟败毒饮效法白虎汤治疗伏气郁热是有据可依的。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邪伏于三焦脂膜之中”[15]。本证热毒炽盛于三焦,本方效法黄连解毒汤,清三焦之热,直达伏邪病位。从病机而言,热毒内窜营血,迫血妄行,可见皮肤紫癜、胁下痞块、瘰疬等痰热瘀血互结证。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指出“灵其气机,清其血热为治疗伏气第一要义也”[11]。叶天士认为“入血犹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16]。犀角地黄汤作为清瘟败毒饮的组成之一,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散瘀之功。综上,从伏气温病角度分析,清瘟败毒饮作为治疗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气血两燔证是具有理论基础的。
4 验案举隅
患儿,男性,10岁。因“发热、咽痛6 d”就诊,就诊时间:2018年5月15日。现病史:发热,咽痛,无汗,双侧颈部疼痛,纳差,恶心欲呕,眠一般,大便干结,小便黄少。体格检查:体温39.5℃,腹部、四肢散在红色皮疹,双侧颈部、腋窝、腹股沟可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最大约2 cm×2 cm,质中,压痛,活动度可。咽充血(+++),双扁桃体Ⅱ°肿大,可见白色分泌物。腹稍膨隆,无包块,肝脏右肋下约5 cm,质中,边缘钝,脾肋下约3 cm,质中,边略钝。舌红,苔黄厚腻,脉数。检查结果:细胞形态示:异型淋巴细胞51%。EB病毒DNA检测:4.12×106copy/mL。肝胆胰脾彩超提示肝脾肿大。中医诊断:温病,证属气血两燔证。西医诊断: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治法: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拟方清瘟败毒饮加减:水牛角 30 g(先煎),石膏 40 g(先煎),黄连 10 g,黄芩 10 g,连翘 10 g,栀子 10 g,淡竹叶 8 g,生地黄20 g,赤芍 10 g,丹参 6 g,知母 10 g,桔梗 6 g,甘草 6 g。共4剂,每日1剂,复煎1 h,早晚分次温服。2018年5月19日复诊。低热,仍有少许红色皮疹,轻微咽痛,颈部疼痛减轻,纳眠一般,大便两日一行,小便正常。体格检查:全身浅表淋巴结较前回缩,咽充血(+),双扁桃体Ⅰ°肿大,可见少许白色分泌物。腹软,无包块,肝脏右肋下约3 cm,质中,边缘钝,脾肋下约2 cm,质中,边略钝。舌红,苔黄稍腻,脉滑。原方基础上石膏减量为15 g,栀子、连翘、淡竹叶减量为5 g。共4剂,煎服法同前。2018年5月23日三诊。无发热,无皮疹,无咽痛,无颈部疼痛,纳眠可,二便正常。体格检查: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咽充血(-),无分泌物,腹软,无包块,肝脏右肋下约1cm,质中,边缘钝,脾脏肋下未触及。舌红,苔白稍腻,脉滑,复查细胞形态示:异型淋巴细胞5%。肝胆胰脾彩超提示肝稍大。原方基础上去石膏、知母、栀子、连翘、淡竹叶、桔梗,加薏苡仁20 g,豆蔻10 g(后下),玄参10 g。共3剂,每日1剂,水煎,饭后温服。
按语:本例发病早期即表现为气营两燔证,选方清瘟败毒饮加减,初诊方注重气血两清,清热解毒,凉血泻火,重用水牛角、石膏。复诊时仍有低热,但热象渐除,继续维持原方,减少清热之力。发病后期虽邪热已退,但时值夏季,岭南之地湿热显著,恐血中余热与湿邪互结,缠绵不愈,故着重祛湿,佐以玄参以清血中之火。本例以伏气学说为理论指导,根据病因病机,辨证遣方,侧重药物用量,因地制宜,灵活化裁,随证加减,故能三诊而愈。
5 结 语
伏气学说从古至今都颇受争议,从伏气学说角度,结合现代医学知识,能更清楚地理解并阐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发病机制,以此为理论基础,指导临床用药也有不错的疗效,故伏气学说值得深入挖掘,应用于临床其他疾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