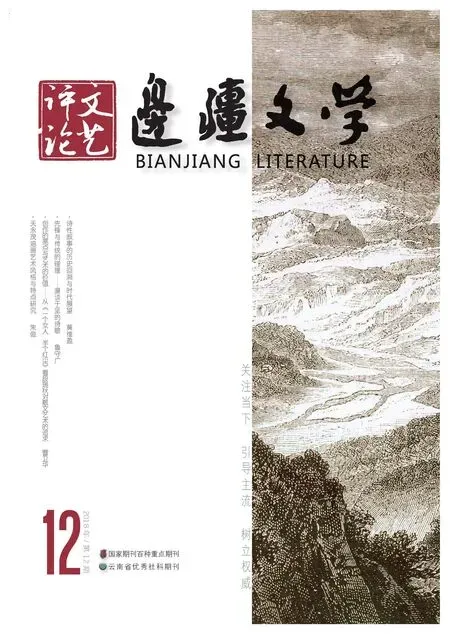浅析于坚及其作品的意义
付冯选
理解于坚是困难的,因其大而无处下手。本文尝试提供一些线索,挂一漏万。“道在何处”一节,主要从“史”的维度来勘定于坚的身位;“诗人何为”一节则从于坚的思想本身着手,试着指出于坚及其作品的意义。
一、道在何处
1.第三代诗的得失
所谓“第三代诗”及其“第三代诗人”,在我看来并不仅仅是艾青、北岛之后的第三代,而更重要的是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是第一代,而他们要“背离”北岛等所建立的诗观及其话语方式,即不想成为沿承北岛一代的第二代。如此一来,第三代就有“他者”的意味,即强调与第一代的断裂而非延续,这从两个诗刊的名字中可以很直观的见出——《他们》《非非》。
毋庸置疑,第三代诗为西方现代思潮所深深塑造,整个现代文学都是如此。质言之,要想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艾青一代(即第一代诗人)的所接受的西方思想主要是西方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及其浪漫主义,如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歌德等。而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冯至等成了北岛一代(即第二代诗人)的先驱,这些现代主义思潮是对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的深化与反拨,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代表性诗人包括艾略特、卡夫卡、里尔克、策兰、特朗斯特罗姆等人。中国先锋文学,尤其是小说,也属于这一代,整体呈现“朦胧”的深度。第三代诗就是针对前两代,尤其北岛一代的诗歌而发。
第三代诗,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决定性影响。后现代本身是个暧昧的词,因为它与现代有时根本就是一回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式深化。西方思想家追问后现代时有时会追溯到古希腊,这就消解了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断裂”意涵。我在这里将“后现代性”勉强区分为三个面向:a现代的延续;b解构现代;c回到生活本身。概言之,a是直面的,倾向于灵魂,属于现代之后;b是反面的,倾向于身体(实则是欲望),属于矫枉过正;c是正面的,倾向于灵肉一如的身体(也就是王船山所谓“即身而道在”的身体,同样也是梅洛·庞蒂区别于身躯之身心一如的身体),既是对a的超越,同时是对b的反拨,即处于临界-中道的位置。需要指出都是,这三个面向往往混合出现于一个诗人身上,并因时期不同而有所侧重。第三代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朝向第b面向的。粗略地说,北岛之后,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如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等)代表了a面向,西方诗人如庞德、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帕斯、博尔赫斯对这些诗人影响甚大;相应的所谓民间诗派就代表了b面向。在b面向上,我可以举出两位诗人,一个是伊沙,另一个是杨黎。西方诗人格里耶、惠特曼、拉金、金斯堡以及弗罗斯特等对他们影响很大。
上述两派各有得失,北岛一代所得还留存在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那些作品中,其所失则集中为第三代诗人所抨击。第三代诗人最大的贡献在语言方面,即拓宽了现代汉语的诗性,其目的是为日常生活辩护。在诗歌政治学上看,是一群为个体、自由、平等而战斗的孩子。这与“文革”后,改革开放所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关。对语言(生活)的这一贡献,首推于坚(早期)、韩东,李亚伟、伊沙、杨黎次之。相应c面向的诗人,情况更为复杂。他们要回应西方诗歌、回应唐诗;他们要直面被现代性所形塑的没有神性的日常生活;他们要在中西古今文明的激荡处处理当下的生活经验。总之,他们的“野心”是要让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成为唐诗一样的经典。朝向c面向的诗人可谓凤毛麟角,以我有限的视野,只能举出于坚。
2.于坚与第三代诗人的区别
我个人以为,于坚实质上从来就不属于第三代,但在反对知识分子写作及北岛一代的90年代,于坚站在了民间诗派一方,这主要是就语言策略上讲的(“反对隐喻”,消解深度和宏大叙事),这一语言策略和韩东(“诗到语言为止”)遥相呼应,实乃一场新的诗歌革命,最终成果,即于坚“诗言体”的提出。杨黎等人今天仍在坚持的所谓废话写作,亦可以看作这一语言策略的延续。
上述两者都认为语言(诗歌)是存在(生活)的家,并且要回到元语言(诗歌)。但区别在于,杨黎等人认为,生活是琐碎的、平淡的,因此以一种琐碎的、口水的“废话”来写作是“回到事情本身(Zur Sach selbst)”,可这一“事情本身”是建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剥离之上的,如果“事情本身”缺失伦理维度,这一“事情本身”就是善恶是非不分的混沌,即文化一词所标识的世界(黄色文化跟圣经文化在文化学上是平等的),此时回到的所谓元语言(诗歌),即未经孔子删定“诗歌”;于坚则认为生活是上手的、日常的,不仅具有常识属性,并且是神圣的,而将这两者不偏不倚地凸现出来就是诗人的本事(本来之事),这才是“回到事情本身”,这一“事情本身”是天地人神一如的,此时的“事情本身”即文明一词所标识的世界,此时的诗歌是孔子删定后的“诗歌”——“诗三百”。
3.现象学视野中的于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西方,有一种理论是有助于理解于坚的,即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诗思合一的存在现象学。这种现象学的方法(其实无所谓方法),即形式显示(孙周兴)或形式指引(张祥龙),中国学者称其为形象显示(丁耘),也就是区别于概念思维的象思维(王树人)。据我所知,海德格尔之后,沿着这一方向致思的思想家还有巴什拉和罗姆巴赫等。于坚对诗文的理解,就属于现象学式的。当然,海德格尔的影响只是一个外在的契机,这种现象学的识度在中国传统典籍中俯拾皆是,如随物赋形、与时偕行等。大禹治水就是中国现象学或道(導)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此,诗歌要呈现的存在即生活世界本身,它是自足的、源发的、不息的,诗人能做的只是守候、倾听,让其自在起来,这就是本源意义上的诗——元诗。此时的诗(语言或词)与生活(世界或物)的关系,是波纹与水流的关系,此时的诗即源初意义上的纹,即爻象。诗人即文人。于坚的诗文有一部分命名为“事件”“作品”“便条”“笔记”等,是因为这不仅是诗人创作出来的作品,而且(更主要的)是存在生活世界自然而然的显现。譬如,《对一只乌鸦命名》《避雨之树》《飞行》等作品。同样,《0档案》作为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亦即那段生“事情本身”的形态。至此,词才是“及物”的。
二、诗人何为
1.于坚思想的结构
80年代,于坚开始写诗,此时的诗呈现出口语化、反隐喻等特征,如《尚义街六号》。其时他思想的关键词大概是:能指与所指;过去与未来;生活世界与意识形态等。诗人立足于前者而批判、解构后者,皆以日常生活为归宿。其思想受到西方,尤其是现代西方思想的笼罩性影响,其视域未能超出现代性(包括西方的“语言学转向”),故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与“五四”一代一致。
大概在90年中期以后,于坚试着将自己从受现代西方影响的现代性传统中区别出来,同时开始强调中国古代传统的重要性,并试图接续这一传统。因此,对现代西方思想以及受这一思想影响的“五四”传统保持了必要的警觉与批评,《还乡的可能性》一书中所收录的文字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直到今日仍在延伸(如《朝苏记》)。此时,以过去为基点批评未来,即以“故乡”为基点来批评“现代性工程”(列奥·施特劳斯语)。然而,站在生活世界的视界来反思、批评一切意识形态则是一以贯之的。
从《棕皮手记》所收录的文字看,于坚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与其说转变不如说深化的过程。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于坚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诗人,以解构及其后现代为标志,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几乎都是现代西方的。90年代中期开始,于坚的思想变得更为圆熟,以对传统态度的转变为标识,故不理解于坚的人误以为于坚“背叛”了“他们”。
顺便一提,于坚早期对语言的可能理解基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同时有误解了海德格尔之嫌。在“语言学转向”中,海德格尔无疑是走得最远的,其拆分语言的游戏以及提出“形式指示”的现象学方法,其目的就是要破除西方拼音文字的局限性,然而作为西方人,海德格尔提倡“语言乃存在之家”,即便此时的语言是本源性的道言,即诗,也是西方语言思维的结果(所谓“太初有言”)。中国则山春草木无不是道之体现,语言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这样的至尊地位。与此相较,中国艺术精神主要在庄禅,其对道与言的思考是以言筑象、以象筑境、以境扬神,最终得意忘言。按照海德格尔思想自身的脉络,海德格尔推崇的一定是中国的“象思维”,这种思维对语言的理解正是“得意忘言”,其在禅宗“不立文字”的教诲中达到极致,故罗姆巴赫沿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脚步一直走到了东方——禅宗。
2.诗学革命
于坚强调语言的描述及其逻辑性(应当受到拼音文字及叙事文学的影响),即是解放汉语或修补汉语自身之不足,为的是诗重新开始其创世功能——命名。然而,古汉语的抒情性变得突出只是隋唐以来的事,而先秦语言则古朴自然,叙事抒情尚未剥离,此时的语言接近元(源)语言,即真正的诗言或道言。既然修辞性的隐喻必须回到元隐喻,那最终诗歌语言就得回到元语言,而非侧重叙述的所谓小说语言。
以传统的文质视角来看,礼法维度缺失会导致质胜文则野,此时的诗不再是诗教(与荷马展开“高贵的竞争”的柏拉图声称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这就是“诗与哲学之争”的古典意涵),正因为如此,此时的诗就成了原诗,这与海德格尔晚年的入思路径是不谋而合的。然而海德格尔的召唤是回到中国的天道,于坚则是要重新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回到原(元/源)诗,以及对世界最初的理解,这不止是一场深刻的诗学革命。
3.回到生活世界
然而,于坚的探索是一以贯之的。于坚从日常生活出发,批判意识形态,从能指出发,回到存在本身;立足故乡或大地,批判“在别处”以及现代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之思。于坚一方面要求回到本体,另一方面又要回到具体(形而下),实则是要从体用两个方面同时回到原初境遇。于坚获得这一识度其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不可小视,但更多是出于自己的身位与自觉,即自身探索的结果。在这一探索中,少时阅读、文革经历、工厂经验、高原漫游、行走世界(深入世界,而非与国际接轨)以及个人性情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其发端则是对北岛一代的批判,即第三代诗的兴起。
生活世界本身即是我们的根,我们只能立足于此,其他都是派生性的。为日常生活辩护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为存在辩护、为人性的辩护,此处即天地人神共处之所(“域中有四大”),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活水源头。于坚作品所展示的正是现象学所追求的,故其作品具有原发性、直接性和当下生成性,一个作品就是一个事件,所谓“以言行事”。于坚写诗、作文、摄影、拍记录片,都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如《建水记》),即庄子所谓“藏天下于天下”。这是一种无为之制,尽可能消除一切多余的东西,让诗意自己呈现、涌出,语言则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谓指示之形式。然而,此时的作品已经不能用俗常的诗歌标准来评判,作品成了艺术,成了真理(参看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
于坚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艾青、北岛,又不同于杨黎的中国新诗之路。这第四条道路是从前三条道路中流出来的,是一条中道,惜乎至今仍隐而不显,但于坚的作品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消息。“诗领导生命(于坚语)”,于坚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值得一过的生活,一条道,其作品不过是诗人沿途的留下的“路标”(如《便条集》)。“道路而非著作”,对于坚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
当所谓的第三代诗人还在那里表演(“不诚无物”)之时,于坚已经走远。

谢 凯 那一片山 60×50cm 布面油画 201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