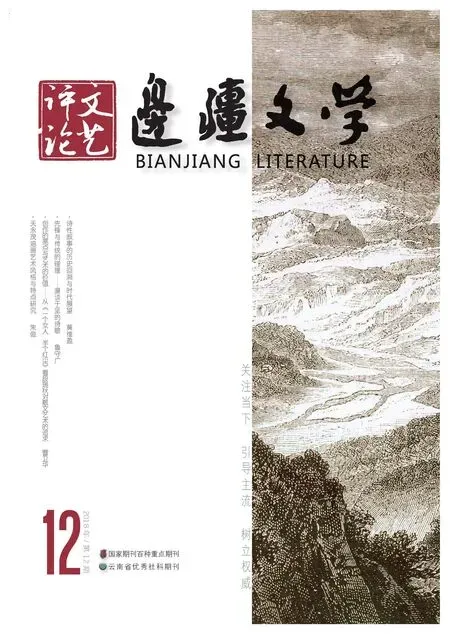诗性叙事的历史回溯与时代展望
黄维盈
1
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代节点,如何抒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沧海桑田里的灵与肉?如何展开有温度有高度有历史纵深的诗歌创作,把“人人心中有”的感受转化为“开卷处处见”的优秀文本?如何克服“眼前有景道不得”与“为赋新词强说愁”双重弊病、避免放任自流的文字把玩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消解?……等等,都是每个诗人面临的重大诗学命题。
晨曦照亮时代羽翼,阳光铺开锦绣征程。时代呼唤大诗,人民爱唱大歌。邓小平时代,我们唱出了《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时代,我们唱出了《走进新时代》。鼓舞人心的盛世欢歌,用诗化语言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高度的概括浓缩,徐徐铺开时代画卷,蕴藏着掀天揭地、扬眉吐气的精神核能量。
我们有幸与新时代相拥,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诗人的创造之根,应深植于当代中国人的鲜活实践,自信地面对异彩纷呈的现实,抒写中国诗篇,以洋溢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传递中华民族的价值与审美追求,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因此,新时代诗歌要创作出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气之作,必须拓展宏大叙事创作理念,拓宽创作视野。只有点,没有面,只有微观,没有宏观,单纯依靠见微知著,依靠以小见大,永远见不到时代的黄钟大吕。所以,一旦抵达诗歌层面,宏大叙事不再是包罗万象,不再是麦吉尔所讲的“无所不包的叙述”,而是一种高屋建瓴、尺幅万里的概括能力和技巧。
在语言修辞和常识、诗识的整合过程中,真正有效的诗歌叙事能够判别或厘清其背后负载庸常生活的轻与重,大和小。那些看起来细碎的、偶然的、逼真的生活镜像,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复制还原,没有被诗人转化为真正的诗学共享经验,这样的经验就不再是经验,而是生活场景和语言文字的杂乱堆砌。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性和多元化超乎想象,素材的盛大壮观给诗性叙事写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继往开来的时代语境和精神激奋昂扬的状态之下,诗人应当在孜孜不倦的敬业探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径,把那些珍贵的现实经验演绎为有效的诗歌范本,让读者读到与时俱进的心灵风景。
如果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创作是一种奢望,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种具有时代意义上的大诗。在我看来,大诗之大,不一定是全景式的描绘,而是气象大,气魄大,意象精雕,内容精当,意境精彩,思想精深,自动生成天下独步、舍我其谁的豪迈雄浑氛围,合成千古绝唱。杜甫的《望岳》,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就是脍炙人口的大诗。所谓文学经典,都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精挑细选出来的。诗人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读者的文学审美能力。几乎每一首诗,都能在时代的天平上秤出它们的文学重量。
当代诗人中,毛泽东就是一位擅长写大诗的高手,雄词丽句数不胜数。毛泽东不但是伟大领袖,还是独领风骚的大诗人。即使把毛泽东诗词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长河中比较,他那些大气磅礴、光昌流丽的作品,足可与历朝历代的经典诗词比美争胜。毛泽东古为今用,以诗写史,让史入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完成了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以此来反映当代生活,反映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程,豪迈情怀登峰造极,表现手法炉火纯青。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经天纬地、气壮山河的大诗气象,大家风范。
同样是吟诗赋词,毛泽东从来不会无病呻吟,诗性叙事的史诗灵感纷至沓来,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不胜枚举。1925年,军阀混战,毛泽东写出名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1934年,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写出名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1935年,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毛泽东写出名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1936年,毛泽东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写出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1949年,南京解放,毛泽东写出名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名诗靠名句传颂。因为名句是思想容量和精神当量的载体,有限的措辞盛载无穷的境界、胸襟和气魄。我始终认为,没有产生名句的诗,算不上一流好诗。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诗篇与之匹配,需要精神上的“满汉全席”。而当下的一些诗人,却一直笑容可掬地给读者上小菜,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就是不见正牌大菜。缺乏毛泽东冠绝天下的大手笔,“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
所以,把诗性叙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除了解决诗歌的思想境界、艺术水准等问题,同时也面临“写什么”的问题。比如,信手拈来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等生活场景到底承载了什么?如何让私人生活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如何让个人生活的特殊性关涉到大众的普遍性,确实是诗人必须正视的问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一定都具有诗学价值,我们当然不是在倡导一种简单的诗歌强行介入,但诗人对自己的日常叙事总得有一些“先知先觉”式的诗性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多寡,应当与文学常识构成审美对应。同样是游山玩水,毛泽东写出来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被放进具有社会现实内涵的历史框架,没有沦为意义缺失的自我把玩?可见,只有在诗性叙事中充分打开个体经验的门户,才能穿越日常生活的表面幻象,在与“大我”的对话中呈现出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样貌。
2
诗性叙事是诗歌创作的本质要求。第一要有诗意,第二要及物。这个“物”,可以是物像,意象,也可以是感情思想。不但叙事诗,其它诗也概莫能外。甚至小说领域,也当仁不让,引进了“诗性叙事”的这一概念,强调诗化倾向,鼓励作家们尽可能把句子写得更优美一些。所以,对诗性叙事重新诠释,进行一次粗线条的历史回溯与新时代展望,确实很有必要。
诗性叙事要求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英国诗人拜伦的著名抒情诗《雅典的少女》:“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我要凭这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我要说,凭爱情的一串悲喜/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你看,诗人抒情的过程,其实也是叙事(或叙述)的过程。要抒情,一定要有对象。交代抒情对象的过程,其实就是广义上的叙事。毛泽东在谈到新诗时,多次主张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借鉴,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古典诗歌和民歌,都是通过诗性叙事来完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叙事,既有古典诗歌的风雅厚重,也有民歌的通俗易懂。老百姓不说毛泽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伟大,而是把毛泽东比作太阳,一个“出”字,任何修辞都要俯首称臣,甘拜下风。“人民的大救星”横空出世,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多么高明的表现手法啊!《东方红》史诗的传唱,亿万人民心里乐开了花,我估计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也一定乐开了怀。只有诗性叙事,才能打开人民与领袖的感情通道,莅临平凡而又尊贵的文学殿堂。
诗性叙事有两大好处:一是艺术层面上的韵律美,二是思想层面上的哲思美,亦即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诗歌中的“叙事”,必须呈现诗化倾向,能够体现对传统日常叙事语法不同程度的背离。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的变形和不完整性,有意识地追求叙事的不完整性,自始自终保持叙事的不透明性,留给读者一种期待中的想象。二是内涵的不确定性。传统叙事的意蕴是封闭而自足的,诗性叙事中却有意地留白,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填充。所以,诗性叙事又是对普遍叙事语法逻辑的背离。
杜甫的“三吏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就是著名的叙事诗。用诗性的叙事,深刻写出了乱世飘零中的民间疾苦,对倍受战祸摧残的百姓寄予悲悯同情。诗中有史,史中有诗,所以被称为“诗史”。
诗性的叙事,最能体现诗人的艺术功力。缺乏诗性的叙事,很容易变成“流水账”,难以让思想内容增值。当下有的诗人,并没有真正掌握叙事性写作的精髓,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处境缺乏切实的体认,滥写跟风之作不断涌现。由于没有足够的生活履历和精神信仰支撑,缺乏“顾全大局”的本领,诗性叙事的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使诗歌沦为生活表象和经验碎片互相攀比的文字展览,迅速加入集体遗忘的队列。
杜甫的作品,主题鲜明,手法高超。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批判精神,始终把握着一个度。杜甫的诗,善于提纲挈领,抓住时代特征,叙事切入点精准,甚至不必太多的修辞,仅仅依靠叙事内容本身就能体现出很强的诗性。《新安吏》就充分体现了杜甫诗性叙事这方面的创作特色。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是全诗的起笔。诗人一出手,就详细交代了当时官军抓壮丁的乱世背景。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按照唐朝当时的征兵制度,中男(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该服役。杜甫也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知道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明知故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也很狡黠,回答模棱两可:“州府昨夜下的命令,要挨次往下抽选青年人出征。”杜甫接着又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青少年又矮又小,怎么能守住洛阳呢?)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诗歌叙事在一问一答中展开,说明诗人一直在场(历史现场),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三贴近”的文学践行者。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无话可说,于是诗人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有母亲送别,长得消瘦的男子则孤苦伶仃,无亲无靠。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人走以后,哭声仍然不绝于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悲惨的场面催人泪下。在这里,诗人通过对人与人、山与水准确而形象的描摹,强烈的诗性在押韵、对仗的句子中洋溢出来,读之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杜甫后来还写到“天地终无情”,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诗人始终维护祖国统一的“大局观”,当之无愧地跻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列。
所以,一流的好诗,必须达成诗性和叙事的高度统一,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做到虚中有实,象中有意,情中有义,“个我”中有大我,观物以取意,立意以尽言。当代诗人中,毛泽东就是首屈一指的翘楚。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名句,就体现了诗性和叙事的高度统一,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指点江山”是叙事,诗人确实在看风景,但诗人不经意间又完成了旋乾转坤式的言志缘情。毛泽东心中的“江山”,是“如此多娇”的江山,又是“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江山。“激扬文字”,毛泽东不是在显摆书生意气,咬文嚼字,而是用昂扬的姿态,激活前无古人的雄才大略。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来口气就大得不得了,毛泽东却来了一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境界!这就是农民首领与人民领袖的区别。“谁主沉浮?”按照正常叙事,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应当问的是湘江,但他偏要问“苍茫大地”,物像移位意象赋形,从虚到实,由微而宏,诗性和叙事浑然一体,立心铸魄水到渠成,这正是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诗词大厦的雄伟基石。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豪情,始终根植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之上。所以,无论多么高明的诗化叙事,也不能背离真实,不然就会凌空蹈虚,重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覆辙,靠虚张声势的口号和感叹号来支撑诗歌文本的空架子。外强中干的“大”,夜郎自大的“大”,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振聋发聩,而是苍白无力。
叙事中的“事”,就是思想内容。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可以拓宽诗歌的纵深,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困囿,衍生出多元的维度。不叙事,托物寓意或借景抒情就没有了“物”的根基。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叙事不能“假大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表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文革”时期,口号诗和标语诗占了很大篇幅,这类作品给人最强烈的感觉是虚假、虚伪和虚妄,有大我无“个我”,有思想激情,无真心实意,叙事与诗性严重脱节,缺乏通常我们讲的诗意、诗思、诗味,阅读价值与文学审美的等高线已经很难持平,从而造成读者审美疲劳。所以,改革开放后,朦胧诗很快就取代了传统叙事诗的位置,在争论中被读者接受,进而成为新诗创作的主流方向。
新世纪之初,有的叙事诗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大量“口水诗”“泛口语诗”。这些手法单一的叙事诗,尽管表现的内容不再是“高大上”,却矫枉过正,对鸡零狗碎所谓的“卑微”事物情有独钟,在刻意低调的语境中展开“向下”“靠后”的书写,生成的诗句严重缺失“居要”的“片言”,从而失去诗性的强大内核,一度成为大众和媒体嘲讽和抛弃的对象。
3
通过上述经典作品和现代文本的条分缕析,不难发现,诗性叙事的解读,完全可以进入诗歌纹理内部去进行,对各种技艺的不断细化和量化,进而获得精神的净化和思想的深化。
诗歌叙事的难度对应着超越现实经验的难度。现实经验的深层挖掘,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诗化再现。没有更新换代的叙事穿透力,就无法揭开时代镜像的瑰丽面纱。在个性张扬的叙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经验将成为诗人观察、思考和归位的对象,并直接反映到诗歌文本,让个体情感与现实生活对接或对撞,进而生发心灵的温暖或隐痛,最终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也就是说,有了诗性叙事的创作意识和能力,剩下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境界问题,灵与肉的问题。诗歌属于诗人个体的言说,这种言说当然是建立在个体对诗歌本身的技艺、语言、言说对象等方面,从自身出发,抵达个体的内心。然而,“诗到语言止”,毕竟是最低层次的表达,属于“形而下”的表达。诗歌的文学价值,除了言下之意,还有言外之意——亦即“形而上”。《易经·系辞》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达到“形而上”高度的诗,才能引起读者思想共鸣,心灵共振,这样的诗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诗。杜甫望岳,当然是他自己在“望”,一切从自身出发,让感受抵达自己的内心。然而,一旦这种内心感受以文学的形式诉诸于诗,公之于众,这种言说就不仅仅是个体言说,客观上又有可能成为群体代言。人们登山时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诗人替自己说了,而且说得你心服口服,把文学的愉悦功能发挥得痛快淋漓,这样的诗人,才是一流诗人。相反,某些诗人的个体言说,由于技艺拙劣,力不从心,思想缺斤少两,境界捉襟见肘,见识比普通读者还要短浅,鸡肠小肚,这种诗你就是想为群体代言,人家也不喜欢让你“代”。杜甫登高望远,表达的是入世思想,积极进取的人生,兼济天下的豪情。只有卓然独立的人品和诗品,才会千古不磨,万代流芳。
诗性叙事是经典诗歌的强项。《诗经》的诸多名篇,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静夜思》《子夜吴歌》,还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等,都是诗性与叙事完美结合的典范。诗性叙事与日常叙事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有意象,有意境,后者有物像,无意境。意象能够生成意境,而物像只能生成环境。同样是分行文字,有的诗诗意馥郁,心香萦怀;有的诗却寡淡如水,索然无味。诗性叙事与否,就是它们之间的重要分野。
多年来,许多诗人热衷于学习和借鉴西方诗歌的一些创作经验,“诗道尊夷”让我们掌握了一些西方诗歌技巧,同时也带来了一股机械化、同质化、泛深化的诗风,催生出大量思想虚高的“机器诗”。“机器诗”先天不足的智能组词模式,决定了它连起码的日常叙事也无能为力。把时代宏大叙事寄托在小冰身上,就像把万吨巨轮托付给山涧小溪。
世代传颂的经典诗歌,不仅诗性是一流的,叙事也是一流的,达到了意象与意境的高度融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诗性叙事;“太阳落山了,黄河还在流。我想看远点,抬腿再登楼。”就是日常叙事。二者表达的内容差不多,却境界迥异,判若云泥。前者有绝句严格的平仄对仗,有意象也有意境;后者完全是大白话,有物像,无意境。
由此可见,景物的精心选取,词语的精雕细刻,言说的志趣表达,感情的向度把控……等等,都是强化诗性最常用的有效方式,不一定需要太复杂的修辞。“诗无达诂”就是诗性叙事多维审美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诗的魂魄是从语言的骨头里散发出来的。从物像到意象,再从意象到意境,经过层层转换升级,才能穿透肉眼凡胎,贴近时代风骨。
一百年来,新诗以灵性之光熔涛精神,净化灵魂,点亮理想,抚慰忧伤。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与密码,彰显着汉语的力量。枝繁叶茂的中国新诗,语言领土不断扩张,扩充着有目共睹的体积和能量。
新世纪以来,新诗的整体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涌现出大量言志缘情、读者喜闻乐见的好诗。所以,我非常认同诗人李少君的判断:“这个时代,已经为伟大诗歌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全国上下迅速形成了一股诗歌热潮,讴歌新时代的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不少优秀之作,风骨之作。上海诗人缪克构的《陆家嘴》,就是其中的一首:
“经济脱实向虚/陆家嘴是反对的/在寸土寸金之地/它越长越高/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每一次拔节/它都没有虚度年华。/与纽约来客谈完一桩国际并购/我喜欢到国金中心的五十八楼/吃下午茶/烈日下的黄浦江/安静极了。/上海证券大厦显示屏上的股指/竖起耳朵/倾听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一艘巨轮的隆隆驶近/也不过是一张轻轻翕动的羽翼。/有那么片刻的眩晕/
让我以为已经君临天下/其实,我的头上,头上头/都还在陆家嘴的脚下/金融城的脑际有一片云/贮存着层层叠叠的密码/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密西西比河每一丝细微的风暴。”
窃以为,《陆家嘴》的诗性叙事确实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诗的内涵是上海的,是陆家嘴的,但它的“外延”,却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整首诗呈现出来的泱泱大国风范,浩浩上邦气派,道出了新时代炎黄子孙的心声。今天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高度,中国气度,中国风度,几乎都能在《陆家嘴》中找到思想契合、精神吻合的共性。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维度,诗性叙事与过去、当下和将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走向真理的诗学探索永远在路上。换言之,诗性叙事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时”的诗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不懈破解乃同道中人的应有之义。
知往才能鉴来,推陈方可出新。新时代开启新的征程,回溯经典,是为了展望未来。在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在文学创新的路途上,有时代抱负、有责任担当的诗人,应当勇敢面对思想观念和创造意识上的社会变革,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温文学经典,善于自我更新,不断锻造审美感悟功能,从而获得更加从容把握当下和未来的能力,用更优秀的作品讴歌新时代新变革,描绘中国人新的精神面貌与心灵图谱。
现代新诗是一项伟大的文学超级工程,新时代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创作自信,始终保持汇入沸腾生活的高涨热情。需要更多的诗人妙笔生花,踵事增华,不断添砖加瓦,在世界历史前进的洪流中构筑花团锦簇的文学家园。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力气花在诗性打磨和叙事提纯方面,将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迎来中国新诗“两个一百年”的完美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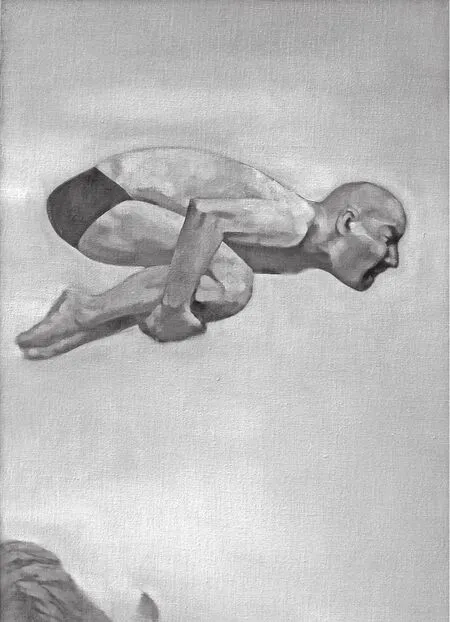
谢 凯 奋进 布面油画 60×9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