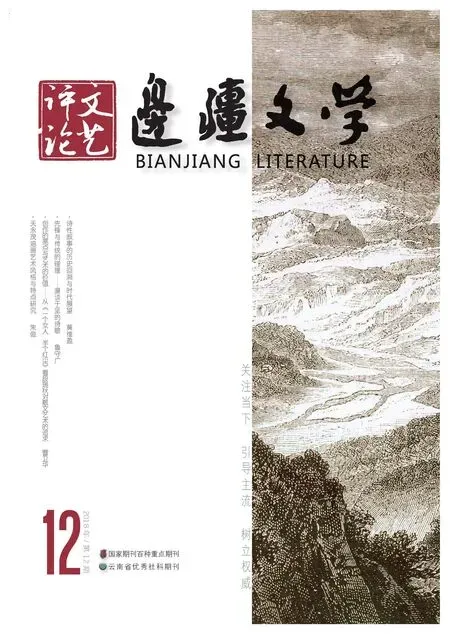凝重的山川
——青年画家王凯骐油画观感
朱思睿
一个痴心画艺的人,作品面貌通常三年一变,五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是自然之事,凯骐也不例外。这些年的展览中,笔者常留心他的画。不时见他在油画、壁画、水墨、甚至版画间穿梭,便一次次诧异好奇,一个人到底要有多少才气或者说心力,才能在不同画种间跳跃转换。近年来笔者发现,凯骐用工最多,出作品最多仍是油画,且作品渐趋成熟稳健。
一个画家的艺术才能形成,获益两个老师,一是自然,二是前人。纵有天才,也须自身灵性与上述二者相遇和激化。在自然面前,人永远是学徒。世界伴随生命的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我们的选择及精神诉求总会在自然中找到心仪的物象,并且在对物象的观照中受到灵性启示,从而寻求精神表达的冲动,而表达的方式同样是这个世界所赐,是已生成文化的第二自然所赐。凯骐遵从这样的自然规律,像大部分本土画家一样,在创作题材和视觉表现上,充分发掘云南这块土地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景观。
人生除去身体、精力、意志是自己的,更多东西应归功于前辈和同辈,很大一部分营养由此获取。纵观凯骐的创作,似乎独创性并不明显,没有看一眼让人记住的形式语言,没有高超的技巧(他本人也说自己不是技巧型画家),没有出人意料的色彩体系,也没有让人惊奇的视角投射或对被人忽略的题材捕捉,没有特别刻意向某位名家大师靠拢,更没有追赶流行时尚的当代绘画样式。因为他笔下的题材,他所用的表现手法,许多人似乎都在用……
笔者是否在说凯骐太顽固倔傲,很失败。你画的毫无新意,不是那块料。别画了!不,相反,绘画从未以新和奇作为标准去评断,也从不以流行和时尚奠定未来。凯琪的路子是今天的许多中国油画家同样在走的路,同样面对的困惑,同样在寻求突破的状态。
凯骐的工作接触艺术的层面多而广,他知道什么样的土壤浑厚,并适于自己生长。而艺术道路上的选择,必然是顺应内心需求,且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最好的诗歌语言最忌讳东施效颦,故作文彩,而是要用自己最顺口最方便的语言表达,绘画亦如是。
人们习惯于为绘画的风格分类,并且分得概括,一见到具象与写实,总会纳入保守的阵营。甚至伴随各种新艺术样式的出现,将架上绘画也归入过去式的艺术。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仍在继续。仔细看,绘画的个体差异性依然存在,无论学院画还是素人画。这是由于艺术活动是从属于心灵的,关乎个体生命的体验,情感与精神的向度。这样看来,凯骐的选择是保守的,但也是踏实和真诚的,且抱有自己内心的呈现。
笔者曾说过:“谈论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必须把艺术置于其产生的时空背景中,因时空是可变的,也得承认艺术价值的可变性。艺术是在特定时空下对所处时代的意识产物,是体验的结果,因此用既往的艺术经典(形式、行为)作为标准来判定今日艺术的价值,只是一种重复认定和相互证明,尤如科学上对一个定理公式的反复求证,沒有任何现实意义,也没有艺术体验的本质含义。经典不是一种不变的规范,其精准性是随适应性可变的,它只具备开拓上的启迪性。因此,艺术创作在任何时候,都要回到当下的日常生活与经验,回到事件本身和集体意识内,才会产生新的体验和价值。”
从来就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即使现代派中的某些倾向,在淡化艺术的传统职能,但任何艺术作品,终究还是社会环境中的产物,无论形式如何改变,推动变革的不是已有的美学经验,而是题材与内容,是当下的生存境遇,对创作者身心的刺激和反映。即使相对恒定的自然景观,古代士大夫审美中的艺术规范和法则,并不适应这个时代。包括今日国内外大师们的探索与成就,也不一定适合此刻此地的你。
任何形式都可通过外向摹仿而拥有,唯精神向度只能从生命内部生发,这是自我得以实现的本真。这种本真伴同生存而来,并在生存的境遇中不断明确,形成坚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如果它是纯正的,就会产生振拔向上的力量。凯骐的风景画没有做成装饰,没有像士大夫一样用逸气,用虚无的技巧为生命的虚无辩护,没有盲目拷贝西方既成的样式,仍然保留着一种不断探索与生长的痕迹。在他实实在在的笔痕下,涌动着一种冲决重围的暗流,不飘浮,不急躁,从容而坚定地面对自然老老实实画,真真切切的感受和体验。
笔者这样判断,并非说凯骐没有借鉴,是个盲目而自以为是的自然主义者。事实上,从他画上,很容易发现中国第三代油画家对他的影响,比如詹建俊、闻立鹏、朱乃正及云南的姚钟华等人的影响。这代人的风景画中有种浩然情怀,气质宕荡,画面刚性饱满,勃发昂扬。他们的境界舒展大方,风格凝重,既重形式上的美感,也关注象征性与抒情性。且色彩一反古典式的细腻微妙,而是清新洗练,笔触也摆脱了苏式的繁琐,印象派的斑澜细密。而是结合中国书法中的笔迹观笔阵法,笔随心动,见物见情,注重表现上的意趣与韵味,笔势劲健整体,节奏流畅明朗。能够于直观书写中将感受与性情形之于外,较少理性的雕琢与克制,尽显大气洒脱的优势。
凯骐在内化这些优点的同时,有意收敛了较感性的一面,使他的画风偏向硬朗,更注重构成上的紧密与动势。看他的风景,整体色调总给人沉郁凝重的荒寂感,很少用柔和的灰色调性,黑白与冷暖的杂陈有些决绝生涩,但笔迹的运动状态却又是活跃而动荡的,这种限定与非限定暗藏着画者内心矛盾的冲突,这或许是一个非全职艺术家真正的生存状态。
此外,凯骐的画,整体看也兼具一些新生代画家的特质,这一代艺术家并不太注重观念性和哲学化的表达,也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约束,更注重日常化和近距离经验的传达,在具像创作中追求表现性语言,自陈画画就画画,追求活儿地道,不评价不表态……
以上特质在凯骐的画中,表现为艺术本体语言的纯粹与朴实,取材上的随性与日常化,尽管也是山野风景,但却滤去了第三代艺术家追寻的象征性与理想化色彩,还自然以自然存在的本质特征,对象在此只是一个生存体验的载体。画者要做的只是凭藉媒材,把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及精神需求借对象之躯转译出来。
所以凯骐这些画不悦目,不欢快,不热烈,也不亢奋,不俗艳也不假装深沉或高雅。这是他目前在质朴路径中行走的基本面貌,符合他内心的创作审美追求,即在凝重的山川中寻找其自由的收放,在坚实的笔触运动中创造劲健的气质,在沉郁的格调中凸显超然的自在。特别是他表现在对光影和时间段的选择和取法上,是精心和统一的,不整体细看,很容易忽略这种与众不同。在那些情绪弥漫的画面之上,幽幽的微凉下,悄然滋长的生机与活力,荒寂而不落寞。这是凯琪艺术中不动声色的情绪,像南高原山林中一丛午后的竹子,一天长出一节,或更像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从容不迫地繁衍生息。你不知道他明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却总让人充满期待,并希望产生奇迹。

谢 凯 头像 40×30cm 布面油画 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