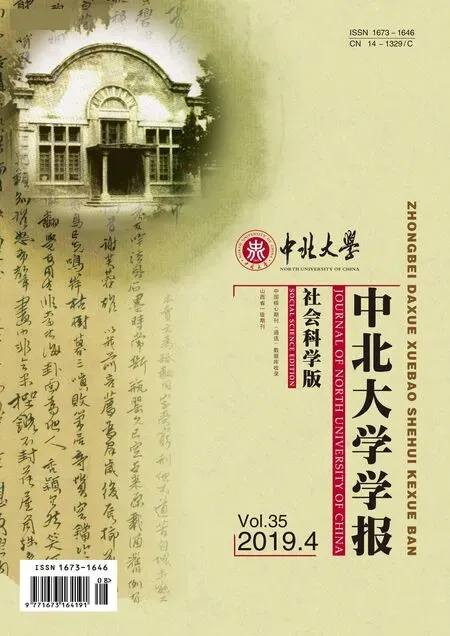杜亚泉中西文化观初探
张慧源
(1.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2.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浙江 杭州 310028)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后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就中西文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场论战最终以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一职渐渐平息下来。此后,杜亚泉被冠以“保守主义”标签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杜亚泉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杜亚泉的文化思想具有非常深邃的内容,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挖掘,更需要我们理性分析。
1 杜亚泉中西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1.1 国际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国内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间的摩擦也日益增加,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欧洲的萧条与衰败,逐渐弱化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心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 探讨、 反思和评价西方文化。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学者们的思考日趋理性和成熟。正是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背景下,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逐渐形成并日臻成熟。
1.2 国内现状
纵观历史,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被逐步打碎,转而主动 “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救国之道。至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向西方学习主要着眼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然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又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此时,社会行为规范、 思想文化十分混乱。这种局面刺激了杜亚泉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将救国的途径转向改造国民、 革新思想文化这一层面。可以说,民初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杜亚泉中西文化观形成的重要背景。
1.3 地区特色
1903年,杜亚泉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和张元济的邀请来到上海,先后任商务编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及《东方杂志》主编,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其思想文化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自《南京条约》签署后便成为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地之一,是当时中西荟萃的思想地。1903年至1932年,在上海生活的这三十年,也正是杜亚泉东西文化观形成与日趋成熟的时期。上海为其提供了现实的、 直观的、 丰富的社会研究环境。
1.4 个人特质
与杜亚泉同时代的文人学者,闻名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的不乏少数。在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如李善兰、 徐寿,但却未能成为时代的思想者; 同时梁启超、 章太炎等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但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则停留在一般常识层面。杜亚泉涉猎领域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备跨学科的思维优势。对于杜亚泉这一思维特质,蔡元培曾评价:“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 个人与社会、 欧化与国粹……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1]7-8糅合多学科的思维特质,可谓是杜亚泉异于同时代多数知识分子的特性,也成为其文化观形成的原因之一。
2 杜亚泉中西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2.1 “化合”东西方文明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一事件引起了杜亚泉思想上的转变。他彻底放弃了之前所学的训诂、 帖括等旧传统知识,“从一个科举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到崇拜西方科学技术的学者”[2]43,这是杜亚泉思想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
1902年,杜亚泉出任浔溪中学校长。开校之时,他在《普通学报》发表了《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一文,杜亚泉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潮流进行了简单评述,进而对当代学生责任进行概述:“第一当研求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足,第二研究固有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之。”[3]12杜亚泉认为,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是西方“形而下之文明”[3]12的显著体现。就物质领域而言,研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弥补中国物质的贫乏具有必要性。就精神方面而言,当时社会上一直流传着“东洋文明,腐败已极,西洋文明,生机勃勃,西优而东劣,西胜而东败”[3]12的观点,对此,杜亚泉认为,中国固有的“形而上之文明”[3]12,由于封建八股的束缚及压迫而出现扭曲。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并未完全表现出来,东方文明的优势也不易被察觉,东西方“形而上之文明”很难判别孰优孰劣。鉴于此,杜亚泉主张在东西文化的互通中深入研究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同时吸纳西方先进文化,使中国文化在不断地改进中重新彰显其魅力。这也是杜亚泉第一次清晰地阐述和表达对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观点,乃其中西文化观的萌芽。
这一时期,杜亚泉对西方文明的阐释并不是很丰富和深刻,他对西方的科学及物质文明总体持较为积极的学习态度,西方文明在其文化观中占据着相对重要的位置。文化建设方案上即表现出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路径。虽然杜亚泉此时的文化理论较为单薄,但较之同时期国内多数改革者停留于学习西方制度的层面,杜亚泉已关注到思想文化层面,这一思想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无疑是可贵的。
2.2 “物质亡国论”与“精神救国论”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人们的生活习俗和社会规范出现大变革,西方的服饰、 娱乐项目、 社会思想等在中国逐渐流行和传播开来。面对社会的大变动,杜亚泉在1913年发表的《精神救国论》一文中将变动的根源归为西洋文明,并指出西洋文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激进人类之竞争,二使人类之物质欲昂进,三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3]150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物质亡国”。西方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自经严复译介传入中国后,国内的竞争氛围日益浓厚,重视物质获得的满足而忽视道德修养。而以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远不能满足人们无限制增长的物质需求,物质的求而不得则往往又使人陷入痛苦之中。所以杜亚泉认为,强弱优劣将会取代是非善恶,精神文明、 道德建设将被淡忘。此外,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致使社会不同人群对物质财富占有量的不同。这种局势的长期发展必然导致富者更富而贫者更贫,社会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的有序发展。
从上可见,杜亚泉对西方文明的看法已从前期对西学的积极向往转变为“物质亡国论”,“从醉心于西方文化、 推崇西方物质文明转变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西融合,提倡精神文明”[2]43。这可谓其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转折。
与此同时,杜亚泉对如何借鉴西方的精神文明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也是其文明调和思想的雏形。首先,杜亚泉坚持: 学习西洋文明要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 乞他人之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3]140。其次,学习西洋文明要考虑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对于传入国的学说要加以辨别和选择,不能实行盲目的“拿来主义”。最后,杜亚泉强调了精神文明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精神救国论”。在他看来,“盖吾人精神上之道德,殆非物质上有形之金钱所能购置也”[3]140。他要把国人从对物质追寻的迷失中抽离出来,重新塑造对精神文化的关照。
这一时期杜亚泉的思想认识逐渐从“物质救国论”向“物质亡国论”转变,进而发展为“精神救国论”。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来看,杜亚泉对于如何借鉴学习西洋文明,如何实现真正救国等问题所提出的思考无疑是超越时代的。他在一战爆发之前就已针对西洋文明的弊端进行了剖析,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仅仅是在一战的后期及战后。这一对西方文化预见性的认识也构成其中西文化观点的重要学理基础。
2.3 东西文明调和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亚泉进一步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标志着杜亚泉中西文化观日臻成熟。
2.3.1 东西文明调和论的理论基础
新文化运动时期,就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学者们有各自不同的观点。陈独秀认为“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4]。强调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要以西方为模板,以西方的发展状态为终极目标,二者是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杜亚泉并不认可。他立足于对中西文明的本质认识,从地理环境差异与民族构成的不同出发,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静的文明”,是自然性存在,西洋社会是“动的文明”,是竞争性存在,二者的差异不是程度之异,而是性质之别。这一思想成为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其中西文化观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经济发展模式与收益来讲,西方通过商业发展所创造的利润比东方农业生产的收益见效快、 利润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发展目的滋生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残酷的优胜劣汰,长此以往,西方人追求之本逐渐演化为取得胜利、 赢得生存; 反观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社会竞争在中国并未发挥深刻的价值,从而造就了国人安分守己的生活态度,且更为关注道德生活。基于这一社会经济模式,西方社会在丰富物质积累时,生活宽裕然而身心忙碌; 东方较西方而言,物质生活虽贫乏,却得以享受安闲的精神生活。“以个人幸福论,丰裕与安闲,孰优孰劣,殊未易定,惟二者不可得兼,而其中常具一平衡调节之理。”[3]317
此外,在经济条件作用下,中西方文明也衍生出更多的差异与调和的可能: 第一,西方社会重人为而中国重自然; 第二,西洋社会的生活为向外的,社会文明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则是向内的,社会上的文明是在个体内省与克己的状态中产生的; 第三,西方社会因竞争而产生纷繁多样的人格化团体,而中国内部则无所谓团体存在; 第四,西方社会重胜利而轻道德,道德只是在团体内部发挥部分作用,在中国,胜利则被视为影响道德建设的障碍; 第五,就社会整体状态而言,西方的常态是战争,东方的常态是和平。
中西文明动静说是杜亚泉东西文明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之一。从东西方文明各自社会发展模式中的差异与困境来看,东西方文明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调剂以求得平衡、 求得发展的内在需求。
杜亚泉文明调和论的另一基础为“接续主义”。“接续主义”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学者佛郎都(1817—1891年)《国家生理学》(PhysiologiederStaaten)一书中,杜亚泉首次将“接续主义”这一概念运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生活。在1914年发表的《接续主义》一文中,杜亚泉对“接续主义”做了界定,即“接续主义是包含过去、 现在、 将来的持续渐进的发展状态”[3]179,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延续性、 连贯性的表现。“接续主义”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接续主义主张的是一种发展的观点,是描述新旧交替的一种变化,不能墨守成规,若“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所用其接续乎”[3]180? 在杜亚泉的文明调和论中,文明调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弊端,实现文化持续性的发展与进步。
杜亚泉认为,发展是建立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盲目搬来他国文化,而将本国文化丢失殆尽,无异于空中楼阁,是不可取的,“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3]180,一个国家固有的文明对于凝结国家力量、 约束国民社会行为、 规范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固有的文明价值理念一旦受到动摇或被打破,社会的正常发展状态将会受到损害,国家的建设也会被破坏。因此,杜亚泉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全盘西化观,力主接纳中国文化的“过去”,并在当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调和、 发展,以实现文化发展新的“未来”,使文化发展的状态不至于中断,进而稳定持久的更新、 延续。
杜亚泉的“接续主义”虽然是以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为例来加以评析与说明的,但是在其东西文明调和论中也彰显着“接续主义”的理论要求,可以说,东西文明调和论正是以“接续主义”为原则和理论指导的。
2.3.2 东西文明调和的主要内容
基于确立东西文明为性质差异的认知,杜亚泉明确否认了陈独秀“打倒孔家店” “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并且在承认中西文明各有利弊的基础上强调东西文明的相互借鉴。杜亚泉在1917年发表的《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明确提出从经济与道德两个维度进行调和。
在杜亚泉看来,“于人类生活有最重要之关系者,一曰经济,二曰道德”[3]358。经济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内化于心的道德标准则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运行提供了保障。中西文化在经济与道德方面如何调和?对此,杜亚泉首先比较分析了东西方各自不同的经济与道德状态。
就经济状态而言,杜亚泉从经济发展水平与目的两方面对东西文明进行了比较。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西方社会“因机械之利用,事物之发明,而日益发达,此固科学之产物,为东洋社会所望尘勿及者也”[3]358; 而对于发展经济的目的,东方社会旨在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达到“充足而无缺乏”的生活状态,西洋社会“则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3]359,其目的已由满足生存性社会资料发展为追求享受性生产资料,而过度关注享受性资料的生产则容易出现生活资料生产的不足,最终会使西方逐步丧失生活资料获取的独立性。如杜亚泉概括,“就经济状态而言,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 西洋社会,则局部的充血症也”[3]359。
就道德状态而言,西方社会的道德建设重视力行,社会慈善团体的不断完善正是这一思想作用下的实践体现,而中国力行的道德实践则较为欠缺; 另一方面,东方社会的道德建设“根本于理性,发于本心之明,以求本心之安,由内出而不由外入”[3]359,以理性为核心的道德建设是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历史上,东西方道德根源有相似之处,但是西方社会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最初的理性已渐渐为后来的权利本位、 意志本位所取代。因而,从精神层面看,“在东洋社会,为精神薄弱,为麻痹状态; 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为狂躁状态”[3]360。
在分析东西方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基础上,杜亚泉进一步提出了东西方文明调和的具体路径,即经济调和与道德调和。
在经济调和层面,杜亚泉期望实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体现。西洋社会在历经国家、 民族之间的战争之后,需要引入东方社会“图全体之平均”的经济发展目标。对于中国经济,杜亚泉承接了前一时期“物质亡国论”与“精神救国论”的观点,更进一步强调西方物质文明引入中国后需要关注其当地适用性、 价值取向与意义等问题。
在道德调和层面,西方社会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糅合作为西方思想源流的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即将崇尚灵魂上帝的克己观念与崇尚自然现实的人力观念进行调和,实现一种新的道德理念。这种理念 “与吾东洋社会之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之观”[3]361。可见,西方社会道德调和的方向即以理性为核心的东方道德模式,而西方社会中“力行”优势则是东方道德建设需要补充和完善的方面。
从杜亚泉对东西方文明的透析及发展方向的设计来看,这一时期杜亚泉对西方的崇拜更进一步弱化,虽亦主张向西方学习力行的道德建设,但其精神文明建设的立足点与方向则是建立在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同时对如何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亦提出了诸多需要防范的要素。
2.4 文明统整说
杜亚泉关于文明分化与统整的思想最早形成于1913年,然而运用此理论阐明自己对东西文明的态度并将其运用至中国文化建设方案中,却呈现于1918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杜亚泉的文化统整说在一战结束之前已初步形成,立足对一战的深刻反思,杜亚泉进一步深化其思想,主张将东西文化调和的重心转移至中国文化上来,以东方文明为主线,统整西方文明。
2.4.1 文明统整说的主要内容
杜亚泉最早在1913年发表的《精神救国论》一文中初步提出有关文明分化与统整的思想。他认为: 事物在发展中,皆是“一方面向分化进行,一方面向统整进行”[3]158。分化是事物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展示事物的个性与特殊性,即所谓“以特殊化之作用而分化”; 统整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使事物在进化发展中保持系统的统一,即“以普遍化之作用统整之”[3]159。
五年后,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杜亚泉具体阐述了文明统整说的内容:
其一,东方文明统整性特征显著。“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 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3]432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延续中,虽学说纷繁,各种思想在不同时代都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来讲,都是对孔孟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其内在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这是中华文明统整性特点的重要表现。
其二,西洋文明以分化为主。西方文化思想的渊源是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的杂糅,而希腊思想本身就是多种思想学派的结合。加之西方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亦是学说林立、 纷繁多样。无论是从西方文化的源流还是从其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其文化分化性特征鲜明,并不具备统整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种特性,无疑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杜亚泉“以文化之‘分化’与‘统整’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在中西会通基础上陶铸中国新文化的文化重建主题”[5]25,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杜亚泉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出路,“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3]434。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将西方优秀文化“统整”其中,自成一种新的文化,它虽以东方文化为主线,但已不完全等同于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同于西方文化,而是两者融合、 统整基础上的创新,这一文明的实践,“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3]435。
2.4.2 文明统整说的理论基础
“分化”与“统整”是事物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方面,失其任意一方都会影响事物的进化,杜亚泉对此亦持肯定态度。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杜亚泉更看重文化的“统整性”,认为在分化的过程中如果失去了“统整”这一大前提,就会发生混乱,导致事物的畸形发展。“分化”与“统整”的相互调剂应是建立在“统整”基础上的调剂。这一观点在杜亚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析的过程中有明显体现。他指出: 在东方文化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统整”占据主流,然而某一历史时期,也出现过百家争鸣、 学说林立、 派别繁多的文化分化状态。这是“有分化而无统整”的畸形的、 矛盾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因发展而失统一的畸变’,是分化偏盛,统整衰微的病变”[6]。可见,杜亚泉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统整性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对期间出现的“分化”状况给予了批评。
2.4.3 文明统整说的后继发展
辛亥革命至1918年间,中国虽然建立了西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但是先后发生了袁世凯复辟、 张勋复辟,社会呈现着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民主共和体制形同虚设。
这一时期,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依旧以调和与统整为主要内容。他强调:“西洋之现代文明,乃不适于新时势,而将失其效用。”[3]498中国固有文明中有许多是值得西方学习的,中国的文明“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成分”[3]499。此外,杜亚泉还指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为未来世界的新的文明贡献力量,在弥补自身文化弊端的同时建构新的社会文明。
因此,与其说杜亚泉的文化主张是探索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不如说是为未来世界新的文明提出了发展方向。在对东西方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差异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杜亚泉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刻。
3 杜亚泉中西文化观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进化论盛行。“这一理论基于由达尔文进化论衍生的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社会进化论,以‘古代或现代’的二分法文化图式,来评判中西文化在人类文化进化序列中的位置。”[7]38根据这一理论,中国文化被置于西方文化之后,而这一理论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变革的理论指导,由此导致学界普遍盲目崇拜西学,以西方的文化发展为取向,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
杜亚泉的中西文明性质差异说,截然不同于当时社会对于中西文化的普遍认识,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一次冲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纵观20世纪初近20年来杜亚泉中西文化观的演变历程,虽然在不同时期,其内容和理论侧重点有所变化,但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理性看待东西文明,强调西方文明中的弊端也需要中国文明中的精华进行救济,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片面追求文化发展进步性、 时代性,无疑是一项重要补充,这实质上是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呼吁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坚持文化自信,突出了文化建设的民族性问题。
其次,杜亚泉理性、 辩证的、 “动”与“静”的东西文明观,在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杜亚泉站在对立面的李大钊后来也用东西文明“静”与“动”的观点来阐释自己的思想,以东洋文明主“静”而西洋文明主“动”为其立论依据。此外,国外学者诸如泰戈尔、 汤因比也深受杜亚泉东西文明“静”与“动”的理论影响。如泰戈尔认为“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8]3。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杜亚泉的文化思想可谓是如出一辙。这一观点也是当前我们认识、 看待世界其他国家文化所应秉持的正确态度。
当然,在分析杜亚泉理论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理论局限性。杜亚泉中西文化观的思想内容立足于对东西文明“静”与“动”的性质区分,为论证这一观点,杜亚泉对中西方社会生活、 社会状态等多角度的不同进行了比对,并将这些差异主要归结为东西方在地理环境方面的不同。这属于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观点。这一思潮在反对宗教神学,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将地理因素视为导致人们的心理及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因素,却是有失偏颇。杜亚泉虽然看到了东西方由于各自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理性分析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 对人们心理、 思想发展的影响,但地理环境终归只是外部的、 非根本的、 非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所以,杜亚泉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存在着漏洞,并非牢固不破。
4 结 语
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性质差异、 东西文明调和论、 文明统整说等,虽然其关于中西文化的理论学说中也存在部分缺陷,且未曾在当时社会产生现实效应,但其文化观点始终立足于本国固有文明,客观理性地分析中西文明,进行调和与救济,始终对文化发展秉持积极的态度,及至今日,依然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宝贵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