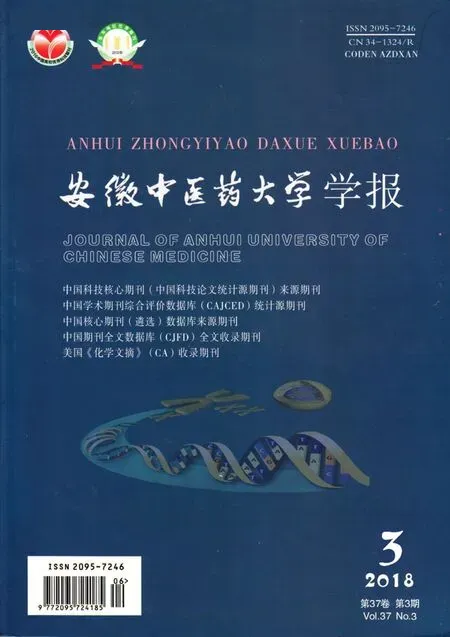李东垣治疗脾胃病用药思路
武子健,赵 炎,付智天,李 娜,金 娟,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李东垣是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其在《脾胃论》中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理论,成为“补土派”的代表人物,并与张元素、刘完素、朱丹溪并称为“金元四大家”[1]。李东垣治疗脾胃病的用药思路对于预防和治疗脾胃病具有重要意义。
1 巧用升阳药
李东垣治疗脾胃亏虚的方剂中,常会使用升麻、柴胡,或二者联用,这与其对脾胃病的核心病机——“阴火”的认识关系密切。李东垣在《脾胃论·饮食劳倦论》中阐述脾胃病的病因为“苟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劳逸过度,而损耗元气”,认为长期饮食失常,过饱过饥,寒热的偏嗜,情志的异常均会影响脾胃功能,出现“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肝,阴火得以乘其土位”的状况。《脾胃论》对“阴火”的定义有二:一为心火,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二为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这里的“心火”可以理解为小肠之火,因心与小肠互为表里,心主火,小肠主热,小肠一旦失常,其泌别清浊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脾胃功能,“相火”伏藏于肾,位于下焦,应该理解为肾中之虚火。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热伤气,少火生气,壮火食气”所言,元气由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滋养,脾胃虚损时元气亏虚,元气与阴火之间动态平衡被打破,则阴火上冲,脾胃充盛时则元气充足,阴火反而潜降,故李东垣所谓之“阴火”皆由脾胃内伤而来[2-3]。脾胃一旦气虚,则脾不升清,胃不降浊,就会出现“清气在下,则生飧泻;浊气在上,则生胀”的病证,且浊气壅遏上焦,日久郁而化热,耗伤阴血,变生他病。
故李东垣用升麻配柴胡,其意在于“下者举之”,取“升阳”之意,引脾胃清气上行于阳道诸经,升发阴阳之气,清气升则浊气自降,基本配伍为补气药(如黄芪、人参、甘草)与升阳药(如柴胡、升麻、葛根)合用。现举例如下:
(1)升阳汤 出自《脾胃论》,治疗肠鸣泄泻。方中重用黄芪补益脾气,陈皮燥湿行气,当归、红花补血活血,补骨脂温脾止泻,甘草调和诸药,升麻、柴胡升发清阳,合而用之,升降相因,恢复脾胃气机而止泻,后世谓之为“升阳止泻”。
(2)升阳散火汤 出自《内外伤辨惑论》,治疗血虚或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致肌热表热,四肢发热,骨髓中热,热如火燎,扪之烙手。方中柴胡升发少阳经之火,升麻、葛根升发阳明经之火,羌活、防风升发太阳经之火,独活升发少阴经之火,取“火郁发之”之意,引诸阳经之火以宣散,人参、甘草补益脾气,芍药滋阴清热,合而用之,疏解脾土之郁阳,使郁热得散,后世谓之“升阳散火”,此方亦体现了李东垣对于引经药的认识。
(3)升阳益胃汤 出自《内外伤辨惑论》,治疗脾胃气虚,湿郁生热,倦怠嗜卧,肢体重痛,口苦舌干,饮食无味,大便不调。方中黄芪、人参、甘草补益脾肺之气,陈皮、半夏、白术苦温燥湿,黄连以泻阴火,茯苓、泽泻淡渗利湿,使湿下行,柴胡、防风、羌活相须为用,一则取辛温发散,引阳气上行,二则取风药胜湿之故,加强利湿作用,二者一升一降,使湿得化,后世谓之“升阳祛湿”[4]。
此外,升阳益胃还体现了李东垣对于“胃气升发”的观点。胃气腐熟水谷精微,通过其蒸腾作用,水谷精微方能游溢布散,上行输送至脾,再经脾的转输布散,上归于肺,肺主清肃而司治节,肺气运行,则水道通调,下输膀胱,如此才能水精四布,外可布散于皮毛,内可灌输于五脏。若胃气下溜而不升,脾亦无所禀也,精微不能输布,则脏腑无以荣养。故治疗胃病,不可一味地使用消导通腑之药,使胃气降之又降,无以升发,延误病情[5]。
2 善用分消药
《素问·痹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李东垣亦指出,饮食不当与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伤饮、伤食虽皆伤于脾胃,但因其病因及病理表现的不同,李东垣提出分而消之的治疗思路[6]。对于伤饮者,李东垣认为“饮者,水也,无形之气也,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饮邪具有扰乱人体气机及损伤肺脏的病理特点,故临床可见喘咳、肿满、水泻等症状。李东垣根据饮邪的特点,提出上下分消的治法,或发汗、利小便,或泻下逐水以化饮邪,其言:“轻则当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解酲汤、五苓散、生姜、半夏、枳实、白术之类是也;如重而蓄积为满者,芫花、大戟、甘遂、牵牛之属利下之,此其治也。”[7]112又如对于长期嗜酒者,李东垣认为“夫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故其多易化热表现为湿热体质,对于长期嗜酒者的治疗提出发汗、利小便最为宜,“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此最妙法也,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分消其湿”[7]48,反对徒用牵牛、大黄之苦寒泻下之药以祛其湿,用之则伤其元气,反下有形阴血,日久阴血愈虚,阴火愈旺,湿热愈重难消。
对于伤食者,李东垣认为“食者,物也,有形之血也”,故伤食日久可以影响气血生化,临床常见疳积、呕吐、痞满、下痢、肠澼等症。李东垣根据伤食的病理特点提出“当分寒热轻重”及“轻则内消,重则除下”的治疗原则。应用消导之品时要详辨所伤之物的寒热性质,对证用药。伤寒物者,用半夏、神曲、干姜、三棱、莪术、巴豆等温药;伤热物者,用川楝子、郁金、黄芩、黄连、大黄等寒药;寒热错杂者,则应寒热并用,且注重寒热之多少、邪气之偏盛。在对消导之药的应用中,李东垣比较推崇其师张元素之枳术丸,并在其基础上加减运用,创橘皮枳术丸、曲蘖枳术丸、半夏枳术丸等方,以内消食积。枳术丸基本用药为白术配枳实,白术苦甘温,补脾胃之元气,除胃中之湿热,利腰脐间血[7]42,枳实味苦寒,泄心下痞闷,消化胃中所伤。此外,以荷叶烧饭为丸,《本草纲目》记载荷叶具有“生发元气,补助脾胃”的功效,增强健脾消痞的作用。枳术丸为张元素在《金匮要略》枳术汤基础上将汤剂改成丸剂,丸者缓也,其作用时间长且能顾护胃气,更适宜于脾胃虚弱之人。枳术丸中白术的用量为克化消导之枳实的两倍,以增强补益脾胃的功效,克化有形之食积,体现“养正积自除”的治疗观念[8-9]。
3 以吐代消,畅达郁木
李东垣认为,伤食与肝气郁滞密切相关,故亦可用吐法治之,取“木郁达之”之意,郁者,结滞壅塞而不通也;达者,畅达也[9]。李东垣用吐法疏利肝气治疗伤食,其意在于“伤食太阴有形之物,窒塞于胸中,克制厥阴木气伏潜于下,不得舒伸于上,故以吐伸之,以舒畅阳和风木之气也”[7]50,即“在上者,因而越之”。“木郁达之”体现了李东垣对于肝肺气机关系的认识,即“左肝右肺”,肝主东方,为气化之始也,肺主西方,为气化之终也,二者如环无端,生生不息[10],故饮食不节可伤及脾气,母病及子,影响肺金肃降,肺气郁闭于上,影响肝气升发,可致木郁,故以吐伸之,乃泻金以助木也。这种认识启发了后世医家从肝肺论治脾胃病的治疗思路[11],如肝气郁滞,气机失常,可致中焦壅遏,影响脾胃升降,出现腹痛、腹胀、不思饮食等症,肺气上逆失于肃降,易引胃气上逆,出现恶心、呕吐等症,肝肺功能失常皆可致脾胃亏虚,故治疗脾胃虚损时可酌加黄芪、人参、山药等补肺气药物,或木香、香附、佛手等疏肝气药物。而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李东垣用瓜蒂散以畅达气机治疗伤食,该方出自《伤寒论》,主治痰涎宿食,壅滞胸脘等证。瓜蒂味苦涌泄,性寒泄热,具有涌吐热痰、宿食之功,赤小豆味酸性泄,合而用之酸苦涌泄,又佐以香豆豉,宣开胸脘郁结,调畅气机。
4 顺四时以用药
李东垣治疗脾胃病的用药特点之一就是顺应四时,酌情加减变化,其根据四时升降浮沉的规律提出了“春时有疾,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秋月有疾加温气药,冬月有疾加大热药,是不绝生化之源也”的总纲[7]107,《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浊气在阳,乱于胸中,则满闭塞,大便不通。夏月宜少加酒洗黄柏大苦寒之味,冬月宜加吴茱萸大辛苦热之药以从权,乃随时用药,以泄浊气之下降也”[7]80-81,又如“夏月腹痛尤宜加白芍,如冬月胃痛,不可用芍药,盖大寒之性也。只加干姜二分,或加半夏五七分,以生姜少许制之”[7]80-81。简而言之,李东垣四时加减用药为春季宜用荆芥、菊花、桑叶、薄荷等风药以疏风邪,夏季宜用黄芩、黄连、知母等寒药以清火邪,秋季宜用苏叶、杏仁、桔梗、沙参等温润气分药以宣燥邪,冬月宜用吴茱萸、草豆蔻、白豆蔻等热药以散寒邪[12]。
5 注重酒制之法
李东垣对于药物的炮制也很有研究,其治疗脾胃病的很多药都用酒制,“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甘苦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肾肝之下,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自偶而奇,奇而至偶者也”,即用酒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东垣先生药物心法》亦指出,李东垣用酒制药物的目的是增强药物升散之力、引药由阳入阴及预防苦寒药物损伤胃气等[13]。
6 小结
中医学认为,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与人体正气盈亏息息相关,并总结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治疗经验。作为“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李东垣对于脾胃病的治疗亦有一套独特的用药思路,如对于脾虚下陷者,提出利用升阳药,如升麻、柴胡提升脾气,以消阴火,代表方为补中益气汤;对于饮食积滞者,提出分消论治,并根据所伤之物的寒热,酌情运用消导之品;通过运用“以吐代消”之法治疗食积,提出了从肝肺气机升降来调理脾胃的治疗大法;根据四时气候特点,提出不同时令运用风药、寒药、温润气分药以及热药调理脾胃;强调药物酒制对于治疗脾胃病的重要性。李东垣治疗脾胃病的用药思路对于指导临床遣方用药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玉清.壬辰之变对李东垣身份、地位及学术思想的影响[J].医学与哲学,2017,38(3A):89-92.
[2] 高青,王华男,吴亚鹏,等.“阴火论”刍议[J].国医论坛,2017,32(3):62-63.
[3] 苏麒麟,郑洪新.李东垣“阴火论”之理论内涵[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12-14.
[4] 唐汉庆.李东垣升脾阳诸法运用钩玄[J].辽宁中医杂志,2010,37(10):1881-1883.
[5] 许勇镇,阮诗玮,丘余良.李东垣“胃气升发”论析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7,23(7):898-900.
[6] 胡冰冰,岳仁宋,周建龙.李东垣伤饮伤食学术思想探析[J].现代中医药,2016,36(6):89-91.
[7] 李东垣.李东垣医学全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8] 陈靓,陈东梅,任北大,等.张元素“养正积自除”的内涵及其临床应用[J].环球中医药,2016,9(4):441-442.
[9] 刘统治,金国娥.浅谈李东垣枳术丸及现代临床运用[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5,27(3):357-359.
[10] 赵心华,王庆其,李海峰.河洛理数与《黄帝内经》[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4):195-197,219.
[11] 林辉辉,刘中勇.从肝肺气机升降论治脾胃病[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27(3):12-13,16.
[12] 高雅婷,包素珍.李杲四时用药经验探析[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3):86-87.
[13] 金国娥,刘统治,李董男.论《内外伤辨惑论》用药炮制内涵[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7,23(3):39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