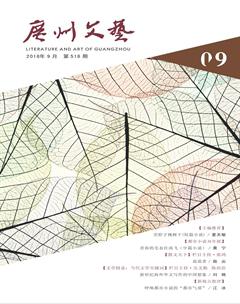人与食物,都逃不出“颜值即正义”
郭珊
梁实秋在《春来忆广州》一文中称赞广州“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人热情,花也热情,院里墙头,四季有花,冬天窗外结木瓜。
岭南的瘴雨蛮烟是历代流放者的活炼狱,却是草木鸟兽的游乐园。除了一年到头叶茂花繁,还有一个好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有吃不完的瓜果。民谚有曰:“三月杨梅四月李,五月枇杷六月荔,七月龙眼八月柿,九月柚子十月桔。”这是极可爱的两广地区的《 豳风·七月》,一个“吃”字春秋不绝。
广州又是南中国贸易要津,洋货特多,水果档开到成行成市,百米以内三四家,通街兜揽声靡沸终日。逢上榴莲、菠萝蜜上市的时节,各间档口异香冲天,浓到设坛斗法的架势。一间寻常的菜市铺头,出售的品种之多,竟也壮观如同“万国博览会”,华夷纷糅,近至州县土产,远至欧美南洋。
最喜歡公私会晤谈至中途,有人将什锦果盘往面前一送:“嚟,食啲生果再倾喇!”于是,众人哔哔啵啵,剥皮吐核,佐些八卦闲话,眨眼间,盘中花果山已是颓圮玉碎。衬在一叠红头文书旁边,犹如舌上的燕乐丝竹,专克“案牍之劳形”,食落下肚,是实实在在的“腹诽”,此风大快我心。
广州人若写“浮生六记”,必定有一篇讲“贪鲜”之法——去郊区果园现摘现吃,相当于在海滨白灼现捞虾蟹。岭南所谓“十大佳果”之中,首推靓绝南陲的荔枝和龙眼,好到未食过从化与增城的荔枝、石硖与储良的龙眼,便不算尝过此二物。
周末随朋友去从化,时间上很不凑巧。今年是荔枝小年,价格翻倍不说,下市也匆遽。七月的骄阳下一片“绿暗红稀”, 荔枝是寻不着了,龙眼亦未成气候,很不情愿地背着人,半掖着并不殷实的串串黄丸。
卖水果的女人带我们走到村子里去,两三步爬上自家屋后的龙眼树,伸长手臂去剪早熟的果子,扯得哗哗响。 树是老树,不知年岁,大约两层楼高。我们在树下接住就吃,像坐在一所绿色的草房子里,抬头便是枝叶映日,嵌着正午晴天的碎片。有风过处,跳出一排光点,似有银色的细泉滴在碧石之上,百叠漪漪。一边吃,一边转来转去地看乡下的瓦房、荒草、菜园、河渠,瘦狗和肥鸡——这里竟然这样静,没有蝉声。
几个人合买了十斤龙眼,肉质虽尚欠丰厚,但已足够爽口、甜润。尝过便知,用硫磺蒸熏、进行过保鲜处理的货色,最多只能算是龙眼的标本。又买了两斤最尾的糯米糍荔枝,有玫瑰味,可惜美人迟暮,核又大,算不得上品。再问有无火龙果,女人摆摆手:“冇咯,仲有黄皮,呢个时候啱啱好,买啲啦!”然而,推来推去,谁都没有买的意思。
朋友笑话我:“居然有你不爱吃的水果?”我嘿嘿一笑。食色乃大俗,向来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除了荔枝与龙眼,金柚、皇帝柑、鹰嘴桃、沙糖桔、糖心菠萝、三华李等土产也都不俗,然而若细细计较,其中定然有“厚此”,有“薄彼”,何必违心强要“雨露均沾”?
至于黄皮,是百果园里的冷门,鲜为岭北所知悉。记得初次在粤西乡村吃黄皮,入口一股激酸,溅出一圈辣星子,连连咋舌。后来才知买的是人家用来做蜜饯的酸黄皮。再后来,尝过用于鲜食的鸡心甜黄皮,记得最牢的还是那股辛凉不驯的山野苦香。食后喉咙甘凉,一气到底,难怪别名又唤作“正气果”。
黄皮说是果,其实更近乎药。相关记载多见于《齐民要术》《本草求原》《岭南采药录》等草木、医典、方志,叶、肉、籽均可入药,有消食降火,疏风解表,除痰行气,止咳平喘等多般用途。诗词歌赋里,只找到明代董传策的一首《噉黄皮果》: “碧树历历金弹垂,膏凝甘露嚼来奇。”民国才女凌叔华也在文章里写过黄皮,但止于采摘的场景,“采的人骑在树枝上,雨点似的掉下那些果子来”,似不曾单独为之着墨。
不入诗文而入药典,是一件略显尴尬的事。好比评价一个女人有淑德而无风姿。“黄皮”这名字,本就形象到省事的地步,等于不客气地唤人“黄脸婆”,不巧又偏与尤物荔枝搭在一起——民谚有云:“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说的是荔枝的糖分和能量高,而黄皮帮助消化。一个是红缯紫绡水晶瓤,一个则是麻子脸皮鹌鹑卵;一个是馥郁而汁蜜,另一个则是味质且带涩——与天生热毒、照样无限宠爱于一身的大明星荔枝比起来,黄皮委实像是一个有些寒素的甘草角色,纵有“金牌戏骨万灵丹”的口碑,也少人追捧。
同人不同命,同遮(伞)不同柄。人与物,都逃不出一句“颜值(好吃)即正义”。对于我这种巴不得“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人来说,若非吃到胃脘饱胀,确需黄皮顺气、除滞,或者喉咙不舒爽,难得主动惠顾一次,完全符合民间所说的 “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
说到钟无艳(复姓钟离名春,相传为齐国无盐邑人,又名无盐女),最初的版本也即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上的记述,实在是一个理想的童话,我一向很不以为然——钟无艳是著名的才女,却因貌丑四十未嫁,丑到《列女传》一连用了六句二十四字形容其外表的惊世骇俗,从身材、五官、头发到皮肤,一无是处。无艳见齐宣王日夜笙歌,朝纲崩弛,遂冒死请见,当众历数齐国的内忧外患,骂了一通宣王的“不作为”,结果反被立为王后。宣王从此罢退女乐,励精图治,终令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这种教科书上才会有的圣贤故事,大约连看戏的群众也很不满意,故而后世戏文演义里就冒出一个“两面派”的齐宣王,以及一个天下女人亘古不变的后院假想敌——国家有难之际,找贤能的钟王后求救;太平无事之日,宠幸美貌的妃子夏迎春。
传说中的钟无艳是个卧龙先生式的人物,既会外交智斗,亦晓领兵打仗,鞠躬尽瘁,值得拥有一个承天辅圣端懿庄肃之类的谥号。美化是应当的,因这丑娘娘的品行可以用来教育子孙,况且谁都不必真的与她可怕的容颜、真实的脾气朝夕相对。中国古代女性向来在牌坊和戏台上地位最高——总之,往往都不是在生之时,虚幻的赞美总是格外隆重的,算是一点可怜的补偿。特别是有些一时的“受宠”,比直接废黜还要可怜。
中国人在吃上面的智慧和做戏一样,真是深不可测。据说新鲜黄皮要连皮带肉并核一起放在口中嚼碎、吞下最好,但我不记得见过身边有谁是这样受刑般的吃法。尤其酸黄皮是“生不如死”的代表——晒干后用蜂蜜甘草来腌渍,能去除涩苦,添加川贝更能增进疗效。好比角色,可以任着人的需求和爱好予以加工。装在塑料罐里,一瓶二三十蚊,销路大开,这大概是最喜闻乐见的归宿了。
《本草求原》上说黄皮果“多食动火,发疮节”。印象中亦从未听说有谁痴迷黄皮吃到生疮的地步,起码比大吃荔枝而进医院的要少得多吧。
这一次因为寻荔枝而不遇,相逢待来年,望着一地酸黑的荔枝过季落果,竟可惜到想起李商隐的《板桥晓别》来:“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悻悻之下,索性连黄皮也不要了。反正还有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