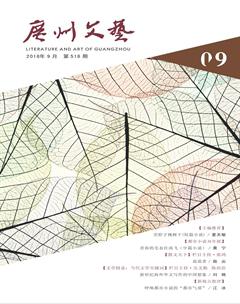新诗眼 异体十四行(组诗)
张桃洲
晚归的鸽子
容许我回到最初的花园里去
在深夜悄然滑过灌木的阴影
然后,一声不响隐向它们
遍地的裙裾后面
为什么不让我暗自悲哀
并且深深惋惜这些纷乱的时光
因为它们,春天早已走远
培养起离群索居的习惯
或者重新审视冷漠的灌木丛吧
还有它们眼里熟睡的月亮
作为归者,我必须轻言细语
避免惊扰屏风挡开的灯萤
它们如一簇簇被钉落的星辰
在风中敲击幽暗的夜之鼓
我不懂得鸽子
我不懂得鸽子
那宛转而来的温和气息
在阴郁的天气里 鸽子
占据了背景上剩余的天空
我不了解这座建筑的脾性
我从不认识这些花园
它们蜿蜒的草丛间
鸽子的花灿然开放
我从未与鸽子交谈
它的声音邻近我的露台
它的红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从不敢正视鸽子的身影
如何纤细着步伐
从后院的空地悄悄移走
壁灯敞开
壁灯敞开。让所有的阴影走近
让所有与我疏远的彗星
走近并让我结识
让那些在水上静止的植物
在九月天空呈云状的飞禽走兽
包括众多飘舞的精灵
走近。我渴望置身它们中间
被它们夸张的声音包围
四面的声音,是为靠近我而涌来么
让描述距离的语言消失
让那些可以成为先哲的石垒
可以并肩而行的山峦
与我咫尺之遥。当我移动一步
壁灯敞开让所有的阴影走近
群山之间
在低矮的群山间俯看
这些石头。拨开深秋的荆披
大小成队的石头走下山来
阵雨覆盖下的石头
从山顶到横亘的那片山坡
石头们滚动着,漫山遍野
它们湿润而光亮
使那些船只和舷边的桅杆
鲜艳。使掀起的水波
轻轻变得颜色柔和
这些坚硬清脆的石头
在群山之间声势浩大
随潮水一直延伸到
你脚下的沙滩
有时候
有时候我让江水的影子走进屋来
无所牵挂的江水的影子
透过窗子它们满怀着热忱
奔放地弥漫进来
我看见汹涌不已的江水
突奔于堤岸的狂暴的浪涛
它们越过峰峦的声音
静谧而稠集的声音敲碎了我的窗子
有时候江水的影子浓重地走近
有时候它们滞留于崖壁的顶端
有时候我走出去眺望阳光
透明的阳光的影子
在沙滩上跳跃的阳光的影子
有时候是一种飞鸟。一只飞鸟的影子
秋 天
那么多人影涌入街市
秋天,我看见更多的树荫
卷走道路的颜色以及
弯曲的道路本身
以及厌倦。我看见更多天空
低沉地压迫着楼群的烟囱
想象的大鸟渐渐消隐
天使离此时不是太远而是太近
但叫卖声嘹亮如歌。
那么多转身,那么多道别
“今晚你将去哪儿销魂?”
渺渺之音抽象成浮动的烟尘
秋天。雨终于成为雨点
成为渗进我皮肤的黑暗
地铁站
午夜之后,四月的雨水
更加明晰。越过灯光的投影
掘土机的巨手从半空径直垂落
仿佛在记忆深处打捞一枚
并不存在的果核。
沿着中山大道的宽阔街面一路
往南,地铁动工的消息
迅速挤进了雨水四散的街衢
连同唇膏、隆胸术和永远的前卫
将市民的日常压缩成一份杂乱的晚报
而我是否需要在这里,在一处
尚未竣工的地铁站中转?
这样想着,公交车已绕过新街口
闯入了一片昏黄的灯火
书 店
此刻书店关闭。文字的声音戛然而止
柜台的左侧,忧郁的老板开始遣返店员
他的神色如此凝重,仿佛一本中世纪诗集
閃耀着幽暗的光焰
所有的细节被尘封。那些店员的青春身影
在墙面上显得犹豫不决
她们不再偷闲去阅读晚报上的爱情
所有的隐秘被释放,被赶到空旷的大街
现在,仅剩下一根不知所往的电话线
握在手中。习惯了摩挲书皮的指尖
把这根柔软的丝线从左至右推向黯淡的
过去
在手中,纸张在沉睡,生活需要重新开始
那是傍晚时分,我路过书店
书店的浅褐色门刚刚发出轻微的“吱呀”
鞋 店
——节日片断之一
这里摆放着城市的木器
那里聚集了一条小街必不可少的噪音
人群的阴影推动梧桐树
一寸,一寸,慢慢改变马路的方向
而她挑选鞋子的姿势充满这个上午。
她漫不经心,灵巧的目光
在鞋架上扫来扫去。试完一双
又把脚伸向另外一双,仿佛
有意考验所有旁观者的耐心
而那位陪伴她的高大男人,她的父亲
已立在路边,叉腰去看街景
微笑着露出困惑的表情
那细碎的卷发映照这个上午。她大概三岁
或四岁。年龄并不重要——隔着玻璃窗
我想
雪天的记忆
独行雪中——多么伤感的主题
在黄昏,“在山的那边……”
北方某处偏僻的寓所,一个青年
倚着窗子写下平生第一行诗
那年冬天的场景闪现又消失
古老的东平巷也已经远去
雪越下越大几乎埋没那棵小树
雪在纸上铺展成另一类主题
独行雪中。在身旁
孩子们好像晚归的鸟雀一闪而过
轻盈如往事掠过眉际
只留下树林里那些摇晃的身影
谁曾经独自穿越那片树林
在雪天,祈求一首诗的诞生
烤土豆
——为像的十周岁而作
到北方后,他爱上了吃土豆
常常费力地搬出烤箱
边操作边喃喃自语:“烤土豆喽。”
烤箱门打开的刹那果然有一股清香
土豆真的有那么多种吃法?
或许,它们的形状隐藏着他这个年纪
特有的混沌:狡黠的童心
与尚未到来的圆熟。它们的排列
就如同一串摇号得出的数字
其中一个恰好是我们到北方的时间
“烤土豆”也能成就一顿美餐?
看起来确实如此:那少年
已把记忆的愁绪搬回了南方
把习性的味觉留在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