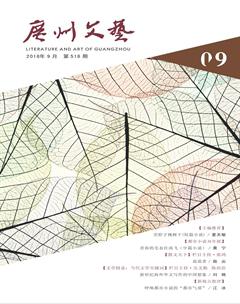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的中国想象
刘艳
海外华文文学被视为是从“台港文学热”引发出来的,而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被学者们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台港文学热及其研究,到世界华文文学,再到海外华文文学,其间夹杂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等的争论,近年又出现了新的概念范畴“华语语系文学”。2001年,张错提出的“华文文学区域”,可视为“华语语系文学”前身,2004年,他又提出“华语圈”的概念。史书美被目为最早明确提出“华语语系文学”并大力提倡者,“华语语系文学宣言”则被认为是王德威的杰作《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王德威近年成为最为积极和活跃宣扬华语语系文学的学者,他在2017年6月7日,由腾讯文化、京东图书、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上,作为首位致敬对象,他的发言《何为中国?何为华语语系文学》①当中,还提出了“华夷风”的问题……华语语系文学的探讨,其实是为扩充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刘登翰先生申述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并且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是移民者的文学。”他还进一步补充这一概念:一是凡使用华文(汉语)创作的文学都是华文文学,二是专指中国(包括台港澳)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他说:“在我看来,所谓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中国海外移民者及其后裔的文学。移民和移民的生存状态,应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背景和起点。他们在异国土地和异域文化环境之中谋生,面临着对移入国及其文化的适应和认同,他们携带的中华文化也在融摄异质文化时发生变异,这些都或显或隐地融入在他们的文学书写,形成新的书写传统。而华人、华族、华族文化、华人多元跨国的离散生存和中华文化环球性的网状散存结构、海外华人的世界体验与母国回眸、移民的双重经验与跨域书写……”,都应该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命题②。
所以,在吸收史书美、王德威意图以“华语语系文学”扩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视阈的内容外,我们目前还是倾向于使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和范畴。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较之此前,发生了很多变化,表现出由离散生存体验更多地向一种迁移之后错位归属的文化价值观和生存体验的嬗变,也表现出双重经验和跨域书写里异域生活的书写在减少,有关中国想象——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叙事”的小说叙事方法在增加和提升。
王德威在他那篇有名的演讲的最后,这样宣告:“我们看到在全球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语境里面,有不同的作家以汉语来书写,来传播他们对于华文和华语的想象,无论是在法国的高行健,还是早就过世了的来自台湾的三毛。但是三毛的写作千万别忘了,她是从非洲开始的,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展开了华语创作。来自于台湾的郭松棻,或者是漂流到海外的张爱玲、白先勇。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黎紫书,香港的董启章,台湾的朱天文,现在在德国的从上海来的作家严歌苓,或者是在美国波士顿的哈金,这些作家以不同的场域,甚至实验着不同的语言,来想象着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华夷风这个词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怎么样扩充我们对华语世界的憧憬,或者是对于华语世界铭刻的开始,谢谢大家的聆听。”①——我们在这里,还是借用王德威的说法,看看在海外的严歌苓、张翎、陈河等海外作家,如何在新世纪以他们的写作来想象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还有他们心目中中国的现实。
一、离散—迁移—错位归属
要想清晰地了解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本文主要分析第一代移民作家)是如何想象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想象他们心目中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恐怕要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命题乃至核心命题有所了解。追根溯源,才能了解变化的其来有自和理出一个更为清晰的脉络。
刘登翰先生指出,相对国内作家,海外华文作家拥有从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这是他们独具的文化优势。他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作家,都有一段难忘的国内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这对于他们后来在异域的文学书写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另一份异邦的人生经历,不是那种由参观访问得来的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真正融入自己血肉和心灵的真实人生的体验。国内的人生经验和海外的人生经验在移民作家那里,形成了一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既互相对视又互相解读的具有互文性的矛盾统一体。由此也构成了他们观察、思考和创作的一种“复眼”式的双重视域。双重人生经验构成了一个互相交叉的文化视角,形成一个互有比较的新的思考空间和书写空间。由此他提出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是一种跨域的书写,不仅是地理上的“跨域”,还是国家的“跨域”、民族的“跨域”和文化的“跨域”,因而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跨域”。由“跨域”,刘登翰也提出了海外华文写作的一个核心命题“离散”——“跨域”是一种飘离,从母体向外的离散。他认为,中国的海外移民远离自己的母土,飘散在世界各地,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的族群,或者说是一个“跨域”的族群。离散或者“跨域”,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既有政治的原因,但更多恐怕還是经济和文化的原因。但将一个跨越全球的离散的族群整合起来,成为所谓的“离散的聚合”,其联结的纽带主要是文化——中华文化①。
不只是刘登翰先生的阐析和申说,“离散”是海外华文写作的一个核心文学命题,也是作家一种最为基本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的状态。在刘登翰看来,“跨域”产生差异,也产生冲突,当然也带来融通和共存。华人移民必须使自己的族姓文化逐渐适应所居国的异文化环境,在历经了不适和冲突之后,也带来自己族姓文化和所居国文化的共存和融变;而所居国的文化也必须从对移民所携入的文化中培养一种接纳不同文化的襟怀和气度(笔者注:尽管这有点我们单方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二者在这种彼此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中,既产生冲突,也走向和谐(我个人认为走向和谐之感,可能更多来自于华人移民主体的主动乃至被迫适应),其过程是互相包容与统摄。在他看来,“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主题,就常常表现出这种不同文化从冲突、排斥到包容和融摄的转换”。“早期华文作家大量存在的对故国文化和人生境遇的怀思,即所谓怀乡思归的主题,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移民对异国文化和生存环境的不适应和难以被接纳的困囿;而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主题更多地转向对所居国生存环境和本土文化的融入和认同,正是华人在海外生存这一历史变化的文学体现。”②
进一步可以补充的是,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主题,除了更多地转向对所居国生存环境和本土文化的融入和认同,还有他们把笔触从海外异域生活的书写,更多地转向了他们的中国想象——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中国历史和现实。同样是“离散”的文学命题,与新世纪之前相比,在新世纪还是有着嬗变乃至较大变化的。我在以前的研究当中也分析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离散”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理论批评界日渐升温,华文文学研究界也有着不少对于“离散”问题的思考。离散(diaspora),来源于希腊语,原来是指“古代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后的大流散”,《圣经·新约》中指“不住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籍基督徒”,近代以来尤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是“移民社群”的总称③。当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的时候,它意指这样的历史文化内涵——古犹太人被迫和被动承受着“离散”的历史境遇时,精神上处于失去家园和文化根基而漂泊无依的状态。当这个词的首字母小写的时候,它泛指一个民族国家分散和流布到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族群和文化中的现象。“离散”几乎是海外华文写作的永恒命题。但是,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其变化也是明显的,从之前的“无根的一代”、无根与迷失、怀乡思归主题和难以融入所居国文化的冲突和不适,到虽经历了“连根拔起”后重新“植根”的过程,到更能融入所居国文化或者说有着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融摄和多元整合的倾向。
中国的海外移民最早可远溯到唐宋乃至更早。但在刘登翰先生看来,20世纪50到70年代,是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三个时期,以留学生为主,主要是台湾香港的留学生赴美。他们最初是随同父辈挟裹在政治漩涡中由大陆来到台湾的青年,对台湾失望,大陆又回不去。1949年前后,国民党官兵和一些文化人士携家眷由大陆赴台,形成独特的“眷村”文化。而“眷村”的后代青年中许多人都把赴美留美当作最高的理想与追求。后来成为“无根的一代”代名词的牟天磊,是於梨华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中的主人公。他说:“在那边的时候我想回来,觉得为了和亲人在一起,为了回到自己成长起来的地方。”“可是回来之后,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样叫我不舍得走,最苦的,回来之后,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客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 ①“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地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与你无关。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前途、学校前途,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的个人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②——这其实是那个时段所有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心声。这种无根与迷失,白先勇將其概括为怀念“失落的王国”的“永远的迷失者”。创作于1970年的旅美台湾女作家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堪称“离散”书写的典范之作,白先勇也认为它是表达“迷失的中国人”症候的一个典型范例。这部作品最为深入并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迷失的中国人的身份困惑。20世纪80年代中期,查建英以中篇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对“边缘人”的文化现象作出形象阐释。查建英本人曾对“边缘人”作了解释:“这类人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经验到了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和谐。”③
漂泊无根、难以真正融入所居国文化,在老一代移民作家像於梨华的作品当中,多有展现,像她的长篇小说《考验》(1974)与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所描写的就是华人知识分子在西方学界的苦苦奋争和所面对的生存困境。《考验》将笔触深入美国学界和重重帷幕下的美国文化,小说对华人知识分子与西方同行之间的隔阂、华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隔阂、华人父母与他们在美国生养的孩子之间的隔阂以及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甚至即便沟通也很难相互理解的状况,展露无遗。《一个天使的沉沦》(台湾九歌出版社1996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更是将“离散”中东西方文化遭遇时的冲突与不适应,推向了极致——东西方文化相遇下父母的看护和教育失效,导致罗心玫被姑爹猥亵强奸、成年后她愤而杀死了姑爹的悲剧故事。王鼎钧这样评价:“依於梨华的诠释,华裔子女的歧途,似乎是他们从中国传统和美国方式中分别取出并不适当的一部分来做了最坏的组合”④。
这种离散之感和“离散”文学命题,从来也没有消逝过,严歌苓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了大量表现异域生活的短篇小说,也是深刻表现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时的冲突与隔阂。长篇小说也有涉及,像写作老移民历史并塑造了“地母”形象的长篇小说《扶桑》(1996),19世纪末的旧金山,扶桑异邦卖笑,即使遭到轮奸时,她也没有反抗,只是奋力用牙咬掉施暴者胸前的一枚纽扣,谜一样收集到一个盒子里,却把克里斯那枚藏于发髻,同时掩藏起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宥。用王德威的话说是“古老中国里解决不了的男女问题,到了新大陆更添复杂面向”。长篇小说《人寰》(1998),是“我”爸爸和叔叔贺一骑的故事,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中国故事”和“我”与舒茨教授之间的“美国故事”的一种拼接和形成参差的叙事张力——小说所采用的是以向心理医生寻求治疗的“Talk out”方式作为小说叙事形式,向心理医生叙说自己在中国的成长叙事和移民后的“我”在美与年长的美国教授舒茨之间的恋情故事。相对于於梨华等前辈作家的“离散”书写,我们感受到的是主人公更加能够落地所居国文化,一种很深刻和内在的融摄和融通多元文化的努力。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2001),虽然初版封底荐语里有“……迫使一些漂泊海外的游子在作无出路的挣扎”,但这个美国外交官和中国女留学生之间的故事,在我看来是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不同中的融通,甚至是对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这里拥有一种文化从容和自信有所表现,严歌苓自言其本意是 “外交官与女留学生之间的爱情,因为‘拯救就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的,是不被享受的,是被思想毒化的”,意指西方对东方拯救的不可能与不被享受——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写作这里很珍贵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近乎有着我们东方的文化自信的东西——我们不能认为它只是严歌苓的个性使然,这背后其实是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的多种因素合力的一个结果。
我始终把《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看作严歌苓尝试沟通东西方文化、作多元文化融摄和整合最为有力的一个代表作。这是一个白种男人购买华人女性作为代孕母亲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购买女体的代孕行为在美国迄今都是很有市场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白人男性亚当因为是同性恋,他想购买母体来获得后代,华人女性伊娃“我”刚刚被前夫抛弃、离婚,要通过出卖自己来养活自己。在这个代孕买卖关系之上,揭示的却是多重的文化意蕴——东方与西方,同性恋与异性恋等,以及多层的人性心理因素。菲比患病乃至夭折,隐喻了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的人,在人性基础上彼此沟通和一种普遍意义的生存困境。说明严歌苓对写“迁移”之后“离散”的思考,已经不是一个“隔阂”问题的思考,也已不是单纯地描绘一种碰撞和激烈冲突,她渐渐能够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和写作姿态。
移居美国的生活在严歌苓那里,“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迁移问题对严歌苓而言是:“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而“伤痛也好,慰藉也罢,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①。在她看来:“‘Displacement意为‘迁移,对于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之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②她有着对于自於梨华、聂华苓那里就纠缠身心的流亡与无所归属之感的充分理解。她举了纳博科夫的例子:“纳博科夫十九岁离开俄国之后,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处房产。因为没有一座房屋感觉上像他少年时的家园。既然没有一处能完成他感情上的‘家的概念,没有一处能真正给他归属感,他便是处处的归而不属了。”①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严歌苓“私自给‘Displacemen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它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②小说《花儿与少年》(2004),可能是严歌苓将移民“迁移”之后的“错位归属”心态和状态表达得最为充分的一个故事了。十年前的晚江,原本有着平常却不失温馨的家庭生活,偶遇回国选妻的刘先生(老瀚夫瑞),丈夫得知后主动提议与妻子离婚,理由是“连一套把老婆孩子装进去的单元房都混不上”,连离婚都颇有些戏谑化意味“托了一串熟人,离婚手续竟在一礼拜之内就办妥了”……而故事的背后,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素都隐约可见。晚江与洪敏的相恋、没有婚房、两人所在歌舞团的不景气、两人的“下海”开餐馆与时装店,乃至两次分房的落空,等等,活脱脱就是中国社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缩影——这是严歌苓心目中的“中国想象”,更是包含她对自己出国前20世纪80年代的真切记忆。晚江嫁给了年纪长自己30岁的美国退休律师老瀚夫瑞,十年来,孩子一个个来到美国,丈夫也来了,这都是晚江努力经营的结果,在与瀚夫瑞、瀚夫瑞前妻留下的苏、瀚夫瑞与前妻所生路易(严歌苓在小说中称路易“血统含混、身份不明”)、小女儿仁仁一起生活的家庭里面,她一直貌合神离地思量与计划着如何与前夫、与儿子九华重聚重温往日幸福生活,她不仅想方设法在经济上资助他们,甚至还要时时跟瀚夫瑞玩“猫捉老鼠”般的游戏——与前夫洪敏与儿子九华联系,电话也好见面也罢,都要费心设计与谋划。只是,这是个危险的游戏,是一种“危险的双重生活”③。
纳博科夫可能是严歌苓、陈河等很多新移民作家对之都能感到彼此身心相通的一个作家了,原因何在?那种可以彼此心灵相通的离散、迁移与错位归属之感。陈河说过:“远离祖国在海外写作的作家名单列起来会很长,外國的、中国的都有,我心中最优秀的是那个俄国人纳博科夫。”“有意思的是,远在我出国之前的八十年代,我就对这些远离祖国的作家有着特别的喜爱。也许是他们的作品中对于祖国的深沉的忧伤和思念打动了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读纳博科夫。”④陈河在新世纪的作品,也多涉及海外生活素材和题材,比如《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的阿尔巴尼亚、《女孩与三文鱼》中的加拿大,《米罗山营地》《沙捞越战事》中写作和还原的是马来西亚的历史故事。这些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想象”,但更多呈现新移民作家在错位归属之后的一种写作上的从容和自信。像写作《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就在繁杂的素材里沟通了历史、战争、爱、死亡等命题,沟通了多种元素,作家把三个时间层面——现在进行的时间,七十年代电影流行的时间,四十年代德国占领下的时间——“要把这三个时间层面统一到小说里面,必须要打通一条时间的通道”①。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小说写法被找到和尝试后,陈河后来斩获中山文学奖唯一大奖(2016)的长篇《甲骨时光》中,对诗性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他能够非常自如地将小说叙事的时光隧道打通,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目前来看创作上更为丰赡的张翎,与陈河一样,也是温州籍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杰出的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其早期的《望月》(1999)、《交错的彼岸》(1999)、《邮购新娘》(2004)等,都有着对移民历史和迁移之后两种文化隔阂、对立并且交融的表现,“离散”并文化融摄主题的思考,一直延续到近年,比如《睡吧,芙洛,睡吧》(2012),迁移之后的生活直到《流年物语》(2016)当中,都有涉及和表现。新世纪以来,“离散”的文学命题似乎更多地是呈现在海外华文作家的散文和随笔当中,小说当中的“离散”命题,已经同新世纪之前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赴西方留学并移民的上一代作家有了显著的不同和差异。2017年12月21日,暨南大学“离散写作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外华文散文丛书”首发式。这套丛书(花城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的第一辑,包括八位作家:陈河、曾晓文、亦夫、谢凌洁、朵拉、刘荒田、林湄、老木。会议的主题是“文化记忆与离散美学”,说明“离散”美学仍然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写作当中有着旺盛生命力,而且散文可能是在新世纪里表达“离散”文学命题最为得心应手的创作体式了。加拿大籍华裔女作家曾晓文说:“海外作家不占天时地利人和,只是孤独地写作。”②她在散文《与多伦多共饮》当中,明确写道:“迁移,练就了人的勇敢,也注定了人的淡漠。”③尽管如此,我们在其创作中,已经更多地看到迁移之后的坚定、自信、从容,是“与多伦多共饮”,而不是“无根的一代”“失落的王国”的“永远的迷失者”。
二、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的
中国想象
“离散”美学和文学命题在海外华文文学当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是在很多的海外华文文学学术会议和学术讨论当中,我都特别提出了“离散”美学和命题,已经越来越无法概括和囊括新世纪以来愈来愈呈现新变的海外华文作家们的创作。新世纪以来,在严歌苓、张翎、陈河等海外华文文学代表性作家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中国叙事或者说中国故事的讲述,或者,用王德威的说法,他们在“以不同的场域,甚至实验着不同的语言,来想象着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2001)已经通过在美国的白人外交官与华人女留学生之间的爱情,在诉述西方“拯救”东方的不真实、是不被享受的。《花儿与少年》(2004),作家将她的中国想象将主人公在国内的遭际视作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缩影,而通过一场离婚再嫁,将对中国的想象或者说叙事延伸到西方,我们看到的不是东方的被虐和挤压,而是老瀚夫瑞在这场婚姻当中的各种近乎可怜的样貌。“十年前,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娶进他那所大屋,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晚江年少他三十岁,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见老瀚夫瑞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花儿与少年》)那本名为长篇、实为中短篇小说集的《穗子物语》(2005),几乎是严歌苓全面开启她的中国想象的开始之作。《第九个寡妇》(2006)、《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是严歌苓开启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书写的长篇之作,用贺绍俊的话来说,《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关于一个女人的革命史和爱情史,《第九个寡妇》是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注:当然,这个生活史同时又富有传奇性)。严歌苓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写乡村妇女和乡村苦难,她对待苦难是什么样的书写态度呢?“但严歌苓不是启蒙主义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义者,她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意。因此她的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即使面对苦难,她不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当然,事实上严歌苓的小说并没有拒绝意义,在她的对生活充满了品赏和体悟的兴趣中,彰显出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她对寡妇王葡萄就是非常欣赏的,她以快意的、鲜亮的语言讲述着王葡萄的故事。”①由此贺绍俊宣称:“她基本上是以西方的价值系统来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从而也开拓了‘红色资源的阐释空间。这也是严歌苓在中国文坛‘热起来的主要原因。”我倒觉得,说她全是西方的价值系统,有失公允,西方的价值系统也不是这样来看取中国的历史的,而且严歌苓未必有意要重新组织“红色资源”的叙述,但她的确是以一种统摄了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且熔铸了她的个性、她对历史和人性的一种女性视阈的理解,来进行她在新世纪的中国想象的。
严歌苓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寄居者》《金陵十三钗》,其实都是涉抗日战争叙事的“中国想象”。张翎的《劳燕》,也是开启一种新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来进行她的中国想象——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还原。陈河《甲骨时光》是双重叙事空间,其中民国时期那段叙事,也涉日本侵华和掠夺中国的甲骨文等文物。《小姨多鹤》可以说是抗战后叙事,小说写了抗战结束时日本在满洲的“垦荒开拓团”村民仓皇溃逃路上留下的孤女多鹤,十六岁就被一个中国家庭(张站长家)用七块大洋买去作为借腹生子的工具,和张二孩、小环组成了二女一男的特殊家庭的故事。小说写出了中国在抗战后几十年的历史和民众现实生活的流转变迁,辐射面从东北到江南,其实是一个部分采用了异族女性视角(也有中国人的视角)的抗战后叙事。《寄居者》(2009)也是对抗战时期上海一段历史的还原,是一个变形了的“沪版辛德勒名单”的故事,這个华裔女子May要以牺牲一个爱自己的青年来救一个自己所爱的青年——这样一个有些传奇的故事。故事延续了严歌苓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但是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小说通篇较少叙述视角的转换和限制性叙事策略的使用,所以现场真实感和在历史与人性的书写方面,不及《金陵十三钗》那般震撼和让人心痛。《金陵十三钗》运用女性的视阈,来还原南京大屠杀的那段惨痛的民族历史。严歌苓要揭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便选择了这个可能只有女性视阈的书写者才会选择和驾驭自如的——强奸和被施暴——来赋形民族的屈辱和苦难,从而获得历史还原的通道。
张翎的《劳燕》是首部涉及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题材和小说叙事方面,开启抗日战争叙事的新维度。①《劳燕》还采用了三个鬼魂——当年在美军月湖训练营是朋友的两个美国男人(牧师比利、美军军官伊恩)和一个中国男人(阿燕当年的未婚夫刘兆虎)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70年后相聚,每个人吐露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以多声部的叙述和追述,还原和补缀出当年发生在月湖的全景历史。三个鬼魂当年都是同一个女孩的恋慕者,他们分别叫这个女孩“斯塔拉”“温德”和“阿燕”。这个小说是有关抗日历史的“中国想象”,作家将她心目中的历史建立在大量的走访抗战老兵的纪实性材料的搜集中,借由丰富的文学想象力,让小说远远超出纪实性文学作品之上,氤氲而出的是张翎的文学想象和中国想象。小说保持作家素有的语言的细腻、美感、节制而又不失灵性,战争的阴冷敌不过人性的温情与坚韧。阿燕面对战争的灾难、苦难、伤害和恋人的背叛、村人异样目光乃至有人心怀趁机再度糟践她的企图,她以德报怨,独立,坚韧,承担,温柔与力量并存,宽容与原则共在,以一个温婉的江南小女子在战争中凤凰涅槃般的遭际,展现了战争和苦难蹂躏下的中华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坚韧和强韧的生命毅力,是战争废墟上开出的一朵人性坚韧与温暖之花,很多的场景描写令人动容②。
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们“想象着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严歌苓《陆犯焉识》是通过对“我”的祖父陆焉识以及祖母冯婉喻尤其是陆焉识的故事的讲述,展现了20世纪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而陆焉识与冯婉喻那“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无疑是小说最为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在用一种相对轻松的笔调写出一个较为沉重的故事和历史方面,是表现出作家高超的叙事能力和中国想象的独特的话语方式的。《床畔》(2015,原名《护士万红》)、《芳华》等,都是对一段历史的书写和她对过去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的“中国想象”。
张翎也是新移民作家的杰出代表人物,其《望月》(1999)、《交错的彼岸》(1999)、《邮购新娘》(2004)、《睡吧,芙洛,睡吧》(2012)等,都有着对移民历史和迁移之后两种文化怎样融摄的思考。但《余震》(2010)、《阵痛》(2014)、《流年物语》(2015)、《劳燕》(2017)、最新中篇《胭脂》等,也是明显的一种向“中国叙事”和中国想象的小说叙事的转变。陈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写华人在阿尔巴尼亚的故事,《女孩与三文鱼》写加拿大的留学生与第一代移民房东的相恨相杀的故事,《米罗山营地》《沙捞越战事》中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故事。到《甲骨时光》,陈河的写作发生了质变,就是放在当下内地文坛,它毫无疑问也是最最优秀的“中国想象”的长篇小说。陈河说,他写作上“这种成熟的能力就是我开始能够看见内心深处那团模糊的光芒”。“在后来的写作中,我不时会迷失方向,可最终都能找到迷宫的出口。随着故事的步步推进,我终于把这条时光隧道打通了。而引领着我最终穿越这条时光隧道的,就是我内心那团‘模糊的光芒。”①我有理由想象,陈河在《甲骨时光》中,他受着内心那团模糊的光芒的导引,彻底飞升起了他的文学想象,飞升起了他的中国想象。大量的、内地作家都罕用和罕见能够运用自如的翔实的史料镶嵌在小说的诗性叙述中,诗性虚构出一个民国与殷商时期的中国故事。《甲骨时光》是通过杨鸣条对甲骨的寻找、甲骨之谜探寻发现的当下叙事以及与之对应的古代殷商的故事这两套叙事结构中完成对中国故事的构建的,杨鸣条一次又一次在与大犬的神交中返回商朝,两套叙事结构所构建的中国故事得以完整呈现,一个美学层面的中国形象也逐渐浮出水面②。
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以写作来完成他们的中国想象——想象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当然还有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现实。《赴宴者》(英文版2006,中文版2009)可能是迄今为止严歌苓对中国现实描摹最多的长篇小说了——也是一种中国想象,似乎比《上海舞男》(单行本《舞男》,2016)还要贴近现实更深。记得毕飞宇曾经讲过聂华苓还是哪位海外老一辈移民作家的一段说辞,大致就是说,第一代移民作家,一旦用英文写作,涉及语气和叙述细部的方面,会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读就知道不是英语为母语的人写作的。这可能也是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坚持以汉语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严歌苓在《赴宴者》中文版后记中会说:“用英文写作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跟自己过不去。”“一个英文句子要在电脑上反复写三四遍,还吃不准哪一句最好,这就证明我不再像写中文那样游刃有余了。”“然而我必须逼自己最后一回,否则对我在美国学了好几年的英文文学创作没个交代。”她把《赴宴者》的写作,视作激发自己潜能之举,其实不只是激发她的潜能,还激发了她对中国现实描摹和进行书写的中国想象的潜能。《妈阁是座城》写的虽然是赌城妈阁的叠码仔梅晓鸥与赌客之间的故事。但也可以算是关联中国现实的中国想象的作品。毕竟,与梅晓鸥发生瓜葛的段凯文、史奇澜、卢晋桐都是内地的男人,借由他们,关联起的也是各个阶层的中国社会现实。《上海舞男》通过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老上海的舞厅的空间叙事,将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石乃瑛和舞女阿绿的故事(1941年前),翻转腾挪并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自始至终与现实当中张蓓蓓和杨东的故事绾合在了一起——小说对现实的反映和关注程度也是蛮高的,是基于中国现实的中国想象。《芳华》(2017)后面的部分也有涉现实的书写。而像主要是对中国历史的中国想象当中,也有涉现实的想象和书写,比如《小姨多鹤》的结尾部分,等等。张翎的《空巢》(2005)、《死着》(2015)[另,《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2016),收录了《死着》《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余震》《雁过藻溪》]是关于中国现实的中国想象,《余震》完稿于2006年,小说最后也落笔在2006年的唐山市和多伦多。而不能不提的一个中篇小说,是张翎的《都市猫语》(《花城》2017年第4期),是直面当下和现实的张翎的中国想象。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能夠写出这样现实关注力度和兼具文学力量的作品,是很让人吃惊的,当然,也是给人以十足的阅读吸引力的。张翎在创作谈《猫语,抑或人语?》里都自言:“《都市猫语》是我近年一系列探险举动中的一部分。在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一直有意识地回避两种题材——关乎自身和当下的,因为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一直看不清楚的事情。我以往的大部分小说题材,都是从时间线上横着片下一个长截面,从历史一路延伸到现今,很少竖着下刀,取出一个当下断面。但这种状况在这两三年里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都市猫语》是继《死着》《心想事成》之后的又一部书写中国当下现状的小说。虽然都可大致归类在都市小说里,但与以上两部不同的是,《都市猫语》引进了一个‘非人的观察和叙述媒介——两只跟随主人公在都市里讨生活的猫——老黄和小黑。”“我赋予了这两只性别体型具有巨大差别的猫以各样神奇的功能,使它们能够在狭小的居住空间中准确地闻出各自主人的不安、躁动,以及佯装成各样负气行为的试探。它们用猫的语言化解着卑微中求生存的人在相撞中必然结下的猜忌和抗拒,它们用动物靠直觉建立的情感嘲弄着人扭捏作态的假惺惺。”记得我读了《都市猫语》,完全感觉不到它有哪怕些许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写作可能罹患的对中国当下现实的“隔”,文学想象和书写的入木、入骨和入心,非通常的作家笔力所能及。这也告诉我们,除却文学想象中国的历史,文学想象中国的现实,对于海外华文写作而言,同样值得期待,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惊喜,更多地到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17BZW17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