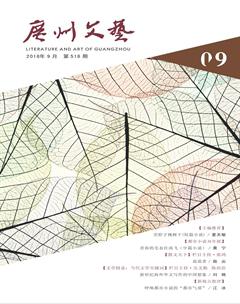细节与悲柔
主持人语:
我以为,指尖是一位没有得到重视的优秀散文写作者。
在读了她的一篇散文后,我急忙向她约稿,就想看看,她的笔下新出现的文字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我一点儿也没有失望。
从这两篇散文来看,指尖的写作是开阔的、包容的,中西兼蓄的。她的文字可以西化,可以地域色彩浓厚;所写可理性可感性;她的文字可以柔美、可以清麗,但不流俗;可以厚重、犀利,但不粗鄙。她是独特的。
《说谎者》以小角度切入后放开书写,适合逐字逐句细读,一定会让读者产生诸多的联想,《细节与悲柔》,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那些在指尖脑海中的雪纷飞而下,在“指尖”的舞动下,幻化出种种细节,且美且悲。
不少的写作者并不在意是否被认同,一味地我手写我心。
——主持人:张鸿
作者简介:
指尖,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槛外梨花》《花酿》《河流里的母亲》《雪线上的空响》《最后的照相簿》等多部散文集。曾获首届网络文学散文奖,孙犁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今我思雪】从古至今,人们对雪,都怀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既有“今我来思,雨雪载途”之苍茫回顾,也有“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的遂顺无聊。雪,似乎因为是一年最后季节的物候现象,而隐约有了终止、完结,乃至死亡的意味,吴文英就有“看飞雪,苹底芦梢,未如鬓白”的句子,对生命循环至老,生无限感慨,仿若死亡紧随雪后,随时都要获取性命般无奈萦怀。“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倒是一片暖意,暗淡的灯盏下,心念里的人终得重聚,惊喜又伤怀。只是所有人都明白,怎样字正腔圆、幸福无边的表象下,都掩藏着生之为人的无望、伤心,绝望,乃至执拗和仇恨,这才是没有被掩盖和遮蔽的生活和人性啊,真正的俗世容颜。也似乎只有雪,才能使那些突兀而无法剔除的丑陋、邪恶和残酷,暂时得以缓解,让人们有时间回望,忏悔和补救,并重获热情和天真,对大雪后的人生充满期待。
大约这世上不喜欢雪的人很少。比如我,活到如今,经历过几十个冬天,见识过无数场大雪小雪,一年又一年,颜渐衰,心渐钝,人渐老,依是喜欢雪。或皆因人生之初,见着天地人间,便是大雪霏霏之故?真相或许完全相反,是我用几十年的幻觉臆想出一幅假画面,仅此而已?我试图跟母亲核实,她竟然一概不知,既不记得我降生于何时何辰,更无法说清有雪无雪。那时人们刚结束饥火烧肠的日子,面上的菜色尚未褪去,蝉腹龟肠的恐惧随时来袭。我的出生,远不是生活中的大事要事。所以,我体谅母亲的遗忘。事实上,这种体谅,更多的是生之无奈,命之无由。《道德经》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句,原来在天地眼里,所谓的万物形姿态度,都是不存在的。万物,无论高矮胖瘦,黑白丑俊,都可被冬天的一场雪包缠裹纳其中。这样想着,便感觉一个人、一件物的一生,也就是一场被大雪覆盖、遮蔽的过程。刚开始,你会心怀侥幸地躲闪、挣扎,渐渐地,看惯了雪的倾盖,无边寒冷,便不藏不躲,迎将上去,允准自己的脚接纳雪的亲近,允准雪带给你的脓疮和痛意。雪,就这样遁着你的侥幸,一点点,渗透你的一生,然后,将你掩埋,致你消散,无痕无迹。
七八岁,除夕,见过一次大雪。不是静悄悄,而是发出噗噗的声响。不到一个时辰,远山近树,温河和村庄,便成了雪世界。小孩对此毫不在意,兴奋得不知所以,跑出去,抓一团雪,放到嘴里。在被大人责骂的时候,雪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大人们刚开始也如小孩般兴奋,拿着扫帚在院子里、街上扫雪,但这样的雪,怎能扫得完呢?当大人们感觉劳累,停止动作歇息,只一瞬,他就成为一个雪人,头上,肩膀上,脚上,眉毛上,睫毛上,手和扫帚上,全是皑皑白雪。雪的力量要大过人的,雪侵袭的速度也要大过人躲藏的速度。很快,大人们就放弃了对它的驱除,讪讪地站在檐下,心怀愧疚地拍打着自己头上身上的雪,一脸茫然。
直到第二天早上,雪还没有停下的意思。担忧的神情开始呈现在大人们的脸上。因为过节,他们又得装出一副欢喜的样子来。大雪地里放鞭炮,黑色的炮灰和牛皮纸屑,飞散在洁白的雪上,乌迹斑斑。但很快,又一层雪将它们埋葬。不久,噗噗的大雪,压塌了邻居家的简易厨房,同时压塌的,还有村里的牲口棚,一些人家的鸡窝和猪窝。要不是那些鸡们飞了一院子,而牲口们暴跳如雷地从草和砖块下飞奔出来,你根本看不出它们已经坍塌。雪,像一个肇事者,同时也是一个掩藏者,它带来的安平和危险一样令人恐惧,慌张,无所适从。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恐惧感常常在我梦中出现,雪,不停歇的雪,覆盖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房屋,土地,恋爱,理想,包括我自己,我只能用梦外的另一只眼,去看见自己的挣扎和覆灭。雪,用时间和耐心,一点一点地制造细节,并使它逐渐圆润,完满,直至成为庞大的事件本身。
【穿过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许多年前,在工厂,曾对对面山顶上,一株孤零零的树充满幻想和猜测。在所有人的想象中,它高大、壮实,且有一股不可摧毁的气势,它让风云无奈,并赶走雨雪。深冬,大雪将整座山都遮得严严实实的,松树柏树的枝条上,沉甸甸地压着雪沫,那时候,摇摇欲坠的,根本不是雪,而是它所压迫的、颤巍巍的枝条。在那些表情恐慌的枝条之上,在那些耀武扬威的雪沫之上,一座山,顶着厚厚的积雪,仿佛已被雪势收买,面上挂着些些谄媚之色。那株孤兀的树,清爽爽,孤傲傲,漠然地站在厚厚的雪中,仿若脱离,又仿若深陷。因为树冠稀疏的缘故,雪竟然也无法如愿,直到高寒处,依旧你是你,我是我,互不相干的绝然无情。
那段时间,我极度颓废,对当下的不满,对未来的迷茫,让我一直发着低烧,像爱上一个人般绝望。站在雪地里,眺望那莽莽苍苍的白色山脉,在刺眼的雪光中,泪眼迷蒙。隔着一条小河,隔着一些田地,隔着密密的雪松林,隔着半座厚厚的雪山,与一株孤傲的树对视,成为我的必修课。
直到,春天来临。
你肯定会心生好奇,说,难道你就没有跨过那条小河,沿着厚厚的山脉,登顶与之相会吗?我可以回答你,但请不要像我当初般失望。
是的,来年春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冒着被初生荆棘刺伤的窘境,伤痕累累地站在它面前的时候,觉得,它是一株更适合远观,仰望,敬爱的树,它适合当理想,希望,光源,而不是与你平视。或者,在你面前佝偻着身体,袒露着伤口,流着血和脓,绝望地看着你。世上最大的震撼,其实就是所有细节组成的绝望之美。就像你爱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从无比狂热的欲望,到最终幽幽的伤怀。當然,我依旧对它葆有敬仰之情,并体谅它在如此艰难之地,于石缝里扎根生存的毅力。但我知道,从此远别,再不回顾。我将在途中,遥远地,满怀深情地怀念它,爱慕它,永世不忘,直到我的生命,被大雪覆盖,消亡。暮色中,雪国的一切都将终结,这是时间的流逝,也是生命和激情的流逝,爱和永恒的流逝,还有希望和理想的流逝。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川端康成《雪国》的开头起句,像某种暗示,让人瞬间便生出欲望,追随他的笔触进入到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日本文学读本,多悲柔忧伤。像一场雪,一点点,一片片地覆盖。无论是国木田独步、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还是更早的紫式部、清少纳言,包括村上春树,他们的作品,无不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悲柔之美。前段,老友推荐日本女作家江国香织的随笔集《下雨天一个人在家》,书中有一只名叫雨的美国可卡犬,让我轻易联想到以前养过的小犬。这是一本看似轻盈、优雅的集子,读完,却依旧有摆不脱的悲情和寡意。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是觉得这种摆不脱的愁绪。瓦匠渐老鬓霜白。冰凝愁肠寒夜泪。却原来是因对生命醒悟而生出的悲凉凄情,是哭笑不得,是方生方死。后来想起,早先读过她的《寂寞东京塔》,恍然,原来,她真实而恣意的另一面在小说里,虚无、寂寞、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迂回着爱和悲,生和死。
文学作品给人的暗喻充满各种可能。据说,小说家就是将现实生活塞进梦境的巫师,他有将梦境不断撑大的能量,他也有让梦境瞬间破裂的魔力。像雪。
【晚来天欲雪】崇祯五年终月,西湖三日大雪后,张宗子乘一叶小舟,穿着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西湖之美,世上无双,雪后更是奇绝,“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了湖心亭,却见已有两人相对而坐,候等旁边的书童烫酒。火正旺,酒将沸。一扭头,两人看到张宗子,惊喜不已,说,想不到这茫茫大雪之中,还有你这样闲情雅致之人。张宗子聪明人,心想这哪是夸我,明明是自夸吗。当下哈哈一笑,躬身作揖,拜过。恰好酒已烫好,也不推辞,痛饮三大杯,方告别下船。《湖心亭看雪》最精彩处此时才出现。远看千里一白,大雪茫茫,鸟迹全无,张宗子踏着船上的残雪,战战兢兢地下来,身后,那布衣草鞋黑面短髯的船夫,轻声笑道,大千世界,不要说只有相公你傻,原来还有和你一样傻的人呢。雪,竟让原本无缘逢着的人,在一叶窄窄的小舟上相见欢,一叹。而这样的皆大欢喜之下,却又蕴藏了多少无奈,和遍拍阑杆无人会的渺茫慨叹啊。
很多人都喜欢“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关乎雪和知音的诗句。似乎雪,跟酒和茶总是结伴而来的。少年时看《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节,对酒产生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彤云密布,朔风渐起,纷纷扬扬,卷起一天大雪,这样的天气,除去家屋,母妻,也只有酒可御寒。林教头便挑了酒葫芦去找酒去了。人之际遇,均是缘法所定。而所谓的缘法,其实也是天地意思。所以他这一找,酒是喝着了,身上也渐渐暖了,且回得头来,草料场的两间破屋却已被大雪压塌,无奈,只好去山神庙暂避一夜。这一避,哐哐当当,重打锣鼓另开张,人生从此又一番际遇,亡命天涯,逼上梁山。昆曲《夜奔》,说的就是火烧草料场之后的事,比书里多了细节和心思,好看多了。
“凉夜迢迢,投宿休将他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奔走荒郊,俺的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又恐怕人惊觉。吓得俺魄散魂消,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婉转不得,悔恨交集,道不尽的人世炎凉。
“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哎呀哭号啕,急走羊肠去路遥。且喜得明星下照,一霎时云迷雾罩。忽喇喇风吹叶落,震山林阵阵虎啸。又听得哀哀猿叫,走得俺魂飞胆销,似龙驹奔逃。呀!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道。”
旧时喝酒,多有烫酒一说。我小时,祖母喝酒,也用专用的酒壶温酒,酒壶是锡制的,凉酒入壶,再放入热水中温着,温好了,倒在小酒盅里,祖母挺直腰杆,抿一口,用筷子夹一口菜,放到嘴里,然后再将筷子端端地摆在面前。年节下拜神祭鬼,也会倒一杯烧酒祭奠。感觉,酒是人间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带来的庄重和恭敬感,让仪式更令人信服。
大雪天,炉火总是旺的,火上放了一壶,盖子会被滚水顶着,哒哒作响。其实,雪天,围炉,少则两人,多则五六人,酌的是酒也好,茶也罢,人们多是贪恋炉和人的温度。一个人,再暖的炉都不足以暖心。而人要太多,炉的暖意,便无法均衡了。凡事都有刚刚好,像歌里要唱,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此刻,哪怕是喝咖啡,喝白水都是暖的。要是用雪烹茶,这多少有点奢侈了。一壶浊酒尽余欢。那时窗外大雪纷飞,一杯水给你的安慰,亦有岁月静好的从容和幸福。
【悲欣交集】雪,落在一年中最后一个季节。落在最冷,也最无措的时候,也落在最终的节点。那年,大雪天,我跌倒在电车旁边,差一点送掉小命。那是一个没有炉火也没有酒更没有知音的冬天。城市的雪,不像山野的雪,有一种洁白而美好的假象,它是乌黑的,绝望的,就像深渊,地狱。没有人可以拉我一把,让我起来。或者再推我一把,让我永远倒下。我们常常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左右,无路可走,这就是人生。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抗争,你只要等着,熬着。等命运之神,想起,扒拉你一下,你就成为永动机。而雪,就是让你凝固,停滞,等待,或者终止。那个冬天,当我摔倒在电车旁,看着面前滚动的巨大的轮胎,看到纷纷掉落的黑泥,闭上眼时,遮天大雪,在我记忆的河床上纷纷扬扬,面前的一切须臾不见,只有水流激荡的温河,春天遍野的桃花,遂生出巨大的活下去的勇气和欲望。
就那样带着满身泥泞,走了三站地,站在一栋楼前。想起高山顶上的那株树,让我仰望,爱慕,并铭记于心的树。大雪噗噗地下,我的脚,我的小腿,很快就被雪埋葬。我将自己拔出来,远离了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雪与告别,似乎最登对。河流冰封,茅草伤枯,雪落下,草亦有泪。要告别的两个人,瑟瑟地站在河岸两边,一条雪河仿若银河,让人生死相隔。或许也不是河,也不是雪,其实是人心,是俗世的枷,套着各自颈项。再想起,时过境迁,天涯零落,相见无望,唯梦闲人不梦君。
《红楼梦》最后一回,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散的散。贾政料理坟基事毕,便乘船回返,乍寒下雪,便打发众人上岸辞别友人,自己坐下写家书,写到宝玉,顿笔抬头,忽见船头微微雪影里,站了个人,光头,赤脚,却披了件大红猩猩毡斗篷,向着他倒身下拜。贾政赶忙出船,欲问对方是谁,那人却已拜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便问,可是宝玉?那人也不言语,似悲似喜。贾政又问,如果是宝玉,怎么如此打扮跑到这里?宝玉尚未答言,便来了一僧一道,左右夹住宝玉,边说,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边飘然远去。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沉湎于宝玉那个似悲似喜的表情,有点弘一法师终前“悲欣交集”的意思,也是终了,了了的意思,渺渺茫茫,归彼大荒的意思。
【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雪跟雪也不同,有时下的是雪粒,打在身上脸上,有痛感,落到地上,很滑。大多时下的是雪片,又称雪花,从天上往下飘,一层又一层,一层有一层的秩序,一层有一层的使命,好像有指挥者,立在遥远的天边,说,一雪,向左。二雪,往右。三雪,要沿着45度角下降。四雪,要旋转180度……据说,斑马的纹路,人的指纹和脸,还有雪花,在这世上是没有相同的另一个的。这样看雪,便觉得它跟人有几分相像,是有性别,情意,格调和欢喜哀愁的。众雪落下,各有各的归处,树上的雪,跟树下的雪是不同的,而落在手心和落在眉间的雪,也各怀各的心思。
上学时读鲁迅的《雪》,觉得他该是没见过大雪的人,因为他开篇便是暖国的雨,结尾还是雨,他说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雨的精魂。那时觉得,雨跟雪是毫无干系的两种物体,它们存在的季节不同,形状和温度不同,这有点像艺术的表现方式,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戏剧、电影等等,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同。风霜雨雪雾,只有雪,是属于文学的,它带着孤寂、细微的冷和润,一点点渗入到文字中间,凝成一种可消融,也可聚集的力量,再慢慢地扩散于文字之外的世界。文学之中的细节,就是一片雪花落到衣襟上,它或许会永存,也或许会消散。它能冻僵,也能浸湿。仿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心,一瓣一瓣翻开来,再一瓣瓣骤然消散。
若果写作者有雪花的耐心。
这样说,我很惭愧。因为我无法完成一朵雪花般的文字,也无法效仿雪野的优雅和悲柔,我总是莽撞的,急迫的,乃至有时会狠心放弃一些美好的品质,变得顽固而自我。于坚说:“最高的写作是我表演的一场升华于吾的、无我的游戏。”读这句,我眼前瞬间弥漫遮天之雪。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宋体字,它们随意落下,各自组合,美妙,可遇不可求。最合适的字句和段落,最好的文章,就像大雪鋪陈,晶莹,自带光芒。
2017年12月10日,寒潮来袭,我无炉可围,也无酒可温,更没有那个说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的人,只有《苦雪烹茶》的箫声。天渐渐暗下去,暗下去。大雪刚过,冬至将来,到今天为止,尚且未见过雪粒和雪花,心下有遗憾。
想起前年冬天,去看望一个朋友,聊得兴起,喝掉一壶普洱。晚十点,出门时,脸上一丝一丝凉意,像被谁的舌尖,轻轻地舔着。那是初雪啊!两个人高兴地在街上跑,也不管年岁多大。“我们都是被雪遮了头的人。”她说。隔天我们在美发院里染发,红红黑黑的染发剂散发出刺鼻难闻的味道。是啊,人生就是被看不见的雪覆盖的过程,一不小心,我们全白了头。
生命的雪,轻柔,小心,隐忍而执拗,它落在我们的身体上,也落在我们的眉间心上,侵袭着我们的脉络和骨头,缓慢,持久,年年,月月,点点,片片,覆盖和埋葬着我们的性命和爱。所以木心先生会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雪,仿佛某种暗喻,某种提醒,又像某段必得熬完的羁旅。它是带给我们寒凉、冷清和圆满的终结者,令我们冰冻成霜,万劫不复。有意思的是人们虽已洞悉,却毫无惧色,依旧守着黑暗而寒冷的冬天,急切而诚心诚念地,等一场大雪,似乎那是爱,希望,力量,勇气,自由和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