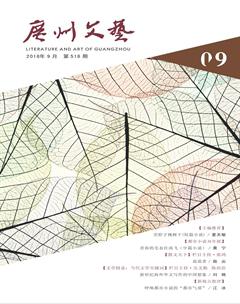青春的毛衣往南飞
黄宁
一
遇见阿艺之后,我治愈多年的焦虑症又复发了。这种病症的起因尚不明确,阿艺可能是起因之一,也可能跟她无关。她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无奈,我们相识很短,而且很浅,我的焦虑症跟她并没有什么关系。她还特别提醒我不要忘了,我是有病史的,我这种病伴随终生。
你们这种人呐。阿艺将她的长发高高盘起。双手在后脑勺扎着,青灰色的毛衣紧贴着身子,我看到了一对饱满的乳房上下运动着。盘好头发,她正了正衣裳,也许是刚才动作太大拉扯到了胸衣。你们这种人,想太多。
你也许是对的。我有些不安地抽着中南海香烟。此刻,我们站在禾祥西街头,吹着春夜的风。我们在等待滴滴快车的到来。下一步,我们各自分开,她将去沙坡尾听歌手马条唱民谣《傻瓜》,我将回家。阿艺,回家之前我跟你讲个笑话吧。今年春节,我一个人留在城市里,我给一个认识的电视台前女主播发微信,告诉她我在开车时听到广播放了一首陈奕迅的《可以了》——我们都喜欢这首歌,她还说这首歌可以算是“我们的歌”。后来,她回我微信,说“过年最重要和珍贵的,就是家人的陪伴”。
她现在哪?
辞职去南加大留学深造。
南加大,UCLA,那里的电影学院很不错。阿艺跳跃了两步。王林,我要是你,收到这样的微信,还不如去撞车呢。
我真撞车了。为了看那条微信,撞到了前方的车,保险杠整个都凹进去了。
阿艺笑了,两个小梨涡非常好看地浮在嘴角。她的滴滴快车来了,我给她开了车门。她坐进车里朝我扬扬手,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的忍受力很好。阿艺明眸皓齿,她看着我说,你应该重新去看一下《了不起的盖兹比》。我说好,但实际上在我跳楼前一刻,我才重新捧起那本书。
我的焦虑症很明显。我努力控制,尽量让自己表现正常。那个美国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飞行家霍华德·修斯,他紧张焦虑时就要洗手,越焦虑冲洗得越久,好像手上永远有污渍,手掌的病菌永远无法清理干净。我多少有点像他。但我不洗手,我抽烟。当心跳突然加速,肾上腺素往上涌时,我就会一根接一根抽。我的手心冒汗,我一手夹着烟,一手不停地擦着裤缝。有的时候,我也会躲到洗手间里,脱下裤子“打飞机”。
“打飞机”与抽烟其实本质上一样,不过是种自我安慰。手抖得厉害,要完全冷静下来,得等病症发作结束——打飞机或抽烟都不是药,不能马上治好我的焦虑症。就此问题,我和毛伦进行过讨论。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往密切,但近几年不怎么联系了。偶尔才打个电话,或者见上一面。
我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过去。所以,当我谈到焦虑症时,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你肯定是缺少女人,和过去相比落差太大,所以你焦虑。我点点头,但马上又摇头,我们都不小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远比女人更重要的事。他反问我,比如呢?我本来想说事业、赚钱、当官啦等等之类,但在一位艺术家面前说这些,实在是无趣。我在毛伦的画室,他租在离我上班不远地方的民宅里。画桌上有一幅尚未完成的画,我暂时看不懂他画的是什么。我说,对你而言,画画不就是比女人更重要?他摇摇头,这两者非要比个高低,我只能说两者在我心中一样重要。我问他,现在还画画吗?他说,喏,你看到的那幅画已经放很久了,一直没完成,画不动了;但女人我还行。
那说明你体力好,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嗯,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有差别。你知道我爱跑步,天气热的时候,我早早醒来,沿着环岛路跑,從珍珠湾到黄厝,大概15公里吧,然后坐公交车回家。吃个早点,回到画室冲凉,然后躺在沙发上。我二十年前能做到这样,现在也可以。体力上好像没什么问题,但精神上差别很大。当我躺在沙发上时,我会胡思乱想。而以前不会这样。
以前怎样?
以前我什么都不想,现在我总会想起以前。
毛伦的这句话有些拗口,我认真想了想,忽然觉得有种浓烈又稀释、猛烈又轻柔的情绪笼罩在我们身上。我隐约觉得我们正在失去很多东西。我又开始有些坐立不安,抽出中南海香烟,但打火机怎么也点不着。毛伦接过打火机,摇了摇,然后将火伸到我的面前。我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之后,我才开口说,你觉得我这焦虑症能治好吗?
这可不好说。你前几年犯过病,这中间过了很多年了,本来无事,但现在又犯了,说明这病有潜伏期。做个假设,就算现在你的病好了,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犯。毛伦也点了根烟,你得找出真正病因是什么。
我和他提起了阿艺。但他听了摇头,她不会是你焦虑的真正起因。你不可能和她发生什么。你遇见她,可能想起以前的某个女人,也可能想起以前的某件事。总之,你想起以前了。而你突然发觉,你好像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其中也许有对你最重要的一件东西。
我夹着烟的手在颤抖,烟灰不加掩饰地坠落在地,粉碎,飘散各处,令人生厌。我说你怎么懂?毛伦笑了笑,他健美的身材一如当初——我们都曾是出走家乡的少年——但他头发里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他说你看到我的白发了吧?你也有了。我最近闲着无事,不想画画,我陪你去寻找那件最重要的东西吧。
烟蒂已经塞满了整个烟灰缸。我满脸尼古丁燃烧后的油腻,我去洗手间用力洗了把脸,然后说,好。
二
出发前,毛伦再一次和我确认,家里同意这样做吗?我往后备箱塞行李,关好后才说,我和家里说是陪你去寻找创作灵感,你现在灵感枯竭,画不出好东西来了。毛伦看了我一眼,你可以啊。
我们离开厦门岛,上沈海高速,然后直奔泉州。我对泉州这座城市很陌生,我不认为在这里会留有我的记忆。毛伦说你不能狭隘地看待问题,我们要找东西,这必然要有个过程,不可能直接达到目标,我们可能“由此及彼”,因为世界是互相联系的。我把车开进了泉州市区,停在中山南路附近。我说,你是想去见那个高个子女生吧,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有点忘记了。毛伦下车,活动了下手臂和腰,叫徐婕灵。
对,就是那个女生。个子很高,我们站在她面前有点抬不起头。她是你大学同班同学,人很开朗活泼,有侠义之风。我记得你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侠女”。
她高大威猛,担得起这个称號。现在她没有除暴安良,但还在行走江湖。
哦,我以为她洗手煮羹汤,嫁作人妇了。
她嫁给谁?我吗?我们这种人,不适合那一套的。
“那一套”指的是什么?我本想追问,但看毛伦并没有想说下去的意思。为了叙述方便,在接下去的叙述中,我们还是称婕灵为“侠女”。我跟着毛伦走在后面,我们要去找一家青年旅舍,是侠女开的。毛伦说有一天她在朋友圈发了个链接,我点进去看,原来是她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报道。那时好像临近春节,她的青年旅舍不打烊,继续为孤魂野鬼提供落脚的地方。我说后面一句话是你自己加的吧。毛伦站在青年旅舍门口,笑了笑说,当然是我瞎扯的,电视采访说她的旅舍有特色,大概意思就是文艺小清新,有别于那些大路货的快捷酒店。旅舍还举办活动,一些无业文青聚在那里唱歌读诗。
侠女开旅舍这件事让我有些意外。她原本是学画画的,我以为她开画廊还靠谱些。或者是去北京文化流氓圈里混,当画家也好,当画家经纪人也罢,一定能风风火火干出一番事业。但没想到她选择回老家开旅舍,做了一件不那么耀眼的事。
傻瓜,为什么人总要做耀眼的事?
毛伦的反问似乎有点道理。可如果能成为梵高毕加索,那为什么要甘心在油画村当画匠呢?
什么叫“甘心”?你怎么就不明白有些事是“不得不”?
毛伦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青年旅舍是一座旧闽南大厝改造而成的,前厅放着和缓的爵士音乐,一个前台小妹好奇地看着我们俩。我隐约觉得毛伦话里有所指,但在朗朗白天之下的旅舍里,我不想再深究下去。我拖着行李坐在布艺沙发上,腰间枕着一块垫子。前台小妹问,请问你们有预订吗?毛伦问你们的老板侠女,哦,徐婕灵在吗?前台小妹笑了笑,我们一般都叫“侠女”,她的真名我们反倒不叫。毛伦也笑了,问她在吗?前台小妹说不好意思,她去上海了,暂时不在店里。
我想,前台小妹一定不知道,“侠女”这个外号是毛伦取的。
好在是淡季,青年旅舍还有空间。我们入住的这间叫作“局外人”,毛伦看到了说文艺青年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别的旅店都是要营造宾至如归的感觉,她倒好,叫“局外人”,好像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真把客人当客人看。我说这并无不妥吧,加缪当初写这个小说,用意可能是不介入别人的生活。侠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旅舍只是给个歇脚的处所,它是旁观者,它不会介入旅客的生活。
毛伦躺在床上,想了半天,然后对我说,你纯粹是瞎扯。
“局外人”的感觉有点像大学宿舍,或者说整个青年旅舍都在刻意营造一种大学的感觉。在房间里,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好像我这个年龄已经不再适合这里。坐在靠窗的桌子前,让我瞬间以为重回大学自习。房间的床是架子床,比念书时宿舍的架子床要大一些,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舒适的程度。
毛伦躺在下铺,我只能选择跳到上铺去了。他瞪着眼睛看床板,我瞪着眼睛看天花板。我问毛伦,在想什么呢?没见着“侠女”,比较遗憾?毛伦摇摇头,我们互相都是“局外人”了。也不单是她,我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去见任何一个故人。当然,包括你,王林。我笑了笑,你们艺术家都是这样。毛伦稍微坐直了身子,床铺微微一动。
很抱歉,我对很多人都不放在心上了。有的故人,面貌可能还是原来的面貌,但其实已经变了,变得我无法相认。谢建,你认识的,我们初中同学,我离开家乡来厦门念大学,他来找我,我们还结拜过。他文凭不够,要找工作,我还帮他做过假证。那时说我们有兄弟般革命情谊。但现在呢?生二女儿,从老家给我打电话,深夜,让我张罗通知其他同学兄弟,他要摆满月酒请客。我没说什么,问他有钱请客吗?他说暂时钱不够,让我借个两三万给他……他可以去死了。我有时候真搞不懂,人怎么能活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也担心侠女和过去不一样了。
她不会变的,“文青”中毒太深。你看她开这个旅舍就知道。房间里还有书架,放了一整排的书,你说有谁会去翻?
哦,架子上有我的书。去年出的一本小说集,《十里春风不如你》。
毛伦探出身子,抬头看我,这么矫情的书名,有人看吗?能卖几个钱?
我说,你的画有人看吗?能卖多少钱?
我们几乎同时摇头,然后又用最舒服的姿势往下躺。过去的时光真是好呢。我说,过去哪里需要考虑钱的问题。那时我们只考虑感情和性。感情和性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真是美妙。你第一次带侠女回老家,你家里考虑到她是女孩子,让你安排她住在外面。你倒是安排她住我家了,但到了后半夜还是敲我家门,偷偷爬上她的床。可实际上,罗琳也在我家。对,就是罗琳,我那时的女朋友。她和侠女都是泉州老乡,两个人居然聊上了。而我们两个大男人陪在一旁,一直打哈欠,心里想着她们赶紧聊完才好上床。
那时确实这样想的。但现在,不要说感情了,就连性我也很少去想。有一次在画室,我和一个画展上认识的女人做爱,做到一半我忽然发现她屁股很美,于是不想再继续,跳下床去拿笔和纸,想着把她的屁股画下来。
那个女的同意你这样做?
不同意。她骂我变态。
你还不如直接和她说没有兴致不想做爱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这未尝不是件好事。柏拉图《理想国》里说,“在老年,对于这样一类的女色欢爱的事情就有了足够的安宁和自由了;一旦欲望停止逼迫和肆虐而平和、弛缓下来,可以说,我们就从无数狂暴的暴君们的手中得到了解放”。
毛伦认真听了后叹了口气。我并不觉得你这是安慰人的话。当我开头听到“在老年”这几个字之后,我就很沮丧。
三
泉州,古称“刺桐”,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万商云集,各色人种都有,也因此带来了各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你不能否认印度教当时也曾在泉州有过弘法。所以,我很好奇,泉州牛肉小吃这么有名,当年的印度教信徒如何能接受得了?
我启动了汽车,向站在青年旅舍门口的前台小妹挥手。临走前她问我们是否要给侠女留个口信。我说我没意见,主要看我旁边的这位。毛伦点了清晨第一根烟,然后说,算了,不用留口信,我和她很熟。前台小妹走后,我说是以前熟吧,毛伦没回我的话,自顾自讲了上面那一通话。
印度教徒可以吃别的,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心里应该早有准备。
我认为你说得对。毛伦摇下车窗,车行驶在马路上,清风阵阵飘进车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的?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准备总归比较容易办成事。但感情这件事却是例外。感情要的是“刹那间的冲动”,激情有感觉,有的时候想太多,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的,往往就把这事给办黄了——等你都准备好了,对象都跟别人跑了。
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莫强求。
你这个态度消极,感情还要主动。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毛伦,笑了笑。车里放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一首接一首经典歌曲,估计再过几年,没有多少年轻人会记得他了。我们听着他的《You are not alone》,有一阵子没说话。等这首歌完了,我才问毛伦,要是刹那间的感觉消失了怎么办?或者换个说法,要怎么维持一段感情?怎么能保鲜?
这个无解。我们的感情总是一段一段的,新人笑旧人哭吧。不要说感情了,世界上有什么能恒久不变?坦白说,就算你我之间的情谊,我也不抱太大信心。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但这不意味着往后三十年里我们还可能保持友谊。有可能未来某一天我们就断掉了,甚至可能此次“寻找之旅”归来,我们就分手了。
前方路口有车经过,我稍微点了下刹车。我不免又看了眼毛伦,他脸上表情依旧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我说,你倒挺看得开,好像不介意,对很多事都不那么放在心上。毛伦说倒不是看开,而是无能为力。我爸爸前年过世,你知道的,他得了那种病,很辛苦地撑了几年,我心里就算再不舍,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要走,我留不住。你是写小说的,你看日本小说就知道,那些日本作家写人的死,好像是宿命一样,怎么都留不住。
死是所有人的终极目标,像火车开往终点,挡也挡不住。
所以啊,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个悲剧。夏目漱石的《心》,一开始写作家和那个“先生”交往,我还觉得蛮有趣,但实际上全书的描写都是在为先生的自尽做铺垫。《了不起的盖兹比》,盖兹比多么风光,最后还是被人迁怒开枪打死,实际上盖兹比完全是替人受过。还有你的处女作《比目夜行》,一开篇就说“我”已经预知了自己会在哪天死。
我们的谈话有些跑偏了。在东孚服务区,我把车停了下来。我和毛伦抽着烟,看着一辆车开进来,又很快地开走,另一辆车马上跟着又开进来。如此循环。我们是要寻找某些丢弃的东西,而不是去想还未发生的。毛伦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吧,要有忧患意识。我点了点头,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虽然我潜意识里觉得他一直在胡扯。
出了服务区后,我们继续上沈海高速往西前行,然后在和溪镇下高速。中午吃了碗牛肉米粉后上路,在国道开了半个多小时后,进入了龙岩市区。
我把车停在登高公园,然后就下车。毛伦拍了我一下,说没事吧?怎么脸色那么差?我手扶着一棵大榕树,大口喘气。我的焦虑症又犯了。毛伦点了根烟给我,我吸了好几口。登高公园已经和我儿时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儿时的记忆也很模糊,只隐约记得奶奶那时还在,她带我去那里玩。五岁之前我生活在龙岩,后来因为爸爸工作调动,回到了下面的县城——上杭。上杭是我们的家乡,在我的理解里,人是往高处走,别人都是往大的地方去,为什么我爸却要带着全家回到了小地方?
毛伦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你对人生的定义有偏差。“高处”一定是好?高处还不胜寒呢。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到世界去》,“世界”就是家乡以外的地方,好像每个人都要到世界去。但外面的世界也未必就好,也未必就适合每个人。你知道的,我正式的工作其实是在龙岩的大学教书,艺术系国画专业教师。如果按照你的理解,那我岂不是“水往低处流”?
我把烟踩在脚底下。那你怎么还经常往厦门跑?还在厦门租了画室?我冷笑出了声,你在龙岩的家怎么办?老婆孩子丢一边,一个人过艺术家的流浪生活?
如果是在以前,我一定會揍你。你知道我是练拳击的,我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不要以为现在年纪大了,就不动手,你再多说几句试试。毛伦逼视我。
我把手一摊,你打我吧,如果可能就把我打死也好。我现在烦得很,昨天一天没犯病,中午吃完饭后突然之间就犯晕了,路上开着车一直强忍着。你应当感谢我没有把车开到山沟里去,或者把车撞向路边的岩石,否则现在你就已经不能站着说话。我拍了拍毛伦的肩膀,我连死都想过,你说可怕不可怕?
你们这种人,就是想太多。你在焦虑什么呢?你在焦虑失去。“失去”对你来说很重要么?在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后,毛伦开口说。他转过身,背对着我。这一次就放过你了,往后再瞎说八道,我一定揍你。
这不是毛伦第一次想打我。在我记忆中,他至少还有两次想要对我动拳头。有一次是在大学,我们一起在谈些什么事,好像还喝了点酒。我讲得有些激动,顺手拍了拍他的脑袋。他沉下脸,握起拳头对我说,不要动我的头,否则兄弟也没得做。还有一次是毕业后,有个朋友开公司要挂一张国画,让我帮忙介绍一个画家。我首先就想到了毛伦,我跟他约画,他大概说了下国画尺寸不同,内容不同,价格也不一样。我当时觉得他真是麻烦,随便画一张不就得了,他收到我发的短信后怒了。跑过来要揍我,说我这是在侮辱他的创作,他对每一张画都是用生命在对待。他同样说,下次要是再这样不尊重艺术,一定狠狠揍我。
前后三次他都想揍我。我总结一下,他大概对自己的身体、艺术、女人这三样东西最为看重,这些不能随意碰,否则就要对我动手。艺术家天然就具有棱角,我予以理解和尊重。在去龙岩宾馆的路上,我把这个观点对毛伦进行了表示。他打开车窗,不屑地“嗤”了一声。他说,难道你没有个性吗?你还是个小说家,写文字的没有点个性,作品怎么会有人看?我说,人的个性与文字的个性并不必然是正相关,再者说了,我不认为自己很有棱角,你看我本职工作是记者,要是太有性格,怎么和人打交道?我在该低头时就低头,该弯腰时就弯腰……
所以你的小说没特色,没人看啊。
我踩了下刹车,看着前方说,你说得还真是呢。
但你又想太多。内心深处渴望飞翔,但肩上的翅膀早就被打断。毛伦转过头看我,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犯焦虑症的原因之一。
对于毛伦的分析,我认为非常正确。我重重叹息了一声。晚上我去找裴斐斐,我一个人去,如果超过十点没回来,你就不用等我,自己睡了吧。
我本来还想问他,晚上真的不回家里看看老婆孩子?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四
裴斐斐这个名字太拗口了。当年我们一起玩的人群里头,就数她的名字难念。毛伦说名字里有三个“非”,这个女人以后不简单,是非比较多。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但后来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很乖,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或者是说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就是很乖。
毕竟,我也已经有七八年没见到她了。
在去见裴斐斐之前,毛伦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里了?裴斐斐你都不见?你和她在一起那么久。我说,我先更正一下,我认识她很久,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我和罗琳分手后,才和裴斐斐走在一起。你也知道的,斐斐原来是和邱劲好的。邱劲是我们的兄弟,我始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毛伦拉住我,你等会儿,你该不会是在斐斐和邱劲还没分手时插上一脚的吧。我瞪了他一眼,西门庆弄结拜兄弟花子虚,把他的妻李瓶儿搞到手,虽然快活,后来还是不得好死。毛伦踢了我一脚,你真是有病。
我说对啊,我就是有病,焦虑症,而且很严重。这句话我也对裴斐斐说了一遍。我和斐斐打电话,说要去见她的时候,她吃了一惊,然后说“你有病啊”。斐斐说,你要去看医生呀,干吗来找我?我说,我现在龙岩,我和毛伦这次出来的主题是“寻找”,我们一起寻找失去的东西。斐斐冷笑,哦,那就是说我是“东西”?我说,你不是“东西”。斐斐气得骂我,王林,你才不是个东西!
虽然隔着电话,但我能想象斐斐生气的样子。她大大的眼睛,像极了那个影星“小燕子”赵薇。就算生气,也只是噘着嘴,从来没见过她真正动怒的样子。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个人想法,这么多年,不知道会发生、改变什么。现在的时代发展太快,专家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国外西方列强曾经足足走了两百多年才完成。一个国家如此,不用说个人了。没有多少人活在过去,也不会有人一成不变。斐斐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应该不可能。
但我会一直记得她原来的样子。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冯小刚导演的一部大片《夜宴》。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毫无印象。我那时只隐约觉得我们之间将要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她脱产来厦门念成人本科,我刚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两个孤单的人碰在了一起。但因为某些令人尴尬甚至难堪的原因(比如她曾是邱劲的女朋友,而我和邱劲一度同穿一条裤子),我们好像有些见不得光。我们心中虽然知道这是毫无必要,但感觉总是有些怪异。这导致我们虽然很愉快度过了一段时间,但都清楚最终一定会散去。
于是,散去前我们看了《夜宴》这部电影。我觉得电影和我们的主题真是贴切。宴席上觥筹交错,杯光酒影,但喧闹过后就是宾主两散。斐斐问我,你是故意选这个电影的吧?我耸耸肩,真是天意。她听后就不再说话,我握着她的手,紧紧地不愿放开。电影结束后,我们在商场里随意走着,似乎都想把时间再拖延久一些。我问,你真的要回龙岩?你来念书,现在拿到文凭了,就不能留在厦门?她笑了,那你留我吗,王林?哈,你好像有点紧张,放心啦,我不会要你答应或者许诺什么的。我要回去,这里没有我的家人。我们都是从家乡小县城出来,但我跟你不一样,你有能力再往前一步,而我能跳出县城,到上面的龙岩市就已经很好了。厦门唉,经济特区,大城市。
这跟城市大小有什么关系?逻辑不对。不是城市越大,越能容留下人吗?
城市越大,越孤单。斐斐停下脚步,很坚定地看着我。在这里,我的心安定不下来。
我本来很想问她,是不是心有所属,就可以安定下来?但后来思考了一下,决定还是放弃了。我那时真为自己的懦弱和無能而羞愧——我什么也答应不了,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敢。
王林,你不用不安。斐斐笑了笑,甩着她好看的长长的马尾辫。你有远大前程,你要一直往前走。
狄更斯写《远大前程》的时候,离婚,与年轻女演员爱伦有婚外情,同时加上对社会黑暗的更加深入了解,因此乐观情绪受到了极大削弱。小说里的皮普最后回归了乡间少年曾经的质朴内心。斐斐也许并不清楚这部小说的内容。但没关系,多年后的如今,我在电话里告诉她,当你见到我,就会知道《远大前程》说的是什么。而我,似乎走了很远很远,但实际上一直留在原地。
裴斐斐在电话里沉思了很久。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我们可以一见。今晚,你来我家吧。
斐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又睁得圆圆大大的。整体看来,她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马尾辫不再扎了,头发剪短了,还做成了流行的韩式空气刘海。我尴尬地笑了,年纪大了么,老是正常的。倒是你还是显得年轻。我看了看她家,没有什么摆设,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显得很空阔。大门入口玄关处还放着好几个大箱子,好像是刚搬进来住。
这是你的新家吗?我问。
算是,住了快两年。她答。
哦,不经常在这里住么?好像家里没添置什么东西。
家里原来东西倒是不少,但最近都被我处理掉了。有的卖掉了,有的则送人。斐斐请我在餐桌前坐下,给我倒了一杯红酒。我准备去厦门了。
我的心一顿,抬起头看她。她说得很轻松,好像一件平常事,而我却觉得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记。敲在心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她煮了一桌的好菜,芥兰炒牛肉、白灼虾、干蒸鸡、酸菜爆炒大肠、西红柿炒蛋以及四物鸭汤,但我没有一点儿食欲。这几道菜我都很喜欢吃,我也曾在我租的房子里给她做过,现在轮到她做给我吃了,但我已经没有了动筷子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