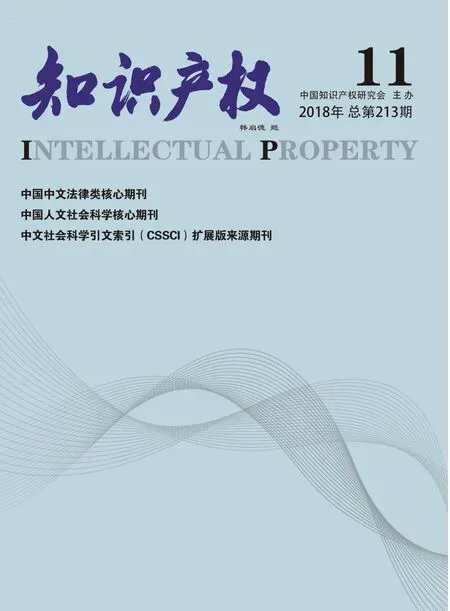论侵害知识产权的裁量性判赔
徐聪颖
内容提要: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在本质上属于侵权损害的法律评价机制,是法官合理解决当事人利益纷争的基本实践模式。就我国而言,法官在现阶段对裁量性判赔的运用存在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裁量性判赔的实效,法官的裁量活动应重点围绕损害评价内容的确定、损害评价过程的呈现以及损害评价策略的选择与运用等三方面工作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一个常话常新的问题。与学界对知识产权侵权构成理论的潜心研究相比,损害以及损害赔偿问题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司法实践中也获得了凸显,一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重侵权认定、轻判赔论证”问题,法官对判赔结果的分析往往具有大而化之的特点,而对参考因素的简单罗列和空洞的说理难免会使损害赔偿救济的公允性受到质疑。
为应对知识产权侵权判赔屡遭诟病之问题,近年来,裁量性判赔作为一种新的裁判观念进入学界和实务界的视野。就性质而言,有论者指出裁量性判赔是知识产权领域法定计算方式的下位概念,①齐茜:《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裁量性赔偿计算方法初探——以日本的损害额认定制度为参照》,载《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第9期。其与法定赔偿不同,是根据损失或者获利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②宋晓明:《新形势下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5期。但也有观点认为,裁量性判赔与法定赔偿实为属种关系,后者不过是裁量性判赔框架下羁束性裁量之体现。③曹新明、崔峰铭:《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实证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这一认知差异在司法审判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琼瑶诉于正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法院终审将酌定赔偿(裁量性判赔)定位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背景下一种有别于侵权违法所得和法定赔偿的损失赔偿方法。④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而在“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诉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纠纷案”和“中国好声音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终审则认为裁量性判赔是对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酌定,由此,相关判赔结果对法定赔偿上限的突破并非适用法定赔偿方式之特例。⑤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终50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京73民终1258号民事判决书。
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将裁量性判赔引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践在客观上令侵权赔偿数额屡创新高,但从裁量性判赔的过程来看,在判决书中占据最多空间的依然是波斯纳所谓的“形式化根据”,⑥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法律条文以及判赔考量因素的狂轰滥炸仍是惯常使用的裁判手段,至于法官的心证逻辑和裁判思路,则往往被杂乱堆砌的考量因素湮没其间。随着裁量性判赔在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被采用,我们必须直面其中存在的诸多基本问题:裁量性判赔的法律意义是什么?裁量的目标指向何处?裁量性判赔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法定赔偿将不再有用武之地?⑦有观点就认为,“法定赔偿的本质是在降低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借助法官的自由心证去获取实际损失、违法所得等要素的估量值。”循此思路,那种摒弃法定赔偿而代之以裁量性判赔的主张也在情理之中。相关论述参见杨红军:《对我国版权侵权赔偿制度的结构性反思》,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张书青:《浅议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完善》,载《专利法研究(201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2页。适用裁量性判赔应受到何种条件限制?裁量的内容应包括哪些方面?裁量的逻辑如何得以展开?对上述种种疑问的思考与回应,都将对合理运用裁量性判赔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也正是写作本文的初衷所在。
二、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的理据
裁量性判赔并非知识产权领域所独有,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于减轻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负担和降低证明标准。⑧有观点认为,裁量性判赔是在计算赔偿所需的部分数据确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下,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要的其他数据,从而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参见《酌定赔偿更接近权利人损失,赔偿数额更合理》,载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0/id/111098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2日。从比较法上看,在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赋予法官根据言辞辩论情况和证据材料对判赔数额的裁量权,已是较为常见的诉讼制度设计。例如,在德国、日本、奥地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在损害或损害额证明困难或者难以证明时,法官可综合考虑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经由心证对损害金额作出判断的规定。⑨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8条,《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73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22条。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损害额认定制度,并定性为证明度减轻和裁量评价的结合。⑩毋爱斌:《损害额认定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对损害或损害额的证明度难易的认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融入法官价值判断与规范评价的过程。在解决损害赔偿纠纷时,法官对损害的概念认知以及对损害范围的合理把握将贯穿始终,是判赔结果最终得以形成的基础,这使得程序法上的裁量性判赔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与实体法上的损害论问题发生勾连。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损害是一种因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不利益结果,对此种抽象“不利益”的把握,司法实践主要秉承的是“自然的损害概念”。自然损害概念体现于差额说,⑪王泽鉴著:《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通过对受害人现实的财产状况和假如损害事件未曾发生时应然的财产状况进行比较,以财产总额的变化彰显“不利益”。然而这一损害认定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每每会遇到与公平正义观念相悖的难题。⑫参见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3页。鉴于有些侵害行为虽不会在客观上令受害人的总体财产发生减损,但如不认定损害,则明显与社会通常的观念认知相悖离,此时法官需在个案中偏离“差额说”转而依赖“价值衡量”对特定损害作出规范评价。从逻辑上讲,此种规范性损害与损害的金钱评价确属不同问题,二者一为损害之认定,一为赔偿之量化表达,但这种区分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损害的定位往往与损害赔偿的范围、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问题交相融合,以至于成为法官裁量性判赔的题中应有之义。⑬在这方面,以精神损害赔偿最为典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以“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这表明“事实上的不利益”必须经由法律的限定方可转化为被法律认可的“可赔偿损害”,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重要考虑因素。
在法律意义上的损害得以确立之前提下,对损害赔偿范围的划定更是需要借助法官的裁量实现从“可赔偿损害”向“应赔偿损害”之转化。换言之,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是经过裁剪的有限范围的救济,⑭姜占军:《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中的法律政策》,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是在特定法律政策指引下藉由法技术工具进行过滤的结果。对此,在民法学界持“有限赔偿原则论”的学者认为,事实上的损害是法律上的损害之存在前提,在对前者加以证明的基础上,还必须经过由各项价值判断构成的弹性评价体系之过滤,根据行为的因果关系贡献度、过错程度、利益受保护力度、行为正当化程度以及受害人自身的归责程度等,来适度消减应赔偿的损害范围,以实现价值上的妥当。为此,损害的金钱评价过程以及计算方法的选择也是形成合理判赔结果的重要技术调控手段。⑮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即便是坚持“完全赔偿原则论”的学者,也认为需要在事实上的不利益、法律上的不利益、经过限定的损害与真正的可赔偿损害这几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分,经过层层的司法筛选以最终确定损害与赔偿彼此对应的范围。⑯曹险峰、徐恋:《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之逻辑进路论纲》,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至于其所倚重的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标准,事实上不过是一种“价值衡量”之化身而已,⑰梅益峰:《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之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是判断赔偿范围之际的利益或政策斟酌工具。
与有体财产相比,裁量性判赔更是法官公允解决知识产权领域侵权利益纷争的基本手段。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其实质是对知识产权蕴含的资产价值的损害,⑱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但知识产权价值形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却对损害事实及损害范围的认定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原因在于:(1)作为知识产权价值形成的基础,知识产权客体是创造物而非种类物,⑲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其价值并不像有体物那样能够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对一部作品或者一项发明创造而言,作者或发明人所付出的智力劳动量与劳动成果的价值高低往往没有对应关系,在此,劳动价值论让位于市场价值理论,⑳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知识产品生产者的成本投入能否获得回报取决于市场的评判与认知。(2)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及其大小,是众多市场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价值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对特定知识产品进行商品转化并对其市场需求加以培育的过程,这不仅关乎创造天分,更与经营资源、经营手段的有无和多寡息息相关。由此观之,便不难理解“纵容侵权”和“放水养鱼”等经营策略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行其道。(3)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知具有长程性和变动性,这意味着,虽然未来的机会利益是知识产权价值考量的重要方面,但却难以被准确把握和预期。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许多作者都经历了生前没落、身后作品却大放异彩的反转。著名者如“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巴赫、后印象派先驱梵高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其作品都是在作者死后声誉渐隆,获得世人推崇。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考量,本文认为裁量性判赔不能被单纯看作是一种用于量化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数额的变通手段,更不应将其定性为在运用具体数量计算规则时解决部分判赔证据缺失问题的权宜之计。面对诉讼当事人的索赔请求,法官所依恃的损害理论、对损害事实的认定以及对损害范围的把握都必须建立在对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予以合理判断的基础上,如此方可确保对赔偿数额的金钱评价能够在符合市场逻辑的框架下展开,并有助于法官有的放矢地甄别筛选证据材料,避免陷入对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要么过于苛责要么过于缓减的怪圈。从这一角度看,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其实贯穿于侵权损害赔偿裁判的各个环节,从赔偿责任的证成到责任范围的划定,从损害构成的分析到赔偿方法的选择,从计算规则的运用到证据材料的运用,无不需要法官的心证活动参与其中。
曾有学者将酌定赔偿(裁量性判赔)视作2.0版本的法定赔偿,㉑宋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探讨——以实证分析为视角》,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5期。但裁量性判赔的内涵远非法定赔偿可比。就性质而言,法定赔偿只是一种与“具体计算”相对应的以“定额估算”为外观形式的简化赔偿计算方式,其以提高诉讼效率为主旨,具有兜底使用的法价值。㉒同注释⑱。虽然法定赔偿的目标并非要达到数学上的精确,以至于被看作是“替代‘实际损害赔偿’的金钱救济途径”,㉓王迁、谈天、朱翔:《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与反思》,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5期。但法官依然需要尽力使赔偿结果在价值判断上具有妥当性。与法定赔偿相比,裁量性判赔在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规的损害评估机制,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将法官的心证活动加以阶段性分解,使之形成一个富有逻辑层次的思维结构体系,引导法官在其中结合个案的诸多考量因素,更好地条分缕析,进而为包括法定赔偿在内的各种损害计算方式的合理选择与运用指明方向。㉔从这一意义上看,本文赞同孔祥俊教授对裁量性赔偿的定位,即“这种赔偿不是法定赔偿,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赔偿方式,裁量只不过是确定实际损失的一种途径,仍然属于按照实际损失赔偿的范畴。”参见孔祥俊:《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期。
三、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的逻辑展开
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救济的逻辑起点,损害认定并非单纯对客观事实的发现,而是一个需要将法律评价融入其中的过程。这正如学者所言,损害兼具“事实—法律”之二象性,现实中的任何损害都有事实和法律的双重性格,只不过不同损害的两种性格权重存在差别。㉕张平华:《事实与法律:损害的二象性及其展开》,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2期。与损害的事实性格具有客观性、有形性、确定性相比,损害的法律性格主要表现为评价性、无形性和不确定性,必须借助法律加以判断。从这一角度观察,损害的二象性决定了裁量性判赔的活动场域,而准确把握损害的法律属性,则是法官合理运用裁量性判赔的关键所在。
(一)侵权行为的成立与损害发生的认定
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侵权事实与损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当然的对应关系,也并非所有的侵权样态都可以借助法技术手段推定损害结果的发生,这在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专利权为例,对他人专利产品未经许可的许诺销售固然构成侵权,但许诺销售仅为一种出售愿望的表达,在实际销售行为尚未发生的情形下,仅凭许诺销售事实通常不足以认定损害的发生,此时只需要责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责任即可,除非有证据表明侵权人实施许诺销售的具体方式、范围或者规模使专利权人遭受了实际损害。㉖尹新天著:《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基于此,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会以被告的许诺销售行为既未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也未从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为由,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而将被告的赔付责任限定于权利人的合理维权开支。㉗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33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4011号民事判决书。而在有的案件中,尽管同样无证据证明有销售事实存在,但法官依旧会综合考虑案情对侵权损害作出肯定性法律评价,只不过此种单纯因许诺销售而引发的损害究竟如何获得定位仍有待进一步澄清。㉘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544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知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三终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10号民事判决书,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初3174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知民终字第009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甬知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在著作权领域,精神损害的认定与侵害著作人身权或者表演者人身权之间无必然联系自不待言,㉙例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发布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中,其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则便明确指出,被告仅侵害著作人身权的,一般不判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在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且采用其他救济手段不足以抚慰权利人的,才可以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之8.3和8.16。类似的规定还可以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即便是对著作财产权的侵犯,法官仍可能会斟酌涉案作品的市场价值,对权利人的赔偿损失请求作出不予支持的裁定。例如,杨振中与杨德栋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㉚参见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庆中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在认定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作品著作权侵犯的同时,也指出原告作品系族谱,只能在族人内部销售,不以营利为目的,据此驳回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而仅对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了支持。
如果说在专利权和著作权领域,侵权事实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具有对应关系仍属于“小概率事件”,那么在商标权领域,基于商标权自身的特点以及商标侵权样态的多元化,将损害认定作为诉讼过程中联结侵权裁判与判赔裁量的单独一环就显得尤为必要。首先,商标价值的形成基础在于使用,如果商标长期“注而不用”,则其徒具形式意义,此种商标与发挥识别功能、承载商誉的实质意义的商标在价值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㉛参见范晓波:《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究》,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第73-82页。而这也将对侵权损害的认定产生直接影响。对此,我国《商标法》第64条有关损害赔偿抗辩的规定即是明证。㉜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没有被真实持续使用的注册商标,没有实际发挥识别作用,没有承载商业信誉,他人也就不可能利用该商标信誉进行牟利。因此,侵权方仅需承担停止侵权责任。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终275号民事判决书。其次,即便商标业已实际投入使用,法官仍会参照商标权的价值高低以及侵权行为对商标权有无实际影响等因素,以“涉案侵权产品未实际进入市场流通”“原告商标知名度过小”“涉案被告侵权情节轻微”或者“原告未提供损失证据”等为由,拒绝对商标权人主张的侵权损害提供赔偿救济。㉝参见徐聪颖:《我国商标权法定赔偿的现状及反思》,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82-83页。再次,从理论上讲,为了能够实现对商标权的充分保护,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商标侵权的认定所遵循的是“盖然性标准”,通常以可能造成混淆或淡化作为侵权成立的条件,但“商标侵权的认定并不能够使商标权人自动获得损害赔偿救济”,㉞Terence P. Ross,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Damages and Remedies,New York, N.Y. Law Journal Press, 2000,§4.01.在“侵权事实”与“损害事实”之间,仍有待法官综合考虑案件的主客观因素作出令人信服的逻辑联结。㉟以商标淡化为例,《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在对《兰哈姆法》中有关损害赔偿部分的规定进行评论时,便特别强调,其所作出的评论并不适用于商标淡化诉讼,因为反淡化法案在此类诉讼中通常仅提供禁令救济。而美国学者麦卡锡教授也认为,在反淡化诉讼中,请求损害赔偿的商标权人仅证明存在“淡化的可能性”还远远不够,其还必须证明确有淡化的现实危害发生,并能提供合理计算损害的方法。
(二)损害的法律评价与赔偿范围的划定
损害的法律评价不仅关乎损害事实的证成问题,更会对损害赔偿范围的合理确认产生直接影响。在学理上,对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划定同样兼具有事实发现与价值评判的双重色彩。为更好地实现侵权损害赔偿的法规范效果,减缓因奉行“完全赔偿原则”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全有全无”赔偿模式对人们公平观念和价值认知的冲击,㊱对完全赔偿原则的检讨可参见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或在司法实务中或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诸如“损益相抵”㊲损益相抵又称损益同销,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16条之1即规定,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受有损害并受有利益者,其请求之赔偿金额,应扣除所受之利益。“与有过失”㊳与有过失,是指在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也存在过错时,可减轻甚至免除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和第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民法通则》第131条均有类似的规定。“过失与责任比例”㊴过失与责任比例原则,是指义务人的赔偿数额应与其过失程度相符,即依过失的轻重认定行为人应赔偿的数额。对此,《瑞士债法典》第43条第1款的规定体现得最为明显。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1条和第32条有关过度防卫和紧急避险失当的赔偿规定也是对该原则的体现。“酌减赔偿”㊵酌减赔偿,是指在赔偿义务人并非以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情形,如义务人因给付赔偿而陷于窘困状态时,法官可酌减损害赔偿义务。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18条和《瑞士债法典》第44条第2款等均有明文规定。等事关损害判赔的配套性规则。虽然这些规则的要件构成各有侧重,但其主旨均在于为法官合理限定损害赔偿范围提供裁量的活动空间,以确保对个案中当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
就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判赔实践而言,“比例协调”是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第(十一)项规定。要求“应注意根据侵权人的性质、作用和主观恶性程度,区分不同情况,恰如其分地给予保护和确定赔偿。”㊷同注释②。对此,前文提及的用以合理限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制度规则理应在其中发挥应有功效,为法官的具体裁量活动提供路径指引。以侵权行为对权利人产生的影响为例,由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形成具有复杂性,相关侵权后果也并非对受害人全然不利。例如,有学者针对发生在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唯冠)与美国苹果公司之间的“IPAD”商标纠纷就曾指出,尽管“IPAD”商标权归深圳唯冠所有,但经过侵权人苹果公司连续多年不遗余力的品牌经营,该商标的价值已实现巨额增殖,在解决双方利益纷争时,应当对此部分增殖权益的归属有所考虑。㊸邓建志、雍彬:《论商标侵权使用中商标价值增殖利益之归属》,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3期。虽然论者建议应以“不真正无因管理”中的误信管理规则解决上述问题,但在本文看来,此种因侵害他人权益并使受害人获有利益之情形,当事人的利益分争更适宜由损益相抵规则加以规制,而与“不真正无因管理”的规范旨趣不相吻合。㊹从学理上讲,不真正无因管理(又称准无因管理或不法管理)制度的法律意义在于,通过准用无因管理的原理,来解决侵权人的利得吐出问题。至于学者所谓的误信管理,在德国等规定有准无因管理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并未得以体现。即便在学界有观点主张误信管理属于准无因管理之一种类型,也是侧重于强调其对于被管理人要求管理人返还利得的意义,而不认为其构成误信管理方主张管理利益的法律基础。参见洪学军、张龙:《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它请求权的竞合研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5期;赵廉慧:《作为民事救济手段的无因管理——从准无因管理制度的存废谈起》,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在知识产权领域,损害的法律评价之于赔偿范围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鉴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当事人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往往因利益多元化保护的需要一并提出反不正当竞争诉求。虽然此类诉讼在外观上均表现为请求权的并存与合并审理,但其成因却不尽相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因同一行为侵犯数个客体,构成多个违法行为的形态,属于“想象的法律竞合”或“外观的法条竞合”,㊺参见谢晓尧著:《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9-80页。此时法律责任(含损害赔偿责任)竞合是法律规范竞合的组成部分,㊻孔祥俊著:《商标与不正当竞争法:原理和判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可由受害人在对不同规范的法律效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择一追究。而在有的案件中,请求权的并存纯系数个违法行为所致,鉴于此种情形已超出规范竞合的范畴,需对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无重合的可能作出合理评价,而这将对赔偿范围的合理划定和判赔精细化水平的提升大有裨益。㊼例如,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红门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法院一审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并据此判赔损失5万元;但在二审中,法院认定被告在其网站销售宣传中使用“红门”标识和在企业名称中使用“红门”文字的行为分别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并就商标侵权损失和不正当竞争损失裁定被告分别赔偿10万元。然而从判决表述看,法官对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危害的把握并无二致,均立足于市场混淆和消费者误认,仅凭此点似乎不足以构成单独判赔的事实基础。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344号判决书。
此外,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也并不完全遵循“回看式”利益救济原则,在某些特定场合,还需要法官运用“前看式”利益调整策略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做出裁定。这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权利的不确定性使得法官必须警醒禁令救济所产生的外部性成本问题,避免因过度适用停止侵害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㊽参见陈武:《权利不确定性与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之限制》,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为此,替代性赔偿成为兼顾私益与公益平衡关系的必要调整手段。从本质上讲,替代性赔偿是一种由法官主导的允许侵权行为不停止实施的司法定价机制,尽管如学者所言,这一定价机制并不完美,其优越性往往受制于司法估值客观真实性的缺失,㊾参见杨涛:《论知识产权法中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适用——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分析视角》,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适用停止侵害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重大失衡或对社会公共利益明显不利的情形,替代性赔偿无疑将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协调效率与公平之间内在冲突的重要裁量场域。
不仅如此,即便从实现“完全赔偿”的角度观察,将判赔范围局限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所遭受的现实利益减损也并不充分,还必须对受害人为恢复其应有状态所需花费的支出给予必要关注。从理论上讲,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大陆法系民法中损害赔偿的两种基本方法,分别与保护受害人的完整利益与价值利益相对应。㊿有关完整利益和价值利益的论述可参见程啸、王丹:《损害赔偿的方法》,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虽然恢复原状乃侵害人的义务,但鉴于由侵害人一方实施恢复原状并不当然对受害人有利,应当尊重受害人选择自行实施或请人实施恢复原状的权利,而侵害人由此需承担的费用也不必以受害方实际先行垫付为先决条件。[51]参见李承亮:《损害赔偿与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上述问题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例如,在侵犯商标权或商誉的案件中,有学者便指出,责令侵权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对于能否使受损的商誉真正得到恢复是值得怀疑的,与之相比,判令侵害人赔偿修复商誉的合理费用是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救济措施,[52]黄骥:《论我国商誉损害赔偿计算规则的完善——以美国相关规则为借鉴》,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而这同样需要法官借助“前看式”的利益调整策略对赔偿范围作出合理判断。[53]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反向混淆案件“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案”中,美国第十巡回法院判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67.8302万美元的纠正广告费用,同时基于初审法院确定的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6:1的比例关系,裁定被告需承担406.9812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但该案的特点在于,因为原告的经济实力有限,其在庭审之前尚未投放广告来消除被告行为的不良影响,这使得所谓的纠正广告支出其实建立在预测基础上。参见561 F.2d 1365, 195 U.S.P.Q. 417 (10th Cir. 1977).
(三)损害类型与计算策略的选择
在损害以及赔偿范围获得确定的基础上,损害计算是判赔的最终一环。然而,损害计算也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数学任务,在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法官所面对的是各种计算要素缺失的不完美状态,需根据损害的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计算策略,进而以市场重构或模拟交易的方式完备损害计算的条件。[5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曾世雄教授指出,损害赔偿之计算,兼具事实、法律二问题之性质。谓事实问题者,盖以损害事故所造成之损害如何,本质上为一种事实。谓法律问题者,盖以探讨该一事实,须借助法律方法。参见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在学理上,损害类型的区分因视角差异而有所不同:如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差额损害与规范损害等。就知识产权而言,因侵权而发生之损害主要表现为所失利益,即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直至损害裁判时权利人应得而未得之利益。为此,法官的所失利益计算原则上应以受害人的现实财产状态与假设财产状态的差额比较为出发点。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对受害人假设财产状态的认定往往陷入“事实真伪不明”的困境,虽然立法或可借助推定、举证倒置或举证妨碍等规则简化所失利益的计算,[55]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专利、商标民事纠纷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将侵权方在市场上的商品销量推定为权利人因侵权所减少的销量的规定。但囿于知识产权所失利益发生的原因力十分复杂,对法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甚至机械运用反而会削弱损害计算的可靠性,为此,法官的“差额比较”必须充分体现市场逻辑并符合相当因果关系要求,[56]相当因果关系在学理上属于损害归责范畴,其由条件关系和条件关系的相当性构成,是法官借以检视侵害事由之于损害发生(责任成立)以及损害结果(责任范围)的原因力强度,进而权衡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妥适与否的法律政策工具。参见王泽鉴著:《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106页。以尽可能地增强判赔结果的可信赖性。[57]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卡斯特商标侵权案”中,法院便言明赔偿数额应当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原审法院查明被告进口的涉案葡萄酒的总价值为3196万元,但考虑到诉争商标的历史纠葛,各自商标及商品的知名度,特别是被告并无侵犯原告商标的主观恶意等情况,不宜认定被告获得的利益全部系侵害原告商标权所致。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将判赔数额由一、二审认定的3373万元大幅消减为50万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5号判决书。
如前所述,“差额比较”也并非知识产权损害认定和计算的唯一视角。在权利人因举证困难或无法满足相当因果关系要求而难以合理证明其财产应然状态的情形,法官可转而基于社会通常之公平观念对损害予以规范化评价。作为“自然损害论”的修正和补充,“规范损害论”是对各种与“差额说”相区别的有关损害赔偿认定学说的概称,其着力考察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和价值,即市场交易机会的破坏,[58]同注释⑱。这与因市场份额丧失或价格遭受侵蚀而导致的“差额损害”明显不同。与之相对应,司法实践中对知识产权“规范损害”的计算也应围绕有效修补市场交易机会展开。一般而言,法官对知识产权“规范损害”的计算可遵从对价逻辑,通过在原被告双方间虚拟交易,以偿付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方式实现对权利人市场交易机会的救济。[59]在虚拟谈判中,作为交易一方的权利人要比其在现实谈判中明显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例如,虚拟谈判双方对于权利的有效性不持任何异议,相对方没有拒绝谈判的选择权,谈判双方知悉与谈判相关的所有商业事实且不存在对谈判达成后的前景进行利益博弈的问题。虚拟谈判的这些特点意味着对知识产权规范性损害的司法定价一般高于权利的现实许可交易价格。而这也正是我国知识产权法规定可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斟酌赔偿数额的原因所在。参见Richard B.Troxel and William Owen Kerr, Assets and Finances:Calcul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mages, Thomson/West(2008 Edition),§5:8.但需说明的是,在侵害商标权的案件中,由于商标权的禁用权大于使用权,这一特点决定了商标权人无权在其禁用权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特定商标,这使得此种情形下的“规范损害”不应表现为许可使用对价,[60]参见李琛、汪泽:《论侵害他人商标权的不当得利》,载《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而应根据侵权行为对商标显著性、功能和知名度等价值因素的影响,合理估算为恢复商标获利能力所需花费的费用。
从本质上讲,对知识产权规范损害的认定和计算是法官运用司法权力参与知识产权市场定价的体现。这其中,无论法官采取的是数量计算规则还是定额计算规则,都应兼顾涉案的主客观(普通与特殊)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市场交易环境的重构。单就此点而言,其与所失利益计算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是法官借助市场假定法、可比价格法和行业平均法等经济分析方法提高损害计算科学性的重要场域。
四、我国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的完善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作为贯穿侵权损害赔偿过程始终的法律评价机制,裁量性判赔绝非为缓解制度运行困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是法官妥适处理侵权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纷争的基本实践模式。在司法语境下,法律问题不是一个真与假的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61]霍海红著:《证明责任的法理与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与之相对应,损害并非纯粹生活事实,对所谓损害事实的还原需要法官借助市场逻辑、公平观念与价值判断对损害以及损害结果进行体系化的认知。基于此,在法官的判赔活动中,心证与权衡必须内化于心,成为其有效解决侵权赔偿问题的思维自觉。
就我国而言,裁量性判赔的适用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已不鲜见,但其形式意义却远大于实质意义。作为损害的法律评价机制,裁量性判赔是否取得实效与法官在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密切相关:评价内容的确定、评价过程的呈现以及评价策略的选择与运用。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法官的裁量性判赔仍停留在对各种考量因素进行简单列示的层面,若非判决书中对此种判赔在称谓上有明确的表述,或者判赔结果对法定赔偿的上限有所突破,法官对裁量性判赔的运用几乎无从获得体现。有观点认为,通过明确考量因素的优先次序并进行释明或理由阐述,也能够使判赔之司法裁量过程获得较为清晰地呈现。[62]同注释③。然而,这一主张的更紧要之处在于,法官对各种考量因素进行排序的依据是什么?又如何对各主要考量因素之于判赔结果的影响进行说理?如果这两方面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澄清,则所谓的“排序”与“释明”难免又将沦为形式,无法起到羁束法官恣意裁判的作用,更不能作为示范性案例为同类案件提供方法论指导。
为确保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真正落到实处,法官的裁判活动应当遵循以下三方面原则:其一,作为判赔裁量的起始环节,损害事实的证明与认定在知识产权侵权判赔活动中不可或缺。法官不应武断地将“侵权事实”与“损害事实”简单混同,而应将后者作为侵权认定与判赔裁定的联结,以便更有针对性的引导案件当事人就“损害事实”问题开展质证分析。其二,裁量性判赔应当清晰地、合乎逻辑地展示法官对损害的具体评价意图。基于规范心证活动和羁束自由裁量权的考虑,法官需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解损害的法律评价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裁量性判赔信息进行规范性填充和准确传达,以有效发挥判决的规范和指引作用。其三,为有效避免当前裁量性判赔活动普遍存在的说理形式化、空洞化问题,法官应进一步加强对参考因素之于判赔意义的说理分析力度。鉴于对考量因素的简单罗列或排序并不能实质性改善裁量性判赔的精细化水平,法官应围绕裁量不同环节的具体评价目标,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有的放矢地选择和利用。有关裁量不同环节的法律评价目标可参见下图1。

图1 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法律评价目标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裁量性判赔并不是法官凭借一己之力的“独角戏”。从某种意义上讲,赔偿问题的根本也是证据问题,作为裁量性判赔的主导者,法官“实践理性”的形成与举证、质证、证据的审核、证明标准的把握以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官并非智识或道德巨人,如果缺乏可信赖证据材料的支撑,所谓的“能动司法”难免会捉襟见肘,甚至易于滑向“任性司法”的误区。基于此,合理的裁量性判赔工作应当在法官与案件当事人的充分互动中展开。诚如学者所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具体诉讼过程中的难题,而“诉讼”是实体法和诉讼法综合作用之“场”,因此对它的分析应当具有结合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二元观意识。[63]唐力、谷佳杰:《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2期。就裁量性判赔而言,法官在判赔证据问题上与涉案当事人的对话交流,无不需要以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为保障。从这一角度观察,本文的意义仅在于为知识产权裁量性判赔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路径,其能否在司法实践中被一以贯之,仍有待对相关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这已然是另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