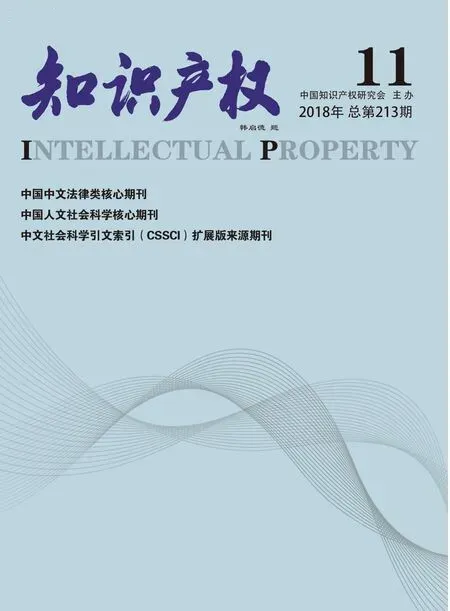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效果
李 扬
内容提要:F R AND承诺只不过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FRAND承诺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在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标准实施者有权获得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 RAND 许可(权利),但应当以符合F 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善意谈判(义务)。相应地,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权获得标准实施者支付的F RAND 许 可费率(权利),但应当以符合 F 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实施者进行善意谈判(义务);二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拒绝以 F RAND承诺的条件给予标准实施者实施许可时,其禁令救济请求以及超过F RAND承诺部分的许可使用费请求,不应当被支持,同时其行为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面临反垄断法上的不利后果。相应地,标准实施者拒绝以F 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谈判,或者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以F 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谈判,但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却违背诚信原则,未尽到善意谈判义务,则可能面临禁令的不利结果。
一、引言
由于专利技术标准化对标准实施者产生一定程度的锁定效应,使专利权人在相关市场中获得一定优势地位,近年来备受苹果、微软、三星、华为、中兴、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全球通讯领域内顶级创新企业的亲睐,并成为这些企业争夺全球通讯领域技术创新市场及其相关产品市场的制高点。不管专利技术被纳入事实标准还是法定标准,①事实标准是市场主体通过公平竞争自然形成的标准。法定标准是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组织制定的标准。2015年3月1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将政府主导的标准分为四类,即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推荐性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由于标准实施者在技术上有可能不存在其他替代性技术方案可以选择,并且可能面临着被禁令排挤出相关产品市场的命运,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可能因此像海浪一样上升,标准实施者因此可能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餐盘中的小菜。②参见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No.1:11-cv-08540 (N.D. Ill.) Opinion and Order of June 22, 2012, slip op. p18, 载 https://www.eff.org/fi les/posner_apple_v_motorola_0.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2日;林秀芹、刘禹:《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法规制——兼与欧美实践经验对话》,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2期。在禁令威胁下,标准实施者为了避免陷入侵权诉讼当中而付出更大代价,最终有可能不得不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签订不合理的许可使用协议,从而发生专利标准化过程中经常被谈论的专利劫持现象。③李扬:《FRAND劫持及其法律对策》,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而且,复杂技术产品往往包含成百上千个标准,每个标准又可能包含成千上万个专利,任何单个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都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必要专利引发市场的断裂,并造成专利使用费堆叠现象。④专利使用费堆叠(Royalty stacking)是指单个产品的生产可能侵犯许多专利,因而该产品生产者可能背负无数个使用费负担。Mark A.Lemley &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 85 Texas L. Rev. 1991, 1993 (2007).
专利劫持阻碍标准被采纳和推广以及专利技术的应用,增加消费者在不同制造商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损害消费者福利。为了消除专利劫持现象,许多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提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言有二:一是以各种理由全部或者部分否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获得禁令救济的权利;二是一些标准化组织在其知识产权政策中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不可撤回地以公平、合理、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以下简称FRAND)许可条件授权现实或者潜在的所有标准实施者实施其专利发明的承诺。
具有抑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专利劫持作用而被通讯领域内一些标准化组织作为政策规定的FRAND承诺,究竟具备何种法律性质,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议,也使得本就非常复杂不易解决的标准必要专利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本文将在评析现有各种关于FRAND承诺法律性质及其法律效果观点的基础上,简要谈谈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
从解决标准必要专利实务问题的角度看,探讨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并无实用价值。在因标准必要专利发生的纠纷案件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标准实施者和法院等中立第三方裁决机构主要关注的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按照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要求作出FRAND承诺之后,在包含必要专利的标准实施过程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各自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颁发禁令的要件和FRAND费率如何计算等问题,而FRAND承诺是什么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无实质性帮助。不过,既然理论和实务界对FRAND是什么的问题存在争论,有必要对该问题纯粹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澄清。
本文认为,FRAND承诺是一种行为,以此为前提,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要解决的问题是:FRAND承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如果属于法律行为,其属于何种性质的法律行为,即单方法律行为还是双方法律行为抑或共同法律行为,财产法律行为还是身份法律行为,负担法律行为还是处分法律行为,等等。
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按照萨维尼给出的定义,法律行为是“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⑤[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现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转引自李艳秋:《法律行为概念的检讨与反思》,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持该观点的还有德国著名民法学者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著:《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人的行为。法律行为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必须是外部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内在的心理活动不是法律行为;第二,必须是基于行为人意思表示的行为。先天无意志能力的行为、后天被胁迫而无意志能力的行为,不是法律行为;第三,必须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行为。⑥易军:《法律行为生效要件体系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常见的社交、恋爱等行为,不是法律行为。FRAND承诺是专利权人按照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要求,基于使其专利进入标准成为标准必要专利的目的,直接面向标准化组织和间接面向所有潜在的标准实施者公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作出后,不可撤销,会引起相应法律后果,因而FRAND承诺属于法律行为,对此理论和实务界应该没有疑义。
根据不同标准,法律行为有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共同法律行为之分,⑦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158页。亦有财产法律行为与身份法律行为⑧李永军主编:《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113页;丁慧:《身份行为基本理论的再认识》,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负担法律行为与处分法律行为⑨李永军主编:《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114页;尹田:《法律行为分类理论之检讨》,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之别。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尽管是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的要求,但其成立并不依赖标准化组织或者潜在实施者的意思表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一方作出FRAND承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因此和设立遗嘱、被代理人对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代理人辞去委托、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等一样,属于单方法律行为。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后,不可撤回,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了一个负担,属于直接使权利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处分法律行为。同时,专利权属于私权,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给其财产设定了一个负担,因而FRAND承诺又属于发生财产关系变动的财产法律行为。
FRAND承诺既非要约,也非要约邀请。首先,FRAND承诺不是要约。我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FRAND承诺仅表明以公平、合理、无歧视条件给予所有潜在标准实施者许可,对方当事人名称、标的、数量、质量和价款等合同基本内容都不确定。FRAND承诺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行为,该负担的设定,并不存在受要约人承诺与否的问题。同时,除了符合要约要件的商业广告外,要约一般是向特定相对人发出,可以依法撤回或者撤销,而按照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FRAND承诺并非向特定相对人发出,而且不能撤回。可见,FRAND承诺并不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其次,FRADN承诺不是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第15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FRAND承诺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⑩袁晓东、蔡宇晨:《标准必要专利转让后FRAND承诺的法律效力——英国“无线星球诉三星案”的启示》,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11期。并不存在希望标准实施者向自己发出特定要约的意思表示,因此也不符合要约邀请的构成要件。
FRAND承诺和诚实信用原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诚实信用原则是所有民商事活动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⑪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过程中,无论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还是标准实施者,都需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善意谈判。但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并不能替代FRAND承诺。一者,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按照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作出FRAND承诺,其专利最终将不会被纳入标准,无法成为标准必要专利。也就是说,没有FRAND承诺,就没有标准必要专利;二者, 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过程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进行了善意谈判,遵循了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表现为其是否践行了FRAND承诺。换句话说,FRAND承诺是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这种特定场景下,具有普适性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具体和特定要求。由此产生了如下不同:判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进行了善意谈判,主要看其谈判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是否符合FRAND承诺,而判断标准实施者是否进行了善意谈判,主要看其谈判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那种认为民法中已经存在诚实信用原则,因而FRAND承诺没有存在意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将FRAND承诺理解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标准必要专利转让之后,未作出FRAND承诺的新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也应当践行FRAND承诺。这类似于不动产所有人在其不动产上设定的负担(地役权)不因不动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改变而自动消灭,该负担将伴随标准必要专利始终。⑫Jay P. Kesan and Carol M. Hays, FRAND s Forever: Standards, Patent Transfers, and Licensing Commitments, Indiana Law Journal, (2014),89(1).至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后进入标准中的新专利,由于专利权人也需要针对这些后进入标准的新专利作出FRAND承诺,因而这些新专利负担FRAND承诺,则更不是什么问题。
三、FRAND承诺的法律效果
学界和实务界多将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混在一起,这使得本就有些棘手的问题更加复杂。其实,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两者并非一回事。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要解决的是,FRAND承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如果属于法律行为,属于何种性质的具体法律行为,也就是FRAND承诺在法律上是什么的问题。FRAND承诺的法律效果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具有特定性质的法律行为,FRAND承诺将会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分别产生何种权利和义务。
以上述第二部分的分析结论,即FRAND承诺只不过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前提,本文认为,FRAND承诺仅仅产生如下法律效果。
一是在标准实施者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围绕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标准实施者有权获得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RAND许可(权利),但应当以符合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善意谈判(义务)。相应地,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权获得标准实施者支付的FRAND许可费率(权利),但应当以符合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实施者进行善意谈判(义务)。
二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拒绝以FRAND承诺的条件给予标准实施者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时,其禁令救济请求以及超过FRAND承诺部分的许可使用费请求,不应当被支持,同时其行为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面临反垄断法上的不利后果。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拒绝以FRAND承诺的条件给予标准实施者许可,一般表现为以禁令相威胁,向标准实施者索要超过FRAND承诺条件的许可使用费。相应地,标准实施者拒绝以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谈判,或者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以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谈判,但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未尽到善意谈判义务,则可能面临禁令的不利结果。这种情况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禁令救济请求则应当被支持。标准实施者拒绝以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善意谈判,一般表现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故意拖延谈判,或者拒绝遵守中立第三方已经作出的有关FRAND费率的生效裁决。
上述法律效果,对于标准实施者而言,一方面可以保护其对FRAND承诺的信赖利益;⑬车红蕾:《交易成本视角下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的司法规制》,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另一方面则可以防止其谈判过程中出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非善意谈判行为,即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反劫持的行为。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而言,这一方面可以保护其专利权,确保其从专利实施中获得足够的回报,从而确保对其进一步进行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则可以防止其以禁令相威胁,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索要违反FRAND承诺的使用费,对标准实施者进行劫持的行为。从我国部分法院发布的相关工作指引或者指南看,应当说这些法院对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效果也进行了上述理解。⑭具体内容可分别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149-153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10-14条。
关于FRAND承诺的法律效果,除了本文上述理解之外,理论界和实务界还存在其他各种观点,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RAND承诺在标准化组织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创设了一个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该合同中的标准实施者为第三人,其拥有请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以FRAND承诺条件给予其实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独立请求权。⑮胡伟华:《FRAND原则下许可使用费的司法确定》,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5期。此种观点在法国和德国存在制定法上的依据,⑯《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人们为自己与他人订立契约或者对他人赠与财产时,亦得为第三人利益订立条款,作为该契约或者赠与的条件。如第三人声明愿意享受此条款的利益时,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契约的人不得予以撤销。《德国民法典》第328-335条对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作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在美国存在判例法以及学理上的依据。⑰美国早在1859年的Lawrence V. Fox一案中就承认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应,并成为近代法上第一个承认第三人享有诉权的判例。美国法学会编写的《合同法重述》对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作了详细的规定。1981年发表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进一步明确规定,受益人即使不确定也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只要受益人可得确定即可。同时该法还强调,如受益人基于对合同的信赖而实质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已就这一合同提起了诉讼,或者已向当事人表示接受该利益,则合同当事人不再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标准必要专利以及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带来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通讯技术领域,并且是总部位于法国南部尼斯的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以下简称ETSI)在其知识产权政策中率先提出来的,因此关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组织之间的纠纷问题应当适用法国法,进而根据法国合同法,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的FRAND承诺解释为在ETSI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创设了为第三人(标准实施者)利益的合同,作为第三人的标准实施者据此享有获得标准专利权人FRAND承诺条件许可的权利也顺理成章。
问题在于,司法实务中围绕通讯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生的纠纷,并不在ETSI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而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而且主要围绕标准必要专利费率和禁令进行,更重要的是,裁判纠纷的法院所在地往往不在法国。⑱例如: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lnc.案、Apple, Inc. v. Motorola, Inc.案、Apple Inc. v.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案和Ericsson,Inc. v. D-Link Systems, Inc.案的审判法院为美国法院;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案的审判法院为英国法院;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ZTE Corp.案的审判法院为欧洲法院;华为诉IDC案、华为诉三星案、西电捷通诉索尼案的审判法院为中国法院;苹果日本公司诉三星案的审判法院为日本法院。这种情况下,直接适用法国法,将FRAND承诺解释成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并据此解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之间的费率和禁令纠纷,可能存在法律适用时的司法主权问题,法理上似乎难以成立,实务上也难以操作。
在我国,至少现阶段认为FRAND承诺在标准组织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创设了为第三人(标准实施者)利益的合同,制定法上不存在解释依据。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明确规定,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据此,尽管理论界存在争论,但司法实务中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合同法对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并未作出规定。认为FRAND承诺在标准组织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创设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观点,在我国现阶段,除了立法论上的意义外,并无解释论上的价值,对司法并无实际指导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就像供水、供电、供气和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一样,处于垄断地位,因此FRAND承诺给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创设了强制缔约义务。⑲田丽丽:《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FRAND原则的适用》,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第2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供水、供电、供气和供热合同中,供方往往独此一家,具有垄断地位,供方提供的服务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使用人是社会公众,供应人对于相对人的缔约要求无拒绝权,其收费标准由国家规定,合同具有公益性、持续性和格式性。标准必要专利虽然由于标准的公益性而具有一定公益性,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即使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必然滥用该地位而存在反竞争的效果,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很大争议。同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最终达成的合同并非格式合同,收费标准也由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确定,而非国家直接规定。一句话,FRAND承诺源于标准化组织的政策,并未源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强制缔约义务,FRAND承诺并不存在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设定强制缔约义务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也不产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负有与标准实施者强制缔约义务的结果。
第三种观点认为,FRAND承诺意味着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默示许可所有标准实施者实施其标准必要专利。⑳易继明:《专利法的转型: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章及修改条文建议》,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7期。我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采用此种观点,其第85条规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不披露其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的,视为其许可该标准的实施者使用其专利技术。许可使用费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此种观点和做法,正如很多不同意见指出的那样:一是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实务中标准参加者很少有不披露其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的,默示许可基本没有适用的场景;二是此种做法将导致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获得禁令救济,因此可能导致产生标准实施者严重反向劫持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现象,造成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过分失衡;三是将许可使用费纠纷裁决权交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是对自由谈判市场的过度干涉,对司法而言,则存在越俎代庖之嫌。
第四种观点认为,FRAND承诺给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创设了一种先合同义务。㉑胡洪:《司法视野下的FRAND原则——兼评华为诉IDC案》,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5期。此种观点更不能成立。先合同义务,是指在要约生效后、合同生效前,缔约双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应当负担的告知、协力、保护、保密等合同附随义务。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我国《合同法》第42条和第43条对先合同义务及其法律后果作出了明确规定。先合同义务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始于要约生效,终于合同生效。要约生效前,双方仅仅是一般人之间的关系,相互间的期待和义务很弱,尚未进入特殊信赖关系范围。随着双方接触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要约生效后,双方进入特定信赖关系,要约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开始产生约束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约的必要准备工作,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才有实际意义。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时,一般与潜在实施者尚未进行任何接触,未针对特定实施者发出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具体要约,更不存在与实施者进行缔约谈判的任何行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的FRAND承诺,不可能给其创设一种所谓的先合同义务。
第五种观点认为,一旦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即意味着金钱救济足以满足其保护标准必要专利权的要求,也就意味着其放弃了请求禁令救济的权利,如其寻求禁令救济,则构成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的行为。㉒丁亚琦:《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反垄断的法律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2期。此种观点某种程度上与上述默示许可论本质相同,即都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后,无权再寻求禁令救济。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抹杀了标准必要专利作为专利权的本质,从根本上剥夺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获得法定救济的权利,必将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陷入被标准实施者反劫持而束手无策的不利境地,将严重减损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创新的激励。而且从我国法院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引看,法院也并未一刀切地采用此种将造成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利益天平过度失衡的观点,而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具体认定双方过错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支持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禁令救济主张。㉓祝建军:《标准必要专利适用禁令救济时过错的认定》,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3期。
结 语
FRAND承诺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场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关于FRAND承诺主要集中在智能手机对蜂窝标准技术的应用方面,现有各种标准化组织中,㉔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标准化组织有: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IEEE-SA) ;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ANSI);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 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OASIS); VMEbus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VITA);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也只有ETSI在其知识产权政策中,明确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据此,对FRAND承诺法律性质及其法律效果的讨论,都不能脱离这个特定事实。甚至可以说,只有基于作为蜂窝技术标准化组织的ETSI的知识产权政策来讨论有关FRAND的问题,才是有基础的、恰当的。脱离这个基础的漫谈,不但没有实际意义,甚至会使相关问题更加复杂化。最理想的做法是,按照ETSI所在地国家——法国的合同法,将FRAND承诺的法律效果解释为在ETSI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创设了一个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此合同之下,标准实施者享有获得FRAND承诺条件许可并承担善意谈判义务(不进行无正当理由拖延谈判等反向劫持)、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享有获得FRAND费率的权利同时承担善意谈判义务(不以禁令相威胁索要违反FRAND承诺的使用费率)。在此基础上,在有关标准必要专利权使用费率或者禁令纠纷诉讼中,法院的工作重心就变成了根据标准必要专利权的贡献率(所谓确定FRAND费率的Topdown方法,实为按照标准必要专利对标准的技术贡献、对终端产品销售的贡献来计算FRAND费率的方法,即贡献率方法)或者可比较的许可使用费率计算FRAND费率,以及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或者标准实施者是否进行了善意谈判进而决定是否颁发禁令。这样一来,标准必要专利中所有与FRAND有关的问题,基本上就变得清晰了。
但正如上述第三部分提及过的,有关标准必要专利FRAND费率或者禁令的纠纷,从已有案例看,基本都发生在法国之外,当事人亦属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在此情况下,要求审理案件的法院直接适用法国合同法,而不是纠纷发生地国家的法律,由于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司法主权之争,可操作性方面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此,寻求另一种解释方式,将FRAND承诺解释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其相应法律效果,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