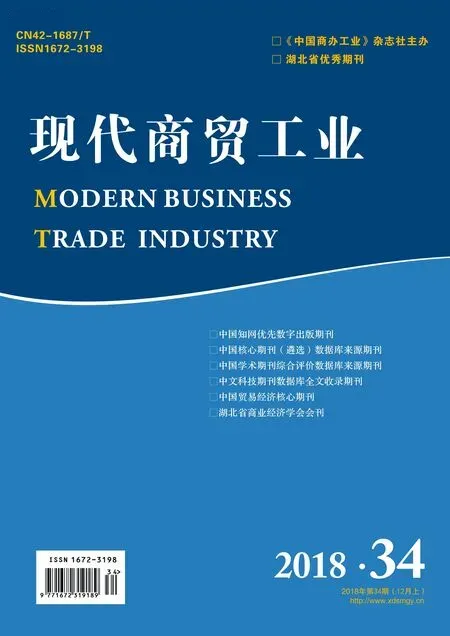正当防卫紧迫性的双重限制探讨
季晨佳
(西南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715)
1 问题的引入
2017年2月,于欢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于欢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公安民警已经出警的大前提下,被告人于欢和被告人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概率变小,并没有正当防卫的紧迫性。二审法院审理则认为,上诉人于欢持刀捅刺阻拦其离开的四个讨债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一审的无期徒刑和二审的五年有期徒刑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对结论部分的所谓正当防卫的紧迫性多有困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将从正当防卫的本质入手,从多个视角进行深入探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尝试对正当防卫紧迫性要件的限制提出看法。
2 紧迫性的必要性
“在认识正当防卫的条件时,首先必须根据刑法的规定和立法精神,解决依据什么因素来确定这些条件。”在界定正当防卫时,何种情况下能将法律所赋予的期待的正当防卫付诸实施决定着正当防卫的时机。以往,主流观点是将刑法规定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因素,将其拆分为两个层次,即“不法侵害现实存在”及“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然而,以“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要素难以说明该时机的来临。即便学者们可以对“正在进行”做复杂的解释,不可否认的是,“正在进行”难以对侵害行为之外的环境因素做出限制,而正当防卫的时机正是行为和环境结合下的产物,紧迫性正是对刑法难以限定的主客观环境因素的总结。
面对日益频繁的民事违法、行政违法行为中受侵害人自行防卫的案件,“不法侵害”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行为性质认定的困难。在讨论过程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且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我国在立法上规定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样一个抽象和比较难以理解的用语,这里给司法认定上带来了一些困难。”在对该标准重新审视时,学者们也认识到需要补充性的标准加以限定。实际上,紧迫性的使用是实务中对于现有复杂案件的总结,一些判例正是以紧迫性为出发点,否定了行为人的防卫权。在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中,“紧迫性”同样出现在结论部分,成为了于欢不具备防卫权的依据。采取“紧迫性”作为确立正当防卫条件的环境要件的补充有着许多优越性。“紧迫性”在现实中使用的广泛性决定了只需要对于这一概念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细化、发展,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刑法论的具体定义即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紧迫性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对紧迫性要件的双重限制说,即私力救济的效力等同或者优于公力救济,并且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足以威胁到合法法益的情形,从而在复杂案件中明确正当防卫构成条件所依据的标准件。
3 正当防卫紧迫性的双重限制
3.1 私力救济效力不低于公力救济
3.1.1 “不得已”的再审视
法无需向不法屈服。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正当防卫不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举措,而应该是鼓励公民与犯罪者勇敢斗争的一种积极手段”,“即使公民求助于司法机关的情况下,仍然有权利实施正当防卫。”从放宽“不得已”这一要件,“正当防卫行为似乎并不强调公力救济的优先地位,甚至有着鼓励私力救济的意味。”然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当今不断出现的暴力反抗违法行政行为、自力行使民法请求权等案件以防止私力救济被滥用。
放宽“不得已”难以直接得出否认公力救济优先地位的结论。公力救济优先于私力救济早有定论。因为私力救济本身所具有的缺点,已经早被公力救济所取代。与之对应的,私人对暴力的任使用被国家禁止,这使国家垄断了暴力。但这种优先性并非绝对。因为只有公力救济能够向公民提完全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的大前提下,禁止私人暴力才有其正当性。如果国家垄断暴力的使用同时却没有向公民提供行之有效的常规法律救济机制,就会变成施行暴力者。私力救济往往有着公力救济无法比拟的及时性,可以将损害降低到最小值。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利弊共存,两者作为公民行使防卫权实现维护法益目的途径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平衡和取舍,而支点便是法益保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互相协调、平衡的结果才有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建立,公力救济的优先权和私力救济的补充性是牢牢根植于正当防卫权里面的内在前提。虽然这一点并未在正当防卫条例中说明,但是丝毫不妨碍这成为指导正当防卫条例解释的根本原则。
3.1.2 私力救济效力不低于公力救济
对比防御性紧急避险,正当防卫不要求“不得已”是为了最大化维护公民的法益,公力救济所保护法益的完整性低于私力救济时,即便可能获得公力救济,公民依然可以选择反击,而不需要刻意遵循可能的公力救济。在实践中,防卫人当然要做出一个主观判断,即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中哪一个能够更好地维护法益。显然,在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保护法益、降低损失的效力基本相同时,私力救济更符合绝大多数受害者的临场选择,公力救济并不天然地获得优先地位。但是在私力救济效力低于公力救济的情形下,如果防卫人依然选择了私力救济,其行为就很难被单纯地解读为“保护自己”。除此之外,许多私力救济效力高于公力救济的情形往往是所涉及的法益有着“不可弥补”的性质。一般而言,当私力救济的效力低于公力救济时,受侵害人并非出于一个“急迫的”状态,其完全应当采取非私力救济的途径。“不得已”强调的应当是在私力救济不低于公力救济的情境下公力救济不因为其附加价值有强制性,此时作为保护受侵害人法益的目的占据了主要地位。
3.1.3 救济途径与防卫人主观认识
有学者认为,承认紧迫性就表明只要事先有提前准备应急措施,甚至有应急预案就说明有可能寻求公力救济途径,从而失去行使正当防卫权的资格。这种说法是指想要有正当防卫权,就需要致自己于没有防范的境地,和施暴方对峙过程处于劣势之中。这种致公民于危险的权利,必然和正当防卫中有效保障公民权益的立法宗旨是不相吻合的。在本可以寻求公力救济但是没有去寻求,而后面临着直接的法益威胁时,恰恰不是不具有紧迫性,“公力救济”此时无法提供及时的保护,正是具备紧迫性的表现。此处混淆了“公力救济当前的可能性”和“公力救济的可能性”两者。“能够寻求公权力救济”和“公权力能够及时充分地救济”应当是不同的问题。
事先的公力救济途径不影响不法侵害发生时正当防卫的优先性。站在维护防卫人法益的角度,公力救济合理、全面,如果能够及时发挥作用,当然能够更好地保护法益。但众所周知,即便公民忽略法益的保护,其对世性的法益也不应当受到侵害。所以不法侵害发生后如果私力相比于公力救济更加及时有效,私力救济应处于优先地位。事实上,“毫无防备”的情况是正当防卫时所面临的大部分情况。
3.2 不法侵害存在的客观威胁
“紧迫性”概括了正当防卫的环境因素,只有具备“紧迫性”的不法侵害才能够成为正当防卫的对象。主流观点认为“不法”即“非法”或“违法”之意,是指行为人实施了为法律所禁止,并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学术界近来提出了防卫起因的不法侵害具有特殊性理论,并由此产生了主观不法说和客观不法说两种对立学说。深入到正当防卫本质的讨论,目前主流学说有德国的“个人确保说”与“法的确证说”,以及日本的 “优越利益说”。而笔者采国内学者陈璇所提出的“双重本质说”。双重本质说定了防卫人法益的可保护性,同时又通过“违反相应义务而导致自己自陷险境”指明侵害人角度侵害人法益受保护性的降低,那么“当不法侵害人值得保护的法益程度降低后,防卫行为者所保护的法益就明显高于侵害人法益的保护价值。这也是正当防卫中不需要严格遵守法益衡量原则的重要原因。”
基于双重本质说,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不仅来源于防卫人法益的可保护性,侵害人有意识地违反不得侵害他人的义务使自己陷于险境同样是来源之一。对符合主观论的具体侵害行为进一步区分,大致可以分为犯罪和违法两个角度。
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也包括违法行为,但并非所有犯罪违法行为都属于不法侵害。不具有侵害急迫性和通过防卫行为有效避免或减轻的性质,即不属于防卫起因的不法侵害。并不是任何一种犯罪或者违法行为都能够实际威胁到行为人的法益,而唯有能够实际威胁到行为人难以弥补性法益的不法侵害才称得上“紧迫”。首先,如果受侵害人认识到存在无法实际威胁到自身法益的侵害,则尽管其身处不法侵害的境地,但是这种情况下没有保护自己的“紧迫”需求,所以当然不存在紧迫性。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只能限定在侵害者已经开始实施对他人法益构成现实威胁的身体动静之上;其次,被威胁的法益应当是行为人被剥夺后难以完全弥补的法益。正当防卫不是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追求防卫目的,通过人身损害的方法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还击的行为。这说明正当防卫行为程度的起点较高,一般都会造成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损害。对那些虽然正在进行,但尚未达到“紧迫”程度的侵害行为,如不含暴力性、破坏性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及渎职犯罪,哪怕其行为“正在进行”,通常仍构不成需要予以“私力救济”的紧迫状态,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司法途径去解决。无限防卫权的存在也便强调了重大的人身安全法益的不可损害性。当然,即便是非重大的法益,有些也难以用事后的补偿措施来完全消除。相比之下,基于行政违法、债权等民法、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就可以通过事后的措施进行弥补,他们所具有紧迫性可能就大大降低。
——以美国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