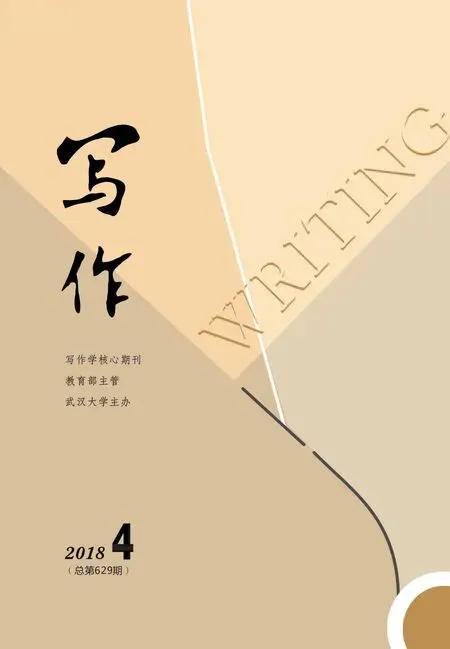罗振亚诗歌: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
姜 超
学人罗振亚先生多年来浸淫现当代诗学,凭借扎实学理与严谨考察,同时注重融入深邃独到的生命体验,在探寻新诗发轫、诠释新诗成就、叩问先锋诗歌、把脉新世纪诗歌等方面步履坚实,成为现代诗歌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专家。罗振亚的学术研究文章讲求宏观把握,脉络清晰,论证精当,论述客观,带着历史同情的目光复现诗歌流派与主张,那些诗学评判是史与论的融合。他的诗歌批评文章感觉敏锐,坚持在场的生命观察,针对腠理、肌肤、肠胃、骨髓等诗歌之弊,均有一叶知秋的诊断与标本兼治的疗救方案。罗振亚的诗学理论与批评像是一场场探险,其意在美的寻觅与真的赞赏。
无论是历史文化阐释,还是文体修辞阐释,罗振亚的行文充盈着美学张力,既鲜活剀切,又游刃有余。他的文章多的是科班理论家少有的敏锐感知,而如是我闻的亲历言说总能切入诗歌要位。兜圈子,说外行话,卖弄理论,这是罗振亚一向憎恶的诗歌研究路数。罗振亚独出机杼的理论判断首先强调要说内行话,学者吕家乡认为罗振亚的研究做到了“理性的闪光,感情的激荡”。他的诗学研究有强烈的语言自律意识,“带领读者进入现代派诗歌的本体世界去作精神遨游,再加上他的意兴酣畅、文采斐然的表述,使他的论著氤氲着沁人心脾的诗意”①吕家乡:《进入现代派诗歌的本体世界——读〈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诗探索》1998年第3期。。
罗振亚是诗歌创作与研究俱佳的双栖型学者。罗振亚痴醉于诗学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很快跻身知名学者之列,其后愈发根深叶茂。作为现当代诗学硕士、博士课徒最多的教授,罗振亚在现代诗学界声名远播,影响愈发深远。罗振亚以施展外科手术的精微,做解剖麻雀式的阐释,他的解诗学实践充满可信度。他对现当代诗潮的理论导航决不意气用事,而是还原现场,带着“历史的同情”,清理认识偏见的故道,让经典作品和天才诗人在历史大江大河的流向中显露身影。他坚持诗歌创作与研究并辔而行,始终不渝地为诗歌、诗学植入生命体验。1980年代初期,时为大学生的罗振亚以青春之我谱写青春之歌,与诗签下了一生的契约,陆续写了几十首诗作。写诗,讲诗,研诗,罗振亚近四十年来从未中断与诗的契约。
睽违多年,罗振亚依然举首性情,在繁忙治学之余,将心偎近诗情,频繁忆往事、伤流年,自在惬意的抒情似在大海里裸游。一般说来,学人之诗很难断离理性过重的纠缠,难以挣脱“影响的焦虑”;诗人之诗以生命的灌注追寻“心地空明”“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的效果。难能可贵的是,罗振亚的诗意源自直寻和即见,提笔写诗从不掉书袋,不制造迷宫,不抖激灵,诗语生发亲切自然,涌动着一派真情真意。当“有心之器”的创作主体面对“无识之物”的自然界时,罗振亚的诗歌如《文心雕龙》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在标举兴会之间情真而语直,涤我尘襟与洗却铅华。罗振亚看重性灵,反对以学问成诗,迥异于批评家的诗作,似乎刻意回避诘屈聱牙,频繁示人以质感强烈的具象。与早年的《挥手浪漫》相较,罗振亚晚近的诗歌题材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宏阔,境界愈发辽远,静思愈见深邃。这不仅有岁月的馈赠,还有罗振亚的情感历练与诗艺圆融。恰如“读书扫俗说,下笔如奔川”,罗振亚晚近诗歌随物赋形、因形敷彩,注重在一般事物上精细地择取发现的新奇。
罗振亚于新世纪元年出版的诗集《挥手浪漫》,青春气息跃然纸上,记述了他在1980年代初期的心灵波动。“任浪漫的鸽子定格为心灵深处一尊圣洁的雕像”,罗振亚将诗歌与鸽子对位,选取的相似点是穿越世俗的浪漫性。作品《铃儿叮当》发出了特属青春的呐喊,表达了生活在别处的青春憧憬。少游他乡,罗振亚见证了浪漫主义者面对现实的惶恐,尤其是毕业之初在边陲小城的教学经历促其“挥手浪漫”,在思想与行动上徐图破壁,清明理性似渐渐主宰了生活。但是,罗振亚深知生活的诗意要守住初心,他始终将青春作为诗歌的常项。他不允许世俗污染了“天心明月”般的诗歌,也拒绝让衰败和暮气靠近诗歌。“田边 阵阵鲜脆的蛙鸣旁/蹲着他和月光”等诗句,是借用青春的各种敏锐感觉的相通而推动主体的内部世界全部打开。罗振亚初展诗艺时,像诗坛青年诗人一样偏爱此种感觉延长的举措。而诗句“1957年洪水凶手归案/历史便把拇指翘向了天空”,则是诗人在生成诗句时抓住了日常认知模式的要义,而诗性表现为体验模式,这样就从熟视无睹的事物发现了新鲜的诗意。这些篇什题材指涉纯粹,形式均为短制,更显青春诗作的艺术质素。其后,罗振亚诗歌内核总有传统理想的精神因子,越岁月与山川,诗心总在召唤青春。青春是一个原点,罗振亚晚近的诗歌创作依然在做卫星环绕运动,这为他的诗歌增添了丰沛的人间属性。
罗振亚的青春带有前现代化的美好象征,诗作《也是秋天》是早年的及物观察与形象表达,“当玉米橙黄的思想/与豆荚还未道破的喜欢/依次站进/和疲倦与时间铺成的场院”,诗句里满是可堪圈点之处:“橙黄的思想”,是语词的超常规的艺术搭配,激活了语词的深层意义,诗歌的语言张力空间瞬时弥满;“惬意的疲倦”,是语词的矛盾形容,抓住了日常的认知模式的要义,而诗性表现为体验模式,诗人借此从熟视无睹的事物发现了新鲜的诗意。罗振亚的诗思让“事物抛弃自己的旧名字,以新名字展现新颜,便在诗人那里暴动起来”①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页。。尽管稍早的诗歌有追寻陌生化以求丰富的倾向,但这些诗作意象集中、分行较少、语流铿锵,散发着浓郁单纯的青春气息。
在踉跄奔向现代化之路上,诗人的脉管里仍然涌动着农耕时代的血液。罗振亚面对天人合一的整体农业生态观的崩溃,一方面拼命追忆美好,一方面哀怒崩溃,饱尝故乡不再、异乡难融的双重精神打压。这些锥心之痛没有使人消沉,反而让罗振亚在梦里醒外放逐诗情,以“青春之我”再造“长恨歌”。尤其是他近几年的诗歌创作,引发了诗坛热议。他将羁旅漂泊、漫游的势能转化为诗歌的动能,“奏出一阙还乡曲”。由青春之轻向生命之重过渡,已然是罗振亚诗歌着重表现的内容,它也带来了诗歌外在形式的新变:意象更加密集,语词越发平滑,分行趋向迟滞,语气里藏有多种疑问、感叹等情绪,这些才更适于表达复杂的人生况味与思索。罗振亚在岁月递进中的诗绪,颇似“青春之歌”向“长恨歌”的迈进。
“飞鸟返林,我独不归”,此种古典的悲伤同样笼罩着当代人。知天命的罗振亚有首题为《朋友远行》铺陈了如斯情绪:“唯有像植物离开土地/此后故乡只是梦中的一道树影/如果你实在想兄弟们了/就在雷雨天尽情地吆喝几声。”罗振亚此时运思诗章时,万千滋味涌心头,与早年的诗歌相比,对经验的萃取更见功夫,更凸显了沉思的韧性。作为情感最小单位的“故乡”,始终是罗振亚取暖慰藉的观照对象。有别于众多乡土诗的是,罗振亚以故乡为视点,身心在乡愁、城愁乃至乡悲中穿越,深入探寻着自我与自然、世界的联系。
罗振亚对乡土故园的眷恋,常常与血缘亲情同义。他的乡愁无论是血缘、地缘、业缘,均涌动着一脉真情。此处必须全文提及诗作《孩子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
月亮是供游子圆缺的
天空由南归的雁阵丈量
档案馆前的几只流浪猫
叫出故乡遥不可及的内伤
日子像疯狗在身后狂追
不知啥时太阳患了红斑狼疮
姑娘穿的少得让人不敢睁眼
性病广告贴到幼儿园的门上
小鱼儿不断浮上水面喘气
岸上人的表情阴晴无常
孩子 在都市的车海里学游泳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
都说家就是足下的泥土
乡音将一直朝着家的方向生长
可为什么脚印留在卧室
灵魂却总迷踪在路上
抵达一次次成为奢望
远方越是谁也到不了
越是诱惑得无数人醉卧沙场
从你太爷你爷爷 到我和你
蓬莱阁旁的满院桃花
讷莫尔河畔的两垧高粱
被置换成哈尔滨天津卫间的高铁
钢筋水泥中的一团雾霾
和十七楼一百多米变质的阳光
自从跪别你爷爷碑前的大片青草
和地图上从未标记的生我的村庄
那条河流的来路就再也看不清了
混乱中的记忆已经改变方向
孩子 在之乎者也的平仄里练平衡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
诗作里的疆域不断变幻,让诗人更加品尝了思乡的艰辛,它原来需要对抗时代与人心的双重压力。诗人宣称“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实际上摹写了故乡在大时代的剧变,尽管诗人返乡之后很失望,罗振亚却拒绝将乡怨当作乡愁,执意为一个时代留下丧乱和慌乱的表情。罗振亚近年来不断回望故土,视域渐趋缩小,“进城后他仅与孤独对弈/李向阳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父亲临终前说出三个字》),父亲的“李向阳”村与诗人心中笔下的神祗高度对位。罗先生将地域降幂排列,“李向阳”像是最为精微的核子,暗藏着诗人一生情思的能量。
“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罗振亚的亲情诗最为动人。尽管身飘天涯,罗振亚心中满是“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的感念,在岁月流金过程中越发觉察出亲情之重。“短脖子的春天还没打一声唿哨/就让北飞的雁阵叼走了/窗外贫血的丁香/咋一下成了病房的颜色。”(《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罗振亚的亲情诗讲求瞻之在前灵动在后,诗中始终有一个倾诉对象,在预设的一个个场景中,情到深处自无华,故而诗语辞温意柔。罗先生追忆父亲的诗歌较多,深切表达孺慕、追怀之情。至亲已逝,隔着厚厚的时空,诗人也只有永远踏上谢吊之旅。“听您喊‘振亚,扶我起来’/即便是瞬间的幻觉/哪怕是梦里的灵光一闪”(《再与老爸聊天》),诗人不断复写父亲在世的情状,入诗则产生了回放之感。而《和老爸聊天》一诗以隔空对话的形式构设场景,其诗的骨肉相附之情深婉动人,诗效如黄宗羲所说:“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除了致父亲的诗,罗振亚写给妻子、儿子的诗作也见赤诚与胸襟。更进一步的是,罗振亚将述写的亲情,宕开为生命的思索,并上升为对时间的深切体验。正如米歇尔·莱里斯所说:“如果写作仅仅是美的、不痛不痒的、不冒风险的;如果写作这个行为没有与斗牛士面对公牛锋利犄角相当的东西;如果写作带来的只是芭蕾舞鞋似的虚幻浮华,写作这件事是不是无甚价值?”①米歇尔·莱里斯:内夹书签语,《世界文学》2015年第6期。罗振亚近年的诗歌创作点染了诸多哲学之味与体察之形,为此,他像打磨钻石一样打磨着思想和诗艺。与《挥手浪漫》相较,罗振亚近作由“倾诉、吟唱和滔滔不绝”转向“叙述、细说和缓缓流淌”,更加注重分寸感。阅世透彻的心态变化,诗人必然主动对经验反复予以筛选。如肖开愚在《减速、抑制、开阔的中年》一文中指出:“探讨摆脱孩子气的的青春抒情,让诗歌写作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这既说明经验的价值,又说明突破经验的紧迫性。”②肖开愚:《减速、抑制、开阔的中年》,《大河》诗刊1989年7期。罗振亚在《五十肩》里写道:“为什么子夜的滴答声里/常伴着失眠与咳嗽/记忆的虫儿总来咬噬我的脸。”自曝中年之复杂况味非只有苦痛,更有无法排遣的焦虑。
布罗茨基说:“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罗振亚晚岁从书斋里抬头回望青春,那些生命里的山川岁月涌入笔端,早已让写诗的人不想“立言”,而大书特书时间的暴政,抒发“无言”的喟叹。在人生的盛年,罗振亚的青春大赋失去了书写的时代背景,而在风霜雨雪中碎裂为一阙凄惶的小令,来感知时光的剑影。他的诗句“冷暖难于自知/他乡错当故园”,写的是五十岁突感肩膀不受用的情状,也描摹了时间的无情流逝让人觉得惶惑与惶恐。
罗振亚近年来描摹了侧身与时光相撞的瞬间感受,其诗分别展示了领会的时间性、现身的时间性、沉沦的时间性、言谈的时间性。《朋友远行》等诗作让诗人领略了时间线性推进的无情,世人几乎与草木一样枯荣盛衰。他写给父亲的系列诗作,那些生活场景的不断复述,在“向后看”的选择中,曾经枯寂难忍的乡村与乡情突然光芒四射了,忽然拥有了拯救的伟力。他总是在他乡中选择“还乡”。在时间表现上,借用怀旧来挽留过去愉快事物的美好记忆。从乡愁的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此种原乡情结会越来越强烈。在空间上,则生成为“恋地情结”,唯故乡才是最美丽的。如斯,罗振亚致青春与望故乡、慕亲思等情思拥有丰沛的时间意识。“杜鹃声里/跪着的阳光/怎么也追不上踉跄的风”,诗人铺展了时间给予人的“畏”和“烦”,唯有克服这些,人生才会完满,诗意才会澄明。
罗振亚总是标举目光,不让诗歌的双翼沾染太多的灰尘,他试图推开生存冷酷的铁门,让光芒涌入。在快的时代找寻慢的美学。若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沿着直线排列,人生就是一场预与、既定的旅程。时光噬人,是悲哀,而诗人在艰难思考后的澄明,则是一种愉悦。罗振亚在《高楼旁,一棵蒲公英的灵魂在倔强地飞翔》一诗写道:“只要灵魂能够飞翔/安定与漂泊 生和死/在辞海里原本是一个意思。”对时间和世界的感悟澄明通透,将严苛的现实与遥远的诗意融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罗振亚了生死、参宇宙的生命思索,弃绝了生命的麻木,也表明了不甘心被时光流随意裹挟的态度。
“诗意的时间形式是流动的,但不是一般的流动,它始终在幻想之中,在超验之中流动。”①敬文东:《时间和时间带来的——论西渡》,《诗探索》2005年第3期。纵观罗振亚近作对时间的诗歌表现,其意核心集中在快与慢,瞬间与永恒的主题。自然时光的快与慢,进入诗歌后则成为一种心理感受,亦可以成为心理时间。是的,罗振亚晚近诗歌里的时光随意流淌,在遗忘与记忆之间,瞬间被拉长,时间变得绵延。此种绵延在表面形式上体现为诗歌意象渐变为幻象,造成了阅读者内心的缓慢感。罗振亚让缓慢成为一种主观化的美学风格,它以低姿态的倾听为特征。“梦游的人已把前脚举起/黄昏笛声一出/灵魂起立。”(《黄昏笛声响起》)早年与现实的抵牾,已消解为澄明的哲思,此在之苦被诗人诗意化,成为灵魂的安在。“在实际生活中,时间是一种财富形式。在文学中,时间也是一种财富形式,可它要被悠闲地花费、淡定地消遣。”②卡尔维诺:《千年备忘录》,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罗振亚的一些诗歌似物主宰着思,实则思规定着物。如此,他的诗歌实现了事物与内心共振,从低处的光到高处的云,都有着朴素的外貌、深邃的情思。
罗振亚一定看到了见证诗学的两面,故而拒绝以表达冲动替代艺术冲动。“文学的虫儿几十年仍默默活着/参观团来时它就钻进花园的洞里/人潮退后再爬出来慢慢学习奔跑。”(《在萧红故居,参观一半便悄悄离开》)他敞开对生活的观察,坚持以平常心写非常心,远离喧嚣的城市,疏离人流如涌的广场,持一颗初心,以警策之眼,对时代疾病予以隐喻表现。诗作《他再也不肯先伸出自己的手》,描摹了抒情诗人面临时代挤压的尴尬形象。在《黄昏笛声响起》一诗中罗振亚讲出了大时代的精神迷茫,“茅台就着金骏眉/不比大葱蘸小烧儿惬意”。阳光之下无法忽视空白,罗振亚连缀起卑微的细节,为蒙尘的生命祛魅,试图听到细小事物的呼吸,听到真理的心跳。正如歌德所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③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罗振亚的诗来自生命深处,坚持在场的原初感受,尊崇着心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