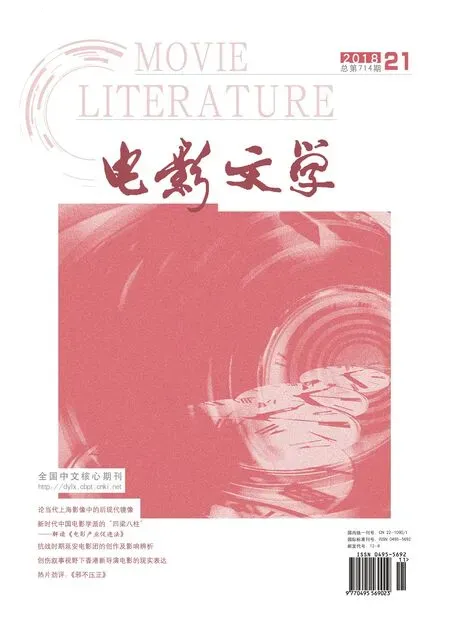张艺谋电影中女性叙事策略研究
金 明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大多数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是以“中国代际记忆”为内容呈现影像叙事,例如民风民俗、历史寓言、地域传奇、上古神话等形式,在其基础上以视觉图谱拼构具有“历史感”的叙事内容,以凸显出“中国故事”的主体性,从而打破中国第四代导演所积极倡导的“样板式宏大叙事”。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历史的重译,让过去被压抑与束缚的情感得以在电影中表达,使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解释权由“国家/民族”转向“地域/个人”,这无疑拓展了中国故事的表达类型与边疆。
第五代导演之前,大多数导演在性别叙事上的表现手法依旧是以男性角色为主角展开的,男性是故事的核心推动者,以其视角展开剧情的延展,他们是电影的叙事者、观察者,并且牵引着电影剧情的走向。而反观张艺谋所指导的电影,女性角色是其电影中重要的叙事者,甚至是命名者(如《菊豆》《秋菊打官司》)。本文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叙事策略,试图厘清张艺谋所呈现的“中国故事”中的性别书写范式。
一、民粹式的东方寓言叙事
张艺谋擅长通俗民粹式的类型电影创作,然而类型电影最为推崇的依旧是个人意志的展现,在庞大的影视叙事矩阵中用程式化的叙事凸显出矛盾与含混。而在张艺谋所创作的电影中,其影像所制造的“东方式寓言叙事”成为其电影独树一帜的标签。他的电影将原文本中时代背景置换到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年代,更能降低批判和质疑的争议性以及政治检查,这种叙事策略融合了历史记忆、民风民俗、东方主义,他的作品擅长在平缓的节奏中,导引人物与环境进行频繁的互动,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中,可以发现他对东方性别博弈的视角,以及其个人独到敏锐的观点。
记忆、叙事、历史、遗忘之间存在着暧昧且错综复杂的关系,张艺谋的电影中对于历史的重现,制造了一种真实,而伴随着电影中对于“历史”的展现,必将一些“记忆”选择性地“遗忘”,以建构出以电影视角产生的“历史意义”。然而在集体历史的记忆中,大多嵌入的是暴力以及伤痕记忆,个人记忆被“遗忘”抑或是“删除”,这种策略的运作模式是充满意识形态控制的。《归来》中,冯婉瑜因为女儿的阻止,在即将与自己的丈夫见面前,目睹丈夫被抓走。受刺激的冯婉瑜患上失忆症,这样的情节设置再现了个人记忆在集体意志中受挫后,选择性“删除”记忆的自愈性保护,同时电影也以冯婉瑜的生命经验书写时代女性面临的特殊处境,拒绝历史解释的同一化倾向。然而女性只有将镌刻自己生命经验的记忆铭记,才可以成为保罗·利科所言的“成为自己过去的主人”,从而进行多重主体的自我命名。
《红高粱》中的叙事是以一种口述历史展开的,这种叙事策略本身就是一种民粹式的个人生命经验与记忆的呈现,以个人化的“私记录”方式将族裔、集体、个人历史认知串联起来。电影中以“代际叙事”作为叙事基础,以男性的口吻讲述女性的生命经验,从而使得个人与族裔的关系生成了新的意义。“九儿”是这个故事中的核心叙事主体,她的家庭建构、婚姻关系、情欲展现成为这部电影的“元叙事”。电影中,九儿在出嫁过程中,一定要经历“颠轿”这一仪式,这个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凸显了一种“性别麻烦”,女性被困在狭小的空间中,经受男性剧烈摇动花轿,这一仪式本身就是对于即将进入新的家庭关系中的女性最后的“性别嘲弄”,而九儿在这个过程中,强忍住未曾出声,这种对于“传统仪式”的抵抗,凸显出九儿坚韧、勇敢的品性。然而,她与余占鳌的情感书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语境之下是违背传统的婚姻道德的,而她依旧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这部电影仍是对历史与政治意识的再现。
而在《英雄》中,视觉画面的呈现仍旧是依照口述为起点进行的,无名口述的“谎言与真实”与秦王口述的“臆测”成为电影影像呈现的关键。在这部开启张艺谋“大片”时代的作品中,他依旧尝试在武侠片中呈现出属于自己的“奇观性”画面,虽然这部电影中的叙事内核是关于“国家政治”,但是性别作为电影中的基本叙事驱动力,在电影中依旧是体现作用的。电影中,男性角色(秦王、无名、残剑)依旧都是“理性、睿智、无私”等“高贵男性气质”的化身,而女性角色(飞雪与如月)则被塑造成富有东方女性气质的形象,电影中一个基本的叙事驱动力就是“飞雪的复仇”,正是由于她的坚持才形成了电影中故事的呈现,飞雪的国族情怀在电影中被化成一种个人主义,而如月则被塑造成一名完全依随于残剑的形象,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庸。电影中最为人称道的“东方奇观”应该属于飞雪、如月的“胡杨林之战”。两人之间的决斗伴随着身体服饰、身体动作的展现犹如舞蹈般,红色服饰凸显出女性强烈的欲望,配上胡杨林凄美的景致与缥缈的配乐,成为这部电影中最为绝美的叙事片断,高频快速跳接和最后的过度曝光所形成的电影镜像,不仅形成了视觉上的丰富性,同时也通过视觉画面使电影与观众形成了一种疏离感,隐约使得电影呈现出一种极具导演个人意志的社会论述基调。这段影像的起因是飞雪嫉妒如月与残剑的“偷情”,一怒之下杀死残剑,如月则欲为残剑复仇,挑战飞雪。此叙事片段中包含的叙事内核是“女性的复仇”,虽然它是出于无名的解释,但是在文本上的设置,以及视觉上的呈现都使得“女性形象”是被男性(无名)“解释的”,女性依旧属于“在场的缺席”。同时,“女性的复仇”也是无名欺骗秦王的解释,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对于“女性气质”的性别偏见仍是父系逻辑中的“刻板印象”。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性别叙事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观看的能力和方式都是权力的运作和展现,而在电影中飞雪与如月在影像上的功能是背负男性观众的偷窥欲(观影者),她们带来视觉快感的同时也制造了阉割恐惧,而这部电影为回避阉割焦虑,女性最终会以“死亡”形式落幕,男性可以在这样的观影体验中消融因视觉快感而带来的阉割焦虑。
二、“铁屋子牢笼”中的伦理叙事
“女性一直被男性统治、压迫,这是最普遍的现象,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家庭”是父权社会最为稳固的堡垒,它看似为女性提供了权利关系明晰的“保护”空间,实质上并未让女性逃离“第二性”的处境。父权社会建构下的家庭女性不但需要成为一名“好妻子”,还需要成为一名“好母亲”。但是综观张艺谋的创作谱系,无论是《红高粱》中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九儿,《秋菊打官司》中执拗为夫寻理的秋菊,还是《菊豆》中在婚姻中不断自我拯救的菊豆,她们都努力地挣脱传统意义上的“家”的牢笼,大胆地接受原始欲望的召唤,这些充满激进色彩的女性角色,虽然她们的个人体验与底层、异质、边缘的生命经验相连接,但是她们一直都践行着“庶民的发声”,为底层女性的生命经验进入历史提供了契机,回避了可能的悲观陷溺。毫无疑问,这些女性都在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因而在政治与伦理权利上也无法与男性享受同样的权利,即权利自决。从这些角色中可见,张艺谋提倡一种由下而上的女性族群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必须经过对于族群历史记忆的不断重现得以实现,在对族裔文化、历史、荣耀与屈辱的不断认同中,为族群文化争取到独立的主体性,使得族群拥有共同的想象力与感召力,从而形成族群的认同感,进而强化到族裔中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加深族裔的凝聚力。这些“寓言化”的历史故事杂糅凝滞形成了“现实历史”与“虚构镜像”的开放性文本,创造出一种女性主义表达方式,否定了传统男性叙事的权威,对女性的身份、主体性、身体进行了想象性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张艺谋式的“女性伦理叙事”模式。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关系反复演练,将曹禺的《雷雨》中的家庭关系置换到更为宏大、复杂的“皇室家庭”中,张艺谋试图以“家/国”文本的重译来诠释“中国式”的伦理叙事模式。电影通过对原文本的重复、嫁接与戏仿,使得整部电影中充斥着性别政治与身体情欲的狂欢化语境。然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对于伦理的展现依旧是通过“身体情欲”来阐释的,电影的第一幕就是以女性身体作为性别展演的场域来呈现的,在这一幕中,宫女们在迎接皇帝归来的过程中,她们的身材、服饰、礼仪无疑都是为了迎合皇权的威严,成为巩固意识形态的唯一表征。而观影者在观看过程中,也伴随着摄像机镜头,以俯视的形式观看到这些身体意象,这种视觉效果依旧是带有性别权利指向的,女性在“被看”的过程中,依旧是“被窥视”与“获取视觉快感”的对象。《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影视文本中皇后的身体则无疑成为权力的交换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同时也是维护“皇权/父权”伦理的工具,皇后诱导自己的二皇子武力逼宫,不仅是因为身体上遭受到迫害,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有自由的情欲选择,电影的这种改编策略使得政治的狂欢与身体的狂欢完美结合。这部电影呈现了一个包含父权政治与身体叙事的镜像空间,试图以最为原始的情欲力量去解构与颠覆父权性别政治的目的。以身体叙事来反向颠覆、解构父权的崇高性,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身体原欲成为电影中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叙事依旧是围绕着家庭进行讨论与展开的,电影展示了“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家庭内部女性互相倾轧的生命景象,大家庭的男主人陈佐千在电影中只有很少的镜头出现,大多数是以声音“在场”,这种“缺席式的在场”的幽灵般的权力运作模式正是父权社会中男性性别权利的凸显。男性才是电影中所有空间与女性的拥有者和实际管辖者。电影中女性的身体与家庭空间时刻发生着共感作用,无论是“点灯/封灯”的仪式,或者妻妾侍寝前的“捶脚”仪式都暗示了女性的被动性,她们是空间化的、可化生的、拟待开发的,陈佐千通过对这个如同“密不透风的铁屋子”空间的支配、操弄来彰显出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利拥有权,也使得女性成为权利边缘化的受驯者。最终,颂莲在这个“铁屋子”中发疯,新的妾室被迎娶进门。这部电影的叙事不同于《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家”策略的视觉展演,他规避了《满》中国家认同的伦理指涉,使得这部电影文本中的暴力冲突或图腾与符号的二元拮抗转变成为伦理关系更为单纯的家庭剧场,故事的记叙时间也由模糊久远的历史年代移位于民国年间的西北城市,电影中呈现出虚构与现实相互指涉谐拟的特质。
三、打破性别迷思的身体叙事
身体在张艺谋电影中的表意是有多重释义的,同时作为电影中最柔性的叙事单元,具有高度的可变性与重塑性,这与现当代的酷儿身体理论所阐释的流动身体概念不谋而合。日常生活审美化加速了对于身体的理性建设趋向,而电影以视觉图谱为样本,大众偶像为范式缔造了一个又一个模型化的身体迷思。“‘身体’本身就是含混且多元的场域,同时‘身体’所隐喻的文本在社会权力建构中有着重要意义。”电影中所展现的性别权利倾斜的社会建构,依旧需要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来展现。她们在张艺谋的电影镜像中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身体面貌,来生成、延续、复制身体的意义。而在电影中所呈现的身体,必须无时无刻展现出多重的身体气质,才能够不断地“打破-重组”,产生新的意义,身体与通过身体意象所产生的意义从“与时”的关系达到“共生”的关系。
父权体系下的艺术推崇“阳性崇高”的审美取向,在这种美学体系关照下,是借用“女性身体的破损与牺牲”来获得艺术诗学的美感。这种牺牲达到内化升华父权体系的需要,女性愿意以身体与主体性的失去换取伦理上的“正义”,这样的策略同时崇高了男性的目标。然而身体是女性主体性觉醒、自决的起点,但是吊诡的是,它也是性别歧视、性别剥削的原点。在《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等“秦淮歌女”为了完成对教会女学生的拯救,牺牲了生命,在这个伦理叙事中,充斥了“国族对抗”与“贞洁锁链”双重压迫的倾诉。“秦淮歌女”在电影中,打破了“不知亡国恨”的“历史寓言”,以生命拯救构筑了超越父系伦理血脉的女性世界。电影中的秦淮歌女以生命为代价,去拯救教会女学生,“女性解救女性的故事框架,使得女性成为性别场域博弈的主体、个人/族群解放的领导者。”这样的叙事策略打破了以往电影中将女性划归于一体的设置,女性在代际之间亦可以完成自我拯救。虽然电影中“失贞女性”拯救“贞洁女性”的伦理议题的激进性有待商榷,但是在这个文本呈现中,女性不再是为了男性而失去生命,而是为了拯救“女性群体”,获得“崇高”。在电影的时空叙事中,城市空间的“殖民地化”与玉墨等人的生命经验形成了互文,将主权的沦陷、城市的破坏与性别的压迫在电影中呈现出和谐的变奏,电影以玉墨等人由“私人领域”越界到“公共领域”的呈现,从而去质疑社会建构与性别压迫之间共生式的结构关系。《红高粱》中也是如此,九儿被日本侵略者杀死,她的身体成为时代的隐喻书写,九儿的原生态、反抗性、自立性成为当时“中国”的象征,虽然“身体”伴随着“殖民”过程遭到了损陨,但是她的后代继承了她的意志,可见伴随着种族与性别在螺旋式的复调叙事中多次展演,张艺谋在“国族创伤”的基础上书写女性传奇。女性的身体时间跳脱出历史秩序,以非线性跳跃式的论述取代了历史的演进,在书写范式上颠覆了传统的男性中心话语体系,寻求时代女性的另类书写,这使得身体叙事成为一种共时性语言。
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如同容器一般,容纳、筛选、滤清了女性的情欲、疲惫、挣扎,将身体的意义重新界定,进而打破了其意义生成的一致性,重新规整了身体意象的象征性。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女性身体空间不再是隐秘的、封闭的、内化的,有了积极的、多样化的想象,这种策略打破了对女性身体物化的刻板想象,从而使得女性身体与空间对话有了可能性,女性以集体意识与父权社会对抗。《菊豆》中,杨金山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染房主,因为身体的“疾病/匮乏”没有子嗣,相继折磨死两任妻子,继而菊豆成为其用金钱“买”来的继妻。可见,在张艺谋所制造的这个视觉想象中,女性的身体与“经济关系”紧密相连,菊豆白天在染坊做长工,夜晚则被围困在“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中,遭受杨金山的虐待。“失德/失能”的男性主人公的设置预示着父权在家庭中的濒临崩塌。然而,菊豆的身体是丰腴、年轻、饱满的,这样的身体意象象征着蓬勃的情欲,她愿意在杨天青面前展现自己的伤痕记忆,也怂恿他杀死杨金山来获得自由与爱情,这种激进式做法也是一种反抗策略。可见当女性的身体成为欲望机器后,伴随着丰沛的欲望流动,开始了对于父系伦理的反抗,以自身生命经验的身体逻辑,挑战父系伦理的制约与禁锢,从而跳脱出被父权社会所制定的情欲“正典”,争取女性自身性别权利建构的合理性与优势。菊豆的记忆之钥,开启了封建时代女性身体与情欲双重禁锢的记忆之门,将那些充满性别压迫的个人生命经验以镜像之思释放,也使得性别解放的潜文本透过电影符码得以诠释,建构了电影中全然一新的女性身体诗学。电影中“男性/女性”欲望引导他们踏上寻找身份的旅程,性别博弈的位置就被挪移到伦理模糊的灰色地带,对主体性的追求让电影中的生命有了多重辩证的起点。
四、结 语
张艺谋将一个个具有地域性与历史感的事件滞凝为具有其个人风格的“寓言叙事”。在其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一个多重的能指,而对历史的挪用与重译,以“女性角色”的“记忆”缔造的一幕幕视觉图谱,刻画出跨越时空、纷繁复杂的中国女性形象,打破了中国第四代导演对于女性角色的“单一的”“去性别化”的“刻板印象”,使用多种叙事策略,以弱势族群的“个人记忆”去回复“国族记忆”中被压抑的意绪,使得女性从父系伦理“正典”中逃逸,将历史中被隐匿和忽略的记忆与情感得以呈现,女性性别对抗的话语权得以正名。
纵观张艺谋电影的创作谱系,他的电影中这些如同万花筒般的女性镜像通过影片中丰富的视觉语言,以拼贴、悬置、解码、编码、重译等多种形式重新界定了身体意义,在主体/身体、镜像/实体、与时/共生的多层次的嵌套式辩证过程中,以寓言化的电影想象对父权社会进行了思考与反省,以女性肉身来再现被压抑的“她者”历史,进而呈现出一种充满自发性与多重思辨指向性的电影表述,供观影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