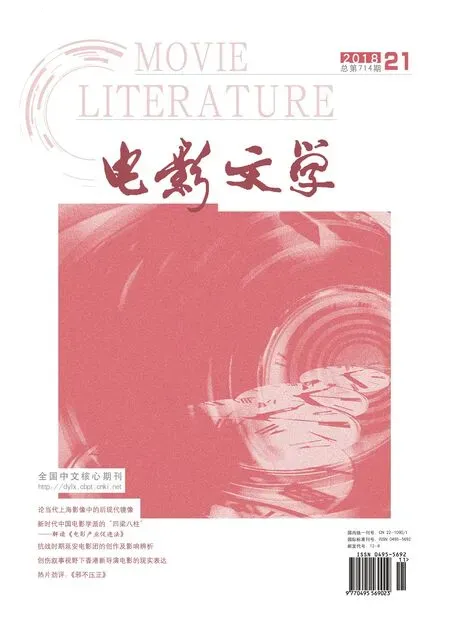文本类型与献礼片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创新
——基于“建国三部曲”的分析与思考
苗 瑞
(大理大学 文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2017年7月,随着《建军大业》(以下简称《军》)在各大院线的上映,系列献礼片“建国三部曲”,即《建国大业》(以下简称《国》)、《建党伟业》(以下简称《党》)和《建军大业》全面收官。作为献礼片,建国三部曲在取得票房突破的同时,在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我国有组织的献礼片的制作生产和展映最早可追溯到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此后,除“文革”期间电影生产全面停滞外,“几乎每年都有相应的生产计划和组织,逢五逢十的大庆时规模更大。”这些献礼片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环境里,服务于特定年代国家主体的时代需求,打上了特定时期的历史烙印,并展现出不同的话语形态。1959年,“改造”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献礼片“意识形态话语真正的核心词”,与此同时,“成长”“集体主义”和“牺牲精神”等解放区文艺主题得到了延续。1979年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价值观重新得到肯定,同时延续和强化着奉献牺牲的主旋律主题。1989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成为主流,传统的奉献牺牲主题开始隐退,开始出现“将商业类型电影机制引入的尝试”;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片,革命领袖开始从银幕中心走向后景,开始以“大国意识包装国家认同,实际表现出用民族认同替代革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五十多年间献礼片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变化与更新,凝聚和折射出新中国诞生以来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内涵,基本满足了国家主体对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论证要求。然而,其中也有很多不足,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创新能力不足,其更新速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需求的步伐,表达方式陈旧俗套、缺乏亲和力。其生存境遇可以用“两高”“两低”来概括:“两高”是首映式规格高,出席嘉宾职位高。“两低”就是除少数作品外,观众关注度低、票房低,“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内的献礼片创作到了一个临界点,夸张一点说,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亟待创新。系列献礼片建国三部曲便是一次重要突破。
通过对三部影片的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它们包含不同的文本类型:《国》和《党》属于论证型文本,而《军》是属叙述型文本。本文讨论了两种文本类型的献礼片在意识形式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与差异,探讨文本类型与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我国创新革命历史题材献礼片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进路。
一、献礼片意识形态表达的大片模式
“建国三部曲”开启了我国献礼片以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大宣传的“大片模式”运作的开端。从“中国式大片”的角度看,它们与《英雄》《无极》《赤壁》《风声》等大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或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作为表现题材,以中国人立场讲述中国人的经验与故事。有学者高度评价三部影片的历史地位,认为这是“‘中国式大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献礼片的角度看,“建国三部曲”首次引入了“中国式大片”强大的明星阵容、视觉奇观的营造、覆盖式的集中宣传的商业运作模式。结合三部影片的两个属性,可以把它们定性为“献礼大片”。
“建国三部曲”是我国电影主管部门基于我国近些年电影市场快速发展和电影大众娱乐属性凸显的市场语境,寻求符合现实和市场方式建构新的话语表达方式的探索实践,即让电影主管部门主导性最强、政治宣传教育功能最突出的一类影片与商业大片相遇碰撞,实现影片在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上的一次“飞跃”。建国三部曲讲述的故事是属“政治或社会前本文”,即“情节冲突在叙事开始的行为中就已得到昭示或解决,而在叙事性结束的行为中不过是得到确认而已”。于是全明星阵容的策略便不难理解了,其意图在于通过众多明星的强大号召力把观众请进电影院,去观看一个观众熟知的故事。其背后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逻辑:只有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看到这些影片,才能获得更多意识形态“消费者”的认同,从而形成“聚焦效应和规模效应”。
在“建国三部曲”中,以往“议论重于叙事”的情形已经很少,只出现在《党》的末尾片段。但由“剧中人物”发表议论在《国》和《党》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即通过会议“讲话”与人物“对白”来发表议论,进行意识形态论证;《军》中上述两种“议论”都大大减少了,明确的论证只出现在片尾毛泽东以“讲课”的形式阐述“党指挥枪”思想的段落,而更多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如影片以朱德等角色两次摘除帽檐上的“国民党徽章”来表达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决裂,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的思想转变和决心。《国》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关键在于影片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论证结构的文本,《军》——这部由以动作片见长的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的“献礼战争片”——其意识形态表达主要是在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里,通过剧中人物的行动及其动机来实现。
二、论证型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表达
在中外电影史上,论证型的电影文本并不鲜见,它们为我国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埃尔温·莱斯在对影片《酷热时分》的分析中为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表达的一些方法,譬如字幕的使用、蒙太奇组接方式以及解说词的论证作用等。它提供的方法是来自一部纪录影片的分析。查特曼在谈到影片中的论证时列举了很多论证性质的影片,如以寓意、讽喻为基础的影片,好莱坞上百部的寓意片,以及1925年至1933年间的苏联电影。他认为,“明确的论证不易成为也不常成为商业电影的属性”,但“无疑有很多虚构影片包含着非标准形式的论证”,而“这些论证一般来说都是通过叙述含蓄地传达出来的”。他分析了法国阿伦·雷乃导演的《我的美国舅舅》中的论证,认为我们无法说清楚影片中议论和叙述的主次关系,到底是议论控制了叙述,还是叙述控制了议论,“它来自叙述和论证之间的那场没有结局的电影控制权之争”。
《国》和《党》主张的意识形态观点是通过论证呈现给观众的。《国》摒弃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叙事线索的做法,采用以军事为辅线、政治斗争为主线的叙事策略,突出两党政治领域的冲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领导战略、政治路线上的胜利。影片的结局昭然若揭,即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影片通过主要角色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张澜等的言语和行动表达了这一“结果”的“原因”,即:国民党内部钩心斗角、人心涣散,民国经济崩溃,军事上节节败退;而共产党内部团结一致,在政治上团结工农和民主党派,军事上节节胜利。影片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因果论证”的论辩结构。
在此举一个片段作例证。1946年11月,国民党“制宪国大”上,蒋介石发表演讲,立志三个月消灭国内之共产武装,实现国家之实质统一,接下来的内容如下:
(1)1947年3月,中共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发表演说,说明中共中央为什么撤离;
(2)上海,民盟总部,张澜表示和中共站在一边;
(3)陕北,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毛泽东为写社论,吹灭半根蜡烛;
(4)民盟总部被蒋查封,病房里,张澜决定在香港重开民盟总部;
(5)战场,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国民党节节败退;
(6)1948年5月,中共中央前往河北。国民党国民大会蒋当选总统,但被告知延安丢了……
以上段落中,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对比蒙太奇在叙述中发挥了论证作用:影片更多地展示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让观众觉得蒋介石等人对军事不管不顾,而“沉醉”于党内的政治斗争,而中共施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获得了民主党派的支持。影片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观点——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历史选择的结果,并由此追溯和宣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也是如此。影片叙事的结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影片叙述了如下事件: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五四运动的兴起,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党》依然是一个“因果论证”结构。影片最后的论议指明了影片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观点:“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两部影片的论证相比较,《国》的论证是结构性的,议论服务于论证;而《党》的论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言是“因果论证”结构,但对影片最后的一段旁白论议,并不具有论证的结构性,即作为影片主体部分的叙述并不能对意识形态观点起到论证作用。另外,这种评判性的议论,也因为隐含作者的倾向过于明显而遭人诟病。
三、叙述型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表达
叙述型文本通过叙述来表达意识形态的方式看起来更加隐蔽或透明。让-皮埃尔·欧达尔和丹尼尔·达扬提出了“缝合体系”理论来揭示电影叙事中的意识形态效果策略。达扬指出,在观影中,观众是被安排按另一个“不在场”的观察者或幽灵的眼光去看的。通过作为叙事基本话语的正/反打镜头的缝合,缺席者成为一个角色,并把电影的视觉世界转变成一个虚构的、不是(由一位电影制作者,由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制造出来的世界,而是直接被看到的世界。经典电影由此成为一个没有制作者的产品——一个“意识形态的操作者”。尼克·布朗指出缝合体系理论的“太过预设性”,并修正了其偏颇。他提出叙事视点(即特定人物的视域)的概念,并将视点看作是“连接着叙事人与人物、观众与人物、故事与话语、认同与拒斥、叙事观点与观看方式、机位、构图与场面调度的节点”,并“联系着本文中的观众之定位与移位,联系着叙境的确立、连贯与明晰,联系着电影叙事人的隐形与显身”。布朗认为这个“看”的视点通常是由被主流意识形态肯定的人物所占有。耐人寻味的是,他认为并非只有占有视点镜头的人物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同,被看者由于观众在叙境中累积的同情与立场,同样可以获得观众的认同。由此认为观众并非认同于摄像机,而是认同于人物。“而正是人物——他在画面空间中的位置、他的视点由此产生出的诸修辞策略,成为电影叙事人的假面;依据某一人物的中心存在(他的形体、他的视点)组织时空的连续与连贯,并因之而建立起‘本文的道德秩序’”。查特曼进一步把视点(眼睛的、视觉回想的和判断的)划分为四种类型:叙述者的倾向,故事中的过滤者,故事的中心人物和故事中的利益焦点人物。“倾向”很好地强调了“叙述者之心理学、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的衍生物”,叙述者的态度在极为宽广的定义下,是“‘叙述者之视点’所能指涉的一切”。在“叙述型”革命历史题材献礼片中,如何通过叙述“视点”隐蔽而有效地表达叙述者的态度成为意识形态表达效果好坏的关键。
通过叙述者的倾向表达意识形态在《军》中有突出的表现。在四一二反革命屠杀段落,刽子手挥舞屠刀和蒋介石站在窗口的画面多次出现,影片运用重复蒙太奇的方式意指蒋介石才是反革命大屠杀的“操盘手”。关于李大钊的死是多视点叙述的典型例子。影片没有仅仅站在共产党一方的视点来叙述,而是通过几方的视点来呈现:俞济时向蒋报告、张作霖向蒋请示如何处置李大钊,镜头闪回张作霖父子拟请示的情景,蒋介石下令处死李大钊,以及李大钊被绞死的镜头交叉剪辑在一起。后来,在中共五大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得知李大钊被害的消息,引发陈独秀与毛泽东“把枪交出去”和开展武装斗争的争论。随后张作霖父子交谈,张学良说“我们可能被蒋介石利用了”,张作霖表示后悔——这些都是来自“居住在故事世界”里的人物的叙述和判断,在影片里关于李大钊的死并非共产党的“言说”,也非故事外部的叙述者的“言说”。历史知识在影片中展示了出来,其表达的意识形态也被隐藏了起来。“叙述的过滤者”在片中也有多次体现,如汪精卫下属向汪报告会昌一战的惨烈、周恩来游说斯烈道出蒋介石之阴谋等。在《国》与《党》中,以上种种“技巧”都有应用,不过叙述的视点往往都是故事的中心人物,即我方阵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权威”角色。他们台词过多,其背后的隐含作者急于言说,往往败坏了意识形态表达的含蓄性与隐秘性,给人以强制灌输之感。包括以往的献礼片在内,绝大多数影片叙述视点单一,敌方阵营的视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者完全被忽视,故事中的人物过于中心化,导致观众敬而远之。
总之,《军》在文本类型或话语模式上有别于前两部,对献礼大片的创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突破,给将来献礼片的拍摄提供了不少成功经验。《军》呈现出不同于前两部的风格特征:前两部是言语型的,堆砌着大量的会议讲话、演讲和对白。据导演黄建新介绍,《国》一共有110场戏,其中有50多场都是开会,几乎占了全片的一半;而后者是动作型的:杀戮、射击、炮击和体态语等。前者主要依赖讲话和对白来推进情节的发展,而后者主要依赖角色的行动来推进。前者以诉诸听觉的意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主要表达方式,后者以诉诸视觉的意义作为主要表达方式。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多地通过造型和动作来讲故事,更具有电影特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军》的票房收入略低于前两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展示的故事时空更不突兀或更透明,意识形态表达更含蓄和隐秘,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革命历史题材献礼大片的文本类型与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概括:第一,文本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同类型的文本意味着其话语模式是偏倚诉诸听觉还是视觉、理智还是情感,从而造成意识形态表达与接受的差异。第二,文本类型,不管是论证的还是叙述的都没有绝对的优劣。论证型并不乏高艺术水准的影片。在我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电影大众娱乐消费属性凸显的语境下,叙述型应该是更佳的文本类型,但论证型影片仍然有较大的探索突破空间。第三,文本类型是相对稳定的,而意识形态表达方式是多变的,创新是永恒的。
当前,革命历史题材献礼片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创新,应该摒弃以会议讲话和演讲等以诉诸听觉的“人声”作为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方式的做法,更多地通过造型和动作等视觉元素来讲故事,使影片更具电影特性,意识形态表达更含蓄、更透明;加强影片的类型化,增强意识形态表达的“亲和力”,探索诸如献礼爱情片、青春片、动画片、纪录片等影片类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平民化叙事视角,更多地反映当今时代需要的、普遍性的进步主题,赋予影片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
注释:
① 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在《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中把小说和电影的文本类型分为论证、叙述和描写三种。关于特定文本的类型分类基于整体结构上的从属关系来做判断,描写、叙述从属于论证,则属于论证型文本;论证从属于叙述则属于叙述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