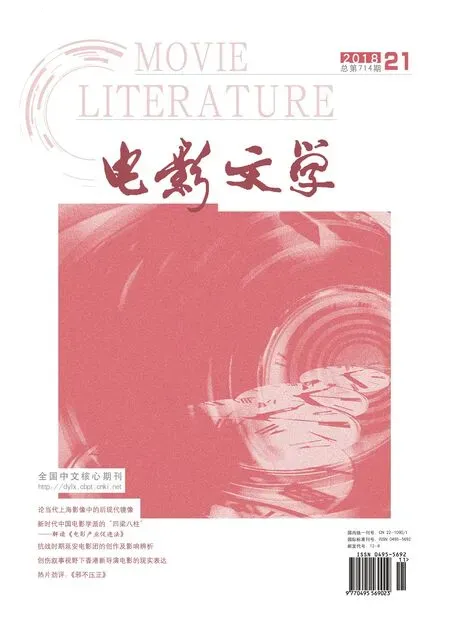抗战时期延安电影团的创作及影响辨析
张 杰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数字艺术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一、延安电影团的创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促使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更好地应对战时特殊环境下的舆论宣传,在思想上有效统一战线,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陈诚是黄埔系的职业军人,副部长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创立之初就担任校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高层中主持文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专家。因此,抗战宣传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是由副部长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具体负责的,逢此机缘,周恩来与奋战在抗战后方的文化工作者便有了诸多交流与沟通。
1938年8月28日,同样通过周恩来的指示,有着“千面人”称誉的上海电影演员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携带着他们刚从香港采购来的新设备,连同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无偿捐赠的“埃姆”摄影机、2000尺胶片,由武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到,眼看人员、物资、设备日渐完备,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在1938年9月正式宣告成立。延安电影团直接隶属于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首个电影制片机构,1938年正值建党十七载,中国共产党终于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属于自己的电影事业。成立之初,当时电影团的全部家当包括:一台由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捐赠的能拍35毫米胶片的“埃姆”;一台16毫米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台相机,一台是徐肖冰的,另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买的,大家戏称之为“两呆三动”,条件可谓弥足艰苦。
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初,仅有六名成员:参加过长征的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具体负责总体把握艺术创作,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工作,而后又从延安抗大抽调来叶仓林和魏起。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袁牧之有着丰富的表演和编导经验。1937年,袁牧之担任编剧并导演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马路天使》,这部由周璇、赵丹主演的电影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吴印咸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上海担任电影布景师的工作,后来改为摄影,与袁牧之合作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草创时期的延安电影团,具有电影从业经验的成员仅有袁牧之、吴印咸两人,而袁牧之和吴印咸都是从事前期制作,无法完成电影后期制作的相关工序。1939年后,电影团又相继调入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钱筱璋1933年后任“明星”“中制”“大地”等影片公司剪辑师。剪辑的影片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孤岛天堂》,纪录片《抗战特辑》等。周从初1932年即到上海明星公司学习洗印、录音技术,是延安的胶片洗印专家。至此,人员的补充完整地衔接了电影团前期编导、摄影与后期剪辑、洗印的制作流程。
二、电影人的精神涅槃
像袁牧之、吴印咸这样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延安的电影人,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环境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洗礼,在来延安之前,上海电影人在对待一部电影的创作方向上遵从商业市场的一般定律,拍什么,怎么拍具有一定的创作自由度,其他行业的文艺创作者也是如此。抗战时期的延安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采取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管理,知识分子的自由创作身份在无形中被共产体制消解掉了,陕甘宁边区所有出版机构、报纸、书刊甚至书店、纸厂都是公有的,因此,电影人随同进入延安的其他文艺工作者一同被划为了共产主义体制内的“公家创作者”。吃着“公家”的粮,穿着“公家”的衣,心怀崇高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延安时期电影艺术创作类型的固定模式。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阐明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要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该决定加强了知识分子与党的联系和沟通,提升了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地位。但也从思想和意识形态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强调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思想要统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和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论题的提出,是亭子间的知识分子如何融入延安农民文化中的问题;也是亭子间文人在延安农民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双重洗礼下,从资产阶级“旧文人”到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精神涅槃。
以上观点在毛泽东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五四运动》中阐述的非常详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次思想和行为改造,从城市来到延安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终于在艰苦的劳动和思想历练中,因获得了“农民身份”,有了“劳动人民的情感”而重获新生。
三、延安纪录电影的类型溯源
延安电影团的电影创作并没有遵从上海电影那约定俗成的“剧本—导演—摄影—剪辑”前后期规范化制作,“影片的具体内容和完整的构思是在拍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一面采访熟悉生活,一面进行拍摄,一面完成整体构思”。这一方面限于延安电影团初期有限的电影制作能力,另一方面是由延安特有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抗战时期,延安独有的公有体制是实行战时的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管理,其特征是讲求成员行动的高度纪律性与规范性。公有体制下的所有生活资料都归属于“单位”统一分配,而非延安以外的区域那样,员工通过与雇主之间的约定获取或多或少的劳动薪酬。在1943年整风审干阶段,延安最桀骜不驯的作家萧军因其所属的“文抗”单位被撤销,在延安的萧军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萧军一家住的地方改为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萧军实际上成了寄食者和寄住者,因与所长发生口角,被所长下了逐客令,萧军遂于1943年12月上旬到延安县川口区农村落户,12月底延安县长来通知今后停止大人孩子的所有供给,这实际上等于开除了萧军的公职,萧军不得不暂借老乡的粮食过冬并计划来年春天开荒种地维持生计,但开荒种地对惯于拿笔的知识分子而言谈何容易,多亏了老乡们的热情帮助,萧军一家东挪西借才勉强维持到1944年3月。后来胡乔木以路过的名义来探望萧军并请其回城,萧军于3月7日回到延安,参加了党校三部的文艺界组织,他的公职也就恢复了。这次下乡充分显示了萧军的气魄和个性,但同时也使他明白离开了‘公家’的日子不好过。在中央党校期间,萧军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外来知识分子在生活配给上的标准化使得个体对于生活、理想的趣味、需求渐趋同一,正如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赵超构在实地考察延安时所指出的:“这是由于生活决定了意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近代城市资本主义土壤中生长并繁荣的中国电影,到了延安的公有制环境中,自然就剥离了电影的商业属性。电影的创作标准及取向不再以由个体审美意识组成的观众群体喜好为衡量尺度。在公有制与军事化主导的延安生活环境中,电影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被放大并成为延安电影的唯一归属。而适用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最为直接、最具时效性,且又最能节省资源的便是影像的纪录形态。
另外,抗战时期的延安电影团不仅电影专业人士相当有限,所持有的胶片总共才只有1.8万尺,如果装载16mm电影摄影机只能拍摄总共大约500分钟素材,35mm则减半,对于像袁牧之、吴印咸这样的上海电影人来说,在延安拍摄电影,每一尺胶片都弥足珍贵。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延安电影团都不具备拍摄故事片的条件,而如果站在观众接受的角度,对于边区文化理解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群众来说,纪录影像画面配合解说词的视觉表达方式无疑是最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表达方式。毛泽东曾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延安文艺作品的大众化论题,将知识分子“不懂听众的语言”阐释为延安知识分子急需解决的沟通问题:“什么不懂?语言不懂,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在这里,沟通语言的障碍是指在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与工农兵的接受认知之间的障碍,自然也包括电影创作者的电影作品。而毛泽东所提到的“大众化”与孤岛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娱乐“大众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延安“大众化”的组成主体是农民,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城市文化相比,乡土气息中的审美体系和言说方式迫使延安电影的创作主体要首先破除亭子间的、资产阶级旧文人式的商业娱乐化表达。而直观、质朴地记录陕甘宁边区生产生活的影像语言,无疑就是最适合工农兵聆听的大众视觉,反而这种全新的大众视觉语言应该是更加灵活、自由的,它也不应像上海电影那样受到商业创作模式的限制。
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意识形态表征
抗战时期的延安共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和《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两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摄于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初,导演袁牧之早就构思过要拍摄一部反映延安和八路军生活风貌的纪录片,让生活在陕甘宁边区及边区以外的人们能够更深入了解延安与八路军队伍。袁牧之负责影片的编导工作,吴印咸担任电影摄影,这部延安电影的开山之作仅拍摄就耗时1年又7个月,袁牧之把影片的内容分为延安生活和八路军生活两大部分,1940年5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延安与八路军》的大部分底片赶赴苏联完成后期制作。但不幸的是,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遗失。新中国成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派陈播至苏联寻回少数残存的珍贵镜头,但确已无法恢复影片原貌。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党的文献》杂志2007年第1期所载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所查,吴印咸是唯一一位延安电影团的与会代表,他同时又负责整个活动的拍摄工作,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现场讲话应该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因此《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主要编导创意应该直接来自吴印咸,而王震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实行的垦荒生产运动恰好为“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影像素材。受当时洗印条件的限制,这部使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纪录片画面质感略显粗粝,整部影片除王震在开场不久后和毛泽东在片尾处有几个单人近景镜头以外,13分钟的影片大部分都是用来表现在南泥湾进行垦荒屯田“工农兵”群众的,凸显了政治宣传的目的,影片从介绍延安的景物镜头为开场,大致分为以下情节结构推进。
1.以全景的图式展现延安风貌,宝塔山—窑洞—延安全貌。
2.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召开干部会议,制订开荒计划。
3.农民身份的转换:浩浩荡荡的战士队伍在遍地荆棘的南泥湾驻扎下来,适时开荒种地,播种丰收,荒地变为良田。
4.工人身份的转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士们在开荒生产的同时,自己挖窑洞、盖房子、架设桥梁,战士们利用柳条、桦树皮编制各种生产生活上的日常用品。战士们上山伐木材,制造车床;辛勤的双手不仅可以满足拓荒的需要,又会纺纱织布;为了政治学习的需要,战士们用马兰草制成纸张,学习革命精神。
5.战士身份的回归:三五九旅贯彻农忙时小训练、农闲时大训练、突击生产时不训练的原则,严格的军事训练锻炼了战士们钢铁般的意志。而声势浩大的骑兵队伍充分表明共产党已经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做好准备。
6.头戴斗笠的工农兵在南泥湾的万亩良田中收割丰收的果实。一垛垛粮食被整齐的队伍运出田地,成了工农兵们桌上的菜肴。在工农兵的双手中,南泥湾从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三五九旅是学习工农兵精神的模范,这一切都是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影片的最后出现了毛泽东的多个单人近景镜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则明显地意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中,影像的意识形态表征显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质朴的乡村影像表达完全区别于城市电影中的摩登与喧哗,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中表述了乡村和城市的两面性:“乡村和城市,没有固定的意象、意义和表征,它们在不同的背景中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乡村可以是18世纪英国油画中美丽的田园诗,也可以是旅游者手册中令人激动的荒野……也可以被看作是单调和落后的,卡尔·马克思曾经称之为‘农村生活的极端愚昧’。相反,城市可以被看作是兴奋的和愉悦的地点,或者是罪恶与危险的所在——同时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两面。”《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部看似简单、通俗的纪录片正试图通过“工农兵”形象的阐释来建构一个积极向上的延安精神的语言价值体系,从开场处反复出现大的延安精神象征物——“宝塔山”,逐渐过渡到对“工农兵”的行为阐释,这些既是工人、农民,又是士兵的三五九旅革命战士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荒、种田、织衣、造纸、修桥、铺路……样样拿手,无所不能,最终凭借坚韧的精神力量撼动了看似不可逆转的自然定律,把贫瘠荒凉的南泥湾神奇地改造成了富庶之乡。
《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组织了一系列连续且富有韵律的视觉符码,在这部纪录片的初级指意系统中,所指的是战士们创造了一个富饶美丽的南泥湾;而在次级指意系统中,所指则表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极具正能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抗战时期的延安试图通过影像的视觉表达建立一套适合解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以用于与国民政府代表的城市资产阶级文化进行对抗。正如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所提到的那样,上海电影的摩登与时尚被解释为奢靡与挥霍,罪恶与昏暗。在大后方生活的左翼作家们则习惯性地把重庆描述成一座“雨雾笼罩下的黑暗之城”,在他们笔下有荒淫无耻的达官显贵,他们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在色欲、物欲、权欲上表现出无比的贪婪性,在本质上与汉奸实属无异。还有暴发户和太太小姐们的纸醉金迷,他们在醉眼蒙眬中大发国难财,在交际场合的假面扮相中尽展丑恶心态。左翼作家笔下的各色人等都带有明显的符码特征,这些有着模式化创作倾向的人物符码把重庆塑造成了光怪陆离的灰暗地带。而延安革命精神的成功阐释则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在重庆躲避追捕的冯兰瑞,在接到南方局转达批准她去延安的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理由相当朴素:延安没有盯梢的,延安吃饭不要钱,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根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的统计,至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了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终构成了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