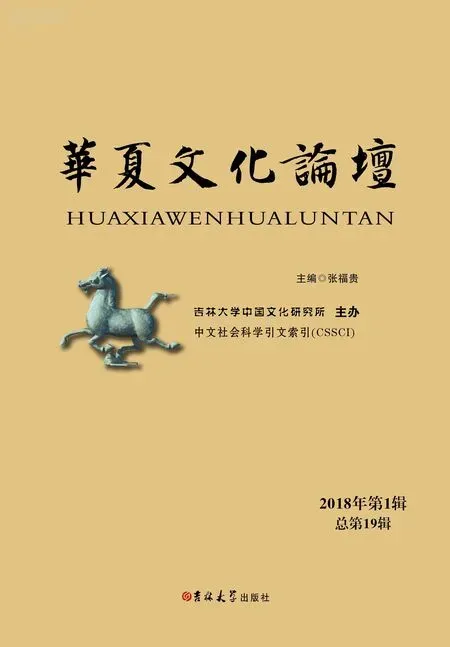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极花》的意象叙事研究
张岩泉 李蒙蒙
【内容提要】作为具有传统性的当代作家,贾平凹在小说新作《极花》中保持着对意象营构的热衷和对意象叙事的探索。在日常生活形态下,小说以具体意象、意象群落和整体意象的有效配合,构建了层次分明的意象系统,传达出作者对于城乡二元结构下乡土发展困境与农村女性命运的关注,寄托着其现代性之思与人性之思。在叙事策略方面,小说将意象叙事与奇幻描写、非线性结构结合起来,营构了文本的诗性审美意境,淡化了故事的悲剧感,体现出虚涵冲淡的传统美学韵味,较好地实现了现代叙事学与传统美学风格的融合。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认为,意象是由主观情思与客观对象融合而成的艺术形象,它承载着诗人的审美意趣与思想感情,对于提升作品的韵味与艺术品格具有促进作用。随着文学的流变与发展,意象元素逐渐渗入到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中,促成了意象叙事模式的生成。意象叙事不仅指叙事作品中的意象描写,更指意象对于小说叙事活动的参与和促进作用,如对叙事结构的贯通和优化、对文本意蕴的深化和凝聚以及对叙事效果的诗化提升等。“意象叙事在其历史进化中,已经具备民族思维的优势和时代思维的优势,它使叙事作品诗化和精致化的生命力是难以磨灭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指引下,贾平凹对意象叙事的热衷与追求由来已久。起初意象只是作为审美元素穿插点缀于文本间,作品基本停留在写实层面,还未形成整体升腾的艺术力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对整体意象的发掘和意象写实主义方法的运用,使其意象叙事渐入集大成的新境界。在新作《极花》中贾平凹将意象叙事与日常写实相结合,建构了充满象征韵味的意象世界。小说在日常生活流之上,以极花为整体意象,以圪梁村为一级意象群落,以风景画意象群、民间文化意象群、梦幻类意象群为二级意象群落,并下设若干具体意象。在整体意象的统率、意象群落的凝合与具体意象的支撑作用之下,各类意象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构成严整的意象叙事体系。概言之,《极花》的意象世界丰厚而不驳杂,意象体系层次分明,具有提升文本叙事内涵与审美效果的功能。
一、意象群落烘托下的圪梁村:“中国最后的农村”
《极花》中存在着以圪梁村命名的一级意象群落,它作为“中国最后的农村”的象征,具有典型的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由于自然资源与地理区位等基础性因素、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程度等经济因素、政策导向与劳动力素质等社会性因素的梯度性差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甚至乡村之间呈现出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致使“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群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如前现代、现代甚至后现代)”。在这一背景下,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性别比例失衡和现代文明严重缺席的圪梁村意象,表征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内地边远农村发展的滞后与落差,为文本中乡村溃败之殇与女性命运之痛的展开提供了悲剧性的空间场域。同时,圪梁村意象群作为一个大的意象群落,整合并凝聚着低层级的意象群落,使农村的现实生存状况和文化形态得到全面呈现,是整体意象赖以生成的现实语境。
(一)风景画意象群:乡土的衰败与凋敝
风景画意象群是对圪梁村客观生存环境的描摹,它烘托全文的悲剧气氛,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和审美功能。其中动植物意象、生活景观意象、建筑意象描摹出圪梁村单调萧条的自然环境、食色不足的生存危机和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呈现出圪梁村衰落性、封闭性与悲剧性的一面。
首先,圪梁村地处高原,交通闭塞,资源与环境危机严峻,自然灾害破坏性强,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圪梁村的动植物景观一片萧条,基本无生气,只有葫芦藤蔓上会开一种小白花,而且越来越瘦。文本中偶尔出现的野生物种意象,如狼、野驴等还标示着一种入侵性的活力,透露着乡土的蛮荒感与神秘感;其次,贾平凹将民俗韵味与象征意味融于生活景观意象中,营造出圪梁村的贫瘠衰败之感,形成悲剧意味。如石磨、水井、木鸡等意象,不仅具有风水学意味,更体现出圪梁村生存资料的匮乏和生活水平的低下,具有挽歌情调。另外,文本中有两类突出的声音意象,即金锁的哭坟声和兔子的哭声,二者都昭示农村女性越来越少的危机。全文在金锁的哭坟声中开始叙事,在兔子的哭声中终结叙事,并以金锁的哭坟声贯穿全文,形成悲剧基调;最后,窑洞意象具有强烈的男权文化意味。就外观而言,窑洞下方竖着的门和上面半圆形的窗子组合起来构成石祖形象,表现了乡村原始的生殖崇拜和男性崇拜。同时这种封闭的内向性建筑,象征男权文化的圈禁与驯化能力,隐喻乡土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命的压抑与摧残。
文本中虽然也涉及了一些现代性的异质意象,如手扶拖拉机、摩托车等交通工具,高跟鞋、丝袜、假发、耳钉、项链、化妆品等生活物件,以及血葱生产基地、血葱公司等新的生产方式,但是在转型期城乡急遽变革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现代性景观在圪梁村的罕见与稀缺程度,正好印证了圪梁村的封闭落后以及发展速度的滞缓。
(二)民间文化意象群:乡土的迷魅与危机
民间文化意象作为民间思维方式与心理结构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审美色彩与文化价值,对于维持乡土内部的和谐安定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现代文明的映照下,民间文化意象也逐渐呈现出不合时宜的一面。《极花》中描摹了大量的民间文化意象,如剪花花、观星、送娃、招魂、补粮等,再现了自然崇拜、鬼神信仰等前现代思维方式。作者在表现民间文化意象的非理性色彩与人文关怀性时,又注重发掘其在现代社会形态中的落后性与危机性。
《极花》中的典型民间文化意象包括剪纸—麻子婶意象组合、星象—老老爷意象组合,作者着意挖掘其审美魅力及叙事作用。剪纸是重要的西北民俗之一,最初被用作祭祀时花朵、瓜果的替代物,后成为装饰品,并被赋予辟邪压鬼和敬神的功能。剪纸的产生与前现代社会的图腾崇拜和象征思维有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沟通的体现,同时其丰富绮丽的造型也传达了人性对美和艺术的向往。如《极花》中的空空树意象是枯树、人头、小鸟、黄蜂的凌乱组合,整体怪诞拙朴,是民间幻想能力的体现。麻子婶意象与民间剪纸艺人库淑兰具有同构性,她们都以剪花娘子自居,都将剪纸视为灵魂寄托,在苦难的生活中探索着精神自由。在“死而复生”的经历后,麻子婶俨然成仙得道,其剪纸造型夸张,并配以自创的歌谣,被村民当作治病的药方,并对胡蝶产生强烈的精神救赎作用,在其多次言传身教中,胡蝶终被感召,成为虔诚的“剪花童子”。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带有迷信性的前现代文明形态仍然顽强存活,并维系着圪梁村的精神信仰与生活方式,这体现出圪梁村人精神面向的僵化与落后。星象—老老爷意象是文本中又一鲜明的意象组合。星象是指星体的明暗及位置等,为人类提供气象、农事依据,也是民间占测吉凶祸福的载体。贾平凹本人对占星卜测之术有一定研究,《高老庄》《浮躁》等作品中都涉及神秘星象的诡奇色彩及其象征意味。《极花》中的星象在神秘的对应性功能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色彩,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天命观,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胡蝶的痛苦和寂寞,具有安抚与延宕功能,是胡蝶完成灵魂摆渡、实现自我确证的媒介。老老爷意象的神秘性体现在其民间原始思维与生存智慧上,作为乡村的精神领袖与传统文明的继承者,他曾对乡村的生产生活与精神领域具有不容置疑的支配作用,其依靠传统伦理道德来挽救败坏的世风人心的济世理想与《古炉》中的郭善人形象具有一致性。同时老老爷意象本身也具有封建保守和悖谬性的一面,如其尊神敬神的思想、封建宗法理念、宿命论观念与容忍人口买卖的行为,都呈现出传统民间文化的落后与不合时宜之处,也表征着圪梁村的现代科学文明、法治观念与制度等的严重缺席。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剪纸—麻子婶意象,还是星象—老老爷意象都无法使现代化进程中畸变的农村走出困境,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仍刻不容缓。正如宋强所言:“这种看上去很美、很深奥的传统,我们可以欣赏、可以把玩,但绝不能把它作为未来发展的依靠。”
(三)梦幻意象群:女性的挣扎与弥合
意象不仅包括自然意象、社会意象、文化意象等类型,也涵盖着一种特殊的饱含作者创造心力的形态——梦幻意象。梦幻意象更多地源于主体心象的投射,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韩鲁华曾对贾平凹小说中的梦幻型意象做出专门分析,他认为梦幻意象的创造以人的意识与幻觉为基础,是作家艺术想象的变异状态。梦幻意象具有永恒性和超验性。同时,梦幻意象也是主人公潜意识的体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极花》中的梦幻意象包括梦境、黑洞、气、黑等超现实意象,这些意象拓展了文本的时空层面,带来了亦真亦幻、神秘魔幻的审美效果。胡蝶梦中出现的自由灵性的红狐意象具有纵横恣肆、奇异超凡的特征,为胡蝶的孤寂提供释放渠道,同时其物我化一与先知先验的特征使这一意象具有了超验性与心理性意味,它作为受压抑的欲望的补偿物,是胡蝶无意识世界的反映,寄寓着胡蝶对逃离困境的渴望和对命运的潜性抗争,暗含着作者的悲悯情怀与人性关怀。黑洞意象是文本中典型的幻化意象之一,它是胡蝶梦中出现的幻化的洞口,具有时空穿梭功能,是胡蝶在非理性状态下对现实的变形想象,具有虚幻性与荒诞性特征。黑洞意象将迥然不同的时空向度勾连起来,使得胡蝶能够在城与乡、梦与现实、离去与归来之间自由跳转,它不仅是胡蝶脱离困境的捷道,更寄托着胡蝶向自由、亲人和城市回归的艺术想象,在超现实的梦幻世界中,胡蝶的愿望得到暂时满足,文本的节奏也得以舒缓。《极花》中最富有意味的梦境意象是结尾处被解救和又重返的梦境,它是胡蝶对自己命运的设想和预演,寄托着其两难心理与自我挣扎,具有浓厚的心理性特征。贾平凹在描摹这一意象时,打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以实写虚,突显真假难辨之感,使文本笼罩着迷离朦胧的虚玄氛围。同时这一超验的梦境意象寄寓着作者对胡蝶的离乡——归乡问题的考量与探究,渗透着作者不无矛盾的价值理念,这种以梦境演绎现实的方式也相对削弱了文本的悲剧感与冲突感,与电影《盲山》海外版中白雪梅砍死“丈夫”的结局形成对照。从整体上而言,梦幻意象的设置打破了意象营构的平面维度,为文本增添了灵动飞扬的浪漫格调与奇幻超验的非理性意味,实现了主体精神境界的升华。
总之,圪梁村意象群的营构使作者对圪梁村生存空间的描摹,并非止步于客观展示的层面,而是渗透着作者对乡土溃败境况的茫然与哀伤之情、对人性的善意情感关怀,以及对传统乡土文明的留恋与审视,从而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与文化根基,也将文本的主题从打击拐卖行为升华到关注乡土发展前景与探索人性内涵的层面,使小说超出一地一事的局限,而具有了普遍的隐喻意义。
二、“极花”意象的整体观照:乡土的异化与救赎
极花是贾平凹在《极花》中的审美理念与创作题旨的凝结物,既是文本的整体意象,又作为标题呈现,统领作品的意象建构,将具体意象统摄起来,并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重要的参与作用,决定了文本的整体内容和基调。整体意象不断向四周辐射分散,形成巨大的磁场,“既有一种辐射作用,又有一种向心的势能,使作品叙说的具象化的人、事、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使作品成为一种整体象征”。极花意象既是现代性进程下乡村与女性的悲剧象征,又隐含着作者对女性精神的礼赞和对乡土未来的期盼,这也是文本的题旨所在。
(一)现代性的悲剧符号
极花意象隐喻着现代性进程中商品性、金钱欲的罪恶性面向对乡村的侵入与破坏。现代性在为人类带来物质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滋生着金钱崇拜、利己主义、生态失衡与人性异化的阴暗面。极花是一种类似于冬虫夏草的动植物混合体,具有商品属性,是现代性对乡土价值的发现与命名。在极花的商业价值被发现之前,圪梁村是相对贫困而和谐的,属于典型的前现代文明状态。但是在享受到极花所带来的商业利润之后,村民们开始不计一切代价地疯狂挖掘,致使土地基本撂荒,并且学会了投机取巧、坑蒙欺骗等商业手段,甚至出现因偷极花而引起的灭门惨案,乡村充斥着贪欲泛滥、利益至上、道德伦理失范等负面气息。从这一意义上说,极花是现代性的悖论与悲剧的表征,它带来了乡村对于致富的焦虑和发展的渴望,却也隐含着中国内地边远农村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惨重代价与创伤记忆。贾平凹的关注点或许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新世纪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吸血性改造的痛苦现状”。
极花意象隐喻着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光棍问题与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严峻性。极花是女性本体的象征物。在圪梁村人的观念中,极花可以招来女性,于是人们纷纷效仿黑亮娘,将干极花装入镜框。极花的稀缺程度和圪梁村女性的匮乏现状形成互文。在这一层面上,与极花相对应的是充满悲剧意味的血葱意象。作为圪梁村的独特产物,血葱以增强性欲而出名,象征着男性强烈的生殖欲求和原始生命力。旺盛的血葱与稀缺的极花形成尴尬的对比,凸显着圪梁村的“种”的危机。“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女性涌入城市,农村男性的生理需求及生殖需求越来越得不到满足,作者以极花命名,既是为了引起对农村“剩男”群体的关注,又是对农村社会中和谐的两性比例的呼唤。
极花意象更是胡蝶自身命运的悲哀隐喻,胡蝶是被移植到圪梁村的女性之花。胡蝶与极花本应享有自由生存的权利,但是却沦为他人利益的受害者,失却自然状态下的顺向发展,而被迫接受了另一段被恶意扭曲的命运。从农村走出去的胡蝶,本想在城市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意外地被拐卖到更加贫困的山村,遭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无望中挣扎,又在绝望中回归,她最终选择留在圪梁村,放弃自我和主体性,成为与镜框里的干极花相映照的无魂之物,这是被拐卖妇女的个人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作者在此寄予了对人口买卖者与暴力实施者的控诉与批判,以及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愤懑。同时,镜框里的干极花意象与胡蝶意象都是一种被禁锢的美的象征,类同于张爱玲笔下的“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绣在屏风上的鸟”意象,散发着一种苍凉之美,隐喻着女性命运的悲哀与无助,体现着作者的悲悯情怀与对女性生命状态的深层观照。
总之,极花意象作为一种混合的二元体,是中国乡土社会复杂难言的矛盾状态的隐喻。在文本中,不仅乡土社会呈现出文明与野蛮共存、现代与传统并置的混沌不清的存在状态,而且作者的价值观念也具有模糊含混的特征,他既痛斥着拐卖现象,又同情着乡村的弱势群体,既无可拒绝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又缅怀着行将消逝的传统乡土文明。
(二)女性与乡土的救赎幻象
极花最奇妙之处在于它的蜕变过程,即由冬天休眠的毛拉虫变为夏天绚丽的拳芽花,实现生命的升华过程。就这一意义而言,胡蝶在城乡之间的命运转化和升华,与极花的生命过程形成呼应。胡蝶作为有过短暂城市生活经历的少女,被拐卖到圪梁村后,与周围的环境形成激烈对抗,她憎恨着乡村的暴力与落后,并努力摆脱被囚禁的困境,但在身心遭受损害、出逃成为不可能之后,也开始尝试适应被扭曲的生命,重新审视圪梁村的人性、伦理与文化,并逐步融入乡村的文化秩序与生存规则中,完成了生命的第一重蜕变。而在离去与归来的梦境中,胡蝶预想到城市的另一层拒绝与伤害,在梦醒之后为了儿子毅然做出留在圪梁村的抉择与牺牲,则是以一种残酷的自我妥协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最后蜕变,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最终确证,“在中国哪儿都一样”。从这一意义上说,胡蝶不仅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更以自己的蜕变保全了黑亮一家的幸福,实现着对他人的救赎。这种坚韧的精神与母性至上的情怀是胡蝶人性中的亮点,也是极花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死之身的映照,作者在此寄寓了对一种柔美宽容的女性精神与生命境界的礼赞。极花成为“整个故事当中充盈着阴柔之美的文学象征和符号”。总之,极花意象的设置使得胡蝶的形象不仅停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层面,更为其增添了柔韧、善良和梦幻的美好意蕴。
极花的不死之身与涅槃重生和中国乡土社会的顽强生命力形成呼应,作者以此寄托对乡土和谐美好的未来的期盼与希冀,以及对乡村发展转机的渴望。作者在这一意象中融入了积极的情感基调与理想色彩,但似乎将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寄托在女性与现实的主动和解上,他期盼胡蝶能用自己的善良救赎黑亮家的苦难,能以自我牺牲与献身来实现对异化的乡土的拯救。“《极花》纵然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的关切之间,打开了通向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的讨论空间,但其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所包含的偏执还是令人倍感不适。”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同样可见于同类型题材的影视剧中,如电视剧《阿霞》中阿霞在被解救后,又返回来与买主丈夫真正完婚并带领村民们走向致富大道。这种大团圆的处理方式虽想象性地解决了眼前的矛盾,但毕竟存在价值争议。只有采取合法合理的措施,才能使这一困境得到有效解决,从而使乡村真正绽放出和谐的“极美之花”。
总之,作为文本的整体意象,极花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催生的乡村“极悲之花”与“极美之花”的双生体,承载着作者的现代性之思与人性之思,凝聚着文本的主要意蕴与审美内涵,也是作者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
三、意象叙事策略的审美生成:多维诗意空间
意象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的重生,对于构建当代文学的民族品质,实现古典美学的复兴具有重要作用。《极花》中贾平凹将意象叙事与奇幻因素、非线性结构结合起来,弘扬了传统意象诗学的蕴藉美和诗性美,提升了文本的审美格调与精神内涵。
(一)意象叙事与奇幻因素的结合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奇幻性与神秘性成为贾平凹叙事作品中呈现出的鲜明的美学质素,各种神秘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被引入叙述中,如鬼神信仰、风水算命、轮回转世、神话传说、奇山异水、灵异动物等,形成了混沌、超验的神秘文本空间,并不断与文本的写实层面交融、互动着,在传达作者的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立场的同时,也彰显着现代意识。
《极花》中弥漫着各种奇幻因素,如关于圪梁村由来的神话传说、老老爷和麻子婶的怪异形象、灵性的野生动物、神秘古老的民俗文化和超现实的梦幻现象,以及天人合一、自然崇拜的原始思维等,这些因素的融入使圪梁村超越了晦暗荒凉的常态,呈现出原始和魅性色彩,同时为意象叙事营造了奇幻诡谲、富有意味的审美空间,使意象叙事与文本神秘奇幻的整体语境紧密契合,从而有利于作品意蕴的升腾。如熊耳岭常年雾气缭绕,野兽出没,并发生过五头野驴掳走陪几个妇女去采极花的小母驴的事件,故事离奇诡异且与文本题材有着对应性,呈现出乡村的荒蛮和野性色彩,为意象叙事的展开提供外部环境。又如离魂叙事中的灵魂出窍描写,每当胡蝶的身体遭受极大磨难时,灵魂旋即跳出身体,俯瞰受难的本体,为文本营造出超验诡奇的神秘氛围,同时隐含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贾平凹常在小说中营构出一些具有奇幻和神秘特征的意象,如神秘文化意象、梦幻意象和自然魔幻类意象等,充分开掘意象的隐喻与象征功能,使文本具有多义性和寓言特征,并弥漫着奇幻的诗性色彩。如《极花》中的星象意象是具有神秘性的审美意象,它关涉着人与宇宙之间的奇妙对应关系,“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的民间思维将胡蝶的关注视点从对外界的愤懑引向对自身的重新发现和对自然的认同与归属上,星象意象的招魂功能强化了文本的奇幻感。
但是贾平凹小说中的奇幻世界并非脱离现实生活本体的凌空虚蹈,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日常生活叙事力度。他倡导以实写虚、体无证有,既追求玄妙空灵的意蕴空间,又注重向原生态的生活流开掘,追求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综合,从总体上营构文本的浑然虚涵之感。就《极花》中的梦境描写而言,贾平凹混淆虚境与真境的界限,构筑文本迷离神秘的审美意蕴,又极尽写实之能事,以极实写极虚,突出梦境的日常生活感与现实意味,使梦境成为主人公潜意识的表征与作者思想观念的外化,体现出虚实相济的审美特征。
总之,《极花》中意象叙事与奇幻因素的结合,打破了平面的叙事维度,建构了虚实相生的多维诗意空间,拓宽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与自由度,构成了文本的诗性审美意境,增强了文本的审美效果与超越性,从总体上呼应着贾平凹对一种雾气氤氲的混沌苍茫的“大境界”的追求,同时也是其生命情怀与写作视野的映照。
(二)意象艺术与非线性叙事的配合
贾平凹说:“最开始写《极花》时,也想写成一个线型结构,后来写着写着就写成一团的,这样我就把字数大大压缩,变成最短的一部长篇。我有意地以第一人称去写胡蝶在被拐卖到的村子里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这种唠唠叨叨的给人诉说的叙述方法,以前我很少运用。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本节对《极花》的“团块”叙事和“唠叨体”叙事进行分析,并进而说明这两种叙事技巧对意象叙事的促进作用。
“团块”叙事并非贾平凹在《极花》中的首创,“早在写作《废都》阶段,贾平凹已经自觉经营他所谓的‘团块’叙事结构。”“团块”叙事又被称为“块状”叙事,它是对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的悖反,它不追求情节的完整连贯性,而是将发生于不同时空的无必然因果关联的叙事片段拼贴在一起,构成不同的叙事团块。这种叙事结构看似散漫无章,其实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并贯穿着统一的情绪基调或主题理念,类似于电影叙事学中的“团块缀合式结构”。《极花》全文由六个叙事团块构成,即“夜空”“村子”“招魂”“走山”“空空树”“彩花绳”六部分,每一个叙事团块内部都蕴含丰富的叙事内容,同时又都是作为独立意象或意象群落而存在。如村子意象是对乡村风俗文化和经济状况的介绍,招魂意象意味着胡蝶在圪梁村的失身、失魂以及麻子婶的救赎作用,走山意象呈现着乡村的日益衰败与凋敝境况,“彩花绳”意象则喻示着胡蝶与圪梁村之间剪不断的命运关联。六个叙事团块之间看似无必然的逻辑关联,甚至自成一体,实则被文本的整体意象和内在的情绪基调缀合着。团块式叙事使每一块状内的意象更具整体性和黏合力,构成鲜明的意象群。同时作为一种散文式的叙事结构,叙事团块之间的非连续性使文本生成了强烈的开放性与发散性,使得叙述的重心从清晰完整的情节链转移到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整体意蕴与诗性境界上,形成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效果,从而拓宽了文本的情感层面与韵味层面,提升了文本的厚度与神韵美。在贾平凹看来,“块状有一种冲击力……块状结构就像冰山倒那种情景,一块子过来了,就像泥石流一样,你能想象得来那种气势。”
“唠叨体”是贾平凹在《极花》中的新创,同以往的“闲聊体”“说话体”类似,“唠叨体”有意对宏大叙事和历时叙事进行解构,它往往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打乱时间顺序和叙事节奏,放任叙述主体的模糊、无中心的唠叨,“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文本中胡蝶围绕着圪梁村的日常、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关于城市的回忆等,以被围困的外来女性的视角,将其在圪梁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随心所欲”地倾诉出来,建构了“圪梁村百科全书式的村庄断代史”。在胡蝶的说说停停、前前后后、详详略略、虚虚实实的唠叨中,文本变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和自由性的叙事体,为意象叙事营造出广阔的空间。同时这种抒情性的小说结构类型将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放置在绝端重要的位置,将人性、人情与文化的因子注入日常生活叙事中,使文本变得诗意连连,也有利于意象叙事的展开。
总之,这两种非线性叙事范式打乱了文本的时序性与逻辑关联,淡化了情节冲突,形成了具有开放性与生成性的叙事模式,提升了文本的表现力与张力,为意象叙事的展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它们又从根本上接受着意象叙事的统构与缀合。这种叙事模式也将读者的关注点从跌宕起伏的情节上转移到文本的韵味性与抒情性上,重塑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综上所述,《极花》的意象叙事既是对传统美学的回望,又是贾平凹主体精神特质和审美理想的呈现,更是对当今乡土发展问题的诗意叩击,是一次较为成功的美学实践和创新。《极花》中没有极端化书写的残忍,而是遍布着一种冲淡与和涵的柔化力量。作者无意于突显故事的悲剧情调,而是以意象叙事点亮文本的写实空间,淡化故事本身的悲剧感,将一种更高的精神指向与超越力量熔铸其中,体现出和谐冲淡的传统美学韵味。但是意象叙事在淡化故事悲剧效果的同时,也相对削弱了文本的批判性,使作者的叙事立场变得暧昧不清。反观同类题材的电影《盲山》,类似于纪录片的叙事模式使故事弥漫着阴沉的冷色调、紧张的节奏感和强烈的批判性,导演李杨说:“我讲了一个故事,把人性中我们习以为常、不觉得是黑暗的一些事情提出来强化,这是我想做的。我就像拿一个手术刀,把它切开了,血淋淋地让你看”,这是《极花》未明确的层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