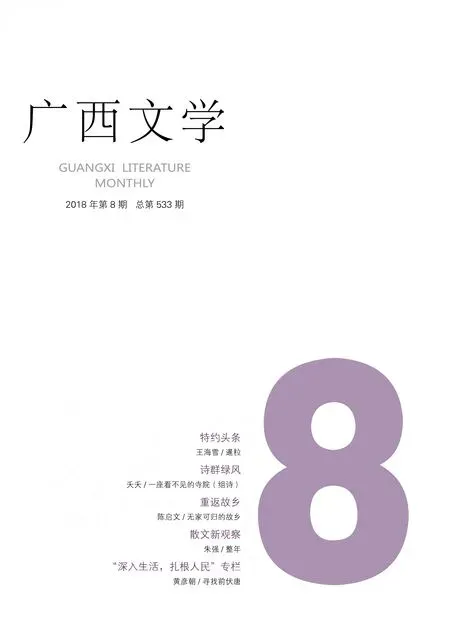日常叙事的深沉诗意
——漫谈壮族作家黄少崇的散文创作及启发
侯 珏
一、黄少崇的艺术场域
生长于广西中部红水河畔的黄少崇,是一位典型的壮族作家,近三十年来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散文创作。但是他的成就和知名度并不对称,若要对他的创作谈论一番,恐怕离不开一个合适的艺术场域。我将这个场域锁定在民族文学特别是壮族文学上面,也许唯其如此,才能谈得更加明晰。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全世界两千多个民族中约占第六十位。放到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来看,壮族的主体地位也是无法撼动的。因此当我们谈论广西文学的时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可以说,壮族文学是广西文学的缩影,或者反过来说,想要考察广西文学的发展脉动,只需分析壮族文学的脉象,便可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近代以前,封建统治者坐北朝南,对于遥远的南方有无尽的遐想,甚至与蛮荒等同,南方在“他者”的描述与阐释中显得非常奇异和另类。虽然“他者”的描述或多或少具有主观的成分,但是古代壮族人民,确实是在相对封闭的南方时空里,创造着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因为地处西南边疆,壮族人创造了有别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特殊民族文化与民间习俗。在历史上,壮族的民间文学十分发达,体现在口口相传的创世史诗、山歌、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形式中。壮族文学中的文人文学部分,从唐初才开始萌生,宋明以后逐渐发展,且深受汉族文人及其作品的影响。明清以来,壮族的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呈两条脉络并行发展。
壮族近现代文人文学的数量,虽然比不上民间文学那么庞大,但这部分作品深深植根于自己民族生活的土壤,一面不断汲取中原和岭南文化的长处,一面又按着本民族的表达习惯向前推进,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具有浓郁的南方民族心理气质和独特的诗意表达方式。即使是现当代,异军突起的壮族文学也没有跳脱过自己的民族属性。无论是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还是韦其麟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莫不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
进入21世纪,壮族文学延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族叙事的现代化传统,涌现出了许多作家和作品。如《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系列,壮族作家就占据了半壁江山;河池市与来宾市近年出版的数十本作家文集,超过八成为壮族作家作品。但是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冲击下,听着文学被边缘化的聒噪,壮族作家不得不在“娱乐至死”、精神消费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面临新的抉择和转型。怎样转换身份、转变审美、超越地域、书写民族、拓展文学发展空间,是新世纪以来壮族文学的时代课题。新世纪以来,壮族作家诗人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反映当代生活、发表独特见解,作家的身影和声音空前活跃。这批年轻的作家所遇到的时代语境、生存环境,都与前辈作家不可同日而语。文学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元化,更加具有挑战性,当然也有机遇。对读者和受众的重视,让文学的商品属性在新的传播条件下,显得更为突出。国内外文学的竞争与交流,赋予壮族作家新的使命,给壮族文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作为一名文学叙述者,黄少崇置身于这种世纪交替的文化语境中,当然也面临着身份焦虑、思想困惑、艺术选择和表达方式的调整等问题。
那么,壮族作家怎样应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怎样调适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壮族文学何为?对此,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文学转型,是必然的。如果从总体上考察新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我们会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主体身份的转换。作家的民族身份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个体的人,壮族作家具有跟其他民族作家相同相通的特点,但是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语境和民族心理,又让壮族作家具有本民族这一族群价值的世界观,他不仅是个人的书写者,还是族群的代言人。放到更宽广的文化视域中,壮族作家的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被建构之中。
可以说,从个体发展需要而超越群体的羁绊,到从群体中寻找个体的价值,是壮族作家主体身份来回转换的两个极端。这包括超越语言的障碍、地域的限制,摆脱民族文化的狭隘部分,以及利用民族题材,吸收与改造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本民族时代境遇的反思,是壮族作家在新世纪里普遍的表现。这种内在的表现更多的是通过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来实现的。一批山沟沟里面的壮族教师、农民、公务员、普通工人等,经过文学的通道,实现了命运的转折,他们集结到文学的旗帜下,重新建构着壮族的当代精神世界和形象。
其次是审美精神的嬗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壮族作家和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汇入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中,壮族文学的审美品格趋于单一化,到20世纪下半叶,壮族作家在沉寂中突破,带着浓郁的民族特色重新登上历史的竞技舞台。在文学工具上,他们逐步完成了从母语到普通话的过渡;在文学形式上,他们完成了民族民间文学形式的现代化转型;在文学理念上,他们完成了对欧美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学习与借鉴,推动壮族文学在当代走向第一次高峰。
新世纪以来,壮族作家在自身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壮族文学在审美精神上因此出现了转向,包括从民族的大审美转到幽微人性的表达,从关注人物的命运到关注生态文明的变化,从社会生存的现状到民族文化的反思,从现实主义写作转向先锋写作的探索,从摆脱母语痕迹到重新审视母语。这其实也就是不断寻找个性化表达的过程。为了在众声喧哗中突出,壮族作家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应和大众、与全国作家同台竞技需要的主流叙述,一种是突出和强调自我的个性化叙事。他们在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中不断锐化差异,强化个性,更好地彰显了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黄少崇,其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一直没有离开过大桂中地区(柳州—来宾),他的文化感知来源于壮族民间,他的文学创作是在壮乡的土壤中分蘖成长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黄少崇已经开始散文创作,90年代初也试过写小说,但写作热情仅仅维持了几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的焦虑和文学的困惑,他和很多当时的作家一样一度中断写作,直到2002年来宾市成立,他成为这座桂中新城的建设者之一,才重新拿起手中的笔。
而此时的广西文学生态,由于受到市场化和全国文学潮流的影响,小说写作成为香饽饽,舆论也大肆宣传本土作家触电的成绩,让许多壮族作家跃跃欲试,希望能够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改善生活。信誓旦旦的黄少崇是文学桂军躁动分子之一,他忘记了自己最初乃凭借散文出道,转而投入到小说写作当中。实践证明,他付出五六年的努力,结果并不理想。这从他在2008年出版的小说集《你凭什么欠我》可以看出来。在这部作品集里,他说自己“觉得脸红”,并没有“产生多少欣慰感”。
让他对文学重新产生自信的,还是散文。2007年,他凭着自己的直觉重新拿起笔,写下了散文《在母语中死去》。这篇作品发表在当年第八期《广西文学》上,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成为他的第一篇代表作。当时的主编罗传洲先生看到了这篇作品后,高兴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篇气质独特的作品,把壮族母语的现代遭遇放到世界民族语言遗产面临同化和消解的危机语境中考察,认识到少数民族语言的淡化与消逝乃时代大趋势可是作为融进血液的母语,作者又对本民族的文明结晶怀有深沉的依恋与惋惜,通篇作品的基调哀而不伤、幽默而不乏诗意,特别是作品结尾表达了自己年迈衰老时愿意在一场母语的唱诗仪式中死去,让读者不禁产生一种敬意与感动之情。总之,《在母语中死去》在思想艺术上既有理性的高度,又有情感的浓度,突破了当时大行其道的游记随笔和空乏矫情的传统写作模式,给广西散文界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和可能。为了鼓励更多人深挖本土题材、深思本土文化,《广西文学》杂志随后开设了“民族血脉”和“文化记忆”两个并列互补的散文专栏。
受到极大鼓励的黄少崇,在此后数年时间,以每年一两篇的发表速度,延续着这条无意中走通的散文创作之路。《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 《花婆的春天》《1976年的毒杀芬事件》《熟食时代的茹毛饮血》《捡金记》《踮起脚尖也望不到的地方》等一系列高质量的文本脱颖而出,连续荣获两届广西青年文学奖,被《散文选刊》等关注和转载。2014年,黄少崇的这一写作方向和计划,水到渠成被列为广西文联重点扶持项目。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的第一部散文作品集《在母语中死去》于2016年5月顺利出版。2017年11月,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广西散文学会联手来宾市文联,举办了这部作品集的研讨会。
在黄少崇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壮族作家在文学之路上苦苦探索的成长轨迹。从技术上解读他的作品,可以管窥当代壮族散文作家的一些普遍优点和问题。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壮族作家在努力地转型,以及写作转型期间存在的困境。
二、黄少崇散文的品质
散文的最高境界是使用极具个性化与风格化的语言,呈现新颖独特的思想与体验,让读者获得刺透心灵的启迪和绵延不绝的回味。当下短平快的社会生活,让人人都可以写一手散文,造成的后果就是把散文的整体水准拉低了,散文与生活、语言之间的艺术张力被极大地缩小,甚至在不少写手那里散文干脆等同于琐碎的生活。而散文作为一门最少受到欧美文学影响的汉语传统文学体裁,仍然需要在一定话语单位范围之内有序列地呈现它的艺术品质,或者说需要用一种稳固独到的艺术形式呈现汉语的艺术内涵。在广西的中青年散文作家当中,黄少崇对散文艺术的追求,无疑是认真和严肃的。
十年前,笔者大学毕业后到来宾市文联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刚好与重新投入散文创作且处于写作兴奋期的黄少崇相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每一篇散文,我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拜读过,也编辑过其中的若干篇章。这些作品大多收入散文集《在母语中死去》,算是他这十多年的主要创作成果。从时下的经济标准来看,他如此之慢的生产速度,委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不急不躁十年磨一剑的写作韧劲,却也令人敬佩。文学的功利性目的在他那里已经趋于零。我曾不止一次建议过他,要抓紧机会好好写一写来宾武宣县东乡镇的清末民初地主庄园题材,无奈他就像一辆不适应新油品的老爷车,怎么点火也发动不起来。由此可见,他是一位执着于向内审视的作家,而不太擅长依靠贩卖技术去搞“外贸”。
保持独立的思辨品格,坚持诗由心生的文学态度,是黄少崇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在这条原则之内,他实现了游刃有余的散文叙述。纵观他的一系列作品,我认为写得最成功的篇目是《1976年的毒杀芬事件》《在母语中死去》《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捡金记》等。这几篇长度不短但也不算长的散文写得最为放松自如,他的知识思想积蓄和写作才华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展现。之所以成功,我以为有如下几个优点:
第一,这些作品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文化独白,是一个写作者的真实生命体验和记忆深处的文化印记。清代壮族诗人郑小谷说,写文章首先要有阅历,其次才讲才情。反观黄少崇,如果他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和真切的体验,是写不出这些文章的。怎样对这些阅历、这些经历材料进行筛选,又是考验作家的另外一种功夫,这就需要视野。非常难得的是,黄少崇站在了文化的视野上来处理自己的经历材料。《在母语中死去》是他停笔多年后重新转到散文阵地来的开山之作。这篇作品讨论了人作为文化携带者所要跨越的第一道障碍,也即普通人作为社会人除了吃喝、生育之外的一个基本问题:语言问题。语言就像空气、筷子、人民币那样,对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乃至忽略其存在本身的符号价值,而作者却能够吹沙见金,从文化的角度对大众习以为常的母语进行文化审视。本来语言是文学表达的工具,作者偏偏要在文学作品中乐此不疲讨论语言问题,这就很像在小说中讨论怎样写小说一样,是叙事学上的元叙述。元叙述的方法在黄少崇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比如《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作者就多次跳出来说明,他当下是在红水河北岸的一间小屋子里书写有关红水河南岸的往事的。这种有意为之的疏离感,算不上是“复调”,也绝对不是新手无意露出的马脚,而是为了增强散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同时,作为叙事时空的坐标,它能让作品本身的时间结构更加明确和稳固。回到视野的话题上来,《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虽然写的是少年时代遇见的那位民间草帽吟唱艺人,但作者并没有以写人作为终极目标,他把人物的命运当成洞察时代境况的准星,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聚焦于壮族民间音乐、文化仪式的兴衰这一靶心。那就实现了从个体到整体的文化思考,从人性到世道的审美转化,这种思考与转化,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宏阔而深沉的诗意。
第二,黄少崇运用小说的技法来写散文,显示出独特的叙事魅力。其实这也不是他的独创,只是他比较早的使用并坚持至今形成特点罢了。早在1993年,《广西文学》曾在头条位置推出过黄少崇的小说作品,在回归散文创作之前,他曾经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小说,发表过二十多万字的中短篇作品。这些叙事练习,让他很好地掌握了讲故事的技巧。就像上文所提到的,无论是《喑哑时光里的苦涩吟唱》《1976年的毒杀芬事件》,包括后来的《捡金记》《踮起脚尖望不到的地方》,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当作小说来读。因为从头到尾,密集的叙事性语言,在比例上均比转场极快的散文语言要多出很多,有的比重几乎占据通篇主体。小说那种情节布局、戏剧冲突、细节描写、氛围营造、人物刻画、对话驱动等等,都在他的散文作品里有非常完整的体现。特别是《1976年的毒杀芬事件》,纯粹就是一篇披着小说外衣的散文,或者说是一篇以散文为文体目标的小说。整个事件的开端、发展、递进、高潮和结局,完全是按照小说的逻辑来处理的,如果要说这是一篇散文,他唯一的依据就是非虚构。即便是思辨议论性很强的作品《在母语中死去》,作者也能恰当地运用小说手法来为散文服务,如这一节对话的使用:
——吃了?
——嗯。
——听说你那儿子……
——嗯。
——不是说……的么?怎么就……
——嗯。
这种巧妙的跨文体技法融合,省去了许多饶舌的笔墨,让散文的叙事流动张弛有度、起伏荡漾,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有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但在以“情理融合的讲述”见长的散文里加入“情节描绘为主的叙述”,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度的把握,因为反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小说家写起散文随笔来容易流于卖弄叙事技巧,而一些散文家由于叙事能力的不足又常常显得语言肌理不够圆润饱满。
第三,自然的幽默感让他的散文充满智慧气息。黄少崇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到河流湖泊之滨钓鱼,上荒山野岭摘果子,或者在院子里下棋,扎起围裙进厨房煮菜,他都能够乐此不疲。前两年笔者还跟他一起带着家眷,在黔湘桂少数民族地区开车转了一圈,所到之处无论多么艰苦,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探索未知的激情。正因为积极地参与生活,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让他对日常细节的触摸无所不至。所谓听千曲而后晓音,一个人见多识广了,就能举重若轻,凡遇大事便没那么紧张兮兮假正经。文如其人,黄少崇在现实生活中给我的印象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了这个特性。比如《1976年的毒杀芬事件》,说到储水柜被细菌污染了,导致全校师生浑身发痒,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个痒的场面、痒的情节、痒的状态,以及人们面对自身持续发痒这个难题时干出那些啼笑皆非的事情。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生动幽默、活灵活现,多位人物的个性特征、人性深处的想法,均被他从一个“痒”字里面挖了出来。在别的一些作品中,同样可以发现不少充满智慧的幽默语句,比如讲到柳州鱼峰山的时候,作者说“鱼峰山”如用壮语连读即“岜岜岜”,“太累,也不好听”。还有《乡村旧物志》等篇什里,也体现出作者细微的观察体验与幽默的语言气质,因篇幅关系在此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他为何有这种幽默?首先肯定是他对生活细节的敏感使然,其次应该是因为他能够始终站在平民的角度来写散文。这就是接下来要谈的第四点。
第四,平民化的语言让他的散文充满活力。在大环境里,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公共语言统治的世界,很多人的语言变得僵化,面目可憎,似曾相识。而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应该是让那些被掏空的僵死语言重新焕发生机,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讲述公共的经历,刺激人们重新对日常事物产生真切感受,进而找到被公共语言遮蔽的真相。关于这一点,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方法》那本书里有过精辟的讨论。他说,我们过着习惯而无意识的生活,人的个性几乎被公共话语吞没,由“电脑系统化的他人的语言统治结构”从各种侧面强制着我们走向行尸走肉般的“自动化”,随着“自动化”生活而来的是个体思想的麻木与个性语言的残废。而想要拾回人性的价值与尊严,首先得从空洞的话语极权中实现突围,让人感受到“物”——这恰恰也是文学存在的价值。
回到黄少崇的散文中来,我们发现他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经常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和立场,时刻触摸到“物”的存在。例如在《熟食时代的茹毛饮血》这篇作品里,他就从自己独特的口舌之欲、肠胃体验出发,对人类的生食传统、“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说教和现代人的消化机能与五花八门的营养学,进行了一段反思。这便是一个去蔽的过程,也是散文作为一个充满理趣的文体所应有的功能。思辨而不狡辩,贵在真诚。我以为,在作家的独立人格越来越稀薄的年代,一个有担当的作家需要对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或说概念,勇敢地进行逆向反思与掘进,这很重要。
总而言之,黄少崇大多数散文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在日常的叙事中蕴含着深沉的诗意,这种诗意的生成,主要得益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真切体验、在散文中呈现了叙事的魅力、在行文过程中散发出智慧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则来源于他的平民立场与思辨品格。
三、黄少崇散文带来的启发
当然,黄少崇的散文创作远非完美,笔者仅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试着分析其不足,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参与探讨。
首先,在写作策略上,黄少崇近来显得有一点无所适从。这从新近出版的作品集《在母语中死去》的篇目编排上可以看得出来。像《瓜果遍地》这样的篇章也许是他的探索和试图突破的方向,但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是这篇作品被抽掉了文化的维度,缺少了厚重的或者有个人体会的故事,倒像是南方水果的一般性介绍。十年之间,带领他走上佳境的民俗文化散文写作道路戛然而止,甚为可惜。
其次,就单篇作品来说,作者有时在一些人性共通的地方,在一些有可能提升文章深度的思辨性表达之处收手太快。比如写农药毒杀芬解除全校师生的身体之病,后来那位老校长却以违禁使用农药被贬了,作者无意之间提了一句“我们心灵的结痂,也需要一种药来治疗”,可是点到为止,没有挖下去。这种反映人类从本能的自救到人性的自救、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没能继续深挖下去。还有作品的开头部分,写毒杀芬泛滥导致水体污染死鱼遍布河流,许多农民争先恐后去捡鱼来吃,那种时代的饥饿感和造成饥饿的历史原因,本来可以写出更加宏阔的内容来,但作者在此处把亮点略过,迅速转场到下一部分故事去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两点遗憾呢?我以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存在普遍性的问题,即文学自信的不足和学识储备的不足。前者容易造成艺术上的迷茫,后者容易造成思考上的乏力。由此可以引出本文的结尾部分,黄少崇散文创作给我们的启发:
第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最好站在民族的立场进行民族性的写作。我们现在的文化语境,信息共享了,但是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信仰依然独特,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而言,依然有参照价值,是很值得书写的。
第二,细心寻找生活的力点,在创作时才能打开叙事纵深的格局。我们看到不少作品喜欢就事论事,拓展不够,或者流于空洞,无法用有说服力的细节支撑宏大的想法。这好比一个攀岩运动员,他要选择很多个下钉的地方挂钩来作为上升的力点。力点的多少,又像一座房子的基线、梁柱有多少,决定着作品的时空坐标和艺术格局。对于力点的发现和捕捉,大量的阅读和阅历不可或缺。
第三,我们需要坚持关注生活中普通人物的命运。在黄少崇的散文里,那位爱唱师公戏的韦国文老师,那位表面严厉心地善良的老校长,那位唱壮诗的草帽外乡人,他们的命运之所以令人唏嘘,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第四,一位有事业心的作家,不能没有一套写作策略。好比一个有事业心的皮鞋匠、钟表匠,哪怕农夫,都有他自己的劳动规划和人生规划;更不用说山上挖马蜂窝的猎人了,他们干起活来,战略和战术的使用堪比军事家。
第五,我以为好的散文一定是使用了充满个性化的生活语言来写作的,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说人话,不是一上来就之乎者也云,书袋掉得比鸡皮疙瘩还多。毕竟,文学作品要有鲜活的体温和呼吸,才能留住眼睛越来越亮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