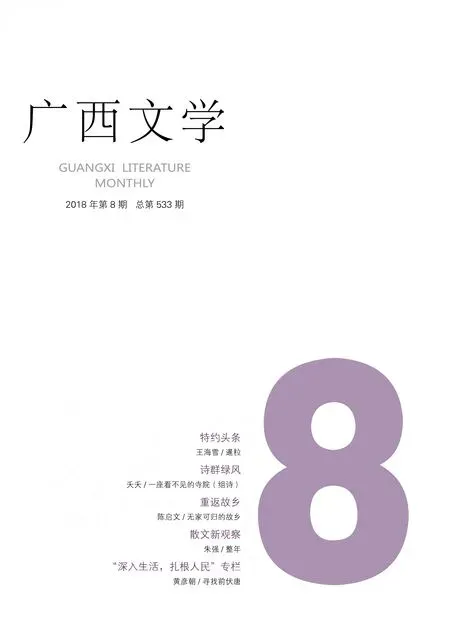整 年
朱 强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过年的另一层意思,也就是还乡、回家。从远回到近,从一个漂泊之地回到情感与记忆可以得到落实的位置。在传统中,家是什么呢?确凿地说,家也就是亲人、家谱、方言、祖宅以及无数能够唤醒记忆的东西。在此处,年才是年,年才有它自身的味。以前每年到了春节,我爸妈就带我往爷爷家去,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很快就融入一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后来我到了外地工作,每逢春节,又风尘仆仆地回到爸妈中间。中间的意义是巨大的。年就是往中间去,往核心去,往来的地方去。它让一个个被拆散的零件再一次地回归整体。我想这个整体的意义就是把传统拧出来,然后对它进行一次重重的强调。在异乡,在一个个被我们逐渐熟悉的环境中,通过努力,我们构建了自己大大小小的朋友圈。这些关系占据了我们一年中的大部分精力。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你的生命得以完整。只有在故乡中间,你才能感受到这种完整与确定性。今天和我家亲戚十几口人共进晚餐,其中的大部分人一年也难见一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交流,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中间”的确认。有人老了,有人胖了,有人高挑了,有人成熟了,也有人老练了。这些外在的变化并没有使我们对他们的身份的确认造成影响。因为我们一直身处其中,一直认同这样一个传统。
每次回家,我都会得一种很多人都容易患的漫游症,到曾经活动过的地方活动。走,皮肉与内脏处于一种松弛状态。然后,你就忘记了现实中的一切,时间仿佛回到昨日。譬如我童年朝夕相处的两棵古榕,它们是我还乡必访之物。这曾经一直是我家门前的大树,繁枝绿叶。而当年构成家的房屋早已经没了,那个叫左营背的地名也已经被时光淹没。开阔的篮球场取代了过去的一切。如此,我绕树的意义又在哪呢?我从树的一侧绕到另一侧,观察并想象我当年看待它们的感受。这个记忆中的整体被再一次唤醒。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只要有这两株树在,我所仰望的就将永远是故乡的天空、童年的天空,以及我心里存放的那个水洗般的天空了。
按理说来,我常年生活在离故乡不到四百公里的另一座城市,这种地理上的跨度几乎可以被忽略。假设高铁通了,来去顶多也就一个半钟头。但事实上,我很难在那里获得属于自己的新年。因为春节除了热闹,张灯结彩,构成它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亲情、血缘与家。新年,回到家,和往年一样,挨家挨户地去给亲戚们拜年。所谓的拜,也就是互相串串门、喝杯酒、发发红包。酒桌上,各种零碎的新闻纷至沓来。它们很自然地出现在我面前。身处其中,我感受这鸡零狗碎与纠缠不清。生活像刚刚榨出的果汁,浓香扑鼻。而别处的天地都是自带屏障的。你自认为认识了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但你永远不能处于其中,不能像在故乡一样,获知他们真实的处境。因为你是被拼接上去的,随时也可以被抠出来,扔在地上,然后就什么也不是了。但故乡你永远和周围世界互为整体。这“整体”是什么呢?想来依旧是青梅竹马、同学少年以及无数件在你的记忆中落地生根的事物。它们与你藕断丝连,暧昧不清。你可能户口已经迁往别处,在另一座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但你仍旧是这个整体中无法剥离的部分。
年前,我爸打来电话,和我讲老家修家祠的事。他很详细地和我介绍了地址选在哪,规模有多大,需要费多少砖,花多少钱,族里有多少人参加了募捐。我愣了一下,因为他所说的那一个家距我实在是太陌生与遥远了。我爸在十分年轻时就已经脱离了那,户口也由菜农转成了城市居民。田地很快就从他的名下给划掉了。他从那一刻起,就成了一个和故乡划清了界限的人,现在这种看不见的关系再一次从他的身上蔓延到我这,让我又一次地和遥远的那个家发生着联系。我爸给我打电话正是为商量募捐的事。按照族里的规定,其募捐的数额男丁每口按一千五百元计,女眷每口按一千元计。算盘这么一打,我家三口人,总共要出四千块。也许是因去年我爷爷仙逝以后,我在省城的朋友很多都送来了花圈,这也让族里人感到我多少是有能量的,这一次,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关系在修祠堂这件事上得到其他朱姓的帮助。而我爸的态度显然有一点尴尬,他一方面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家里很多人都没有了走动,关系也都已经疏远,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实在是没有更好的理由拒绝。但我很快就表明了态度,这钱一定要出,且一定要出得干净痛快。也无论我们将来往哪里去,无论在这个气氛中,我们的角色显得怎样的不融洽,至少我们身上流的都是朱家的血。祠堂落成了,募捐者的名字将出现在石碑上,这份金色的名单构成的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全部,每个名字都意味着一种承认以及在场。
大年初五,我终于看到了即将完工的家祠,它所在的位置是一块荒废已久的晒谷场。高踞于大多数建筑之上,它拥有青灰色的山墙、朱漆的柱子,还有明亮的琉璃瓦,和那些灰头土脸的民宅比较,它通体显示了一种拔俗的亮光。然而,我并没有走进去,在这个家族中,我觉得自己始终是说不上话的,家祠的整个建设过程我都未曾参与,说白了,我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在场者。这是我在面对自己庞大家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份怯弱。这情绪,我战胜不了。这个下午,按照我爸的意思,我先去祭扫了我的爷爷,又去擦拭奶奶的墓碑。黄昏提前降临了,我一遍遍温习着祖先的名字。这样满山地跑,也终于累了。我奶奶在我还没有出生时便已离世,她一生并未存有一张照片,其实她在我头脑中的印象一直是模糊的,这些年,我只有从父亲伯伯的长相中想象她曾经的样子。爷爷在世时,每年到了春节,与他拜年以后,我爸就带我拧着篮篓,去给奶奶还有其他的先人上香,这几乎已经成为每到新年的一件必做的功课。但自从我家的祖山多了爷爷这一位新的成员,我对这山的理解,就不再觉得有那么深奥。我摸过爷爷银色的发茬、左额头眉边的疤痕,还有他手上长期吸烟被熏成明黄色的烟斑。他们都那么清晰、具体地在我的头脑中呈现。时间把家族中每一位长者都带到了这一座山上,无数个故事被黄土掩埋了起来,它们构成一部厚厚的家族史,经年之后,周围长起了参天大树。当点完最后一炷香时,我远远地看了一眼家祠屋脊上尚未飞起的青龙,又一次想到传统中的那个关于整体性的问题。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先人们对那个心里的完整如此贪迷。记得我爷爷那时还并未十分衰老,他的眼中还闪烁着思想者的光,但早早地就为自己备下了棺木,又在周围四处勘察,左选右选,最终也没有脱离掉这一座山的包围。要知道,再强大的个体都会在这整体面前变得恭恭敬敬,再傲慢的身段都会弯下来。这个整体,就像是立在人心中的一根柱子。明白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乱世你所看到的不只是滚滚黄尘、铁骑刀枪、飞溅的血与滚落的泪珠。同时,也看到浩浩荡荡的移民将祖宗的灵牌举过额头。那地名——生老病死的故乡,原本是属于北方,它周身常年覆着一层冰,但随着蚁群一样的迁徙队伍,它们被搬运到南方,被搬到一个拥有花香的陌生之地。这一并搬来的,还有方言、风俗、建筑、美食以及节日。一切都被那么细致而完整地搬来了,以至于让这里的日月、天空都发生了变化。
而现在,我什么也搬不动了,只能搬起碗里的三个酒酿蛋,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囫囵吞下。这时,我明显有一种哽住的感觉。这是我们客家人的风俗。大年初一,对于男丁都是用这三枚元宝伺候,以祝愿在新的一年,万事吉利。我家所在的位置叫塘窝里,聚居了大量的客家居民。所谓的客家,就像古诗里讲的,客里似家家似寄,家一直揣在路上。五胡乱华以后,祖先们举家南下,但这个南,并没有确切的指向。他们也不知要去往哪里,好像哪里能为他们提供一亩三分地,哪里就是故乡了。今天,塘窝里在手机地图上并没有显示。去日,它因地势低洼,水塘遍布,梅雨季节常常被沦为水泽河乡。水塘周围的高地,分布着周姓、郭姓、陈姓等几十户居民。家谱上说他们多来自两百年前的闽西以及粤北。那时客家人返迁内地的风潮正劲。他们被命运裹挟到了这个偏僻的位置,终年以务农、打鱼为生。这种生态大概持续到2000年前后,后来就陆陆续续地被一些外来事物给打乱了。最初是为了安置周围的拆迁户,那时地价也很低廉,拆迁户们失去了家园,很快就在这拥有了新的宅基地,水塘被填平了,他们在上面建筑房屋。之前的那个水洼很快就成了一片居民区,大大小小的窗户中透出锅碗瓢盆的声音。楼房鳞次栉比,房屋与房屋之间形成狭长的通道,这些通道与外面的大路相连。繁华与热闹相应地就将它包裹了。这些年,城市气氛被一点点带入。大桥、邮局、银行、商场、酒吧、KTV、公园以及学校也都变得近在咫尺。而这些户主常年利用多余的房屋收租,逐渐也成了社会上清闲阔绰的阶层。
新年,因为这个“整体”的作用,我又一次地回到了这。现在,在它外面是一条新修的大路,叫稼轩路。许是因辛弃疾的缘故,但据史书上载,辛弃疾并没有到过此地,他只在城北的郁孤台上举目四望了一阵。如果真要牵扯出什么历史人物,王阳明倒是距这最近的一个了。塘窝里向东五百米是滨江二小,再过去是公务员小区,这儿曾经是王阳明点兵用过的大校场。校场两旁,分别是左营以及右营,作为屯兵之用。而我童年时的家所在的区域就叫左营背——左营的后背。可以想象那儿曾长期作为官家的田土。春天,紫红的桑葚熟了,秋天的稻穗金灿灿的,田垄上到处是使人眼花缭乱的花香与草香,白云停泊在树梢头。它们和将军们脸上的刀疤、手上的胼胝结合,构成了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整体。
然而,往事已矣,这一切都没有人记得了。塘窝里,左营背,它们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有近二十年时光停滞在这样的两个点上。它们承载着我青春的重量,是我每次回到故乡都要反复打量与寻味的名字。曾经的我,试图以仰望天空的方式恢复记忆里那些已然消亡的坐标,试图用虚无主义的做法建构我心里的那个全部。我在这自欺之举中,也因此获得过短暂的快乐,可一旦回到现实,又愈发地悲伤了。没想到它们的消失会那么干脆、彻底。其实,我特别理解我爷爷还有爸爸心中的那个整体以及那整体对他们的作用。尽管故乡——曾在我爸的心口上留下过一道血淋淋的疤痕。失去了田土的他,在身份上曾一度感到尴尬。但从这二十多年来,春节、清明他都带我回老家扫墓这一件事上,我就知道他心里其实是有故乡的。不然,他就不会打电话跟我商量家祠的事了。每当想到他们心里的那份复杂的情感我眼睛就开始湿润了。正如家门前的榕树盘绕的树根对每片叶子的引力。枝叶与根之间,既传递着各种悲欣,也传递着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新年伊始,我在塘窝里某某门牌号享受着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常。我家的楼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露台,在上面可以看到迁徙的星斗与过往的白云。吃过了年夜饭,我就躺在那把陈旧的摇椅上观看逐渐变暗的天空。暖风黏稠,低矮的夜空有蝙蝠在飞,夜空是青蓝色的,飞机的屁股上拖着长长的白烟,石台上蜡烛的火苗带着一种温暖的喜悦。佛手是金华产的,它的香味和蜜橘、甜柚的香味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清的喜庆。我在摇椅上一边刷朋友圈,一边感受这种立体的年味。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回到了故乡,在圆桌的周围是许多碗筷。他们在这个时刻享受一种叫团圆的幸福。今年年夜,我外婆选在了二舅舅家过,她也是家庭中唯一的老人了,我外公在十多年前就已离开了我们,他曾经当过中学校长,是一位出色的体育老师。在当地,外公家也算得上是一支旺族,儿女众多,且各有所长。弟兄们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之间,也偶有过结与争吵,但很快也都化解了。短暂的乌云之后依然是一片高远的青空。这种情感上自我痊愈与修复的能力在别处一般是少有的。亲情总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点上站出来,消灭之前所谓的不共戴天。
有时候,这种争吵,当然也是很有意思的,不吵怎么能叫生活呢?尤其是家族中上百年间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一旦发酵成争吵的事实,就更让人感到当初的那个家的存在了。根据我外婆描述,年前她那里聚集了几十口人,闹哄哄的,当时房子外的水泥地上都站满了。这些来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派。有一派来自这个大家族里的大房,还有一派来自二房,所谓的大房二房,其实也都是弟兄一家。一百年来,他们各自繁衍了无数的子孙。其实这闹剧说到底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话要从2000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左营背拆迁了,家族里的祠堂毫无疑问地也就拆了。这祠堂原是属于大房的,但后来二房的人拿去用了,久而久之,产权就有了变化。祠堂被拆以后,因为产权上的纠纷,大房和二房的人各自团结成两派,都不认为这祠堂是对方的。因为这争执一直得不到解决,政府的补贴款就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款终于拨了下来,却全部落到了大房人的口袋。那么多年了,这事情差点都要被淡忘了,大家都有了新房子,谁还缺那一点钱呢?但事情终究还是走漏了风声。二房的人硬觉得理亏,闹腾了好久。我外婆是家族里最年长者,要说老辈人的事她应该是最有资格评判的一个,于是,大伙就到了她那里唇齿相见。这样一来,那个长期被瓦解了的家突然又合起来,成了一个金灿灿的整体。而新年的意义,我想就是把这个长期被瓦解、被边缘了的“整体”唤出来,然后对它进行一次细细地打量,看见它细密而结实的纹理。
聚会时,我大舅母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她说人到了年纪,年总是聚一次少一次。尽管这话说得有点悲伤,但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在别处,也许根本感觉不到“老”这个字眼。老来自连续的变化,只有在印象中构成了某种可比性,老才成立。在过往云烟中,很多面孔都存在于瞬间,因没有所谓的比较,所以也就看不见所谓的老。唯有在亲人中,这些条件都一一地具备了。此地,时间以整体的形式存在着。你既看见吹弹可破的肌肤、含情脉脉的眼眸,也看到丘壑纵横的脸与雪一般的白发。要知道任何人都无法抗拒老这个事实,时光总是催人老的,尤其是回到家的中间,老也就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刻了。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在计划生育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一辈,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生态。从我妈妈家说起,我拥有三个舅舅三个姨娘,爸爸家又有好几个叔叔与姑姑,他们使每个个体与这个家族的关系都变得异常复杂,任何人都很可能是以好几个身份出现的。可是到了我这一辈呢,国家在人口政策上突然收紧,全家宠爱在一身。这种过分集中的欢愉在将来的一天终于变本加厉地转化成某种残酷。这境况在我近几年回家就越来越可以体会得到了。家庭中大面积的衰老就像秋天如期来临,千树万树一夜就枯黄了。我舅舅前年因为轻微的中风步履蹒跚,我姨娘也因高血压每天需要坚持服药。衰老以成片的方式进行,空气中弥漫的都是暮色,它使人倍感到压抑。
当然,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居民区周围建造了休闲广场。小区北面还有一个大型公园也将动工。这些过早失去了土地的居民,在生活上虽然早已被城市所同化,比如用燃气灶,坐马桶,刷信用卡,等红绿灯,没有哪一件在他们不是驾轻就熟。虽然他们也享受了城市变化所带来的红利,顺顺当当地成为城市中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但,人毕竟是老了,老就成了一个大麻烦事。人一旦老了,相应的就变得无聊。究竟该怎样来打发这看不到边的落寞呢?尤其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而言,他们早年并没有受到多少教育,假如真是艺术家、医生、老师或者诗人,还可能在老之将至时为生活带来一些新的精彩,但他们什么也不是啊。我大舅舅退休以后,开始在楼顶养起了鸽子,但没有几年,就受到家庭中大部分人的反对,这不仅仅是因为脏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他中风很大程度是他养鸽子这事所致。既如此,他又开始在屋顶上种菜。时间每天并没有减少,依然在一分一秒地进行着。女人们到了傍晚,就在附近的休闲广场上跳舞。生活是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啦,缓慢,幽静,心平气和,没有了一丁点儿的脾气。
相应的,家里的晚辈开始从桌底下蹿出来,一会儿就高人一头了。他们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长辈们心里眼里都是他们。至于酒桌上所谈的,也多是他们升学、成婚、购房、升迁以及出国的事情。家长们曾经的那些颐指气使与不可一世都熄灭了。往日庞大、生气勃勃的家族变得暮气沉沉。当一切以整体的方式沦陷,便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诞生。总体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时间,也是观念以及心态。父辈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我们多有不同。在朋友圈,很多年轻人过年都没有回家了,他们利用难得的假期开始了异域之旅:西欧或者南非。新年在别处。年轻人感受着不同季节里的年味。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演变,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也许,这就是未来世界的样子了。那时,也许我们都不需要故乡了,但不需要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中就没有了乡愁,或许,到那时,故乡可以被带到世界上任何的位置,彼处也即此处,而我们将在一个新文化的整体中看待这个古老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