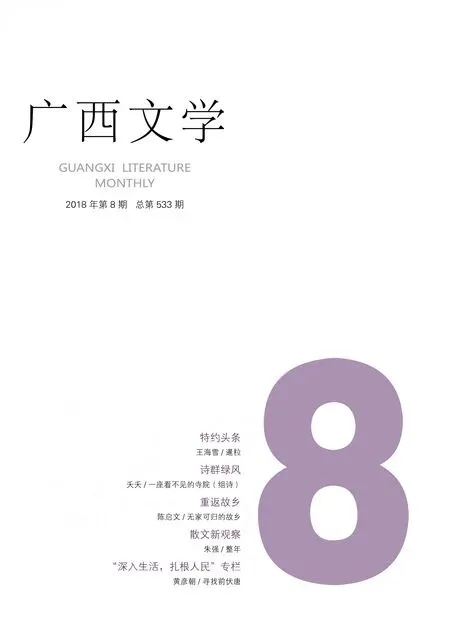海,是地球的第一个名字
胡森林
自由的人,你将永把大海爱恋!
海是你的镜子,你在波涛无尽,
奔涌无限之中静观你的灵魂。
——波德莱尔《人与海》
一
对于只知四时变异、草木盛衰的内陆居民而言,很难理解海对人的意义。
在我出生的南方丘陵,人们忙于农事,向土地讨要生活,被连绵的山峦和茂密的丛林挡住了视线,海在这儿是一个异常遥远和陌生的词汇。我对海洋的想象,最早来自“挑南盐”的故事。在老人们的讲述中,交通不便的年代,有一群人跋山涉水,用几个月时间挑一担海边的盐回来,为每家每户餐桌上增添味道。父亲去了一趟北海,带回关于海洋的只言片语,是我对于海洋少得可怜的感知。
世代根植于土地的人,对海洋并没有太多的渴求。在我们的文化里,脚下的土地比不可测的海洋更值得信赖。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个词“水土”,最通俗地概括了中国人传统的自然意识。对乡土的依恋,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乡愁。
在一部分中国古人看来,“天涯海角”即到了陆地的终点,也是人的足迹最远之处,汪洋大海则是难以企及之地。孔子发狠话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他终究还是没去。浪漫到手可摘星辰的李白,说起大海也觉得“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令他裹足不前。白居易“忽闻海上有仙山”(《长恨歌》),也只听说而已,并未曾亲见。
明代中叶以后,政府实行海禁,数百年间“片木不准下海”。大洋隔断了不同的洲,人们无法互通信息,由此产生许多想象和误解。清代李汝珍写小说《镜花缘》,其中的海上游历故事在当时看来,和今天的玄幻小说差不多,而此时西方的坚船利炮都快要攻到国门了。
到清末魏源撰《海国图志》,一些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更多人对远方的世界缺乏兴趣。1876年郭嵩焘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公使,因为在日记中对西方的描述不合时人的胃口,遭到无情的口诛笔伐,被讽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很多人来说,远涉重洋,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不是那么容易。
二
与此同时,海洋意识也在中国文化中悄然生发,不断拓展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古人把能够成为经典著述的才唤作“经”,为数并不多,其中就有一部《山海经》,显示了上古世界的中国人面对大海神游八荒的想象力,与之相比,现代人琢磨出的科幻形象简直是弱智的产物。“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渊明《读山海经》),可以说,从《山海经》开始,海洋就成为中国人与厄运抗争的象征。
先秦的庄周在文学史上以汪洋奇诡的想象力著称,后世无数诗人从他那儿获得过启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逍遥游》),出手就气吞万里,然而构成他想象基础的是北冥,即北边的大海。庄子没说“北冥”多大,但那里一条鱼就“不知其几千里”,水面之阔还得了吗?
正是面对大海,戎马倥偬的曹操写下了壮阔无比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胸中的豪情倾泻笔端,化为气象万千的诗句,以至于一千多年以后,一代伟人毛泽东还发出了“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赞叹。
在汹涌的大海面前,有安土重迁传统的中国人,并没有望而却步。濒海而居的渔民靠海吃海,将足迹印刻在了浩渺烟波,一直到“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一些更有冒险精神的人,将中国的物产经过海上运输到大洋彼岸,开拓了光耀千古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条海上商路,萌芽于商周,形成于秦汉,勃兴于隋唐,鼎盛于宋元。最早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正式记载。经过数百年孕育发展,一度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并形成了三条航线,最远之处西至欧洲及非洲东部,东到美洲。可以说,除了航行速度和运载物品有所不同外,我们的古人所到之处与今天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在民间故事中,徐福、李俊等人都曾流寓海外,生息繁衍,这毋宁说是中国人亲近海洋、融入海洋的心理投射。流传至今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更是书写了世界航海史上精彩的一页。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论证,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船队,但郑和留下的是和平、友谊、互利贸易和相互尊重,而不同于后来的西方航海模式,留下的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摧毁。
这是中国人探海涉海的现实与精神旅程,海洋精神从来没有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缺失。
三
在地球的另一面,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就试图认识大海、驾驭大海。公元前五百多年,阿尔凯奥斯在《海上风暴》中写道:
前浪过去了,后浪又涌来,/我们必须拼命地挣扎。/快把船墙堵严,/驶进一个安全港。/我们千万不要张皇失措,/前面还有一场大的斗争在等着。/前面吃过的苦头不要忘,/这回咱们一定要把好汉当。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凭着智慧和意志挣脱羁绊,冲破险阻,回到故乡,展现了人类在大海面前的某种自信。对大海的这种认知,一直伴随着人类走进现代文明。
然而,海洋并不友好。海的险恶、暴躁、神秘、变幻无常,对人类有着巨大的挑战。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海是令人敬畏的,蕴含着极大的破坏力,神话中的海神就是个暴躁易怒、心胸狭小、爱报复的家伙。这种形象反映了古代海洋民族生之艰难,以及对海的怨怼。在《荷马史诗》中,那些迷惑人心的、变人为猪的、吃人的妖魔,实际上就是诡谲多变、凶险四伏的大海的形象化,它们使奥德修斯失去了所有的战士,饱受磨难。
英勇的古希腊人并没有因此退却,在这辽阔海域围绕的地方所诞生的神话里,海被作为了苦难人生的代名词:英雄赫拉克勒斯乘一叶扁舟渡过茫茫大海,去解放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工匠代达罗斯带着儿子扬起羽翼,飞跃波涛汹涌的海洋前往幸福的彼岸。那些依靠海洋生活的水手,不得不为了生存终日乘着孤帆,漂泊在这充满了未卜的危险与艰辛的无边苦海中,无依无靠,时刻都感觉到人生的无助和对未来的迷茫,所以他们是一群痛苦的人、悲剧的人,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厌世或逃避命运,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勇敢的人、坚强的人。
海洋交织着绝望和希望,这一形象在籍里科所画的“梅杜萨之筏”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绝望与恐怖,在黑沉沉的大海上,木筏载着妇女儿童无目的地漂流,有人绝望地哭号挣扎,有人已经长眠不醒。木筏的小帆灌满了风,后方有一个大浪即将拍来,仿佛再下一秒,所有的人都将会被浪花卷走。在这么危急的状态下,在画面的右侧,仍有一群人拼命要垫高身体,挥舞着手中的衣物,努力向远方求援,那一丝远处陆地传来的微弱曙光,带给他们无穷的希望。
人类与海共舞,不管是主动的征伐,或是被动的流徙,总不断有人葬身大海。美国女诗人文森特·米莱为此写下《海葬》:“让骇人的巨鱼啮我的骸骨/你们生人想起了得发抖/让它们吞我,趁我在新鲜时/别等我死过了一年半载后。”这可以看作所有海葬者的墓志铭,但愿海豚能托起他们的灵魂。
四
在人与海洋的不断搏击较量中,海洋成了展开想象的翅膀、显示人类意志力量的理想场所。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海,仍是诗人以优美诗句营造的想象王国,诗人借此演绎了一个善恶有报的寓言故事,人在大自然中是如此渺小无助,唯有神佑才可使他逢凶化吉。
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开始远涉重洋,海盗和冒险家横行,海的形象一如既往,但人类接受挑战、顽强生存的自信与日俱增。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有冒险家的胆略,更有实干家的生存技能,凭着坚韧的意志和丰富的知识,他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顽强地生活了二十八年,并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风起云涌的19世纪,海洋作为一种审美形象进入文学和艺术,海洋精神得到空前绝后的张扬。英国诗人拜伦被称为自由思想的化身,他在《海盗》中塑造了一位孤傲、勇敢、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康拉德,拜伦的诗中写道:“在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地泼溅,/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不受限……/我们过着粗犷的生涯,在风暴动荡里/从劳作到休息,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大海如此威严、有力、粗犷,那是“波浪滔天的地方”,有着“剧烈的风暴”。这些,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拜伦式英雄”的精神投射。
诗人们赋予大海一种浪漫主义的人格。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致大海》中,进一步塑造了大海的自由品格。这种审美态度在海洋童话中持续下来,远在北欧的丹麦作家安徒生以其童话《海的女儿》,丰富了大海神秘、奇妙、瑰丽、哀婉的美。
海的神奇与险恶、海上生活的惊险,也使海洋成为通俗文学作品的理想背景。在历险、寻宝、漂泊等故事中,主人公们充满勃发的勇气和澎湃的力量,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
人类为了驾驭浩瀚无垠的大海,发明了渡船、海图、罗盘、航海定位、测算技术等,这些航海的能力保证人能浮于海上前进。在达尔文主义的驱使下,人们有了新的目标,渴望把大海的阻隔连通。野心家和勇敢者们,以意志和毅力作为罗盘,征服恶礁和风浪,一次次眺望,一次次穿越,在波谲云诡的大海航行,穿越重重迷雾,抵达大洋的彼岸,找到理想中的领地和财富。
原本只懂得在陆地上生活的人类,经过在海上成百上千年的挣扎和拼搏,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终于累积了足够的知识,从被动承受到主动索取,从被迫臣服走向大胆征服,人类似乎从来没有如此意气风发。
五
20世纪初,巴黎有一位从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绅士,在欣赏德彪西的交响音画《大海》时,仿佛真的看到了惊涛拍岸、浪花飞溅的景象,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当他到海滨旅游时,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反而觉得有些不够劲了。待他旅游归来,得以再次欣赏德彪西的《大海》时,才找回当初的感觉。此时他不禁惊叹道:“哦!这才是大海啊!”
德彪西把大海融入自己的头脑当中,并用音乐演绎出来,大海的节奏、色彩、质感已与他融为一体。新的科学地理知识,已使人们知道地球主要由大洋组成,但当美国宇航员从太空拍摄到地球的影像,犹如一个悬挂在广袤苍穹中孤独的蓝色水球,人们还是因此而震撼。
海,是地球的第一个名字。人,与生俱来就在大海之中,这使人萌发了将自己视为海洋生物的新意识。
1895年4月,史洛坎驾着自己建造的船“浪花号”启程,环航世界一周。一个人,五十一岁,除了风帆,没有其他动力。三年后,他返航回到美国罗德岛,一共航行了四万六千公里,绕行地球一周。
环球独行要经历许多危险,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时,强风一度将他的船吹回马六甲海峡,短短几百海里的航程,史洛坎花了几个星期才走完。那片海域如此凶险,让他无论如何不愿钓食鱼类或捕杀鸟类,他感到与这些生物有着共同对抗自然风浪、艰苦求生的相同情感。
史洛坎撰写的《环球独航》一书,语调平缓,从容不迫,一点都没有创造历史的冒险家的那种傲慢与夸张。在海上,他和“浪花号”几乎成为一体,任何细微的变化,他都能立刻凭直觉做出反应,他甚至可以手握着船舵睡觉,边睡边维持方向。
海上自有其热闹,自有其趣味,史洛坎真正懂得如何亲近海洋,活在海洋的怀抱里。他可以用船帆和风进行对话,可以和大型候鸟并肩齐航,所以在无聊单调的海上,他不寂寞、不孤单,他仿佛生来就在大海之中。
史洛坎的心情迥异于几百年前的哥伦布和麦哲伦,海洋不再是必须被跨越的障碍,也不是必须被征服的挑战,海洋是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是包容、接纳人类的新环境,只要人类愿意去适应海洋。
六
我早已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海时心情的激动。这些年,我看过很多的海,不同颜色,不同形态,在渤海、黄海、南海、东海,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有浑浊的,也有清亮的,有平静的,也有汹涌的。我在海边的沙滩和浅水流连,或者乘坐渔船、轮渡或者直升机抵达它们的深处,也从万米高空俯瞰过大海,在黑夜与白天交界时感受过它异样的美。这种种体验,足以补偿我儿时关于海的缺失。
在所有关于海洋的故事中,我偏爱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渔夫桑迪亚哥出海很久,成功了又失败了,他说,“人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他可以被消灭,但永远无法被打败”。我很早就喜欢引用这个故事,但越大我才越明白,海明威并不只是在讲一个捕鱼的故事,他说的是人生该有的一种态度。
桑迪亚哥要征服的并不只是海洋,更是要战胜自己的怯懦和灰心,一旦他做到这一点,便没有什么可以将他打败。对他而言,海洋已不是异己的力量,而是他精神展开的场所,与海洋的搏斗其实也是与自我的对话,从中他认识了自我,塑造了自我,成就了自我。
桑迪亚哥是所有人乃至人类整体的象征。在困难和厄运面前挺立不屈,是在彰显一种精神的力量,这正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高贵。人的肉身终会磨灭,但精神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
就像我热爱的苏东坡,他被流放到了海南这个当时最偏远的地方,大海之中的孤绝之地,但他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而是变得更加坚韧和伟岸,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在传诵他那些动人的故事。
而我听过更多的,是现实当中人与海相处的故事,捕捞的渔民,探宝的队伍,钻采油气的工人,守护海疆的军旅,还有独自航行的孤胆英雄……相比于他们,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游客。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海洋,他们领略过更多海洋的美。
临海而居、涉海而行的人,理应有海一样的气魄和胸怀,理应对海有不一样的认识。海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世界的图像,是人生的譬喻,更是人类命运的折射。
若干年前,我在印度洋果阿的海边停留,蔚蓝的阿拉伯海碧波荡漾,椰林摇曳,海鸟低回。黄昏时分,我向大海深处游去,感受到从没有过的畅快。海浪冲刷涤荡着身体,人不停地随着海浪起伏,一个个巨浪迎头袭来,巨大的力量把你往岸上推。远处是一望无垠的海面,平静之下是暗波涌动。那平静抑或汹涌的海面,不正是人生的预示吗?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际遇,或困厄或顺遂不可预料,就像一片辽阔的海洋,有五彩缤纷的美景,也有凶猛的鲨鱼,有坚硬而冰冷的礁石,偶尔平静,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暴风雨。但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正蕴藏在此。往后,固然有一片沙滩,可以安享一片平静,但选择了平静便失去了浸润在海水中,与海水搏击、随海水起伏的乐趣,只能做一名用欣羡目光看着别人的看客。
海的意义是多重的。对于个人,它是内心的向往、精神的体验,是人与海激情的交互。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能容许海洋意识的缺席。作为一个内陆型国家,中华民族历史上饱受了海洋权益弱小的灾难,近代中国更是饱受了有海无防的巨大苦难。今天的中国,仍有大片海洋国土遭到他人的垂涎。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离不开海洋。中国近代的耻辱始自海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必定离不开海洋。
而对于这个世界而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着历史的光影,带着对未来世界繁荣与和平的企望憧憬,将连接起被大洋阻隔的诸国,共奏一曲激荡悦耳的海洋乐章。
大海,以它澎湃的激情,无休止地在诱惑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