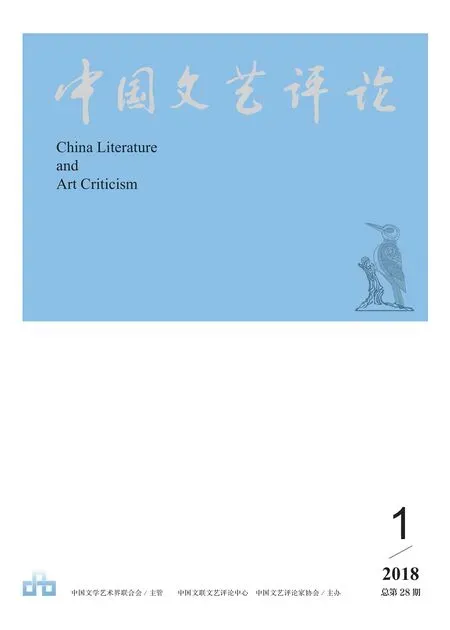小说与非虚构的混融及其文体创新意义
李朝全
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这话落在他心坎上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在袁隆平的脑子里一下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了,他感觉自己茫然的眼神终于对准焦距了。
——这是摘自陈启文的报告文学新作《袁隆平的世界》里的一段心理描写。心理描写通常被视为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法。类似的想象虚构式的小说笔法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可谓俯拾皆是。特别是2010年非虚构创作兴起并形成潮流之后,小说对包括报告文学、散文在内的非虚构创作的逆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虚构文本。小说对非虚构的逆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虚构手法在非虚构文本中的运用。在李修文的散文集新作《山河袈裟》中,出现了类似当年王旭峰的报告文学《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的亡灵叙事——由亡灵担当叙事者,这无疑是小说的虚构笔法。
事实上,小说与纪实、虚构与非虚构的交织混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纪传、史志与小说相互混融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久最悠长的是歌咏和纪传两大流脉。从劳动号子衍生出来的歌咏与诗词歌赋绵延上万年。从结绳记事、绳陶甲骨、青铜铭文直至后来的史册典章,基本上传承的便是纪传、纪实的文脉。而纪传叙事作品自诞生伊始,便混杂了许多虚构想象的内容。人类早期的叙事作品多为神话。后来出现的历史典籍纪事亦不排斥想象。在被普遍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雏形的《史记》中,就有不少凭借想象揣测臆度而写成的内容。譬如,在《鸿门宴》中:“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段关于樊哙言行神情的描写无疑是想象的,甚至是虚构杜撰的,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史著中,这种笔法常被称为文学手法,其实质便是小说笔法。
神话传说更是人类的想象、虚构与真实和历史混搅在一起的叙事。关于女蜗造人、有巢氏筑巢、燧人氏钻燧取火、神农尝百草、尧舜禹禅让等等,都是虚实交融亦真亦幻似真似假,难辨真伪。据此可以推断出,中国文学或史著的早期创作中,纪实中大多有虚构的萌芽、小说的成分。这大致是不虚之论。
反之,小说也受到纪实的深刻影响。四大古典小说,均由真实历史和纪实演绎而来。《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小说版,《西游记》是玄奘天竺取经的神话版,《水浒传》是宋江起义的英雄传奇,《红楼梦》则有着作者自传的影子。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些小说类作品亦常被冠以“××传”“××记”(《红楼梦》亦名《石头记》)这样的纪实性名称,纪传和纪实对小说文体的介入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报告文学包容可然性或然性描写
到了现代文学时期,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最初出现的乃至走向成熟期的作品,对于该文体的限制性特征还都是比较模糊或含糊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可然性、或然性的想象甚至是虚构内容。譬如,夏衍的《包身工》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上文中对人物心理和神态的描写,都是属于想象性或虚构性内容。这些描写都是由可能发生或或许会发生、有可能如此或或许会如此的内容,亦即可然性、或然性的内容。它们未必是真实历史或事件本身的物理性还原与再现,而是一种文学化的、艺术性的重写、重塑和表现。这样的描写在报告文学之类的非虚构作品中,是合乎情理和事理的存在,不违反艺术真实与事件真实的统一,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
即便是到了当代,被称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奠基之作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同样有一些准虚构或类虚构的想象性描写。譬如:
他(指陈景润)默然收下了。他噙着泪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如此细腻的描述,似乎只有小说中才会出现。但是在报告文学中读到这样的段落,读者亦不会感觉诧异,反而觉得真实可信。这是因为,作者描写了可然性与或然性的内容,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心理和情感共鸣,宁愿或情愿相信这些描写都是真实无欺的。毫无疑问,这些内容均属于艺术真实、想象真实与事件真实、历史真实和判断真实相统一的内容。
《寻找巴金的黛莉》其主体内容是一个悬念迭生的故事。这种故事性便决定了这部报告文学必然具有鲜明的小说性。而作者赵瑜采用的也是小说层层剥笋、逐步揭开谜底的笔法。2006年冬天,作者从古董商手中获得巴金写于1936年寄给山西黛莉的七封信。收信人“黛莉”是谁?她与青年巴金有无恋情?她后来的命运如何?如今究竟是还活着或已去世?作者为了揭开60年前的这一个个秘密,驱车万里,苦苦追访,寻求答案。这个寻找过程处处布满玄机,富于悬念。通过寻找,作者揭开了一段又一段尘封的记忆,打开了少女黛莉曲折坎坷的人生画卷,一部不是小说却酷似小说故事的报告文学浑然天成地写就。
由此可见,小说的故事脉络与结构,小说的叙事手法和技巧等,都可以对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渗透,造就一些类似小说或像小说的非虚构作品。
虚构与非虚构犬牙交错
2010年以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创作潮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之作。今天回头剖析这些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奇特却真实的现象:许多引起轰动和广泛好评的作品都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手法。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所写到的地点梁庄都是虚的,似乎可与作者的家乡相对应,写到的人物及其故事亦可从其家乡的人事寻找对应,但作者却并不严格遵循真人真事的写法,而是杂糅了多个人物的故事、命运遭际等于一个人物身上,是将多人多个故事多种命运曲折映射到一人之上。换言之,作者采用了完全如鲁迅塑造小说人物的手法:“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样艺术化地刻画和描写的人物及其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一对应关系,也无法得到印证或验证。其实,用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非虚构作品,并非标准的非虚构,实质上是一种虚构或准虚构作品。在随后的作品《神圣家族》中,梁鸿将自己的这种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技巧更向前走了一步,并且坦率地将其归入小说范畴。其日前出版的小说新著《梁光正的光》故事同样发生在并非实有的“梁庄”,并以作者已故父亲富有典型意义的一生为原型;表现出对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现实的关切和介入精神。这是以非虚构的纪实“逆袭”小说,使文本呈现出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效果。事实上,《中国在梁庄》在《人民文学》杂志以《梁庄》为名发表之前,作者对自己的这部实验性文本的文体和门类归属并不明晰、不确定,是编辑主张将其命名为非虚构而已。而即便是编者自身,对于非虚构究为何物,亦无清晰判断或定位,只权且当作一种文学的“乾坤袋”来使用。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取了与《梁庄》相同的创作手法,将农村农民的自杀现象进行了典型化、集中化,将几个人的命运和故事打碎重新组合安排到一个人物身上。作者采用了田野调查式的创作线索,具有很强的带入感。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容易相信作者笔下的描述全部为真。因此这是一种高境界的仿真、拟真或逼真,有着很强的可信度即艺术真实。但是,孙惠芬并不回避自己作品中带有虚构的内容或色彩,事实上,她自己愿意将这部作品定位为长篇小说。尤为有趣的是,在近期推出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中,孙惠芬又采取了类纪实或准写实的手法,通过寻找儿子的好友张展,层层推演演绎,塑造了一个当代青年的独特形象。
不仅在被定义为非虚构创作的纪实领域情形是如此,在散文领域,同样一直存在着准不准许虚构的纷争。不少作者和研究者趋向于接受允许和接纳虚构内容或虚构成分的散文作品。因此,在近年来的许多散文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虚构的却逼真的内容。也有更多的散文所写的内容令人感觉真假难辨。这种含糊、模糊或混融状态,或许也是散文创作的一个发展方向。正如周晓枫近期在自己的一篇创作谈中提出的,她的散文创作一直都在“试错”,都在“冒犯”各种已有的“散文律法”和“警戒线”。通过这种大胆的试错和“犯忌”、尝试与实验,她为自己的散文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生面。
小说于非虚构相互逆袭的意义与影响
小说对非虚构的逆袭,与非虚构对小说的逆袭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在当下的许多作品中,时常分不清其究竟为小说或非虚构,甚至分不清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内容所占比例大。因此,这就给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念提出了新的课题或挑战。有人认为,非虚构是一种高度融合的写作样态,它已经漫溢出了传统所称的报告文学或纪实的范畴。也有人提出,文体序列并非一成不变亦非古已有之,文学发展到今天,很有可能催生和出现新的文学体裁及样式。
毋庸置疑,当下许多非虚构作品,很难被简单地归入报告文学乃至广义的大报告文学范畴,也无法简单地将其纳入小说领域。所谓的非虚构作品或许是一种杂交的、杂糅的文学样式或类别、创作手法或技巧。非虚构似乎已经漫溢和淹没、摧毁并重建了纪实创作。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打开了文学观念的新视阈。换言之,它有可能正在引发文学创作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引导作家重新思考以往的文学定势、成见或各种固有的、看似为金科铁律的“律法”、定理和限制,从而找到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新的生长点。
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的相互渗透与交合,可能带来创作手法上的一次刷新。就像当年拉美文学大爆炸带给中国作家的震撼一样,这种新的交融有可能启示中国作家,文学写作其实并无任何包括文体在内的桎梏或藩篱,写作是一种放飞想象和思想,可以自由驰骋聪明才智的事业,所谓“思接千载心游八方”,所谓“文无定法文以载道”,到了今天,或许正在拓展并生成着新的事物、内容及形态。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当今的文学生态,无论是文学思想观念,内容主题,形式样态、手法技巧、载体途径……多元多样新的可能性正在逐渐打开。文学创作,将以何种形态与身姿华丽亮相或转身,更是令人充满期许。脑瘫农民余秀华的诗作,打工者范雨素的自叙纪实,网络文学中的穿越架空、玄幻仙侠等各种类型小说……一切新的现象都在提示我们: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文学正在遭遇千古难逢的微时代、万人万物互联时代、数字信息时代、智慧生存智能人类时代,它不会永远是小说、诗歌、散文框化的老面孔,它可以是虚构非虚构混融的四不像样式,可以是文学历史学社会科学杂交的作品,可以是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混融的形态。文学将走向何方?文学的将来还会好吗?这些都将取决于时代的变革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时代和需求的发展,必定会催生出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异样的文学。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永不枯竭,文学也就完全具备这样丰富多样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