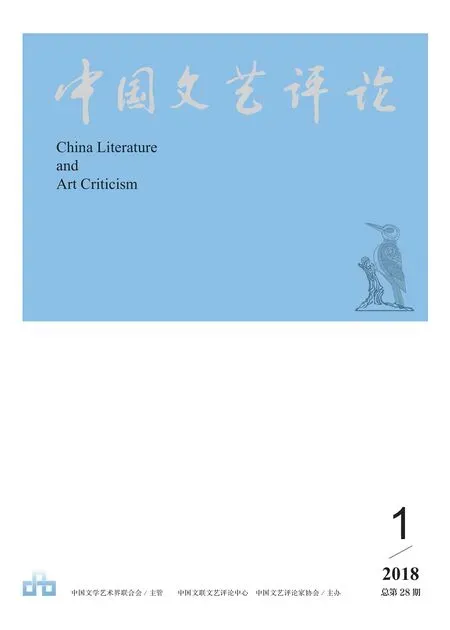凸显中国当代艺术结构价值
尚 辉
有关艺术“当代性”的认知与实践,似乎构成了2017中国美术界的主题曲。与西方当代艺术将架上艺术边缘化截然相反,2017年的中国美术不仅在油画、壁画、雕塑等领域策划组织了一些专题性和回顾性的大型学术展览,而且也因广东百年展、全国画院院展及潘天寿、刘海粟、张仃等纪念展的举办而引发中国画学对百年中西之路的回望与反思。还不止于此,已淡出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观照范畴的历史与现实主题性创作,在2017年因某些特定历史节点而获得重力加速,宏大叙事与史诗书写似乎依然是造型艺术“当代性”的价值目标;而北京双年展、凤凰艺术年展提出的由各国族艺术互交互鉴的世界全球化艺术观、“超当代”艺术观等,则倡导了一种新的全球当代艺术价值理念。显然,面对2017年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对于艺术政治学、艺术媒介学的持续升温,中国美术界更加鲜明地凸显了东方艺术传统与文化思维的当代艺术价值判断。
书写新时代的视觉史诗
史诗无疑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与艰难蜕变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和民族英雄的书写与歌颂,也是以诗的情怀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与艺术再构。通过艺术创作所记录所传诵的这些事件与人物,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穿越历史限度的永恒性,并成为激发民族斗志、铸造民族灵魂的一种文化象征。史诗无疑也是一个伟大时代民族精神的浓缩,一个伟大民族在一段历史巨变的急流中启航与远行的艺术见证。描绘历史与现实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因迎接庆祝建军90周年全国美展、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全国中国画展和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最美中国人”为主题的大型美术作品展以及十位中青年美术家“深扎”主题实践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年初就开始筹划的香港回归展,除了广泛发动、精心组织有关香港回归主题的中国画创作,更调动中青年美术精英创作了有关香港从被殖民到回归祖国这浓缩了一百七十余年历史的九幅历史画巨制。从《英国侵占香港》到《香港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再从《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政府成立》到《不忘初心,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更美好》,这些用中国画呈现的一幅幅历史瞬间,既再现了历史事件与人物对于香港近现代历史的深刻影响,也探索了中国人物画在还原宏大历史场景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众多人物形象塑造与恢弘气象营造成为这些画作书写历史的艺术基调。在历史题材创作上,庆祝建军90周年全国美展中的《红军北上》《翻越夹金山》《1936年12月,历史的瞬间》《金戈铁马》《我的父辈》和《八路军大刀队》等,让人们看到了当代美术家对于人民革命战争的真实描绘、对于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塑造;这些创作还让人们看到了美术家追求历史真实的严谨创作态度与通过精湛的艺术语言重构历史的想象与创造,这种历史书写在当下更加鲜明地凸显出英雄主义的精神底蕴。
作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纪念,从全国军内外送审的应征作品多达七千余件,最终评定的入展作品531件,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装置、水彩画、宣传画和连环画等,可谓气象恢弘。这个大展上最惹人眼目的还是对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当代军人风采的深沉描绘。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军事题材美术创作往往偏向军人休闲情景的描写不同,本届许多力作如《热血·青春》《训练日志》和《整装待发》等,都以艺术的正面刻画来直呈军训战士的威武形象,并试图通过对于硬朗阳刚的军人形象塑造,揭示这些钢铁之师所深蕴的富有血性的民族精神,从而展示了和平年代另一种青年形象的社会人生与人性品质。还有许多作品如汤婷婷《待发》、张蕊《中国琨行动》和吕宛宣《南沙天门》等,描写了高科技军事装备下的现代军训场面,这些现代化装备的表现促使了艺术语言的现代性探索,甚至于这些现代化装备与现代军训生活成为军事题材美术创作进行艺术语言变革与艺术观念突破的载体。建军90周年全国美展对于当代中国军人铁血形象的塑造、对于军队现代化发展的艺术呈现,既有现代高科技军事生活的宽广度,也有家国英雄主义精神的深层发掘,而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重要开拓。
十九大召开前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的以“最美中国人”为主题的大型美术作品展,以中国画、油画的超大幅面形象地展现了以郭毅力、罗阳、高思杰和阎肃等为代表的当代英模形象。围绕这个展览而开展的现实题材绘画创作,再次把当代美术如何塑造英雄形象、如何绘写当代视觉史诗的课题凸显出来。在普遍沉溺日常书写、崇尚消费审美的当下,通过造型艺术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理想信念与崇高精神的追求,不只是艺术回到人民的一种真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而且是艺术回归视觉史诗创造的一种时代诉求。客观说,审美地描绘现实生活中那些闪烁着理想主义思想火光的人物形象,在当下是存在某种创作难度的。这种难度显然不是视觉素材的匮乏,而是在驳杂的生活表象中如何萃取真正能够凸显英模人物的精神与品格、又富于造型表现性的那些素材。这里既涉及创作者驾驭造型艺术技艺的能力与水平,更关涉艺术主体是否能够真正与被表现对象的思想情感形成高度的统一。或许只有深入被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找到表现这个人物的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塑造英模形象,同样需要审美发现与审美创造。
继2015、2016“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2017所选择的十位中青年美术家的主题实践,让人们看到了这个代际美术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当代精神的探索。曾深受欧美现当代艺术影响的中青年美术家,在他们面对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的长期实践中,逐渐把现代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艺术思想方法转向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不过,在表现方法上,他们比前辈们更具备这个图像时代的审美思考,也有意汲取了当代艺术的一些表现方式。“让艺术创造生活”的超现实主义和“让生活本身创造艺术”的新现实主义,都曾给予他们的艺术变革以某种程度的启迪,正是这种启迪使他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显现出更加多样与多元的表现方法与呈现方式。如果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多样表现形态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美术处理艺术主客观关系最重要的价值观,那么,“70后”“80后”这批中青年美术家才是这种价值观最忠实的践行者与探索者,正是他们的创作实践,发展并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内涵与当代性的表现方法。
当代中国美术家对于历史主题书写的浓厚兴趣,无疑体现了民族复兴的当代国家意志,这是继2016年完成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热潮的持续发酵,也是迎来新时代国家综合实力再度提速发展、抒发诗史情怀的必然审美诉求。而当代视觉史诗的书写,更是当代美术家的审美担当,当代视觉史诗的书写虽不乏丰富的视觉素材,但由实写而升华的诗写,必然是艺术主体容涵这个时代精神的诗性创造。其实,不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视觉史诗的美术创作都离不开真实,但也都不是真实的复制,因为它是现实审美诉求的表白与凝缩。
守望中国画学现代之路
中国画学从20世纪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社会转型、西学东渐的产物。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变革思想,可谓影响了一个世纪中国画学的发展道路。及至今日,中国画应当“缩小距离”还是“拉开距离”,已不再激烈论辩,但一些纪念活动和大型展览,却不断让人们从这种历史的回望与思考中来反刍当下中国画的发展理念问题。
作为今夏美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展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与“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让人们思考的是广东百年美术与整个中国百年美术、香港水墨画发生与内地现代水墨运动之间构成的某种深刻联系。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以“其命惟新”为主题,不仅浓缩了广东美术百年变迁与变革的思想主脉,而且隐含了广东美术对20世纪中国美术所具有的启蒙、开创与探索的引领作用。的确,康有为发出的“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思想,几乎整整影响了这一百年中国美术的发展路向;“二高一陈”提出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现代国画”概念,也几乎是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基本方法。这一百年,继李铁夫、冯钢百作为中国自主引进西画的先驱之后,不仅有符罗飞、司徒乔、余本、胡一川、罗工柳等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代表,而且有林风眠、胡根天、赵兽、丁衍庸等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先锋;就是鲁迅先生悉心扶植的新兴版画,也离不开李桦、赖少其、黄新波、古元等这一代最有影响的践行者。引进移植,融合中外,面向现实,张扬个性,这四个主题词所构成的百年中国美术运动,几乎都可以在广东美术这百年历程里寻绎到先觉的火光、斩棘的路标。
曾作为岭南画家过往与落脚之地的香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渐形成独具香江文化特色的现代水墨画形态。香港水墨画的产生是在殖民文化语境下进行文化变种的结果,即水墨画承担着表达多种非汉语文化体系的人文诉求,这种诉求在远离本土文化中心的殖民地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媒介还原。而回归后香港水墨艺术跨文化的深度实践所呈现出的新转机,一方面表明了香港水墨创作不断滋生于这个多元文化混融的鲜活机体,从而赋予其水墨艺术以不断被刷新的国际视觉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则因其与内地文化的互动性与参照性,而形成了香港水墨艺术的文化归属指向。也即,香港水墨艺术不断在跨媒介、跨观念和跨文化的当代性开拓中,始终和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构成一种深广的关联性。也正因如此,“水墨中国”在当下已成为中国画现代性的全球艺术标签,并将成为21世纪中国艺术在全球进行文化辐射的重要艺术媒介。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粤港文化对于中国画学打开的一个新世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中国画学在中国文化腹地发生变革的路途却并不平坦。2017阳春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以450件参展作品覆盖了国、油、版、雕、书等美术门类,全面呈现了当下全国画院建设的最新创作成果与学术水准。这一方面体现了全国画院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办院理念,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画院在中国画学承传与探索上所具有的强大优势。选入此展的中国画,让人们较清晰地看到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经观念更新、媒材实验和语境转换等变革之后,再度回归中国画本体的演变脉络。相对于当代艺术大尺度的颠覆与跨越,画院系统的中国画创作显得扎实而稳健。所谓扎实,即对笔墨、气韵、格调等中国画传统艺术精神深广厚博的研习;所谓稳健,即对西画的有益借鉴、对现代艺术理念和当代视觉经验的适度融入与新锐探索。因而,这些中国画不仅是在“新”上下大气力,更是在“好”上做足功夫。他们力求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更深刻地体现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并于此加入自己对艺术、对生活、对时代的感悟。
立足传统,或许正是当代中国画家成就自我的艺术变革前提。这种艺术思维模式,其实也正是新中国建立画院体制的基本文化方略。的确,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画院的建立,保全了民国时期形成的京派、海派这一南一北的画学面貌,这使得50年代开始的面向现实、以中融西的中国画变革具有了传统画学的基底,新金陵画派的产生其实就是依托江苏省国画家的画师从传统迈向现实的典型创造。的确,七八十年代画院的恢复、兴建,使得传统画学在经历了严寒之后迅速获得了复苏,并在经历新潮美术运动的洗礼而展开轰轰烈烈的中国画大论争大论辩中持变守恒,显现出画院在传统画学断裂后所进行的承传与创新。的确,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语境使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并举的艺术生态,但多元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消解,画院的职能与使命被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这就是当代中国美术是西方艺术模样的翻版,还是创建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东方当代艺术模式。
中国画学在新中国以来发生的从“保全与变革”到“承传与创新”、再至“寻根与拓展”的历史兴变,正是对传统中国画学现代人文精神追求从西而中、从外而内的一种探寻过程。而2017年初和岁末迎来的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张仃诞辰110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以及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刘海粟、宗其香等大型个人回顾展,则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呈现了他们的艺术思想与变革成就。譬如,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立论,因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而再度成为美术界的热点话题;潘天寿这一于20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社会环境阐发的中国画学思想,也再历经门户开放的时代变革而于文化自觉的当下语境获得了一种穿越历史的烛照。
现代性转型无疑是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主题。对于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诉求,一方面来自中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革,以及由此而折射在人们精神心理与视觉体验上的新变;另一方面则是西画被自主引进,在审美观念、创作方法与语言样式上给予中国画的冲击、参照、介入与改良。不论以西入中的改良派,还是中西合璧的融合派,抑或全盘接收的西化派,在客观上都对建立怎样的现代中国画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显然,这种现代性转型也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传统自身进入现代性的可能。潘天寿作为身处这样一个中西融汇时代大潮中的画家,能够清醒而鲜明地提出拉开中西绘画距离的主张并进行中国画现代性的探索,这无疑为中国现代美术史打开了一条从传统进入现代性的路径。在笔者看来,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其实是个文化镜像。也即,富有图像性的西方再现性绘画恰恰是潘天寿反省中国画乃至绘画自身存在价值的一面镜子,正是从这面镜子里,他才一再反对中国画对于西方图像性写实绘画的引用,而在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从笔线图形走向了更加自觉的笔墨抽象,在绘画自身特征的探索上缩小了中国画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距离。
在今天看来,“拉开距离”与“缩小距离”都只是相对的,并都构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画进行现代性探索的方法与路径。我们既不能因长久地关切中西融合命题而忽略“拉开距离”的学术主张,也不必过度夸大“拉开距离”的学术慧识而否定已走过并将继续走下去的文化跨越之路。
油画、壁画、雕塑对现代性的再出发
相较于欧美造型艺术的冷淡,油画在当下中国依然显现出强劲的张力。2017年度,不仅有中国百家金陵油画展、江南如画——中国油画展(2017)等较具规模的油画专项年度展,而且迎来了中国油画院十年展。
以“江南如画”为主题的2017中国油画作品展,是本年中国油画界既富特色也颇见水平的展览。相比于本年度盛大而惹人眼目的北京双年展、建军90周年全国美展等,这个展览显得相当精小而平实,但也因这种并不十分明确的主题,给表现中国南部的油画创作带来了一种本真的探索性。油画在中国江南获得的本土化,更鲜明地呈现了现代性特质。这种现代性显然不同于塞尚及印象派之后那些对于绘画性语言独立价值的凸显,也很难简单地把它们归属于法国现代主义某一派别,而是在中国人比较倾向于具象写实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平面化与抽象性因素的探索,从而使这些油画具有现代性的视觉经验与审美趣味。这些具有中国江南地理环境与人文特征的油画,并非一味地进入绝对理念的抽象或心理情绪的表现,而是将画面总体特征控制在某种含蓄内敛的情境内,情境似乎是那些人物、风景与物品所共同呈现的一种审美境界。显然,诗性是深埋于江南文化之中看不见却可以被深深感受到的一种情愫。
已连续举办了12年的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开始收获了良好的业界反响。以“色彩中华”为主题的2017百家金陵油画作品展,不仅呈现出较高的整体水准,而且一些获奖作品也让人过目难忘。当《共享时代》画出了“00后”的纯真、当《微光》画出了这个社会生存的孤守、当《诗和远方》画出了我们的忧伤,我们相信油画这个舶来的古老艺术媒介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审美诉求中获得了某种审美的穿越。这种穿越,无疑是以本土的现实关怀为基底、以指向未来的当代生活为路标。如果油画就是人类艺术的一种公共媒体,那么,我们坚信,在当下中国我们分享了这种艺术给我们生活与思想带来的阳光和色彩,这就是色彩中华的时代共享。这个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刻录了欧洲文艺复兴,见证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等兴衰的绘画媒介,在成为我们共享的艺术时,既需要我们深入研习这个媒介所凝固了的技艺传统与审美品质,也需要我们面对当下进行本土的、当代的和个性的创造。它所面临的学术课题,既在于如何运用这种共享媒介通过对当代生活的深入表现而创造新的视觉体验,也在于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本土并更深入地研习与转化欧洲油画传统的审美意蕴。
油画在当下中国的火热,还体现在中国油画院的创立与发展上。大概在世界艺术院系范围内,还没有单独以“油画院”命名的学术机构,这个学术机构命名本身就很中国。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绘画以国画为主体,油画、水彩、版画等这些舶来的艺术必然存在并不能都平行移植的艰难性,这意味着我们每代人所进行的本土化探索,也都是在重新回到原生语境下对其艺术进行深入研习的过程。自2007年创立的中国油画院,至今已走过十年历程,为此而举办的中国油画院十年展,充分展示了这十年学院师生的创研成果。这个展览更加清晰地呈现了中国油画院以“寻源问道”为校训的教学理念。的确,这所学院几乎荟萃了中国当代那些最具实力的具象写实油画家,他们以自己的才智显现了对西欧油画传统的深入研习,并以此体现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的人文情怀与审美创造。他们探究的是西欧油画艺术传统的深厚度,并以此表达油画本土化的艰难性首先就表现在必须以对西欧油画艺术传统的精深理解与高超驾驭为前提。
显然,中国油画院的成立及其十年纪念展是在西方丢弃了写实绘画之际产生的,它在东方文化语境中追问了一个写实绘画在图像时代的价值命题。写实油画在中国获得的复兴,还得益于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油画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清醒认识而形成的作用力。在大都美术馆藏品展所举办的以“油画表现语言与文化创造价值”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靳尚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油画艺术的研究方法不是依据风格流派、观念更新等外部因素,而是基于画种的特点进行技术层面分析来展开的。如对素描造型的研究就基于体积空间、物体结构的表现方法;对色彩的研究就遵循光照下的颜色、色调与油彩的关系。他认为,新时期以来关于美术教育有一种观点,认为重视基础教学没有用处,全都是技术问题。然而,这其中所说的“技术”不仅与科技并不等同,而且它既包括构图、形式、色彩和整体效果的考量,又包括艺术家对生动性、艺术性、精神性的完整表达。“我几十年来研究的都是技术问题,因为技术问题、语言问题不解决,油画水平上不去,光依靠观念是没有用的。”尚辉指出,中国在20世纪对西方油画的引进移植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流派的概念和主义,而没有很好地在实践和语言层面解决油画的基本与基础问题。其实,基础决定了高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中国油画的发展看似流派纷争、多元多样,但总体艺术水准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油画进入世界艺术史的观照视野。
2017年中国美术界对造型艺术热度不减。壁画这个几乎已被边缘到只有在全国美展中通过“架上壁画”得以存在的画种,于今年10月在广州美院大学城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第一个镶嵌艺术展。这个以“镶嵌中国——马赛克艺术邀请展”为展名的大型壁画艺术展,是在玻璃马赛克镶嵌壁画走进大型公共空间与家庭室内装饰的现实需求下策划的,也是市场需求与艺术提升相结合的一次完美尝试。画展中的许多作品虽是对一些著名艺术家原创绘画作品的二次创作,但玻璃马赛克材料的半透光性、色彩的饱和度、不同剪切工艺的分块、不同方式嵌块拼接所形成的肌理痕迹以及各种料器并置所产生的对比,都向人们揭示了马赛克镶嵌壁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以“镶嵌中国”为主题,不仅暗含了中国镶嵌壁画艺术的复兴,而且是在科技与材料的当代发展中对马赛克材料工艺的点状突破与壁画艺术的纵深挖掘。
中国雕塑的现代性是雕塑自20世纪从西欧引进中国后最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艺术命题。中国引进西方雕塑的这百年并未完全按照欧美艺术的演进路线,而是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进行了中国雕塑的现代性发展。因而,中国雕塑的现代性也便不能完全等同欧美现代主义雕塑的概念。2017年9月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全国雕塑艺术大展,是对20世纪中国雕塑现代性演进轨迹的一次全面梳理。当从李金发、滑田友、刘开渠等这些第一代留欧雕塑家开始的百年名家雕塑、约590件荟萃于中国美术馆所有展览大厅时,人们对于中国雕塑的现代性进程也便形成了一种清晰的感性认知。从张充仁的《恋爱与责任》表达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启蒙到滑田友的《轰炸》对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揭露,从余积勇《五卅惨案纪念碑》对那些牺牲者形象的抽象概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通过八块浮雕所浓缩的中华民族从觉醒、抗争到解放的宏大叙事,这些雕塑作品对于民族精神的揭示,是一幅绘画、一部文学作品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是去具象的雕塑语言自立、以某种抽象性的现代性雕塑就能够完成的,因而,中国雕塑的现代精神是以表现这个民族国家的现代精神为内核的,只有那些真正凝固了民族悲剧性的历史瞬间,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当代社会民族精神的来源与力量。
而同期在长春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城市雕塑高峰论坛对于世界当代城市雕塑发展的探讨,也再次彰显了中国雕塑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意象美学与写意语言上的独特价值。显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雕塑,并不完全盲从于以装置、新媒体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雕塑概念,而是回到中国文化本体,以意象美学与写意语言探求中国雕塑跨越写实的方法与路径。吴为山提出“文心意写”的写意雕塑概念,是继滑田友、王朝闻等一代雕塑大家之后提出中国雕塑写意论最为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是面对世界以装置代替雕塑的流行趋势而提出中国雕塑现代性发展的基本理念与应对策略。中国雕塑的现代精神既是中国引进西方雕塑百年历程对于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也是在欧美当代艺术理论中反刍中国意象美学,从而寻求人类雕塑艺术发展新方向的文化思考。以“艺术永生”为主题努力回归艺术本体的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试图用装置、影像、新媒体艺术来诠释艺术的永恒性,这种对艺术永生的追问与呈现似乎仍只偏执于对艺术不断变革的“当代性”的演绎,而轻视或放弃了人类已有的造型艺术传统。以“以雅典为鉴”为主题的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试图以希腊和卡塞尔这两座城市的展区来探讨曾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在当下面临的文化边缘化与经济、政治双重危机的窘境。不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对于艺术本体问题的追问,还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对区域政治问题的热情,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艺术的“当代性”命题设定在装置、影像、行为和新媒体艺术范畴,并以此作为唯一的当代国际艺术,仿佛在此之外的造型艺术与非欧美国家的艺术类型都不是“当代的”,也不具备“国际性的”。与此相反,已连续举办15年的北京双年展,以“丝路与世界文明”作为第七届的策展主题,这或许也最鲜明而精准地传递了这15年来北京双年展从创
构建新的全球当代艺术理念
每十年一遇的两个国际艺术大展——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于2017夏季相继开幕,并构成了策展理念上富有意味的比对。设到繁盛所持守的文化立场与艺术主张,那就是当代艺术的全球化是个由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艺术互交与互鉴的结晶,而不是全球艺术被欧美艺术的殖民化与同质化。
当来自102个国家、567位艺术家的601件作品俱陈于中国美术馆所有展厅时,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其参与国之多、涵盖种类之全、艺术样态之丰,或许都完美地诠释了本届北京双年展为不同国族的文化艺术进行平等交流、互学互鉴而提供展研平台的丝路精神。以“丝路与世界文明”为主题所调动的全球艺术家创作,无疑是一次富有挑战性的美学重建。它一方面倡导能够体现各国文化特征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则聚焦各国在艺术当代性上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创新。其挑战性显然在于,如何从各自民族传统的来路中来理解艺术的当代性开拓,它既同于人类艺术发展的某些共同走向,也依然葆有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印记与审美特质。这就是人们在展览现场观赏到的缤纷多彩的艺术景观,它不仅呈现了许多国际双年展通行的新媒体艺术,而且较多地展现了造型艺术的当代探索;它不仅呈现了一些欧美国家对于当代视觉体验的试验,而且较多地展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于视觉艺术文化内涵的求索;它不仅呈现了包括抽象、表现和符号表征在内的非现实形象的视觉艺术探寻,而且较多地展现了再现写实或具象超现实的现实形象系统多样表意方式的拓新。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层解读,人们似乎可以触摸到这样一种贯穿于作品之间的创作思想脉络。“丝路与世界文明”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恢弘而深广的历史背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正是从这个历史穹顶里探寻了连接他们各自文化存在与现实处境的审美通道。远古的丝路遗存与现实的丝路构建,唤醒了他们积蓄已久的艺术想象力与重构当代美学的渴望,而这些想象与渴望正源源不断地转换为他们进行媒体实验、语言探寻和观念寄寓等的创新实践。“丝路与世界文明”还为艺术的全球化提供了这样一种新思维、新参照,这就是从由某种艺术史进化逻辑所推演的当代艺术路线图里解放出来,不以追逐欧美流行的以新媒体取代造型艺术的当代艺术理念为人类艺术当代性发展的唯一方法与路径,而是把世界艺术的展延置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中,促进全球文化艺术的多元与多样性发展。
而另一个来自中国湘西凤凰的“凤凰艺术年展”则举起了“超当代”的策展旗帜。曾在沈从文笔下描绘出的“边城小镇”因为其独特的客家文化、边城景色而成为艺术当代性创作的特定“情境”,并因“凤凰艺术年展”的举办而使这种边缘和世界当代文化中心构成了某种意味的解构现象。以“超当代”为主题的凤凰艺术年展,给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把装置、影像、观念等新媒体艺术当作当代艺术的独角戏,而是以当代人文精神的表达为内核,从新媒体艺术的视觉化突进和造型艺术本体语言的时代性变革这两个方面予以诠释。“超当代”艺术概念的提出,让人们开始思考艺术有不断“当代性”的一面,也有超越“当代性”的另一面。就人们今天看到的“当代艺术”而言,它是针对当代高科技研发而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并根据解构主义理论而新生的一种艺术类型,这是艺术当随时代并具有“当代性”的一种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造型艺术的终结,也不能表明造型艺术不能被赋予“当代性”,更不意味着造型艺术不能在不同国族的文化互鉴中获得新的演变与拓展。因为,这种由人的生理机能所创造的造型艺术体系,是审美地解放人性与人性的审美解放的必然表征,从人的劳动而开始的生产的对象化,也就孕育了审美的对象化;由此而形成并高度发展的造型艺术规律——这个有关人的审美对象化的高级形态,正是造型艺术的本质。
绘画、雕塑等有关人类手的创造性与精神情感表达的高度统一,无疑是一种超自然的人文诉求和人文表达。就此而言,这种对人类审美的人性创造与人性的审美创造而形成的造型艺术及其规律,也具有某种超越“当代性”的永恒性。这正像奥利瓦在谈论20世纪80年代欧美绘画复兴时所认识到的“手工技巧”的价值那样,“创作过程的愉悦将绘画传统再次引入艺术”。只不过,包括绘画在内的造型艺术创作与发展在中国从未中断、也从未失去信心;而其所言绘画“创作过程的愉悦”说得还欠缺些底气,人手对于形象的艺术塑造,早已超越“愉悦”层面而进入了更深层的精神创造。
北京双年展、凤凰艺术年展释放出的艺术“当代性”的新思维,既体现了中国艺术的主体立场,也表达了中国美术对于人类造型艺术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艺术是穿越历史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的精神隧道,因而,艺术的穿越也总是在变革与守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