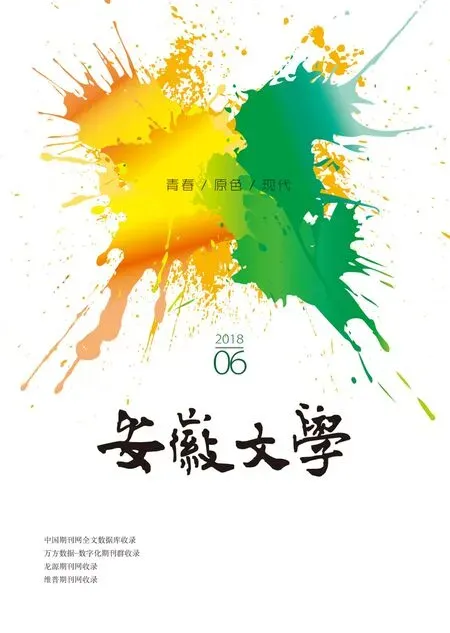唐传奇中的神话因素
——从《山海经》到唐传奇
贺丽璇
首都师范大学
《山海经》是中国神话保存最为原始和最朴素的总集。神话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想象力的源泉。《山海经》中的神话对于后世的艺术创作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如魏晋六朝时期小说的写作思想:“其中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①六朝小说以志人和志怪为主,其所著文章多含光怪陆离之象,其中多有夸张虚构成分,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原始神话有着较大的联系。这种以怪奇为文的写作心理,又为之后唐传奇写作中之“作意好奇”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故在应运而生的唐传奇中,天马行空的神话就成了作者们最佳的素材选项之一。而来自于上古神话的素材体现在唐传奇中,既有对神话的改造,又有借用素材等方式进行的再创作,这些故事的出现,也丰富了神话的内容。
一
在唐传奇中,为了使故事达到光怪陆离的效果,经常会用到一些上古时期的神话,很多故事甚至就是先秦神话的翻版或扩充。如《山海经》中提到的大禹和夔牛的神话,到了唐传奇中,被李公佐写入《古岳渎经》,变成了无支祁的神话;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聂耳国”,到了李冗《独异志》中就变成了“大耳国”;再如《琱玉集·鉴识篇》中记载的汉宣帝开山,岩下得二石人的故事,则是本于刘歆的《上〈山海经〉表》:“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②到了唐传奇中,则更加天马行空,汉代的刘向与黄帝时期的诰窳国臣处在了一个空间,将这段上书本事敷演为了刘歆见多识广而最终得官的故事。
唐传奇最大的特点,便是将引自古代的神话给民间化和丰富化了。而进行民间化和丰富化的重要一步,便是将神话故事仙话化。上古之神难以接近,而古代神与仙的分界并不明确,有时二者甚至可以混同,但是秦汉以来,方术与道术的盛行,开始流传着普通人也能够飞升成仙的仙话,这样一来,神和人的距离被大大拉近,所以唐传奇中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仙化,便极大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和丰富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海经》中的“草神话”的演变。
这则神话见《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非常简单:“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③
草神话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关。最早宋玉在《高唐赋》中的表述其实非常含糊,巫山神女和后来的帝女瑶姬也并无联系。“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④姑媱山与巫山同属三峡地望,而荆楚地区自古盛行巫觋之风,不仅巫山神女传说有极大的空间可以糅合其他传说,草神话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古代大山与草木密切相关,如屈原笔下的“山鬼”形象,作为山神的她掌控着一方山川草木。“帝女”与草木山川结合,使得当时的人们在对这一神话传说加以演绎传播的同时,极易将其与当地流传的“巫山神女”形象结合在一起,所以“草木神”的形象转化为山神,是颇为自然的。
草神话的影子在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中还依稀可见:“(神女)叆乎若云,焕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漂如停。详而视之,西子之形。王悦而问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依草,实为灵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于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⑤可见后世流传的神女瑶姬故事,在此处已具备基本雏形。但这基本上还是两个故事的结合。到《水经注》中郦道元笔下,将姑媱山隐去,把草木神与天帝之女分开。“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⑥郦道元进一步分化了“草神话”,并明确地将瑶姬与巫山联系在一起,成为将瑶姬神话与巫山神女传说一体化的有力推动者。
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中指出,高唐神女虽然是文人笔下的形象,但其在古代神话中有原型可考。闻一多的论证,是高唐神女与很多的神话形象都有关联。结论就是这几个不同民族的女神最初出于一个共同的女性远祖,涂山氏简狄高唐等,都是那位远祖的化身。⑦因此高唐神女或巫山神女,其形象非常容易与上古神话的女神形象产生联系,或者更可能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逐渐演变为最后的帝女瑶姬。
到了唐初,《文选》中《别赋》李善注引瑶姬之言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曰灵芝。”⑧387而《高唐赋》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云:“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⑧708唐初年的草神话就已经出现了“帝女”死后,化为草和人两种版本。而“巫山神女”版本则更是因为《高唐赋》被文人墨客所广泛接受,频频见诸诗笔。
到了唐传奇中,“草”已经固定为“瑶姬”,其神话则变成了杜光庭《墉城集仙录》笔下的瑶姬神女帮助大禹治水的故事。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回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游东海,还过江之上,有巫山焉,峰崖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平博可玩,流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其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力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长、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谒其于崇巘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不知其常也。禹疑其狡狯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复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宫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抱阙,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作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禹拜受而去。又得庚长、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赐玄珪,以为紫庭真人也。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以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赋》以寓情荒淫,托词秽笔,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峰有神女石,即所化之身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坛侧有竹,垂之若簪,有槁叶飞物著坛上者,竹则因风而扫之,终岁莹洁,不为世之污,楚世世祀焉。⑨
《墉城集仙录》是杜光庭为众女仙所作的传,且此文也有为瑶姬从宋玉笔下正名之意。尽管故事中的仙话气味已经很浓厚了,但是依旧能够看出这个故事是以《山海经》中的草神话作为最初蓝本而演变过来的,只是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结合了一些其他的神话和传说,《墉城集仙录》是结纂古书而成,所以有很多材料取自唐前古籍。
从“草神话”到“巫山神女瑶姬”,其中既有唐代流行的山岳信仰以及对道教的推崇,也有当时“仙妓合流”思想的影响。杜光庭在自己编撰的故事中将神女仙化并结合大禹治水的神话,对其进行了合乎道教信仰规范和理想的修改。然而草神话毕竟与高唐神女不同,草神话本不是“遇仙”,所以最后仙化的,帮助大禹治水的云华夫人瑶姬,也不同于其他“遇仙类”唐传奇里大胆追求情欲的仙女,而“帝女”这个形象也更加动人。类似这种对于上古神话的丰富和发展,从中可以看出一丝神话到传奇故事的演变方式。
二
唐传奇中除了这种对于神话故事的丰富和发展,更多的是对于上古神话中的某些元素加以使用,来达到“传奇”的目的。
如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很多的传奇志怪杂事,其中有一篇《长须国》,就是借助《山海经》中的地名,想象出了一个在“扶桑州”上的“长须国”。《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⑩扶桑乃大木,为日所栖处。旧题东方朔《十洲记》载:“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地多树木,叶皆似桑。又有椹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⑪段成式将长须国置于东部大海,故借《山海经》中地名。我国古代称日本为扶桑,而且结合扶桑树为日栖之所,故有学者认为这篇传奇中地名的极有可能指的是日本。但其实作者笔下,长须国中的原住民为受到龙宫欺凌,而不得已向凡人书生求助的虾精,而且他在其中描写的各种海上精怪,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山海经》中对各种神奇国度的描写。
再如裴铏《传奇》里《陈鸾凤》中对于雷兽的描写,明显借用了《山海经》中对雷神的描写。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注:雷泽即震泽;《汉志》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⑫(《山海经·海内东经》)
再看《陈鸾凤》中陈鸾凤与雷斗争的情节中对雷神的描写,这里将雷神想象为了“雷兽”:
鸾凤持竹炭刀,以所忌物相和啖之,果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以刀上挥,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⑬后世传说中,有很多讲述雷的故事。《论衡》中有“雷公”说;《搜神后记》中有“阿香推雷车”之说;《酉阳杂俎·雷》中有“霹雳车”之说,都是将雷想象成与人有关的事物。而这里将雷想象成“雷兽”,就是借鉴了《山海经》中“龙身人头”动物状雷神的再创造,以雷兽的凶猛,来突出陈鸾凤的勇敢无畏。
唐传奇中有很多人兽合一的形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龙王形象,而广为流传的李朝威的《洞庭灵姻传》又使得龙王形象深入人心,还影响了后期的《灵应传》,创造出另一个龙神形象“九娘子”。这反映了当时的神话形象在发展中不断丰富,由单一的形象逐渐到由面貌、图腾和人物所共同构成形象的趋势。《山海经》中的海神造型本与方位有关,在其中记载的东海神禺虢,南海神不延胡余,西海神弇兹,北海神禺疆,都是“人面鸟身,珥两青蛇”的形象。海神的形象与蛇相关,龙蛇为相近意象,到后世逐渐演变成为与龙相关。而华夏族的龙图腾,佛典中的那伽,还有民间流传已久的河伯神话,则都为“龙王”这个形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唐传奇中,远古图腾、自然神为精灵故事提供了原型,而历史情节或人物的神话则提供了灵感,死亡或复活就成为了故事的重要背景,故事就会在人与自然物的互相变形中产生。古代有“神鬼不辨”的思想,在唐传奇中便增添了很多的新神。鲁迅曾指出:“神鬼之不别。天神地衹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衹。人鬼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⑭所以在唐传奇中,又有了一个大放异彩的东西——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或不死的思想源于战国方术,发展于秦汉,和道家关系密切。在《山海经》中“不死药”的记载已经出现。虽然唐传奇中的“长生不死药”和《山海经》中的记载已经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却意外地有些相通之处。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昆仑开明北有不死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药以距之。”⑮6其中“不死树”和“不死药”,都是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神药,因为《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记载:“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⑮1窫窳已经死去,所以众巫们拿着他的尸体,是用起死回生之药复活他。
在我们今天看来,神仙都是不老不死的存在,然而在《山海经》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神仙是会面临死亡的,比如死去的夸父和女娃。因此,相比起后世道教仙话之中所传说的长生不老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药或不死药,并不是吃了使人长生不死,而是吃了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后世神话中所说的吃了仙药之后能够长生不老或者升天为仙,都是仙话与神话互相渗透的结果,《山海经·西次山经》中所记载的黄帝在峚山种玉和服食玉膏的事,可能就染上了一部分仙话的色彩。中国古代神话的仙话化,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期为春秋战国,高峰期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补充完成期是在唐朝到宋朝。所以唐传奇中的故事情节,仙话色彩就比较浓厚了。但是在其中,亦有不少描写起死回生的例子。
如在《薛昭》中,书生薛昭遇到了自称为杨贵妃侍女的张云容,她说自己遇到申天师:“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⑬2180也是吃了仙药之后并不能长生不老,而是需要在某种契机触发之后,如遇到活人,才能起死回生。
在《张无颇》中,传说为袁天罡的女儿袁大娘给了张无颇一个膏药,并说:“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⑬2213当然在小说中,袁大娘是让他拿着这个东西去给贵族小姐治病,说白了便是让他有攀龙附凤之“利器”,而后来张无颇果然与广利王之女结成婚姻。唐人有很强的门第观念,男子都希望自己的妻子是高门贵族,故唐传奇中的女子都貌美如花、出身名门。而这些应考学子们笔下故事的男主人公,以书生才子的数量最多,故唐传奇中,经常出现得道高人帮助才子佳人成就良缘的故事。在《元柳二公》一文中结尾处也出现了一个还魂膏,原文如下:“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⑬2151
文章中涉及的各种“长生不死药”,都是吃了能够让人起死回生,不同于道家所说的服食后延年益寿或飞升成仙。而“不死药”不管是在神话还是在仙话中都有出现,是因为长生作为人的终极欲望,它强烈的反映了普通人的心灵寄托。人类用“长生不死药”来构造象征“自由”的意象,就有可能带来神与仙的混同,跳脱自然规律以得到一种终极的自由,正是仙话所追求的境界。
三
神话本就带有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而唐传奇的“作意好奇”“始为小说”等新特点,尽管是在搜神志怪的六朝小说影响下形成的,但它也和志怪小说一样,保留了非常明显的神话思想遗留的痕迹。
唐传奇重新塑造故事,不仅仅是借助上古神话的素材,更多的是在传奇作品中体现神话意识,正是神话意识的存在,才给了唐传奇鲜活的生机。如敢于手劈天雷的陈鸾凤,就是一位充满了神话中英雄色彩的人物形象。他就像上古神话中救民于水火的那些英雄一样英勇无畏,而后来陈鸾凤成了可以与他曾经较量过的雷兽比肩的雨师,自己也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这些都是神话中英雄意识在后世小说中的反映。
再比如《山海经·北山经》中所记载的“精卫填海”神话,它极有可能开启了后代传奇中的女性复仇模式。女子本性柔弱,但是在复仇中的女性却表现的坚毅刚强,她们面对男权迫害时的勇敢抗争精神,与女娃死后发誓愿以一己之力填平东海的作风十分类似。唐传奇中的复仇者,代表人物有霍小玉和谢小娥。霍小玉死前发愿,她死后化为厉鬼,使李益和其妻妾终日不安,人变鬼化形以实现其复仇的目的。本来是全心全意爱着李益的霍小玉,当李益变心,无奈身死之后,却非常果断地进行了她所能做到的复仇行动,化身厉鬼的小玉,充满了抗争男权不公的勇气。谢小娥则更加不幸,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害,自己流落尼姑庵。后来父亲和丈夫给她托梦,但实际上若不是谢小娥的复仇之心强烈,心念不已神感鬼神,又何来托梦之事。小娥在得到消息之后,果断地开始了复仇行动。她女扮男装作帮工寻找仇家,忍辱负重不辞辛劳,最终手刃仇人。小娥在已孤苦伶仃的情况下,以弱女子身份坚持向江洋大盗复仇,其心智坚韧性格刚强可见一斑,亦不亚于填海之精卫矣。
唐传奇中展现的神话因素,并非用其来表现世事空幻、及时行乐的荒诞感,而是一种世俗生活下带有社会普遍思想的反映。神仙鬼怪不是用来充塞故事情节的材料,也不是文章里的一种象征符号,而是经过形变和改造后的真实,它依旧保持着生活本身的完整性和真实感。我们可以在神妖精怪的身上看到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念,也能够在其中窥看出唐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情绪化和诗意化的追求,以及唐传奇中很多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变革性美学因素。
神话对于唐传奇的影响,更多的是作为故事的素材或者灵感来源,而非作为故事本身。但是上古神话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滥觞之一,在唐传奇中所体现出的神话意识和对唐人思维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使得唐传奇能够在后世依旧焕发出瑰丽色彩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27.
② (晋)郭璞,传.(清)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第一卷)[C].中国书店,1991:14.
③ (晋)郭璞,传.(清)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第五卷)[C].中国书店,1991:22.
④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二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75.
⑤ (晋)习凿齿,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M].荆楚书社,1986:302.
⑥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中华书局,2013:756.
⑦闻一多.神话与诗[M].世纪出版社,2006:91.
⑧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87.
⑨ (唐)杜光庭,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下册)[M].中华书局,2013:604.
⑩ (晋)郭璞,传.(清)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第九卷)[M].中国书店,1991:3.
⑪ (汉)东方朔.十洲志[A]//诸子集成补编(十)[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0-381.
⑫ (晋)郭璞,传.(清)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第十三卷)[M].中国书店,1991:2.
⑬ 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第四册)[M].中华书局,2014:2236.
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12.
⑮ (晋)郭璞,传.(清)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第十一卷)[M].中国书店,1991.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2](晋)郭璞,传.(清)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第一卷)[C].中国书店,1991.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晋)习凿齿,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M].荆楚书社,1986.
[5](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中华书局,2013
[6]闻一多.神话与诗[M].世纪出版社,2006.
[7](唐)杜光庭,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下册)[M].中华书局,2013.
[8](汉)东方朔.十洲志[A]//诸子集成补编(十)[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9]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第四册)[M].中华书局,2014.